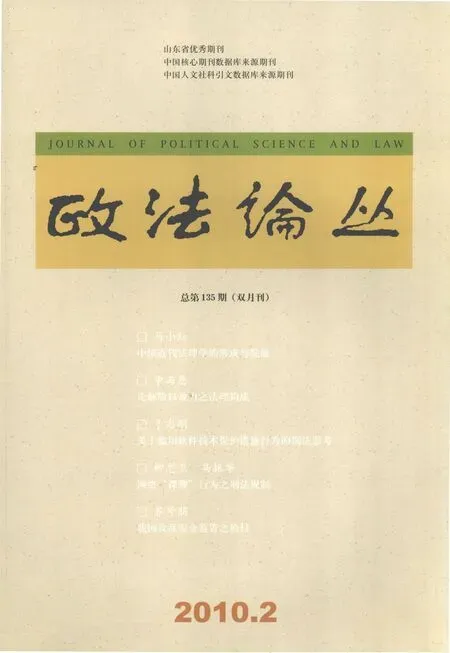真理符合论在法律领域的困境及其超越*
陈 锐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400031)
真理问题是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法律真理问题是法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在各种各样的真理理论之中,真理符合论影响最大,它几乎成为各种真理理论的起点。在法律领域,自古希腊以来,人们一直在探寻法律真理,试图通过真理这一路径来解决法律的权威问题。在法律领域,真理符合论也是影响最为巨大的一种真理理论,美国学者丹尼斯·帕特森就说过,法学史上几乎所有法学家的理论都可以归结为真理符合论。此说虽有过分夸大之嫌,但起码能够说明真理符合论在法学领域影响之一斑。但真理符合论是一种科学真理观,将它应用于法律领域是否恰当呢?如果不恰当,则应从何种意义上来理解法律真理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认真地思考与探究。
一、真理符合论在法律领域的影响及面临的困难
(一)真理符合论
“真理符合论”是真理理论中最有影响的一种理论,它将真理归结为命题(或判断)与实际(或认识)的符合。真理符合论有多个变种,但一般地都可以分析为三个核心要素:一是真理承载者;二是真理制造者;三是符合关系。如果某一真理承载者与真理制造者之间是符合的,则它就是真理,反之就不是真理。
据考证,真理符合论的最早代表应是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就评价说:“亚里士多德这位‘逻辑之父’把判断认作真理的原始处所,又率先把真理定义为‘符合’”。[1]P247亚里士多德认为,命题或判断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它的真假取决于是否如实地描述了客观事物。“真理符合论”在近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并几乎在哲学领域确立了其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洛克。洛克明确地将真理定义为:“在我看来,所谓真理,顾名思义,不是别的,而是按照与实在事物的契合与否而进行的各种标记的分合。”[2]P566洛克认为,人的认识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认识主体通过与外部事物接触以及对自身心灵活动的反省,就得到了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这些观念如果与外部世界相符合,则就是真理,反之就不是真理。到了现代,逻辑实证主义从洛克手中接过了“真理”的接力棒,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等等,虽然他们之间的观点差异巨大,但都主张真理是人的认识与客观世界的符合。
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中经洛克,再到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这是一条唯物主义的真理符合论路线,也是我们通常都能够注意到的真理符合论路线。其实,还有一条唯心主义的真理符合论路线,它常常为人所忽略。这条路线始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中经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再到近代的康德、黑格尔。与唯物主义的观点正好相反,这一路线认为,事物的真理在于与知的符合。但无论如何,所有的符合论者都主张说,所谓真理,不过是指真理承载者与真理制造者之间的符合关系,这就是真理符合论。
(二)真理符合论在法律领域的影响
虽然法学家们很少谈及法律真理问题,但毋庸讳言,他们一直是在追寻法律真理,这是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使然。如丹尼斯·帕特森所说,法学史上大多数法学家的思想都可以归结为真理符合论。[3]P3
帕特森发现,在美国法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形式主义法学家欧内斯特·魏因瑞伯(ErnestWeinrib)的思想就带有“真理符合论”的痕迹。[3]P33因为魏因瑞伯认为,一个法律命题是真的,仅当被描述的命题与得到正确理解的私法结构一致。也就是说,一个私法命题是否是真的,主要看它是否符合矫正正义原则,如果符合的话,则它就是法律真理。
按照帕特森的建构,形形色色的自然法理论都可以归约为“真理符合论”。从古希腊以来,众多的自然法学家认为,在“实在法”背后,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永恒的“应然法”,这种“应然法”实际上是一种绝对的法律真理,它是作为评判实在法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标准而存在的。法学家的任务就是追求与发现这种普遍的法律真理。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真理符合论”,其中“应然法”是“真理制造者”,有关“实在法”的描述是“真理承载者”,检验一个实在法的命题是否是真理,就要看它是否与“应然法”相符合。
虽然很多法律理论都可以被建构为符合论形式的真理理论,但与作为科学主义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相比,它们在典型性方面要逊色得多。法律实证主义理论是真理符合论在法律领域的典型代表。按照科尔曼的观点:法律实证主义的本质在于寻求一种标准,以便将法的正确解读从错误解读中区分开来。[4]众所周知,“社会事实理论”是法律实证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这一观点宣示了法律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主张:法律是一种社会事实。判断一个法律命题是否有效的渊源在于社会事实,是社会事实使得法律命题真或假。当然,不同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对“社会事实是什么”有不同的看法。奥斯丁认为,这一社会事实是作为主权者命令的法律,凯尔森认为是由基本规范衍生的有效法律规范,哈特则将法律命题有效的渊源归结为“承认规则”。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实证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认为,检验法律命题真理的标准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事实。此外,几乎所有的法律实证主义者都称自己的法律理论是“描述性理论”,即使是哈特在对早期的法律实证主义思想进行了诸多改进之后,也不忘重申自己的理论是“描述性社会学”。他们反复申述这一立场,目的是为了彰显几乎所有法律实证主义者都念念不忘的初衷:使法学成为一门科学。这门科学当然是由关于法律的真理性认识所组成。这些都反映了法律实证主义者是法律真理的持有论者,并且是真理符合论的坚定支持者。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将更多的法律理论建构为符合论模式的真理理论,而不只以上提到的那些理论。为什么如此多的理论都不同程度地与真理符合论相暗合呢?这是因为:真理符合论能够为人们探讨实在法背后深层次的东西提供方便的解释模式,能够对法律权威问题提供某些有一定说服力的说明,并为批判实在法提供一种可靠的工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真理符合论代表的是一种科学真理观,因此,用之解释作为人文社会真理的法律真理时会面临一些困难。
(三)“真理符合论”在法律领域面临的困境
真理符合论在解释法律真理时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首先,按照真理符合论,法律真理不过是法律命题与法律中的真理制造者的符合。但是,法律中的真理制造者又是什么呢?不同的学派对此问题的回答差异巨大,纵使在同一学派内也很难达成完全的一致。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如何判断一个法律命题是真的?是按照它与自然法相一致呢,还是看这一法律判断是否有实在的法律规定与之对应呢?是看法律施行的后果是否令人满意呢,还是其它的东西呢?这说明法律领域的真理符合论面临着“符合对象缺失”的问题。
其次,人们对描述法律规范的法律判断能否用真假来刻画也表示怀疑。人们普遍认为,法律判断不同于科学判断,我们不能说某一个法律判断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因为真假值只能应用于纯描述性的判断。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哲学家们就对此有过充分的讨论,这一问题又被称为“约根森困境”①。“约根森困境”是人们在价值真理领域无法绕过的困境,这一困境实际上反映了真理符合论应用于价值领域(包括法律与道德领域)存在着某些“先天不足”。
第三,人们还会质疑这样一个问题:真理符合论中的“符合”是什么意思?不同的学者对于“符合”的界定不同,按照从弱到强的顺序,大致有“相似”、“不矛盾”、“一致”以及“完全同一”等意思,人们所说的“符合”到底是哪种程度的符合呢?并且,符合的证明也是非常成问题的。
第四,真理符合论还无法解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多元真理的问题。在自然科学领域,对于同一现象的正确认识一般都只有唯一的正确答案。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情形则有很大的不同。在人文领域(包括法学领域)中,人们对于同一问题的认识,经常存在着多种合理的解释,这些解释几乎都具有同样程度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哪一种解释是法律真理呢?真理符合论显然难以解释这种多元真理并存的情况。
一些学者看到“真理符合论”存在如此多的问题,他们就断然得出结论说:法律根本就不是真理!是否真的如此呢?且慢,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急于得出这种结论,这种论调在哲学史上也非新鲜之物。在哲学史上,真理符合论在解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真理时产生了许多问题,当时就曾有许多学者指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根本就不存在真理。这种观点当然遭到了诸如普特南、伽达默尔等学者的严厉批判。这些学者认为,真理符合论遇到的困境并不能证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存在真理,而只能反过来说明这种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真理理论不能适应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需要,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问题,而是要反思“真理符合论”的恰当性问题。
二、超越真理符合论:对法律真理的诠释学理解
如何解决真理符合论在解释法律真理时所遇到的困难呢?许多学者做出了努力,伽德默尔、海德格尔为我们解释法律真理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一)诠释学真理的提出及在法律领域的影响
伽达默尔通过对知识史进行考察之后发现,近代的认识论走上了寻求真理的错误路径,因为近代的认识论试图借助科学方法达致真理。伽德默尔认为,方法不是通达真理的唯一途径。这里的“方法”特指自然科学方法及从自然科学那儿借来的方法。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这种所谓的科学方法造就了对人的控制意识,使人异化为物,在这种异化面前,真理不再是对存在和人的生活意义的揭示,而变成与人相异的东西。
伽德默尔主张恢复“真理”一词的原初意义。在古希腊,“α λ υ θ ε τ α”一词的最初含义是“去蔽”、“展现”、“揭示”,即真理不意味着关闭,而是指开放。在早期的希腊人那里,真理意味着去蔽,意味着对存在的解释。只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中,对真理的本体论理解逐渐湮没在西方理性主义认识论洪流之中。伽达默尔主张恢复“真理”的本体论意义,从而对抗近代的认识论真理。伽达默尔通过对艺术真理的揭示来说明真理的本质。他认为,艺术是一种认识,艺术中存在着真理,这种真理是作为一种自我理解的方式而存在的。如果我们用理性去把握这种真理,则就偏离了真理。并且,真理的范围不仅包括科学真理,而且包括艺术真理、历史真理等等。
狄尔泰、伽德默尔以及海德格尔所创立的探究人文科学真理的理论启发着某些睿智的法学家,他们开始尝试着将这种理论应用于法学领域,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德沃金,德沃金是诠释学真理观在法律领域的坚定推行者。
与现当代的大多数法学家有很大的不同,德沃金明确地谈到了“法律真理”问题。1996年,德沃金发表了“客观性与真理:你最好相信它”一文,在文章的开头,他开宗明义地问道:“存在客观的真理吗?或者说我们最终必须接受‘根本就不存在真的、客观的、绝对的、关于事物的正确答案’的观点吗?”[5]在《法律帝国》中,德沃金也谈到,自己与实证主义的不同是对“真理”意义的理解不同。[6]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的正当性理由来自于法律规定自身,不需要向外追求,而德沃金显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法律的正当性理由必须来自于那种超乎法律规定之上的东西。
德沃金明显地受到了伽德默尔的启示,他同样是从“艺术真理”联想到法律真理本质的。他认为,法律诠释与艺术诠释一样,并不是简单地复原作者意图的活动,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诠释者通过赋予原作以意义,不断地重构原作。他还举出了“系列小说”的隐喻以说明诠释的过程。他认为,法律真理的产生过程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每一个诠释者就像一个系列小说的作者一样,旨在用已有的小说材料,再加上自己的东西去创作一部小说,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添加那些他认为最适合的材料,从而创造性地建构这部小说,以便使得这部小说似乎出自一人之手,因此,诠释者实际上处于联结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过程之中,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生成了法律真理。对于如此的法律真理的理解,我们不可能做到如实证主义所说的客观性、中立性。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德沃金认为,人们在理解法律真理时不可能消除“前见”,并且,这种“前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理解法律真理的前提。
对于“什么是法律真理”,德沃金作了明确的回答,那就是:“这就是法律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为了我们想要做的人和我们旨在享有的社会”。[7]P367也就是说,法律真理就是人成其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人自我理解、自我实现的一种生活方式。
正如德沃金所说的,法律是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种现象,是人们为了保障个人自由、实现社会福利而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法律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奴役人的工具。从本质上讲,法律是一种游戏活动,不同类型的人参与其中,除了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一目的以外,另外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展现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法律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生活方式。
(二)诠释学真理观的超越意义
诠释学真理观的兴起表明人们在法律真理问题上实现了某种超越。
首先,诠释学真理开启了探索法律真理的新路线,那就是内在主义路线。这一路线主张:我们在研究某一理论时,只有站在这一理论之内问“这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才能得到真理性的认识。
在西方法学史上,外在主义研究方法曾处于统治地位,许多法学家都试图从法律之外为法律的正当性、法律命题的真理性寻找根据,哈特曾形象地称之为“外在视点”。哈特认为,奥斯丁和凯尔逊在追问“什么是法律”时,都将自己当成了一个社会规则的外在观察者,他们只是注意到了法的外在方面。这种外在方面可以使法律更加科学,但是,它是较低级的形式,因为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看,很难区分“一个人由于被迫而行动”与“一个人由于义务而行动”,因此,他们的理论无法为法的有效性提供合理的解释。哈特认为,我们在理解法律问题时,采取纯粹的外在主义方法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现象包括了自我意识的人的行为,为了合适地理解这些行为,有必要参考行为者对自己实践的理解方式。由此,那些寻求对社会实践进行理解的人必须考虑实践者自己的想法和感觉。[8]基于这种认识,哈特认为,一个法律规则如果是有效的,它一方面要求普通公民的服从,即对主要规则的服从,另一方面又需要官员把次要规则作为公务行为的重要的共同标准来接受。其中,官员的接受是维持一个法律制度统一的必要条件。
在探讨法律真理时,德沃金同样采取了“内在主义方法”。他在《法律帝国》中明确地说道:“本书采纳了内在的、参与者的观点;试图通过参与这种实践并努力分析参与者所面临的有关真实性和可靠性问题,以掌握我们在法律实践中的争议性特点”。[7]P13德沃金还对“外在主义”方法进行了批判:“这些理论无视法律争论的内在特性,因此,他们的解释就像不可胜数的数学史方面的问题一样……显得贫乏而有缺陷。”[7]P1
确实如哈特、德沃金所言,外在主义虽然能够揭示法律的某些表面特点,但随着这些法律理论越来越精致,其离法律真理却越来越远,因此,法律真理的理解离不开参与者的内在视点。
其次,诠释学真理观的引入,消除了法律真理问题上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扫荡了法律中的“工具主义”思想。
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反对自近代以来的主客体分裂对峙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这种主客体的分离助长了主体对客体的计算或征服。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主体对客体征服的深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于是,关于存在的真理都失去了家园,甚至隐而不显。因此,必须重新追寻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真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主客体二分这种认识模式所带来害处的反思非常值得人们警醒,这种主客体二分认识模式在法律领域同样贻害不浅,它使得“工具主义”思想在法律领域盛行。曾几何时,法律被当成了统治者镇压被统治者的工具,被当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法律这一人造物“异化”为压迫人的工具,“沦为”少数人手中挥舞的大棒,这不正是伽德默尔所说的“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吗?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真理被严重地遮蔽了。
(三)诠释学意义上的法律真理
那么,这种超越了认识论路径的法律真理是什么呢?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所谓真的行为,就是从“自己最本己的能在方面来领会自己”,是“此在在最本己的能在中并作为最本己的能在把自己对它自己开展开来”[1]P267。海德格尔认为,真理的本质不过是人生本来状态的一种展开,就是此在“去是”,去“成其本质”、“实现本质”。也就是说,真理是使得人成其为自身而不是他者的一种方式。因此,法律真理也不过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是人展现自我、规划自我的一种方式,是人为实现自身本质而进行的一种制度安排。
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最能体现人的本质,实现人的价值呢?从历史上看,那种限制人身自由、剥夺人的权利,使得人压迫人正当化的法律显然不能成为法律真理;那些为了保障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设定的制度安排,也算不上法律真理;只有那些最能充分保障人的自由与权利、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全面展现人自身本质的法律才是法律真理,只有在如此的制度安排中,人才能够自由自在地追求自己的价值目标,实现人的本质,使人成其为人。
当然,法律真理也具有历史性。所谓法律真理的历史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任何法律真理都要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亦即存在着相对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针对于人的最好的制度安排,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律真理。第二,人们对法律真理的理解也具有历史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每一种理解都是在“先入之见”和“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解的历史性是理解能够发生、理解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传统之中,被传统所塑造,“先入之见”与生俱来,且无法通过“心理移情”或其他方法彻底克服,甚至文本赖以栖身、理解赖以进行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先入之见”,当人的理解活动展开时,“先入之见”已经渗入其中了。我们对法律的理解也是如此。一个社会的法官、市民以及法学研究者总是生活在一定的传统之中,他们都打上了一定的法律文化的烙印,因此,他们对法律真理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的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政治道德观念的约束,不可能达到法律实证主义所鼓吹的、对法律的纯客观的理解。
我们是否可以借助科学的手段来认识如此的法律真理呢?如前所述,由于近代以来的“科学”观念假定了主客体的分离,假定了“是”与“应当”的分离,并将自身的作用域限定在“事实”领域,因此,对于探讨价值真理来说,它起到的作用确实有限。借助科学手段,我们也许能够认识到法律真理的某些片断、某些局部,但并不能真正地达致法律真理。基于此,探究法律真理的最好手段就是进行法律实践,只有在法律实践中,人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律真理。这好比一个游泳者非得进入到游泳池之内,亲身体验,大胆实践,才会掌握游泳的技巧一样。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正确理解法律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其运用为前提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律的每一次应用决不仅限于对其法律意义的理解,而是在于创造一种新的现实。”[9]P506也正是在法律实践之中,法律规定不断地突破自身的真理性意义,向其它的理解方式推进,从而使真理性认识在认识运动中永远不会成为僵死、不变的东西,从而使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在千变万化的语境中向有生气的、生生不息的意义转变,实现意义的数量级增长与翻新,最终使真理由教条、机械的唯一形式向广泛、灵活的动态真理转变。
很多学者不愿意承认法律真理,或者不愿意接受“法律真理”这一说法,其中的原因很多。意大利哲学家安娜·平托的观点也许最有代表性。在《无需真理的法律》这本书中,他说道:“虽然我们需要真理的思想,但是,当我们将它应用于规范与法律领域时,这种思想就会走向其反面。尽管人们的目的是将法律拉回到现实世界,但是,在价值层面上,真理符合论为法律提供的现实根基无情地转变成了一种主观的帝国主义,它为法律权威(真理的主人)提供了一种全权委托的训令,使规范意志具有了明确的合法性。”[10]安娜·平托说出了很多人想说的话,因为她从真理的历史中看到的是少数人以真理为借口对人的压制,很多统治者都将自己打扮成真理的化身,或者“口吐真理的人”,如果我们再承认存在着法律真理,那法律不就变成异化了的“利维坦”?
安娜·平托的担忧不无道理,这也是人们的一种普遍担忧。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安娜·平托的著作,就会发现,他所担心的“真理对人的压迫”实际上主要表现在各种各样的真理符合论上。按照真理符合论,判断某个法律是否是真理,要么看它是否体现了上帝的旨意,要么看它是否与某种抽象的形式相一致,要么与统治者的命令相一致。无论在那种情形之下,人都处于一种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之上,都会导致法律真理对人的压迫。但是,我们此处所理解的诠释学意义上的真理就可以避免这一问题。按照诠释学真理观,所谓法律真理,就是人为自己所设计的、实现自身本质的一种制度设计,这种法律真理是在法律实践之中生成的,对这种法律真理的理解离不开从事法律实践者的主观体验,因此,那些压制人的东西自然不会成为法律真理。诠释学真理观的独特性还在于它将法律真理的发现、判断都托付给人的实践理性,承认法律真理的多元性,承认人们在发现法律真理的道路上是民主的与平等的。
注释:
① “约根森困境”(Jorgen Jorgensen’s dilemma),以20世纪30年代瑞典哲学家约根森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探讨而得名。“约根森困境”是在价值真理问题上坚持符合论立场的人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价值判断是一种评价性判断,不能用真假来刻画,而科学是以陈述性命题为基础的,科学命题是一种具有真假值的命题,因此,试图用科学方法研究价值问题、创立价值科学体系的人都会面对这一困境。
[1]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上海:三联书店,1987.
[2] [英]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3] DennisM.Patterson.Law and Truth[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4] Joles Coleman.Book Review[J].Cal.L.Rev.,1978(66):855.
[5] R M.Dworkin.Objectivity and Truth:You’d better believe it[J].Philosophy&Public Affairs,1996.32.
[6] R M.Dworkin.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Law[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5.
[7] 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8] H.L.A.Hart.The concept ofLaw[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
[9] 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M].台湾:东方出版社,2001.
[10] Anna Pintore.Law without truth[M].Deborah Charles Publications,Liverpool,U.K.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