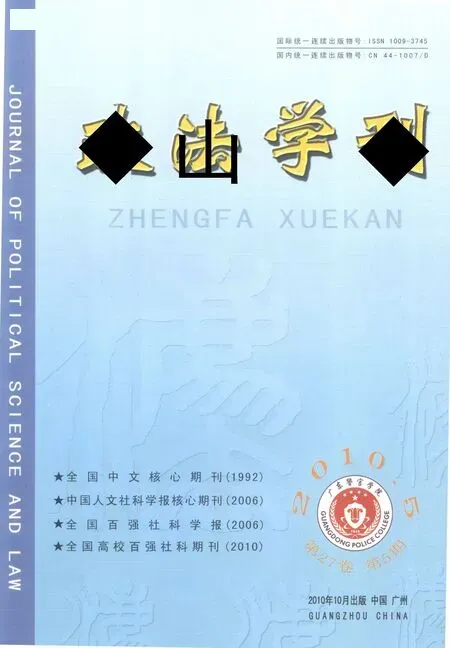对中国立法权设置的反思
——以几个法律文本为考察中心
沈寿文
(云南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对中国立法权设置的反思
——以几个法律文本为考察中心
沈寿文
(云南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通过对现行《宪法》,以及《立法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文本的考察发现,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关于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自治法规制定权、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的规定并不一致。导致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最为浅显的是立法者 (以及修宪者)在制定法律性文件时没能与其他法律性文件相协调;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根植于两种错误观念中:一是误解了人民权利的正当性基础与国家权力 (包括法律性文件制定权)合法性来源的差异,二是混淆了《宪法》和法律在规范国家权力中的不同作用。
立法权;设置;混乱
一、中国若干法律性文件的设定状况
(一)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设置
1.《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 《立法法》的规定。首先,在现行宪法(1982宪法)体制下,我国一定层级的地方权力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直接来源于 1982年 12月 4日通过并公布施行的《宪法》本身。《宪法》第一百条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此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 2004年的四次宪法修正案均没有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内容,因此,至今为止,《宪法》关于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仍然保留了 1982年制定时的状况。其次,地方性法规的内容同样出现在《地方组织法》中。1982年 12月 10日修改后的《地方组织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第二款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此后,1986年、1995年和 2004年的修正案均没有涉及地方性法规的修改内容,保留了 1982年第一次修改后的内容。再次,地方性法规的内容还出现在 2000年的《立法法》中。《立法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较大的市 (含省会城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立法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地方性法规备案的机关和程序: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2.三部法律性文件规定的比较。令人费解的是,《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并不一致。首先,在制定主体上,《宪法》规定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主体是“省、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而《地方组织法》则是在《宪法》的基础上增加了 “自治区的人大”和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同时减少了“省、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而同样令人不解的是,在地方性法规制定主体上,相对于《宪法》而言,《立法法》增加了“自治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 “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相对于《地方组织法》来说,《立法法》增加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省会城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常委会”和“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其次,在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和审批上,《地方组织法》在《宪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备案对象——国务院;此外,针对新规定的省会城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组织法》规定必须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立法法》在《地方组织法》的基础上,省级的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对象一律确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的备案或者审批对象和程序也比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就《宪法》没有规定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与《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不一致上看,似乎可以从《宪法》第 115条中推论出来。因为该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其中,自治区的自治机关还“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而这里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指的就是非自治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因此,从级别上看,自治区与省、直辖市是平级的地方单位,其国家机关自然可以行使与省、直辖市相同的职权,而这些职权就包括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然而,这种推论仍然存在问题:一方面,即使可以这么推论,《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所谓的自治区的自治机关指的是自治区的人大和人民政府 (《宪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并不包括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虽然推论后和《地方组织法》一致,但与《立法法》的规定同样不一致,因为《立法法》还规定了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另一方面,如果这种推论可以成立的话,则自治州的权力机关 (至少其人大)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几率应当比较大。这是因为,从级别上看,自治州与设区 (县)的市是平级的地方单位,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 (1984年制定、2001年修正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条第二款);而设区 (县)的市在当前有四种情况:一是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二是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四是除此之外的其他设区 (县)的市。在这四种情况下,前三种的市,根据《立法法》,其人大及其常委会均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如果严格按照《宪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至少作为自治机关的自治州人大应当享有 3/4几率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但实际上,自治州却与上述第四种情况下的市一样,并不享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综合这两点可以断定:《宪法》第一百条没有规定自治区 (当然还有自治州)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并不是因为《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已经隐含这种职权,而是立宪者根本没有考虑自治区 (和自治州)应当拥有这种立法权。
(二)自治法规制定权的设置
1.《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自治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权来源于 1982年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该条并规定:“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在此后的四次《宪法》修改中,并没有涉及本条内容,因此,迄今为止《宪法》仍然保留了 1982年制定的状况。有意思的是,在 1982年宪法颁布后的第四天所颁布的《地方组织法》中,并没有涉及自治法规的内容,此后的三次修改中也没涉及这一内容。而 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照搬了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该法第八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在公布后的三十日内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2001年在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时涉及自治法规的制定在内容上与《立法法》一致。
2.三部法律性文件规定的比较。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与《立法法》一致,一方面突破了《宪法》的规定,在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批的对象上增加了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另一方面,在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生效后,备案的对象增加了国务院。
(三)地方规章制定权的设置
1.《宪法》、《地方组织法》、《立法法》关于地方规章制定权的规定。1982年制定的《宪法》并没有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有地方规章的制定权;此后的四次修改也都没有规定这一职权。在现行宪法制度下,地方规章最早出现在 1982年的《地方组织法》中,该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报国务院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报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此后《地方组织法》的三次修改中,均没有涉及这一内容,保留了 1982年制定时的条文。在 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中,涉及的地方规章的条文主要有第六十三条、第七十三条和第八十九条。其中《立法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而第六十三条第四款界定了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 “较大的市”的范围:“本法所称较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2.三部法律性文件存在的比较。首先,《地方组织法》突破了《宪法》的规定,增加了 “地方规章”这种新的法律性文件,并且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有权制定这种法律性文件。其次,《立法法》进一步突破了《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增加了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有地方规章的制定权;同时,《立法法》在较大的市地方规章制定的依据上,增加了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
(四)部门规章制定权的设置
1.《宪法》、《国务院组织法》、《立法法》关于部门规章制定权的规定。国务院部门规章这种法律性文件最早出现在 1982年制定的《宪法》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中,该款规定 “各部、各委员会”有部门规章的制定权。此后的四次宪法修正案均没有涉及部门规章的内容,迄今保留了1982年《宪法》规定的条文。此后同年通过实施的《国务院组织法》也与《宪法》的规定一致。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在第七十一条、七十二条规定了部门规章。《立法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立法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
2.三部法律性文件的比较。从上述三部法律性文件看,《国务院组织法》关于部门规章的规定内容与《宪法》一致;但是《立法法》却突破了《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增加了审计署、中国人民银行和直属机构的部门规章制定权;增加了两个以上部门联合制定规章的权力。尽管从法理上看,由于审计长是国务院组成人员之一(《宪法》第八十六条),审计署完全可以涵盖在《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关于国务院 “各部、各委员会”的范围内,但是《立法法》却单独列举出来,至少说明《立法法》的制定者认为它们之间并不相同。
二、对中国立法权设置不一致的反思
(一)“立法权”设置依据不一致的处理方式
1.宪法与法律之间的规定不一致的处理方式。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为了维护法制统一,法律性文件之间规定不一致的,高位阶的法律性文件效力高于低位阶的法律性文件。然而,中国现行法律性文件的依据却存在 (甚至是普遍存在)与《宪法》不一致的规定,而且似乎被官方不假思索、不加质疑地接受。首先,就地方性法规的依据而言,《宪法》规定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主体只是“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并没有规定自治区有这种职权,我们的分析也证明了 1982年立宪者根本就没有赋予自治区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意图;然而仅仅过了 6天,同一制定机关便在《地方组织法》中增加了《宪法》规定的部分内容,同时也减少了《宪法》规定的部分内容;与此情况相同,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也突破了截止 1999年修正后的《宪法》的规定。法律这种公然的与《宪法》抵触的状况,至今仍然有效的奇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当然,或许有人认为,这些法律之所以继续有效,乃是《宪法》默认的结果;但是,假设《宪法》默认了《地方组织法》规定的合宪性,为什么后来宪法的四次修正案都没有作相应的修改,以与《组织法》、《立法法》相一致?我们不应忘记:《宪法》的最近一次修改是 2004年 3月 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完全可以通过修改与相关法律规定一致,却没有涉及这些条文。其次,就自治法规而言,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和 2000年的《立法法》均突破了《宪法》的规定,增加了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报批对象和备案对象。而令人费解的是,20001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时,并没有与当时的宪法(1999年修正后的《宪法》)相协调。反过来,即使《宪法》默认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的规定,2004年修改宪法时,《宪法》修改的内容中也没有涉及这一内容。此外,在地方规章和部门规章的依据上,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在此问题上,有学者在“’较大的市’之人大与政府作为地方立法主体的资格”的问题上,便中肯地指出“存在了违宪嫌疑”,[1]实际上,针对法律性文件与《宪法》明显不一致的效力如何确定问题,并非没有依据:现行《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宪法》第五条都明确了宪法效力高于其他法律性文件。
2.法律与法律之间的规定不一致的处理方式。与不同位阶法律性文件效力等级这种令人一目了然的情况稍微不同,当同一位阶的法律性文件存在不一致时,到底应当适用哪一个法律性文件,问题较为复杂——至少在中国现行法律体制下如此。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上,《立法法》与《地方组织法》并不相同;在地方政府规章的规定上,《立法法》与《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也不一致;在部门规章的规定上,《立法法》与《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同样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到底应当如何处理?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法律的性质。按照现行制度,法律分为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的“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即 “一般法律”),从理论上看,它们之间实际上应当有效力上区分的必要,否则也就没有必要划分这两种不同的“法律”了;然而由于理论储备的不足,当前关于什么是“基本法律”、什么是“一般法律”,它们之间划分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并没有获得理论上的解决,而现行宪法的规定也十分笼统,我们仅能就《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判断其中列举的 “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内容的法律属于“基本法律”范围,因而仍然无法从理论上对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中进行区分,只能是通过制定机关“倒读”法律是否属于 “基本法律”还是“一般法律”: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就是“基本法律”;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制定的,就是“一般法律”。我们很幸运地看到,《立法法》、《地方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它们显然处于效力等级相同的位阶上,由此我们也可以避免“基本法律”与 “一般法律”不一致时到底适用哪一种法律的理论困境。其次,既然位阶相同,当两部法律规定不一致时,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立法法》第八十三条)。然而,什么叫 “特别规定”、“一般规定”、“新的规定”、“旧的规定”?在 “立法权”的设定上,《立法法》的规定相对于《地方组织法》和《国务院组织法》是 “特别规定”吗?假设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自然是应当适用《立法法》。不过,我们注意到,《立法法》是 2000年制定的,而《地方组织法》却在 2004年修改过,换句话说,“新的规定”和“旧的规定”的判断标准是根据制定时间,还是根据最后修改的时间?从法理上看,显然应当根据最后修改的时间来进行比较,如此一来,便产生了一个问题:从“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上看,应当适用《立法法》;但从“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上看,至少在《立法法》与《地方组织法》不一致时,却应当适用《地方组织法》。由此带来一个困境:底应当适用哪一部法律呢?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将这一矛盾的解决丢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法律没有《宪法》作为参照时,探讨这一问题才有必要;当存在作为上位法的《宪法》时,只能适用与《宪法》相一致的法律。
(二)“立法权”设置依据不一致的原因分析
显然,之所以会出现对同一问题法律与宪法规定不一致、法律与法律之间规定不一致,最为浅显的原因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性文件时根本没有注意与其他法律性文件相协调,然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根植于官方的两重误解中:
1.官方误解了人民权利的正当性基础与国家权力 (包括法律性文件制定权)合法性来源的差异。在官方看来,人民的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只要法律性文件没有明文规定为人民的权利,人民似乎就不能享有这些权利,这也就《宪法》不厌其烦地罗列人民的各种权利的原因,而这种思路的弊病是:把人民的权利视为是 “授予的”不仅在法理上导致混乱,在实践中也带来危害,首先,从权利的范围看,它强化了这样的观念,即人民的权利是有限制的,这个限制就在于法律和宪法文本的规定,换句话说,人民的权利仅仅存在于法律或者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其次,从权利的来源看,这种观念导致了一个本末倒置的可怕后果,即人民的权利来源于法律或者宪法的施舍,甚至进而认为人民的权利来源于国家的认可。与这种对人民权利的正当性基础的思路相一致,在国家权力 (包括法律性文件的制定权)的合法性来源上,官方认为,国家权力是可以通过《宪法》之外的法律性文件予以 “授权”的:只要先前的法律性文件 (包括《宪法》)没有明文禁止,之后出现的其他法律性文件就可以增添。在这种思维之下,《宪法》没有规定的法律性文件制定权,便丝毫不影响此后的立法者在法律文本中予以增添;与之相同,先前的某一法律没有规定的法律性文件制定权,同样丝毫不影响立法者在之后的另一部法律予以增添。于是,便出现了上文提及的中国现行《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性文件的制定主体或者制定程序,在后来的法律中出现的奇怪现象。
事实上,国家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力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运行规则:一般情况下,国家权力遵循的是法 (包括《宪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除非该行为可以从国家权力行使机关的性质中推导出来)的规则;人民的权利遵循的是法 (不包括《宪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原则。对于后者,一方面,基于宪政的立场,宪法主要是用来约束政府的,因此从逻辑上看,宪法不应规定人民的义务[2],而近代以来有的国家宪法中列举“人民的基本义务”,事实是为了避免政府 (国家)没完没了、任意科处公民的义务而设置的,[3]因此人民的权利所遵循的 “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中的 “法”并不包括《宪法》。换句话说,用以规定人民义务或者限制人民权利的,政府的立法分支可以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对人民的某些权利加以一定限制。另一方面,既然主权在民,既然政府产生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人民享有的权利自然是第一位的、根本的,是先于《宪法》和政府的,由此也决定了人民的权利是在《宪法》和法律中罗列不完的。与之相反,对于前者,一方面,从人民主权的立场出发,既然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第二条第一款),那么由人民制定的宪法产生的政府内部权力便是根据《宪法》和法律进行配置和分工的,甲权力由甲机关行使、乙权力由乙机关行使、丙权力由丙机关行使,依此类推,这些权力便必须由《宪法》或者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否则便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甲机关纂夺乙机关的权力,乙机关纂夺丙机关的权力,丙机关纂夺甲机关的权力,而各个机关均可以对人民实施自己和其他机关的权力的混乱状况。另一方面,国家权力行使的前提是《宪法》和法律,而《宪法》是最为重要的前提,这是因为人民制定了《宪法》,《宪法》产生出政府 (Government),因而政府的合法性来正是源于《宪法》;政府的立法分支制定法律,法律可以规定政府的具体职权,但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宪法》的权威必将遭到动摇,宪法秩序必将受到危害。因此,国家权力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 (包括《宪法》)的依据。然而,中国当前“立法权”设定上存在的混乱,正是官方误解了人民权利的正当性基础与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这种差异。
2.官方混淆了《宪法》和法律在规范国家权力中的不同作用。从宪政立场上看,人民制定出《宪法》,《宪法》产生出政府,政府立法分支行使立法权 (狭义的立法权)具体规定政府各个分支及其内部的权力配置和分工。由此,《宪法》和法律共同完成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在这一秩序的建构和维护中,《宪法》和法律充当了不同的角色:一方面,《宪法》是政府权力来源的基本依据。所谓的“《宪法》是政府权力来源的基本依据”主要指的是《宪法》确定了政府权力的横向和纵向结构模式:从横向上看,《宪法》规定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或者它们的变种)的横向关系,确定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或者它们的变种)的基本框架;从纵向上看,《宪法》确定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 (单一制国家)、联邦权力和组成部分权力 (联邦制)的基本框架。作为一种规定政府的权力责任、人民的权利义务,确立普遍遵守的规则的权力,立法权 (在中国,广义的立法权包括宪法以外的法律性文件制定权)是一种基础性的权力,《宪法》显然应当成为这种政府权力来源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作为政府立法分支制定的法律 (在中国,甚至是更低层次法律性文件)是政府权力的具体依据。“所谓法律是政府权力的具体依据”指的是:尽管《宪法》规定了政府权力的基本框架,但由于《宪法》无法详尽规定政府权力的具体内容,不得不授予政府立法分支通过行使立法权 (在中国,甚至是更低层次法律性文件)来详细规定“立法权”本身、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具体行使部门、运作程序;由此,法律 (和其他法律性文件)便充当了落实《宪法》概括性、抽象性规定的重要角色。然而,这种政府权力的 “具体依据”必须以政府权力的“基本依据”为前提和基础,不得与 “基本依据”相抵触,如此才可能维护宪法和法律秩序。在“立法权”的问题上,法律 (或者其他法律性文件)所应当充当的角色在不改变《宪法》所明确规定的享有“立法权”的主体及其职权的前提下,进一步规定该 “立法主体”如何具体实施其 “立法职权”的内容,而不是增添或者删减其内容。然而,中国当前立法权设定上存在的混乱,正是官方混淆了《宪法》和法律在规范国家“立法权”(广义的 “立法权”)中的不同作用。
三、尾论:错误的立法 (宪)思维与独特的政权制度
如前所述,在观念上,当前《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关于若干 “立法权”设置存在的不一致,根植于官方误解了人民权利的正当性基础与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差异、混淆了《宪法》和法律在规范国家权力中的不同作用。然而,试图打破或者消除这种观念错误并不容易,因为这种错误观念,与现行政权制度 (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 “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宪法》第五十七条);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宪法》第五十八条);此外,全国人大的职权之一是“修改宪法”(《宪法》第一项)、“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宪法》第三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二项)、“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三项)。由于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处于整个国家机关金字塔体系的最顶端,其他中央国家机关 (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由它产生出来的,“只是根据它的意志和制定的法律,进行具体的行政管理或执法活动”,“它有广泛的、最高的、几乎不受约束的立法权”。[4]29这种体制决定了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一切它认为必要的“基本法律”。然而,正如张千帆指出的,“宪政的基本前提是承认’有限政府’的原则。所谓’有限政府’,就是指所有的政府权力都是有限的——不仅是行政权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立法权力,因为它是法治国家所有权力的来源。如果不承认立法权力的有限性,那么即使是法治国家也是一个权力无限的国家,因为立法机构可以制订法律去授权政府做世界上的任何事,不论它如何伟大或荒谬、仁慈或暴戾。”“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承认立法权力的有限性,谈论宪法甚至是一件多余的事情:这部宪法是多余的,或者是因为它完全没有约束力,或者是它和普通法律一样可以被议会随意修改。”[5]14不幸的是,中国当前采用的正是这样一种 “立法权无限性”的制度。这种 “立法权无限性”制度,也为中国现行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一般法律)与《宪法》规定不一致、法律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现象留下可能的空间。因为正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的无限性,即使“基本法律”与《宪法》规定相抵触,“基本法律”与 “基本法律”之间相抵触,实践中也不存在予以矫正的路径和可能,只能寄托于最高权力机关自己的“觉悟”而已。
[1]郑磊.“较大的市”的权限有多大——基于宪法文本的考察 [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 (1):58-59.
[2]张千帆.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 [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3):27-28.
[3]沈寿文.中国宪法文本规定公民 (人民)义务的原因探析 [J].云南社会科学,2009(4):98.
[4]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5]张千帆.倚宪论道——在理念与现实之间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林 衍
A bstract:By examining the provisions of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 Law,Legislation Law,Organic Law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 and Government,Organic Law of State Council and the Law of RegionalNationalAutonomy,we find that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as to the prescriptions in current Constitution Law and other laws on the for mulation power of local laws,autonomy laws,ministerial rules and rules of local government.The apparent reason lies in the lack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legislators of Constitution Law and for mulators of other laws.The underlying causes are deeply rooted in two false conceptions:one is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origi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ights of people and the power of state;the other is the mixing up of the functional differences in regulating state power between ConstitutionalLaw and other laws.
Key w ords:legislative power;placement;perplexity
The Perplexity of Legislative Power Placement in China:Exam ination of a Legal Code
Shen Shou-wen
(School ofLaw,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DF01
A
1009-3745(2010)05-0005-07
2010-09-12
沈寿文 (1974-),福建诏安人,法学博士,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从事宪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