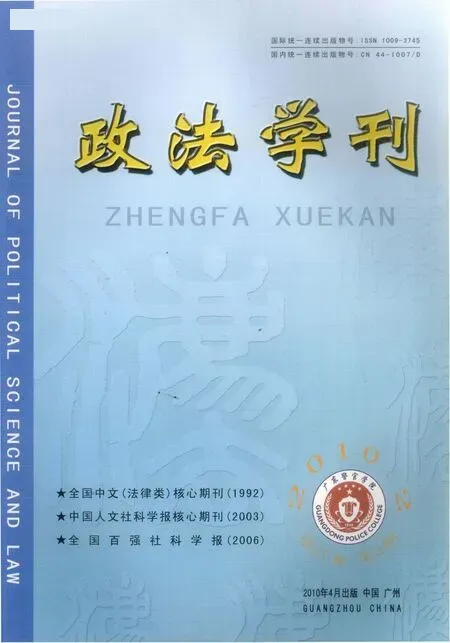乡族与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
田东奎
(宝鸡文理学院 政法系,陕西 宝鸡 721007)
乡族是区域基层社会两个以上的族姓基于公共事业和文化信仰而形成的协调、管理公共事务的实体组织。[1]78它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地域为纽带,以乡里制度为依托,是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基层事务的主要组织。其承担的角色是多样的,既包括对家族事务的管理,也包括对部分公共事务的管理,如水利工程的兴建、维护等,甚至还包括部分司法职能,如民事争议,轻微刑事案件,以及水权纠纷的调解等。乡族在水权运行中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以家族、血缘、地域为纽带,维护现存水权秩序,避免纠纷,有积极一面;另一方面,它以小集团利益为依归,谋求乡族利益,客观上不利于水权秩序的运行。进入近代,虽然乡族制度的功能有所消解,但其影响力仍然存在。它以血缘家族为基础,通过地域纽带,团结乡里非家族群体,成为影响地方基层水利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水权纠纷的发生、争议的解决,甚至水利共同体的构建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较大的乡族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控制水资源。在中国基层农村,一般都是聚族而居,因此,村庄就是乡族的代名词。当然,由于地域不同,战乱的影响,乡族规模大小不一。一般而言,南方聚族而居的现象较北方普遍。北方农村,由于各种原因,一般是由一个较大姓氏组成一个村社,但大部分村社是由一个或几个小姓围绕一个大姓,组成一个村社。大姓家长或族长往往就是这个村社的实际的族长。村社重大事项一般由其主导,并做出决定。家族内部,族人依靠祠堂及祖产,信仰凝聚向心力。村社重大事件的决策,名义上,其他姓氏成员也可发表意见,但实际上,他们很少这样做。一方面,这是出于对大姓族长的尊重,避免议而无果;另一方面,也是各姓氏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必然结果。更何况,大姓族长在长期处理乡族事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很好地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会或尽可能不损害其他姓氏的利益,甚至还会照顾其利益,以换取其对乡族事务的支持。这是村社内部的关系,如果村与村之间因为用水发生纠纷,那么,不分姓氏都会一致对外,绝不会发生意见相左的情况。地跨山西洪洞、赵县、霍州三县的民间水利组织四社五村,包括仇池社、李庄社、义旺社、杏沟社、孔涧村、刘家庄等 15个村庄。从这些村庄名称,可以看出,基本上都是聚族而居。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些村庄的姓氏是比较杂的。但是其村社治理,也遵循以一个大姓为主导,其余姓氏配合的格局。每一个社或村,都有一个社首,相当于族长,它是村社的精英,负责管理水资源分配、渠道维护、费用摊派、水规执行与处罚等。社首在村里享有绝对权威,对违犯水规的村民有处罚之权。在高于村社的水利自治组织内部,也有一个拟制的血缘家族组织系统,“四社一直按家庭兄弟排行,奉老大为四社的总社首,其余三社都低老大一等。他们在任何场合下,都按照这种家庭齿序排序出场,便从无争端”。[2]226对水资源的掌控,不是建立在表面一团和气基础上,而是人们在长期竞争、流血、冲突后,达成的一种暂时的共识。这个共识是以占优势的一方的取胜,弱势一方的称臣为前提。例如,晚清,广东的“地方习俗使强宗大族占有最好的土地和最有用的灌溉系统,弱小宗族以他们的妇女受侮辱作为代价……‘广州人’①应指前文所称的 “广东人”。……在处理争端的时候蔑视诉讼,不考虑促保全生命。为了追随他们祖先沿袭下来的世仇,他们开始将一部分族众召集在一起,手拿梭镖、剑器,以及其他武器,共同战斗”。[3]133当然,争斗最后会停下来,达成某种妥协或平衡。但这只是一种动态的妥协或平衡,当内在力量打破平衡时,也就是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在争夺水资源的战斗中,每一个村民必须服从社首或乡族首领的指挥,不能临阵脱逃。
其次,利用乡族优势,掌控水利组织、水权分配、水权资料,以及祭祀活动,进而取得地方水利社会的话语权。控制水资源是享有水权的重要一步,但是要长期保持对水资源的垄断,就必须借助其他手段,如制定水规、保管水权资料、垄断祭祀、培养民众用水信仰等。在全国各大水利区,都有比较健全的水利组织,解决用水过程中出现的纠纷,保证水权秩序的平稳运转。以山西晋南地区为例,水利用户普遍成立了类似四社五村的民间自治机构。这些民间水利组织的运行有非常浓厚的家族特色。组织内部有主社村、附属村。所谓主社村就是拥有水权的村社,采用家庭兄弟排行方法,以兄弟相称并排序。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意义在于,它也是分配水权、祭祀权的重要方式。水利自治组织的核心集团是社首组织。社首分正社首和副社首。各主社均设一名正社首,二到三名副社首。附属村既没有正社首,也没有副社首。各社正社首组成决策集团,掌管着四社五村的水利命脉,主要职责是制定用水方案、规划水利工程、管理水利经费、处理水权纠纷等。副社首管理社内财物账簿、水利摊派、祭祀操办、工程检查等。正社首一般通过选举产生,可连选连任。所谓附属村,由主社村携带,利用主社村的余水,安排村社的生活。四社五村水利组织,有九个附属村。南川草窪村和北川草窪村附属于老大仇池社,琵琶塬和百亩沟村附属于老二李庄村,桃花渠、南泉和南庄村附属于老三义旺社,窑塬村附属于老四杏沟社,刘家庄附属于老五孔涧村。附属村从属于主社村,没有水权,但有用水权。其主要义务是维护水利渠道的正常运行。其具体方式可能是出工,也可能是出钱。此外,应主社村要求,替主社村看水。如果附属村违犯水规,其处罚是非常严厉的。通过社首组织,社首集团牢牢地掌握了对水资源的控制权。为了强化这一具有地方法效力的习惯,社首通过祭祀活动,不断向附属村及其村民灌输遵守这一水规的好处,以及违犯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四社五村每年对水利簿的祭祀仪式安排在清明节前后举行。这是一个非常庄重而严肃的庆典。在这个日子里,通过一系列宗教仪式向民众传达其所使用的水来自神灵,因此,任何人都不要试图去改变它或以其他方式表达对水利簿的不敬。同时,祭祀活动也是清理水利账目,处理水权纠纷的重要场合。当然,像许多类似的祭祀活动一样,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狂欢节。辛苦劳作了一年的人们,在祭祀后通过观看戏曲,放松一下。妇女、孩子们可以借此获得精神的享受。亲朋好友也可通过这一机会,联络感情,交流生产信息。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以愉悦的方式教化人们遵守水规,节约用水。通过这些手段,族长或社首就可永远掌握对水资源的发言权,并左右乡村社会的话语权。社首的意思也就是整个乡族的意思,社首的意见就是乡民的意见。当水资源短缺或气候异常,用水紧张时,他就会以族长或社首的身份将分配水资源的方案朝着有利自己的方向倾斜;当水资源能够满足人们需要时,族长或社首引导人们合理用水,杜绝浪费。
再次,处于优势地位的乡族对水权纠纷的解决起着阻碍作用。如果说乡族因素在预防水权纠纷方面还有积极作用的话,那么,乡族因素介入水权纠纷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有时候,甚至使对立双方走入死胡同。因为,水权纠纷的解决必须建立在水资源国家所有的观念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水资源共享的前提下。但是,以乡族观念为主导的乡土社会,以乡族、地方利益为最高诉求,排斥水资源共享理念。在他们的观念中,要么由“我”家族主导水资源分配,要么由 “他”家族主导水资源分配,妥协余地很小。而且,发生水权纠纷的地区,一般都有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纠纷后遗症,双方情绪对立,很难协商、沟通。有些村社之间甚至是世仇,不往来,不通婚。因此,一旦发生纠纷,双方往往情绪对立,反应激烈,很容易失控,酿成群体冲突。即使动员国家力量,也难以解决,有少部分甚至酿成血案。而这些血案,又会变成水权纠纷的历史记忆。胜利一方,以此作为激励乡族精神的支柱,鼓励后代保持对已有利的水权分配方案;失败一方,以此作为耻辱的标志,时刻寻找机会,以夺回水权,报仇雪耻。即使今天,纠纷双方县志对同一案件的记载,往往观点对立,褒贬不一。由可见此,乡族观念、地方利益对水权纠纷的影响是多么深远!乡族势力在水权纠纷解决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水权纠纷发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看到乡族力量的存在。在纠纷酝酿阶段,它起着社会动员的角色;在纠纷发展阶段,它又是动员群众,对抗国家力量的中坚;在纠纷发生后,甚至冲突发生后,包括血案之后,它又是抚慰受伤者,惩罚肇事者,并对受害者进行物质救济的福利组织。民国年间河南灵宝县虢略镇发生的涧东、新庄两村争水惨案,就是典型的例子。新庄村利用妇女、儿童向对方施加压力,面对强大的良心谴责和道德压力,①因为水权纠纷,导致新庄村两名村民死亡,故面对打着死难者家属旗号的妇女、儿童,涧东村民处于两难境地。涧东村既不能还手,又无计可施,最后只能逃离家园。很难想象如此组织严密的行为,没有乡族力量的介入,能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甘肃北沙河流域的水权之争,涉及永昌县乌牛坝、武威县三岔堡、民勤县蔡旗堡,从明代崇祯三年一直延续到民国。纠纷的根源是由上游乌牛坝蛮横截霸水源所致:“看到水利之所在,人人有必争之心,而未有若乌牛坝诸人之贪,而日校父子祖孙,如出一辙也。夫以一河之水,三岔、蔡旗一年之中,仅得七日,其余则皆上坝之源源用之不穷者,亦云足也。乃推满河以自润,而必不肯分一勺以救人,当五月用水之时,故意与之相打,故意与之告状,有事则众人为之出力,有罪则各家为之朋当,官事未休,田苗已割,今岁已断,明岁复翻,是乌牛坝之人年年享满沟满车之利,而三岔蔡旗无及终岁坐枯鱼之肆”。[4]360也就是说,上游乌牛坝从狭隘乡族利益出发,无视下游两县用户正当权利,主张绝对用水权,使纠纷不断发生的主要原因。为了达到长期独占水源的目的,乌牛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故意与下游打官司,遇有纷争则村民集体响应,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加。如果因此而导致犯罪,则由村民共同承担后果,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每遇用水高峰,他们故意引发纠纷,霸占水源,等到官司完结,已过用水高峰期。当然,也错过了最佳耕作期。他们不断重复这一过程,从而达到了长期独占北沙河水资源的目的。这样,上游以家族以核心,通过各种策略的运用,达到了对北沙河水资源的长期垄断。从北沙河水量来看,完全可以满足下游全年七天的用水量。但是,乌牛坝就是不肯答应,一年一年地挑起和下游的纠纷。历代王朝、政府对此案发布的水利执照、水权令多达 10道,如临洮同知于 “明崇祯十四年判发北沙河上游五坝与下游三坝用水执照”、“康熙四十九年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用水执照”、“雍正十二年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用水执照”、“乾隆九年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用水执照”、“乾隆十六年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用水执照”、“道光二年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水利告示”、“道光三年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水利告示”、“光绪四年铁道台判武威与永昌两县互争水源案文”、“光绪十年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水利告示”、“民国三十八年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水权案文”、“民国二十七年省政府发北沙河上游五坝与下游三坝用水训令”等,但是,水权纠纷一直没有解决。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执照、水权令只是纠纷发生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部分而已。实际上,每一个执照或水权令都包含了多起纠纷,以民国二十七年“甘肃省政府所发训令建二已字第 1132号”用水训令为例,就涉及了民国 16年、17年、19年、22年、23年、25年的用水纠纷。[4]357-359因此,乌牛坝对下游两县截霸行为可以说是经常性的,几乎每隔一年、两年就要发生一次。而每发生一次就意味着下游两县部分村民收成的减少。事实上,武威、永昌、民勤三县关于北沙河的水权界限自崇祯十四年临洮同知下发水利执照时就已明确,但上游乌牛坝拒不执行历代王朝地方官员,以及民国政府下发的水利执照、水权令。每一次解决,就意味着新的纠纷的重新开始。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就是上游片面的乡族意识和地方意识。
最后,水权纠纷解决以后,仍然面临着如何落实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乡族势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起着阻碍作用,消极影响大于积极作用。乡族势力对分水方案的消极抵抗,或不执行,影响水权处理结果的法律效力。水权纠纷,不论是以调解方式、行政处理方式,还是以司法方式解决,最后都要求双方做出一定让步和妥协。根据调解中立性原则,行政决议执行性原则,以及司法权威性原则,这些处理决定都应无条件遵守和执行。但水资源的稀缺性,乡族利益、地方利益至高无上,决定了纠纷各方很难达成双方都满意的水资源分配方案。而且,优势一方常常以先例原则,压迫对方接受对已有利的方案,那怕这个方案不合理,不公平。因此,达成协议本身就不容易,即使达成了协议,要将其付诸实施更不容易。而且,水资源变化的无常,加大了信守协议的难度。例如气候、植被等自然条件的变化,会影响水资源总量。一旦天气干旱,水量减少,刚达成的协议又可能付之一炬,导致争端重启。四川湔江堰,春季灌溉用水较多。每年这个时候,就会发生水权纠纷。1946年 (民国三十五年)5月 10日,彭县县长刘度为缓解用水矛盾,在该堰试行轮灌制度,以解决水权冲突。虽然,县政府事先已行文各乡镇及水利分会,要求其向用户讲明道理。但执行当天,上游各河堰民众数千人,聚集一起,反对轮灌。他们 “荷锄持械,聚集堰首,寻衅闹事,捣毁器具,毒打工人”,气焰非常嚣张。[5]106县长刘度闻讯后,立即派警察处置。但肇事者早已逃之夭夭。几千人公然违抗县政府做出的行政决议,说明在乡土观念、乡族意识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政府决定、法院判决是多么苍白无力啊!
因此,乡族意识、乡族观念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带有明显传统色彩的落后观念。作为一种传统资源,既有其积极一面,也有其消极一面。就水权问题而言,它在动员乡村社会资源,建设水利设施,构筑水利共同体,抵御干旱,排除洪涝灾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我们也要看到,乡族观念是一种与身份、血缘、地域相联系的保守意识,是传统社会宗法制度的残余,与近代中国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等观念格格不入。特别是,它以身份、血缘、地域为基础,依据亲疏远近,将人分为不同等级,给予不同待遇;凡是与自己有血缘、有地域联系之人,可享受一定优待,反之,则会受到歧视性待遇,甚至不公平待遇。水权纠纷反复发生,固然有水资源流量变化等自然因素,但是,以家族利益、地方利益为价值准则,忽视、漠视,甚至篾视他人权利,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水权,固然是一项物质权利,但是,在水资源短缺地区,它关系到民众的生存,又是一项人权。因此,片面强调自己的水权,势必导致侵害他人水权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族意识、乡族观念与近代进步水权观念是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乡族因素在水权纠纷形成过程中,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促成纠纷解决的积极一面,也有激化矛盾,使纠纷升级的一面。如果从水资源短缺的前提出发思考水权纠纷的解决之道,我们只能说,乡族因素往往激化了矛盾。因为,乡族组织的主要职能就是为了在资源争夺战中,取得优势地位,从而控制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人们信服族长或社首,就是因为他能够在与别的乡族争夺水资源的斗争中,以自己个人能力和威信为乡族争得实际利益。
[1]张研,毛立平.从清代安徽经济社区看基层社会乡族组织的作用 [J].中国农史,2002,(4).
[2]董晓萍.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Z].北京:中华书局,2003.
[3]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M].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武威市水利志 [Z].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5]成都市志·水利志 [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