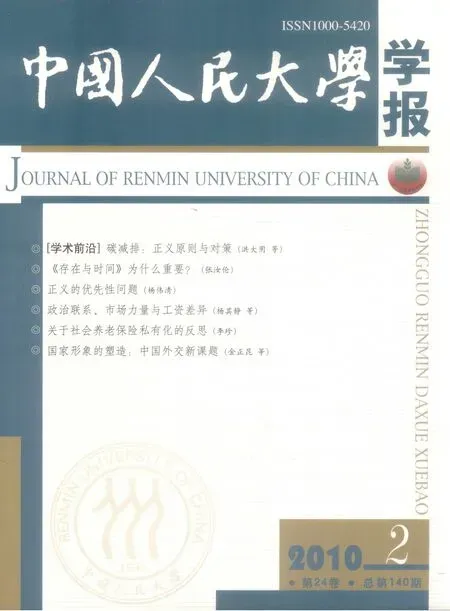从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过程看国家权力、公民权利与义务
欧阳景根
从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过程看国家权力、公民权利与义务
欧阳景根
在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过程中,权利与义务的边界不是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的结果,而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由一群理性人基于现实需要而相互选择的结果,是现实合力和管理需要的结果。不能停留在政治哲学层面上去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而应该从现实管理与现实政治的角度去理解。无论是公民权利与义务,还是集体权利,都有着上下两条边界。国家权力在扮演危机管理者的角色时,它的权力上限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如无授权,则不能与公民权利的下限即公民的最基本权利相冲突。
公共卫生事件;国家权力;公民权利;义务
2009年10月,甲型 H1N1流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大面积扩散,而不同国家在应对这一流感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成效却有天壤之别。在爆发和应对以传染病为主要表现的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定情境中,“我们最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或者“你最不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以及实现这一生活选择的具体哲学方式是什么?在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过程中,为了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更好行使,应在何处给它们划定一条明确边界并同时给履行应对职能的国家权力划定边界?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在这一特定情境中,国家与个体之间以及在公民权利、义务和公共权力之间,其合适的边界应当置于何处的问题。
关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包括自由主义学派、社群主义学派和共和主义学派在内的很多政治哲学家们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探索,主要是基于应对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的考虑,分析在以传染病为核心表现方式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过程中,公民和国家权力的代表者分别应该持何种态度,取何种立场,才能一方面既有效保护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不会受到公权力的侵犯,同时又能更好地保护集体权利,更有效地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的扩散。本文的出发点是从政治哲学层面对现实政治和管理过程中应该如何明确划定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合适边界,并因而划定集体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边界,从而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现实政策的尺度和思想基础。
一、公民权利的边界
在政治哲学史上,范式间的争论始终不曾停止过。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争论、帝国主义时期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争论竞相粉墨登场。争论的双方都认为他们所持的观点无法在政策上共存,或者说都无法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去思考自己和对方的未来,因此,力求彻底消灭对方并从而一举成为指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正统学说。这种思维缺陷进一步扩散到了晚近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及公民共和主义之间的学术争论。在这场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学术论争中,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原本是争辩的双方,后来,公民共和主义力图整合并超越二者的主要观点以开辟“第三条道路”而加入到论战当中。然而,各个派别一直深陷其中纠结不清的首要问题是:权利与义务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有了权利才有了义务,还是因为有了义务才有了权利?
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政治哲学战场上才会有两个阵营的分野与对抗。阵营的第一方包括了自由主义者和权利至上主义者。虽然前者的核心主张与后者有较大差别,但如果以对义务的认识为标准,那么,本质上他们就属于同一阵营。而且,恰恰因为自由主义是建立在权利理论的哲学基石之上,自由主义者往往也是权利主义者,这一阵营以德沃金为主要代表,在他看来,个人权利是个人手中的护身符,凡是义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得不到充分证明的地方,就是权利应当存在的地方。因此,这一阵营的思维逻辑是,“如果某人对某事享有权利,那么,即使否认这种权利符合普遍利益,政府否认这种权利也是错误的”[1](P352)。由此可见,权利至上主义因权利至上而成为一种绝对意义的观点,又因“只要说明不了义务的合理性,就存在权利”的否定逻辑而成为一种反证性学说。总之,正是因为它的绝对性和反证性,它必然无视甚至否定义务从道德到逻辑、到现实的一切存在基础(并因此而变得在现实生活中毫无意义),就更不用说在权利与义务之间划定一条边界了。
阵营的另一方由社群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构成。这个阵营的共同特征是:因为对公共生活、公共利益的高度关注和强调,而在逻辑上必定导致对义务之必然性和绝对性的强调。在他们眼中,集体、社群的权利和利益,高于个体的权利和利益;个体权利与利益的正当性,以集体的权利和利益为基础和前提;维护社群的公共利益既是个人的义务,还是实现个体利益与个体权利的必由之路;集体、义务是绝对的,而个体、权利是相对的,集体和义务随时都可以自由地向个体和权利扩张渗透。他们是集体至上主义者和公共利益的理想主义者。在思想上,这种观点的必然逻辑结果是“牺牲小家,成就大家”原则的教旨主义化和意识形态化;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它们又因无视义务的边界而必将滑向对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
总之,阵营双方之间首先是因其逻辑假定上的先验式对立才变成了貌似范式之争。其实,只要在权利与义务之间、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划定一条明确边界,这场范式之争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两个阵营的争端也就迎刃而解并显得无足轻重了。在笔者看来,诸如此类的政治哲学上所谓的范式之争,多可归因于在某一个本无关大局的问题上一方加以放大,而由一方把另一方想象为假想敌和“稻草人”,把虚构的敌对的另一方从后台逼到了前台,这样,另一方就只能被迫应战,原本并无意义的观点差异也因而显得生死攸关起来。我们需要跳出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之争的思维陷阱,直面权力、权利和义务之间的边界,直面国家权力和集体权利的边界。
如夏皮罗所意识到的,“建立一套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理论而不考虑人们实际上如何履行它们是无意义的”[2](P204),所以,要考察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公民权利的边界等问题,只需考察公民最有可能实现的他最希望实现的权利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假定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情境中,自己就是一个病毒携带者或密切接触者,然后再紧扣在这一特定情境中,回答“我们最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或者“你最不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
在正常情况下,每一位公民都享有自由行动权等权利。①正常状态下公民享有很多权利。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状态下,公民应该享有和行使的权利的范围和边界(不管它是哪种类型的公民权利)都是重合的,并不会因为它是不同的权利类型就应当相应拥有不同的权利边界。那么作为一个病毒携带者或密切接触者,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他的自由权(包括其他形式的权利)的边界应该划定在哪里呢?在任何情况下,公民权利都不会是一无所有、消失殆尽的,同样,公民权利也不是无所不包、随心所欲的。因此,公民权利的边界就包括权利的上限和下限。这样,结合在这一特殊情境中,“我们最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或者“你最不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病毒携带者,你的公民权利的上限就是:当你作为一位健康者,同时也是一位理性人,你也不希望别人(病毒携带者)这么对你,不希望别人在这种情境下接着拥有和行使的那种权利。换句话说,当你的权利行使威胁到他人安全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为了你的这一权利的行使而履行他们对你的义务——即尊重你的这一权利的义务,而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是会尊重你的这一权利的。
以人身自由权为例:当你的情境和他人情境发生置换时,作为一个理性的健康者,你也希望过一种安全的生活,不希望过一种病毒四伏的生活,因而不会赞同携带危险病毒的别人自由行动。在这个时候,只要你的行动和人身自由可能威胁到别人的健康,你的人身自由权就受到限制,你就应该主动居家隔离(这是作为公民的义务而积极履行),或者说国家权力对你采取强制隔离是正当的、合法的(你的人身自由权就被暂时合法终止)。所以,当你是病毒携带者时,你就不能充分地享有和行使人身自由权。而作为一个病毒携带者,是不是你的任何公民权利就都不复存在或不能行使了呢?其实不然,你依然拥有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依然可以行使某些公民权利,这些权利就是任何国家权力和集体权力都不能触碰的个体权利下限,具体言之,就是作为一个正常生理或心理状态下的理性公民,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主动放弃、在任何情况下也要拼力保护的那些最为基本的权利,比如生命权。不能因为你是一种致命病毒的携带者从而就剥夺你的生命权而把你处死。专制社会、极权社会的国家权力往往无视这种公民权利的下限,而随意加以侵犯和剥夺。因此,只要携带病毒的公民没有实际危害或威胁到其他人的安全(比如居家隔离或被迫隔离),就至少依然应该享有在这种隔离状态下还能正常行使的其他公民权利(比如选举权利就可以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来行使)。
二、公民义务的边界
从动态方面看,公民身份是一个公民化(citizenize)的过程。如果从静态方面看,它同时也是公民之间的一种共同身份,因此,公民身份还是一个获得和其他多数人一样具有的相同合法身份的过程。由于身份的相同,获得公民身份的过程也是进入一个大家庭的过程,这一“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对其他人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高尔斯顿指出:“如果说公民身份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它意味着大家分享和接受的一堆好处和负担。”[3](P250)很多社群主义的学者和共和主义的学者也强调,在这个大家庭中,每一位公民都应为了集体大家庭的利益而履行自己的义务。然而对这种义务的界限,这些学派始终都含糊其辞。我们赞同公民对社群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但认为这种责任与义务,并不是如社群主义者——如建基于社会本体论上的社群主义学者通常认为,“个人主义在对公共生活的投入中才得到了其最高的表达”[4](P224)和共和主义者——达格就认识到,共和主义者眼中的“好公民是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他将共同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5](P203)那样先入为主地强加在公民身上的、没有明确边界的义务,这两派学者所认同的公民义务是不容置疑和理所当然的,并且高于和先于个人利益。共和主义及社群主义都过分强调公民推动公共利益的主观愿望,并把这种愿望及行动视为评判公民的主要标准。
我们不应从道德的角度来强调公民对集体和社会负有的义务。从来就没有绝对的个人权利和义务,更没有必然的、绝对的集体权利。集体并非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它是由一个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组成的。那么事实上又是什么原因让个体承担着对其他个体的义务并因而对集体负责呢?是理性以及集体得以有序运行下去的必要性,在驱使每一位个体履行自己对其他人的责任及义务。如米尔恩所认识到的人们“在享有一项权利时,他人的角色至关重要”[6](P112)一样,在认识和履行义务时,他人的角色同样至关重要。对于任何义务而言,都必须有可能说出何种作为或不作为将构成对义务的违反,如果没有此种作为或不作为可以证实,那么就不存在一项义务。换句话说,如果你认为并希望,和你具有相同身份的别人也应该这么做或不应该这么做,那么这就是你应该履行的义务。这样看来,公民义务的边界就是:第一,每个人都应该承担的最低义务即义务的下限是:如果换作你,你也希望别人这么做或者不要这么做、希望别人愿意并坚决履行的那种义务。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这一特定情境中,如果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位病毒携带者,你就有自我居家隔离的义务,因为换作你是正常的健康人的话,你也会希望别的病毒携带者居家隔离,而不至于加大你受到他的传染的机会。第二,每个人最多只应该承担的义务,或义务到此为止的临界点,即义务的上限是:集体中的其他每个人也都不希望自己去行使的那种义务,或者说,如果被迫履行了这一“义务”和“责任”,就意味着会危及换成集体中的别人也不愿意失去和放弃的那些基本权利,即个人义务的履行会危及权利的底线。
这些义务是一个公民作为和他人具有相同身份的一员也希望别人履行的义务,它们与共和主义者及社群主义者所主张的那种先验认定并强加在个体身上的、认为个体就应该对集体负责的义务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共和主义者及社群主义者不是从他人的角色来考虑权利及义务的关系,他们只是先验地认为,集体高于个体,权利低于义务,更为致命的是,共和主义及社群主义都没有认识到义务是有边界的,或者即使认识到了义务是有边界的,为了实现他们的主张,也拒绝对边界进行明确的划定。
公民并不先验地对集体承担什么绝对义务。公民之所以对集体和社会负有责任及义务,只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个体在履行着对其他个体的义务时,他也就自然承担了对由诸多个体组成的集体负责的义务——相对而言的。
三、集体权利的边界
集体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组成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受着它的存在。可以这样理解集体:除了个人以外的其他所有人,都是一个集体。对于这样一个集体,它拥有权利吗?如果拥有,它的界限又在哪里?它的权利所对应的义务又应该由谁来承担?
与集体权利相对的是个人权利。既然集体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组成的,没有任何一位个体对其他个体负有某种绝对的义务,那么集体权利就必定低于个体权利。从这个角度看,行使集体权利的边界就是:第一,当集体权利的行使和维护与个体权利的下限发生冲突时,就应该牺牲集体权利,尊重个体权利的下限——这就是集体权利行使的上限。在特定的情境中,坚持集体权利止于上限,就是坚持:即使是为了个体自己的其他利益和权利而去维护集体利益和集体权利,集体中的大多数个体也都不愿意主动牺牲的、那种属于个体与生俱来的核心利益和基本权利。如果为了不使集体感染到我的病毒,为了顾全集体权利和集体中其他所有个体的身体安全,从而牺牲或剥夺我作为个体的最基本权利的生命权,这就是不合道德的,也是不合法的。所以,集体权利的上限是个体权利的下限,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只能牺牲前者而选择后者。第二,当集体权利与作为个体权利下限的最基本权利保持高度一致时,就必须优先照顾集体利益,尊重集体权利,并牺牲个体的其他非基本性的次要权利。比如在飞机上为了飞机飞行安全,就必须接受关掉手机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最基本权利和集体权利保持一致。为了保护这种集体权利,被迫关掉手机从而牺牲个体非基本的通信自由权利,并不存在问题。因此,在特定情境中,即使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当集体中的大多数人也都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某种个人权利,这就是集体权利的下限(即集体至少应当拥有的权利)。但是这种集体至少应当享有的权利必须与公民的最基本权利(比如生命权)保持一致——正常情况下人们是不会为了集体的安全而主动选择牺牲自己生命的——只要集体权利与公民最基本权利保持一致,集体就拥有这种权利。
集体权利边界的划定之所以要结合个人权利,并在维护集体权利时先检视它是否与个体权利的下限即个体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愿意放弃的权利发生冲突,目的就是要防止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出现过的那种悲剧:为了集体利益和集体权利,根本无视个体的权利和利益。这也就是为了防止以维护集体权利和集体利益的名义而行独裁与专制之实的现象重演,防止出现个人权利在集体权利面前显得无足轻重并被淹没在集体权利和集体利益的汪洋中的人类悲剧再度发生。当集体权利与个体最基本权利发生冲突时,没有人必须为了集体利益和集体权利而牺牲自己的个体最基本权利,也没有人有权利要求和强迫他人牺牲个人权利来维护笼统的集体权利。
四、国家权力的边界
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过程中,个体权利、个体义务以及集体权利的边界,往往都要靠国家权力来维持,那么国家权力能不能够、有没有可能为了更大的集体权利而肆意牺牲更小的集体的权利和个人权利?国家权力的界限在哪里?国家权力应该止于何处?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看看国家权力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过程中充当什么角色和发挥何种作用。在危机处理与应对中,国家权力至少要承担两种角色:危机组织管理者的角色和权利义务边界守卫者的角色。
当国家在危机过程中承担危机组织管理者的角色时,它的主要职能就是疫情控制、疫情通报、制定危机应对方案、对人力及物质资源进行集中调配管理、对各地政策及其危机应对进行协调统筹。在国家承担这种危机组织管理者的角色时,最容易侵犯到公民和集体的权利,尤其是在我国尚没有出台紧急状态法的情况下,国家权力的越界行为更是时有发生。
尽管我国2003年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4年出台了《传染病防治法》,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方面规定得并不全面和清楚,同时对危机应对过程中的国家权力也缺乏较为明确的规定。更为重要的是,当大规模的传染病爆发时,国家权力完全可以把普通的危机升格为实际的紧急状态。但是由于立法的缺位,在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界限、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明确界定,因此,不利于国家权力的规范化和法治建设的推行,也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比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指定的专业技术机构,有权进入突发事件现场进行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验,对地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进行技术指导,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拒绝。”这一条就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边界划定上考虑不周。为什么任何单位和任何个体都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拒绝呢?假定当这种国家权力的进入威胁到了一个生命垂危心脏病人的权利下限即作为最基本权利的生命权时,国家权力的进入还能做到如此理直气壮吗?又比如《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了当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如鼠疫和霍乱)时,对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但在对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病人方面,却含糊其辞地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在这一点上,国家权力的界限模糊不清。而恰恰是这种模棱两可,容易导致公民权利的被侵犯。比如说,如果我是丙类病人,医疗机构和公安机关要对我采取强制隔离措施,他们的强制行为是否侵犯了我的公民权利?如果是的话,我又能否获得司法救济?这些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因此,当国家权力在承担危机组织管理者的角色时,它的权力界限的上限有两条:第一,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如无明确授权,则禁止此类国家权力的行为;第二,即使法律有明确授权,国家权力也不能侵犯与触及作为公民权利下限的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哪怕是为了由更大多数人组成的集体的安全而行使这一权力。
当国家权力在履行权利义务边界守卫者的角色时,它的权力和职能就只是守护着个人权利与义务之间的边界以及集体权利的边界,而对于越界者予以制止和惩罚。如果没有人越出这一权利和义务的边界,国家权力尤其是它的强制力(比如强行隔离某人的权力)就失去了存在与发挥作用的逻辑基础和事实前提。这时,国家权力扮演的就是一种秩序维持者、权利义务争端的仲裁者和边界守卫者的三合一的角色。比如,当某一单位为了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而采取了侵犯到公民权利的措施(如对本单位职工的强制隔离)时,国家权力就应该对这一越界行为予以坚决制止。而当公民没有履行自己在特定情境中应尽的义务下限时,应对其予以教育批评,并责令其加以改正。
总之,给国家权力设立边界,目的是要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防止国家权力为了集体权利而肆意地侵犯和牺牲个人权利。
五、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根本不是如社群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们所想象出来的那种关系,也根本不是由他们根据某种道德准则想象出来的应该形成的那种关系,甚至也不是如托马斯·雅诺斯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有限交换和总体交换的关系。[7]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的认识和确立,离不开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没有抽象的权利,也没有抽象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的存在不是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的结果,而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由那一群理性人基于现实需要而相互选择的结果,是现实合力的结果,是现实政治斗争与妥协的结果,甚至是管理需要的结果。所以,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并不完全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哲学层面上去理解,而应该从现实管理与现实政治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它们并不是一种孰先孰后、孰高孰低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也是相生相克的。有些权利需要有更广泛的义务才能使之得到充分行使,我们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自然也让别人承担着对应的义务;反之,我们履行义务就是为了让别人享有他们有权享有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每一个公民都承担着不得做任何侵犯他人权利的事情的一般义务,同时又拥有享受别人在履行他们的义务时而给自己带来间接好处的一般权利。
在某一公民、某一集体的权利行不通的地方,当某一公民、某一集体的权利履行不了的时候,就是公民、集体履行义务的地方和时候;当国家权力遭到顽强抵制的地方和时候,就是国家权力应该终止执行和存在的地方和时候。我们无法设想,每个人都只讲权利,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因为,如果那样的话,这些权利将失去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并失去其得以实现的可能。当此之时,个体自己的权利必定与其他所有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我们同样无法设想,每个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如果那样,就没有谁还会去履行这些义务。权利与义务的同时存在,就是为了让二者相互补充,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从而不至于出现权利之间的冲突。从这个角度看,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这里,不从道德的角度说,因为你享受了权利,你就“应该”、“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而是说,如果你只享受权利,而不履行义务,那么你的权利必将与别人的权利形成根本冲突,那时,你的权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谐社会也就无法存在。作为一个理性人,你在行使权利的时候,还必须履行义务,你没有选择,如果你逃避这种被迫性,你将受到由其他所有人组成的集体的制裁。在一定程度上,“义务”一词的英文(obligation)就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说明,因为在英文中,“obligation”源于“oblige”,而后者正是“强迫、迫使”的意思。
六、结论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公民权利与义务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问题,它还涉及公共管理及国家权力的问题。结合政治哲学与公共管理这两种视角来看,一方面,特定情境下的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实际边界,是不同于常规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边界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确立权利和义务边界的原则与标准都是不变的;另一方面,在应对本国的流感疫情方面,有必要引入公共安全的概念,而在应对全球流感疫情方面,也有必要引入集体安全的概念。无论是国内法的立法,还是国际法的制定,为了公共安全和集体安全,有必要依据一定的原则把公民和国家的义务法制化,以明确在特定的情境下,特定的个人(比如病毒携带者)对集体、特定的国家(疫情国)对其他国家(非疫情国)负有何种义务和多大的义务。
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于国家而言,权力运行者要时刻明白并牢记,他们行使的权力是有限的;于集体而言,集体的权利也是有限的,它是建立在个体权利的基础上的;于个体而言,他们的权利与义务都是有明确边界的。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两条边界。如果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能够坚守各自的边界,那么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时,就既能防止完全不顾集体的极端个人主义,又能防止借集体权利与集体利益之名而大肆侵犯个人权利,这样,就既能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又能收到疾病防控的最佳效果。
总之,要为个人权利与义务、国家权力与集体权利划定明确的边界。
[1]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2]伊安·夏皮罗:《政治的道德基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3]Willam Galston.Liberal Purposes:Goods,Virtues and Diversity in the Liberal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4][5]恩靳·伊辛、布雷恩·特纳主编:《公民权研究手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6]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7]托马斯·雅诺斯基:《公民与文明社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State Power,Civi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during Dealing with Mass Public Health Affairs
OU YANGJing-gen
(Party College of Hebei Provincial Committee,CPC,Shijiazhuang,Hebei 050061)
During dealing with the public health affairs,the boundary between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s not so much the consequence of moral choice and judgment as that of rational realistic choice of rational man.As a result,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rights and obl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on.Both civi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have their own top and bottom limiting lines.The state power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mpowerment of law and congruent with the bottom line of the civil rights.
public health affairs;state power;civil rights;obligations
欧阳景根:法学博士,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副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61)
(责任编辑 林 间)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政治能力比较研究”(HB09BZZ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