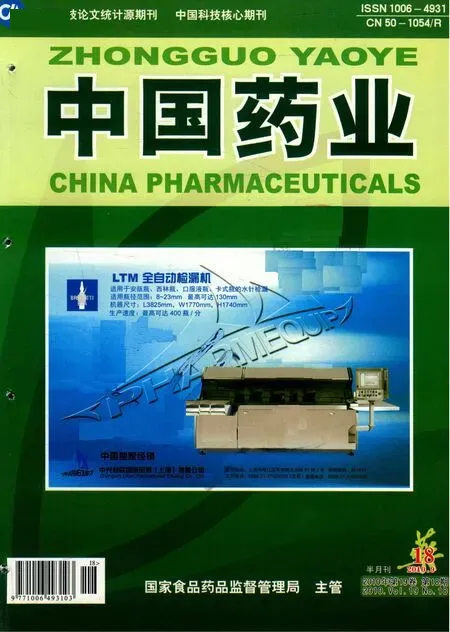植物成分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
朱 婷 ,蔡光先 ,吴 海 ,文 丹 ,谭周进
(1.湖南中医药大学湘杏学院2006级药学4班,湖南 长沙 410208; 2.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208;3.湖南中医药大学2009级研究生班,湖南 长沙 410208)
肠道微生物在机体的食物消化、吸收、免疫调节和阻止病原微生物感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宿主的健康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常肠道菌群的功能体现在防止有害菌感染、合成维生素、提高免疫力、从未消化的物质中获取能量以及抑制肠道腐败物质的产生等。不同的植物提取成分对肠道菌群的影响不同:多糖可明显促进有益菌生长、抑制有害菌,且作用随着浓度的增大而加强;黄豆苷元能促进乳酸杆菌的增殖,提高肠道菌群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伴大豆球蛋白酶水解肽可增加双歧杆菌量,并减少肠球菌量;植酸酶能降低大肠杆菌量等。在此介绍了主要的植物成分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
1 植物多糖
1.1 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正常情况下,肠道菌群对宿主的多种生理功能乃至生命活动至关重要,尤其与宿主的营养、免疫、代谢等方面紧密相关[1]。肠道菌群主要由厌氧菌构成,优势菌有双歧杆菌、乳球菌、乳杆菌等。在肠道内,这些有益菌可将碳水化合物分解成有机酸而被机体消化、吸收。研究表明,植物多糖具有促进肠道有益菌增殖、抑制有害菌群生长、降低血压、防止便秘、抑制肠内某些酶的代谢活性和致癌物质的侵害,以及提高机体免疫力等一系列作用[2]。目前研究的有以下几种植物多糖:
牛膝多糖(achyranthes bidentata polysaccharide,ABPS)是苋科植物牛膝中的水溶性多糖,具有抑制机体肿瘤生长、增加白细胞数量等提高机体免疫力功能的作用。陈清华等[3]研究发现,牛膝多糖对肠道中乳酸菌和双歧杆菌有明显的增殖作用,对大肠杆菌等有害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大豆低聚糖(soybean oligosaccharides)是大豆中低相对分子质量糖类的总称,主要成分为蔗糖、水苏糖和棉子糖等寡糖。范小兵等[4]研究发现,大豆低聚糖能有效促进双歧杆菌在体外的增殖,且几乎不能被产气荚膜梭菌分解、利用。
另外,一些中草药植物中的多糖对维持肠道菌群平衡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决明子(cassia)为豆科植物决明和叶决明的干燥成熟种子,李琨等[5]证明,决明子的活性成分为水溶性多糖,它能促进双歧杆菌的生长,并且作用随着浓度增大而增强。杜仲(eucommia)是一种雌雄异株的独特树种,自成一科一属。高致明等[6]发现,添加杜仲提取物可降低盲肠和回肠内容物的pH,增加肠道中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量,并可明显抑制条件性致病菌大肠杆菌量。刺五加(acanthopanax)为五加科植物刺五加的根及茎,主要活性成分为皂苷和多糖,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和抗应激等作用,有利于增加盲肠内容物中微生物的多样性,提高肠道乳酸菌的数量并抑制大肠杆菌繁殖,从而有利于动物的健康生长。曹华斌等[7]的研究也表明,刺五加能刺激网状内皮系统,提高淋巴细胞转化率和增强单核细胞系吞噬功能,并对双歧杆菌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
1.2 对肠道微生物作用的机制
相关研究报道比较多,现以低聚果糖为例。研究表明,低聚果糖单糖分子间以α-1,2糖苷键结合,而动物自身分泌的酶只能降解α-1,4糖苷键,因此低聚果糖以未被降解的形式直接进入后段肠道,后段肠道中的微生物就会将其作为营养物质,并产生CO2和挥发性脂肪酸等。胃肠道中不同的菌种对低聚果糖的利用情况不同,其中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等能很好地利用低聚果糖,而大肠杆菌和沙门菌等有害菌不能利用低聚果糖。双歧杆菌和乳酸菌可将肠道内的低聚果糖发酵生成有机酸,从而降低肠道pH,抑制包括很多革兰阴性菌在内的病原菌繁殖,同时还可在动物肠道中合成蛋白质、B族和K族维生素[8]。可见,低聚果糖能促进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增殖,并通过有益菌的增殖来抑制病原菌的生长,从而改善动物肠道内菌群状况、促进动物健康生长。
2 植物激素类物质
近年来,植物雌激素因有多种生理及药理学作用而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较多的是异黄酮类和木脂素类。异黄酮(isoflavones)是一种植物雌激素,能抑制癌细胞增殖。大豆异黄酮可被肠道微生物分解成作用更强的产物,如黄豆苷元和染料木素;还可被进一步降解成活性更强的代谢物,如O-脱甲基安哥拉紫檀素(O-DMA)和雌马酚等[9]。Yao等[10]发现黄豆苷元可促进仔猪肠道食糜中乳酸杆菌的增殖。Tamura等[11]报道,饲喂黄豆苷元的成年小鼠粪便中梭菌的数量显著降低,乳酸杆菌的数量显著增加。于卓腾等[12]的研究表明,仔猪肠道微生物区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增加了,尤以结肠和盲肠明显。木脂素(lignans)是一类以芳香基团为母体的化合物,植物木质素是合成动物木脂素的重要前体物质。Wang等[13]推测,植物木脂素对人体保健方面的作用并非来自植物木脂素本身,而是源于其代谢产物动物木脂素,其中又以肠二醇和肠内酯为主。因此,植物激素也可以增加肠道内有益菌的数量,降低有害菌的数量,提高肠系菌群的复杂性及多样性。
3 植物肽类物质
动物通过蛋白酶作用于蛋白质而产生肽,肽在动物的生命活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参与生命活动调节的肽被称为肠道食物源活性肽。活性肽产品已应用于医药、营养保健和畜牧兽医。左伟勇等[14]的研究表明,伴大豆球蛋白水解肽可增加双歧杆菌数量,降低大肠食糜pH,使肠球菌及肠杆菌数量下降,从而调节肠道内环境,使感染大肠杆菌后的小鼠恢复健康。尹君等[15]就棉籽粕等4种植物蛋白及其酶解产物对鱼类肠道中大肠杆菌、芽孢杆菌、乳酸杆菌的生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除菜籽粕外,其他蛋白及酶解物能促进芽孢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长,棉籽粕酶解产物能促进大肠杆菌的增加。芽孢杆菌和乳酸杆菌是有益菌,因此这两种菌群总数的增加会改变鱼类肠道微生物区系,使有益菌变成优势菌种,并通过争夺营养物质和定植位点、影响微生物代谢途径和增强免疫功能等抑制大肠杆菌等有害菌的增殖,促进鱼类健康生长。而对于乳酸杆菌,4种蛋白均可明显促进其生长。
4 植物酶类物质
酶是一种高效的生物催化剂,生命活动中的消化、吸收、呼吸、运动和生殖等都是酶促反应过程。目前关于酶类对肠道微生物影响的报道不多。植酸酶(phytase)是指能将植酸(肌醇六磷酸)及其盐类水解成肌醇和磷酸(或磷酸盐)的一类酶的总称。大量研究表明,植酸酶作为单胃动物饲料添加剂使用时,可有效地降低饲料成本,使植物性饲料中磷的利用率提高60%,并减少饲料中无机磷的添加量,还能有效降低盲肠内大肠杆菌数量[16]。甘露聚糖酶(mannanase)是一种半纤维素水解酶,能水解甘露聚糖类物质成甘露寡糖。沈庆[17]研究发现,甘露聚糖酶可显著降低肉鸡肠道内容物pH,促进盲肠内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增殖,并抑制大肠杆菌繁殖,改变肠道酸碱度,维持肠道菌群平衡,保证动物健康。这可能是因为,水解后产生的甘露寡糖与病原菌在肠壁上的受体具有相似的结构,而且它与病原体表面的类丁质也有很强的结合力,可竞争性结合病原菌,使其无法摄取所需营养而死亡。
5 其他植物成分
止痢草提取物的主要成分是香芹酚和百里香酚,属于生物类黄酮化合物。有研究表明,它们可以加速肠壁绒毛表面成熟肠上皮细胞的更新速率,促进消化道内皮层的成熟,减少病原菌在消化道内皮上的依附,提高营养成分的吸收[18]。膳食纤维广泛存在于植物细胞壁,主要为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果胶类物质。研究发现,不同的营养底物到达结肠后再被细菌利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淀粉类与非淀粉类聚多糖,说明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6 展望
动物肠道微生物分为有益菌和有害菌两大类,有益菌占总数的90%以上,主体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和肠球菌等[19]。微生物与动物之间组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生态关系就是微生态[20]。随着微生态学理论的发展,人们发现肠道微生物群落与宿主的生物拮抗、免疫、营养、肿瘤和急慢性感染等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参与了动物的生理、病理和药理(毒理)过程,形成了动物代谢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1-22]。因此,通过调节动物肠道微生物区系来改善动物机体的健康状态、增强机体潜在的疾病抵抗能力值得探讨。
植物中各种成分对肠道微生物有着重要的影响,总的来说,它们可以增加有益菌、减少有害菌,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具有可观的利用价值和经济效益。如今,在禽畜养殖业中,为加快畜禽生长速度,提高饲料报酬,常在饲料中过量添加某些负效应很高的添加剂(如抗生素),这将严重危害动物和人的健康。因此,迫切需要安全高效的饲料添加剂来代替上述物质,进而推动产业的快速、安全发展。研究表明,饲料中添加刺五加提取物可提高仔猪免疫力,改善血液组成成分,增强血清抗氧化酶活性,显著防治腹泻,促进肠道对氨基酸的吸收,提高仔猪生长性能和饲料报酬[23]。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中药治疗疾病主要是利用中药材的各种有效成分。研究证实,中草药有效成分的代谢与肠内菌群有关。目前已经发现,许多种中草药的有效成分被肠道菌群代谢后,可产生出具有较强药理活性的代谢产物。有些中药可能通过人体的消化酶或肠道菌的代谢后才起作用[24]。学者们研究了肠道菌对苦杏仁苷类、香豆素类、黄酮类、蒽醌类以及萜类化合物的代谢作用,并鉴定了其代谢产物,发现通过研究肠道菌对中草药的转化作用,可以开发出被人体直接利用的中药制剂,满足一些特殊的用药需求,从而提高中药的使用价值[25]。因此,加强药用植物中的有效成分与肠道微生物的结合研究,有利于发现有特色的、新的、高效的植物活性成分,加大药用植物活性成分的利用面,对于推动药用植物的研究开发及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1]Round JL,Mazmanian SK.The gut microbiota shapes intestinal immune responses during health and disease[J].Nat Rev Immunol,2009,9(5):313-323.
[2]张延坤.大豆低聚糖的特性及其生理功能[J].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1996,14(1):75-78.
[3]陈清华,贺建华,刘祝英,等.牛膝多糖对仔猪肠道微生物及小肠勃膜形态的影响[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33(6):723-724.
[4]范小兵,钱利生.大豆低聚糖对肠道微生物的作用效应及各组分含量检测方法[J].中成药,2000,22(8):572-575.
[5]李 琨,刘安军,王稳航,等.决明子活性成分对小鼠肠道菌相的影响[J].天津科技大学报,2005,20(2):19-20.
[6]高致明,王太霞.杜仲叶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化学成分含量和结构的变化[J].河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31(2):145-148.
[7]曹华斌,郭剑英,苏荣胜,等.中草药及提取物的免疫增强及抑制作用[J].当代畜禽养殖业,2009(1):24-25.
[8]Kuba M,Tanaka K,Tawata S,et al.Angiotensin I2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y pep tides isolated from tofuyo fermented soybean food[J].Biosci Biotechnol Biochem,2007,67:1 278-1 283.
[9]Wang XL,Shin KH,Hur HG,et al.Enhanced biosynthesis of dihydrodaidzein anddihydrogenisteinbyanewlyisolatedbovinerumenanaerobicbacterium[J].J Biotechnol,2005,115:261-269.
[10]Yao W,Zhu WY,Han ZK,et al.Daidzein increasedthe density but not composition of Lactobacilluscom-munity in piglet digesta during in vitrofermentation as revealed by DGGE and dilution PCR[J].Reprod Nutr Dev,2004,44:17-18.
[11]Tamura M,Hirayama K,Itoh K,et al.Effectsof soy protein-isoflavone diet on plasma isoflavoneand intestinal microflora in adultmice[J].Nutr Res,2002,22:705-713.
[12]于卓腾,姚 文,毛胜勇,等.黄豆苷元对仔猪肠道微生物区系的影响[J].营养学报,2007,29(1):82-86.
[13]Wang LQ.Mammalian phytoestrogens:enterodiol and enterolactone[J].J Chromatogr B,2002,777:289-309.
[14]左伟勇,陈伟华,邹思湘,等.伴大豆球蛋白胃蛋白酶水解肽对小鼠免疫功能及肠道内环境的影响[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5,28(3):71-74.
[15]尹 君,刘文斌.植物蛋白及其酶解物对鱼类肠道微生物生长的影响[J].淡水渔业,2005,35(2):25-27.
[16]杨立彬,李德发,谯仕彦,等.日粮营养水平对生长猪生产性能、胴体品质和肉品质的影响[J].饲料工业,2000,21(8):14-15.
[17]沈 庆.β-甘露聚糖酶对植物胶的酶解及其产物对双歧杆菌的促生长作用[J].天津微生物,1996(2):1-5.
[18]Namkung H,Gong MLJ,Yu H,et al.Impact of feeding blends of organic acids and herbal extracts on growth performance gut microbiota and digestive functionin newly weaned pigs[J].Canadian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2004,84(4):697-704.
[19]Vaughan EE,Heilig HG,Ben-Amor K,et al.Diversity,vitality and activities of intestinal lactic acid bacteria and bifidobacteria assessed by molecular approaches[J].FEMS Microbiol Rev,2005,29:477-490.
[20]Blaut M,Clavel T.Metabolic Diversity of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implications for health and disease[J].J Nutr,2007,137:751-755.
[21]Rakoff-Nahoum S,Paglino J,Eslami-Varzaneh F,et al.Recognition of commensal microflora by toll-like receptors is required for intestinal homeostasis[J].Cell,2004,118(2):229-241.
[22]Hattori M,Taylor DT.The Human Intestinal Microbiome:A New Frontier of Human Biology[J].DNA Reseacrch,2009,16(1):1-12.
[23]刘 勇,董宏伟,张 勇,等.低聚果糖在断奶仔猪生产中的研究与应用[J].畜禽业:南方养猪,2006(10):29-31.
[24]Li M,Wang B,Zhang M,et al.Symbiotic gut microbes modulate human metabolic phenotypes[J].PNAS,2008,105(6):2 117-2 122.
[25]Morrison M,Pope BP,Denman ES,et al.Plant biomass degradation by gut microbiomes:more of the same or something new?[J].Curr Opin Biotechnol,2009,20(3):358-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