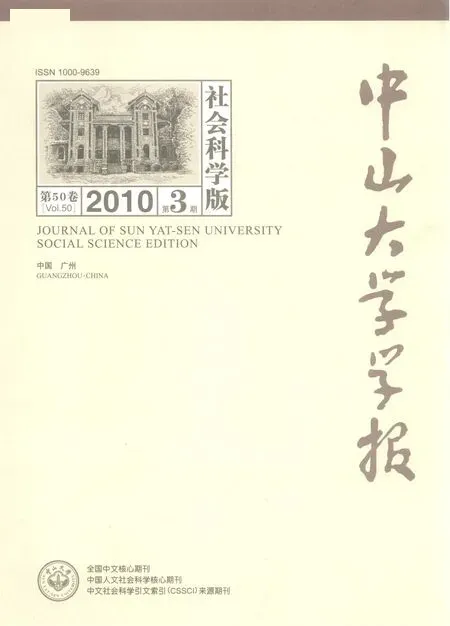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
——从《尺度的意义》看罗伯特·克里利的诗歌尺度
区 鉷,刘朝晖
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
——从《尺度的意义》看罗伯特·克里利的诗歌尺度
区 鉷,刘朝晖
罗伯特·克里利是黑山派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在论文《尺度的意义》中,他阐述了“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之诗学观。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不是约定俗成的规则,也不是学术说教规定的典章,而是一种自发的或灵感的秩序。该尺度是诗人把握日常现实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在诗歌中该尺度体现为强调时间的偶然流动及瞬间先于形式,彰显主体性的消解以及世界的破碎性、边缘性和偶然性。
罗伯特·克里利;尺度;后现代;瞬间;形式
罗伯特·克里利(Robert Creeley,1926-2005)是“投射派”(或“黑山派”)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在美国及海外出版了六十多本诗集,数十年蜚声国际,1999年当选为美国诗人学会会长。他得过多种荣誉,曾获兰南终生成就奖(the Lannan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以及耶鲁大学伯林根奖(the Yale University Bollingen Prize)。该奖项威望极高,诗人中有幸享有此项殊荣的只有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 illiam CarlosW illiams)、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以及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等其他为数不多的诗坛巨匠。在20世纪50年代,克里利和“投射派”诗人有着密切的往来。他主编了《黑山评论》(B lack Mountain Review),并和“投射派”首领,时任黑山学院院长的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奥尔森以其名篇《投射诗》(“Projective Verse”)明确了“开放诗”(open verse)的原则。他把首要原则“形式向来不过是内容的延伸”①Charles Olson, “Projective Verse, ”in Ralph Mauded. , A Charles Olson Reader. Manchester: Carcanet Press Lim ited, 2005, p. 40.,归功于克里利。可见,克氏在投射诗理论的推出中功不可没。在诗歌创作方面,克里利认同并成功实践了奥尔森的诗歌创作原则。他被公认为投射派中成就最大的诗人之一。在诗歌理论方面,除了名言“形式向来不过是内容的延伸”外,其诗学观散落在他的论文、信件以及他各种场合的言论中,也体现在他的诗歌和其他体裁的文本中。本文试图从阅读克氏的《尺度的意义》(“A Sense of Measure”)入手,分析他所提出的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的内涵以及该观点在他诗歌中的体现。
一、“尺度”的意义
尺度(measure),顾名思义,就是衡量事物的标准。在诗歌赏析中,它指的是音步的排列方式,即格律。但是克里利所说的“尺度”不是指格律,而是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在《尺度的意义》的开篇就说:
对艺术上的说教性项目,我都很谨慎。然而我不能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诗歌存在于毫不含混的秩序里。我认为,这种秩序的获得或认可,既不可以通过学术声明或意志,也不可以通过某种创作行为本身不揭示的、故意打造语言的意图。①下文中其他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Robert Creeley,“A Sense of Measure,”The Collected Essays of Robert Creeley.Berkeley,Los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486-488.
这几句话明确指出,诗歌中有秩序,但是这种秩序不由学术说教所规定,也没有目的性,而是由诗人在创作行为中“揭示”。所谓学术性的或说教性的秩序,是指当时流行的诗歌评论标准:
在(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的时代,一个人的写作是否得到承认,取决于其是否和当时的“诗歌”评论的关注相吻合。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这方面便受到了很多批评,既因为他所言说的东西,也因为他言说的方式。
20世纪40至50年代在美国文坛占据统治地位的批评流派是“新批评”。新批评坚持文本中心论,强调文学是一个自足的独立结构,是一个由语言的反讽、悖论、象征等构成的张力结构,在理论上突出了语言的重要性。新批评提供了阅读一部分现代主义文本的理想方法,即“细读法”。该方法十分强调文本中的反讽、张力和分解作用,要求读者高度自觉地注意文字或诗歌的本质而不是意义。这就要求诗人在创作时使用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即艾略特的主张:“对诗人的个性(情感)作最少的要求,对诗人的艺术(技巧)作最大的要求。”②T.S.Eliot,“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见朱通伯编:《英美现代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148-149页。而奥尔森和克里利等投射派诗人则反对新批评给文学创作所带来的束缚,追求诗歌创作的形式自由。克里利引用E.R.多兹(E.R.Dodds)的话来说明他所指的尺度:“自发的或灵感的语言在各个地方都形成韵律模式。”由是观之,克里利的尺度并非先在的规则,而是即刻的、无意识的,是灵感驱使下自然形成的韵律。他之所以偏爱这样的尺度,是因为他认为当今的世界“复杂多样”,学术说教的规则不可能表现现实。他认为诗人“对一致性有着直觉的领会”,“这使得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接近现实,接近现象世界”。
克里利进一步把艺术和宗教相比,来说明他的尺度。他所谓的宗教不是“社会秩序或义务”,“更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基本的灵异体验”(“a basicvisionaryexperience”),是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现象性的尺度,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用直接的直觉去掌握事物的结构或本质”③参见董学文编:《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7,328页。。胡塞尔认为,“现象学家和艺术家都对世界的存在进行‘悬置’,都不关心和追问对象在外部世界的存在与否,只对显现在意识中的对象感兴趣,只关注对象本身,并且,都对对象采取非设定的态度,都必须采用直观的方法来获取本质或意义”④参见董学文编:《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327, 328页。。克里利在《尺度的意义》中写道:
在这一意义(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上,目前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赋予我去写的东西。我并不清楚在写作前我要说的是什么。对我自己来说,清楚地表达就是认识词语中所给予的体验之灵性能力……
我对这样的尺度的行动深深地感兴趣,我觉得它比一个学究式的尺度含有更多的意义。这可能不再是同抑扬格和相似的词语有关的对于诗的格律的意义的讨论,……我也不认为尺度由此含有把所有现象与人类鉴赏的级别联系起来的人道主义企图……
克里利的这一席话说明,他的尺度是“当下”的,在写作之前并不存在。在这一尺度的作用下,诗人在创作时只关心瞬间、偶然,而不遵循特定的形式。在他看来,这种尺度比“抑扬格”和“格律”之类的“学究式的尺度”,即形式,更有意义。在《尺度的意义》一文的结尾,克里利对这种“尺度”之于他的意义有清楚的表述:
我不想证明我的思想——那似是而非的同一概念,而是想证明,作为单纯的中介,在这样的行动中活动的我是什么。我想像奥尔森所说的那样介入世界。那么,尺度就是我的证明。使用我的东西就是我所使用的东西,在此综合体中,尺度是关键。我不能用赤裸的手去砍倒树,这一行动是树和手的尺度。在这方面,我觉得诗歌在同意象和韵律的微妙关系上,提供了此类事实的大不相同的记录。诗歌是此类事实中的平等一员。
这就是说,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所证明的,不是具有同一性的自我,而是行动中的自我。奥尔森说过,诗人要“时时刻刻,照日常生活,去把握日常现实,……不断地向前,保持,速度,神经,它们的速度,各种感觉,它们的,各种行为,顷刻的,整体的,尽快地向前运动……”①Charles Olson,“Projective Verse,”in Ralph Maud ed.,A Charles O lson Reader.Manchester:Carcanet Press Limited,2005,p.41.这正是克里利所想要的“介入世界”的方式。诗人所把握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顷刻的现实,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顷刻的现实对诗人的反作用,即“使用我的东西就是我所使用的东西”。在克里利看来,诗歌是尺度的反映,既表明了诗人把握了哪些现实,又表明了这些现实如何进入诗人的意识。
克里利的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是瞬间的、个人的,它根据外部现实变化而变化。在这种尺度的观照下,瞬间先于形式。这和西方诗学形式先于暂存性的传统正好相反。斯潘诺斯(W.V.Spanos)在《同罗伯特·克里利的谈话》(“Talking with Robert Creeley”)中指出,在奥尔森及克里利的开放诗中,暂存性在本体论上先于形式,而在他们之前的现代主义,乃至整个西方形而上学思维中,情形正好相反,即形式先于暂存性②W.V.Spanos,“Talking with Robert Creeley,”inboundary2,Vol.6.No.3,Robert Creeley:A Gathering. (Spring/Fall,1978):pp.13-14.。回顾西方文论史,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现代主义者,文论家们都认为,形式在本体论上都先于暂存性。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原型,是正本,经验世界是摹本,是理念的范型铸造出来的,而艺术世界又是经验世界的摹本,和现实隔着三层。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理念论存在缺陷,但他说“(诗人)必须模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③亚里斯多德著,罗念生、杨周翰译:《诗学·诗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92页。。可见,不管是对于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艺术都是对某种先在形式的模仿。后来的文学理论,基本上都沿袭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辟的模仿论道路行进。现代主义将文本看作是整合了各种张力、含混和对立的“精致的瓮”,这样的文本是一个浓缩了本质瞬间的永恒统一体。但是后现代主义则对传统进行了彻底的反拨和超越。后现代主义文学“破坏了形而上学的永恒静态,强调时间的偶然流动”④Steven Connor,Postm odernist Cul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the Contem porary.Cambridge,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89,p.125.。由此可见,克里利的尺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
二、“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在克氏诗歌中的体现
克里利的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不是先在的形式或规则,具有不确定性,该尺度在诗歌中表现为:强调时间的偶然流动及瞬间先于形式,彰显主体性的消解以及世界的碎片性、边缘性和偶然性。在《年轻女人》(“YoungWoman”)一诗中,克里利写道:
年轻女人,年纪更大/的女人,话语一/开始,你/就正当地,离开。…………/我思,故/我不在,/我本要像你那样,成为/另一回事。⑤Robert Creeley,The Collected Poem s of Robert Creeley(1945-1975).Berkeley and 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238.这几行诗说明,每一瞬间都在流逝,刚刚说完“年轻女人”,“你”就成为了“年纪更大/的女人”。一开口说话,那一刻的你,就随着话语离去,不再回来。该诗的最后一节则进一步表明,伴随着时间的偶然流动,是主体的“我”的消失,笛卡尔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被克里利替换成了“我思,/故我不在”。“我思故我在”,“我”思的绝对性成就了“我”在的绝对性。故而笛卡尔认为:“我”在是不容质疑的,因为我思本身是不容质疑的,它成为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也是他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克里利却质疑并推翻了这一观点。“我”分分秒秒在思,分分秒秒都是不同的思,因而分分秒秒都是不同的“我”,作为永恒的同一性的主体的“我”不复存在,所以“我思,/故我不在”,像“你”那样,在时间的流动中,这一刻的“我”,相对于其他时刻来说总是“另一回事”。克氏的另一首诗《转》(“The turn”)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但我们想要的/不是我们得到的。/我们看见过的,我们认为/会再次看见?/我们不会。动,/我们将动,然后/停止。①Robert Creeley,The Collected Poem s of Robert Creeley(1945-197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272,290,290.
“我们想要的”和“我们得到的”不一样,“我们看见过的”,我们不会再次看见,如同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河流。”时间在流逝,事物在发展变化。发生的才是现实,没有人能控制偶然。我们只能“动”直至“停止”。在这个动的过程中,我们成为了丈量偶然的尺度:“我不能/后退/或前进/我羁绊//在时间中/作为尺度。”②Robert Creeley,The Collected Poem s of Robert Creeley(1945-197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272,290,290.“我”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尺度,既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去往将来,只能衡量瞬间,因而也是自我当下经验的现象性的尺度。如果把该诗和拉斐尔前派诗人罗塞蒂的《题乔尔乔内的威尼斯》相比,其瞬间先于形式的后现代特征就更为鲜明。罗氏所描述的画中的“她”快乐“伴随着愁苦”,“双目不知迷失何处”。该诗的最后几行是:
任她去,此刻莫说,免得她悲泣,/今后亦莫提起。任它永远如此——/生命用“永恒”触及了嘴唇。③黎华编:《外国唯美诗精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66页。
显然,罗塞蒂把乔尔乔内的绘画阐释为永恒一刻的再现。为了维护这一刻的永恒性,诗人提议“此刻莫说”,“今后也莫提起”,让艺术留住永恒。从短暂中抽取永恒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共同特征。“查尔斯·波德莱尔倡导一种能够记录短暂瞬间,而不损害其流变性的艺术,沃尔特·佩特要我们从流动之中抓取强烈的瞬间,亨利·柏格森让一代人相信需要一种不会将意识的纯粹时间之流错误地空间化的表征,弗吉尼亚·伍尔夫寻求一种能够按本来情况方式记录强烈内心经历的艺术。”④Steven Connor,Postm odernist Cul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the Contem porary(2nd edition).Cambridge, 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89,p.4.相比之下,《尺度》则放弃这种企图,因为它明示“我羁绊/在时间中”,不能动弹,只有当下,没有永恒。《尺度》的后六行进一步暗示瞬间先于形式:“我们想起的/我们想起——//毫无他因/我们想/只是想/人人自己想。”⑤Robert Creeley,The Collected Poem s of Robert Creeley(1945-197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272,290,290.我们所想的内容以及想这一动作都没有原因,只是即刻体验,具有偶然性。同时,由于没有先在的形式,个人的思维也因此而没有统一的模式,“人人自己想”,每个人所想的内容和方法都不一样。克里利在《写作》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这种尺度必然是个人的,不管它们看起来多么像一般或热门情形。也许无数的人被鲍勃·迪兰的话打动,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听到的都是一个独特的情形。⑥Robert Creeley,The Collected Essays of Robert Creeley.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523.
可见,对克里利来说,不仅写作的尺度是个人的,理解的尺度也是个人的。他的尺度是瞬间或暂存性先于形式的表现。瞬间先于形式,也意味着中心的消失,因为所有的瞬间都有着同样的意义,没有哪个瞬间能超越其他而成为中心。正因如此,斯潘诺斯认为,克里利的“作品反对意义的静态冥想,突出了阅读和创作过程”①Steven Connor,Postm odernist Cul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the Contem porary(2nd edition).Cambridge, 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89,p.125.。
既然时间是“偶然的流动”,瞬间先于形式,基于同一性和确定性的主体性也就不复存在。人的主体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指的是主体的属性,是处于主客体关系中关于人的属性,是区别于物性和神性的人的特性,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自文艺复兴以来,主体性就一直是现代哲学的基础。克里利的尺度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这在上文提到的诗歌《转》已有体现,在其他的诗歌中也有生动的表述:
我的脸属于我自己/我的手属于我自己/我的口属于我自己但我不属于②RobertCreeley,The Collected Poem s of Robert Creeley(1945-1975).Berkeley and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152,282,105,294,365.
“我”的脸、手和口等器官都属于我自己,但“我不属于”。这里的“我”是指以同一性和确定性为基础的主体的“我”。在《行走》(“Walking”)中,克里利写道:
我的脑中我在/行走,但我不/在我的脑中。/走过的地方,/没有想过,/路本身超过//所见。我想/也许这样,感觉着/脚的感觉,/前行……③RobertCreeley,The Collected Poem s of Robert Creeley(1945-1975).Berkeley and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152,282,105,294,365.
该诗的第一节暗示了“我”不属于“我”自己。“我”虽然在思考,但同一性的“我”不“在我的脑中”。从“走过的地方,/没有想过”,“感觉着/脚的感觉,/前行”这几行可以看出,“我”的行动没有预设性,是完全偶然的。克里利在其他许多场合也反复强调过这种观点。在《为了爱》(For Love)的前言中,他声明他的诗歌是“他偶然漫步闯入的地方”④RobertCreeley,The Collected Poem s of Robert Creeley(1945-1975).Berkeley and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152,282,105,294,365.;在《〈美国的新写作〉引言》(“Introduction toThe New W riting in the USA”)中,他引用威廉·巴若斯(W illiam Burroughs)的话来说明他“只是一个记录的工具”⑤Robert Creeley,The Collected Essays of Robert Creeley.Berkeley,Los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93,493.;在《关于“自由诗”的短笺》(“NotesApropos‘Free Verse’”)中,他把写作和开车类比⑥Robert Creeley,The Collected Essays of Robert Creeley.Berkeley,Los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93,493.:开车时,道路仿佛是临时创造了自己,出现在司机的视野里,在车前被看到;写作时,素材也仿佛临时成形,出现在诗人的意识中,被诗人所注意。开车时,司机要边开边注意路况;写作时,诗人也要边写边捕捉进入到他意识里的事物。“路本身超过/所见”说明了“我”的有限性,“我”不能看见路的全部。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能进入“我”的意识。这和现代主义对秉有理性的同一性自我以及“自我中心”的强调形成鲜明对比。在克里利的笔下,自我只不过是个记录瞬间的工具,暂存性是其基本特征。在另一首题为“模式”(“The Pattern”)的诗歌中,自我的同一性也被诗人分解:
我一说话,他我就说。它/想独立但/不动声色//朝着它话语/的方向。⑦RobertCreeley,The Collected Poem s of Robert Creeley(1945-1975).Berkeley and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152,282,105,294,365.
“我”开口的那一瞬间,此“我”就逝去,马上出现的是另一个“他我”。由此可见,企图靠话语来建构一个同一性的主体只是痴心妄想。而“他我”“想独立”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用动声色,只需“朝着/它话语/的方向”,让话语去塑造住另一个“他我”。“我”在时间的偶然流动中,只是一个“尺度”,由“我”所衡量的或衡量“我”的东西来决定:“我/是谁——/身份/在歌唱。//置/湖泊/于地面,水/找到了形式。”⑧RobertCreeley,The Collected Poem s of Robert Creeley(1945-1975).Berkeley and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152,282,105,294,365.这里,“我/是谁”的问题在一个比喻中得到解答。正如水总由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的特定容器决定形式,“我”的身份也总是相对的,由所在的环境决定。
由于不存在固定的尺度,只有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在这样的尺度度量之下,不仅仅主体的同一性被消解,世界也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再有本质:“发生的/一切/构成/世界。/生活/在边缘上,//打量。”⑨Robert Creeley,The Collected Poem s of Robert Creeley(1945-1975).Berkeley and 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364.克里利说过:“四十年代二战的混乱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人感到,可能存在于别的时间或地点的那种一致性不可能再存在。……似乎没有哪种逻辑能把一个人体验到的所有剧烈的零乱集结起来。”①Robert Creeley,The Collected Essays of Robert Creeley.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367.也就是说,“发生的/一切”使得世界支离破碎。破碎的世界多边缘而缺少本质,所以人们生活在边缘上,“打量”周围的一切。碎片太多太零乱,以至于打量的人感觉沉重:
……多么/沉重,这缓慢的/世界,一切都被/还原。一个/人走过,他的/身旁有一辆轿车/在下坡的/路上,一片/黄叶/将要//落下。一切/都落到/本来的位置。我的//脸因窗景/而沉重。我能/感觉到眼睛在破碎。②Robert Creeley,The Collected Poem s of Robert Creeley(1945-1975).Berkeley and 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284.
在这首题为“窗”的诗中,“沉重”一词出现了两次,首先是世界“沉重”,然后是看世界的“我”感到“沉重”。“一切都被/还原”的世界充满着碎片:人、轿车、路、树叶。一切都在该在的位置,要把所有这一切尽收眼底绝非易事,所以“我的/脸因窗景而沉重,”“我能/感觉眼睛在破碎”。这首诗对事物都进行了现象性的还原,人、轿车、路、树叶都按照本来的面目进入“我”的意识。该诗的景物描写让人想起威廉斯的“红色的手推车”(“The Red Wheelbarrow”),想起威廉斯的名言“没有意念,除非在物中”。威廉斯的诗是意象派诗歌的典范,强调寓“意”于“形”,寓“抽象”于“具体”,寓“理性”于“感性”。从本体论的层次去理解,那就是诗人不承认意念的超验存在,摆脱了现代主义遵循的柏拉图理念超验论。威廉斯对克里利有着巨大的影响。克里利在《罗伯特·克里利论文集》(The Collected Essays of Robert Creeley)的前言中就两次提到威廉斯对他的影响,在该文集的“英雄/长者”篇的20篇文章中,有5篇专门讨论威廉斯的诗歌及诗学观,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威廉斯的敬佩,对他的诗学观的推崇。但是比较威廉斯的《红色的手推车》和克里利的《窗》,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不同之处。威廉斯的诗歌把现实中的意象并置,不相关的事物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诗歌总体呈现的是一幅和谐的图画。而克里利的诗歌则不仅仅是意象的并置,它强调的是事物的“还原”,其效果是破碎性而不是整体性。这种破碎性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符。这验证上文提到过的克里利的话:“(诗人)比其他人更能接近现实,接近现象世界。”同时也说明,克里利并未简单地模仿他所推崇的前辈,而是探索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
概而言之,克里利在《尺度的意义》中所论述的诗歌尺度不是关于诗歌韵律的传统的规则,也不是任何有固定秩序的形式。这种尺度是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尺度,它灵活而无定形,衡量的是显现在诗人意识中的对象。诗歌是诗人的尺度,是诗人介入世界的证明,即诗歌体现诗人如何把握外部现实。克里利的诗歌对偶然性、瞬间性的强调,对人的主体性和世界的完整性的消解可以证明,他所介入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瞬间性的世界,是一个不存在主体性的充满碎片的世界。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克里利并非认为诗歌完全杂乱无章。正如他所言,诗歌通过其和“意象及韵律的微妙关系”,提供了有关“尺度”的记录。克氏诗歌中的音节、诗行、意象、声音等虽然没有统一的模式,但都和表现的内容有着微妙的关系,体现了诗人创作时的思维和呼吸节奏。因篇幅有限,在此不作赘述。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赵洪艳】
I106.2
A
1000-9639(2010)03-0036-06
2009-10-07
区 鉷(1946-),男,广东南海人,英语语言文学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英美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英诗研究所所长(广州510275);
刘朝晖(1970-),女,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512075),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副教授(深圳518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