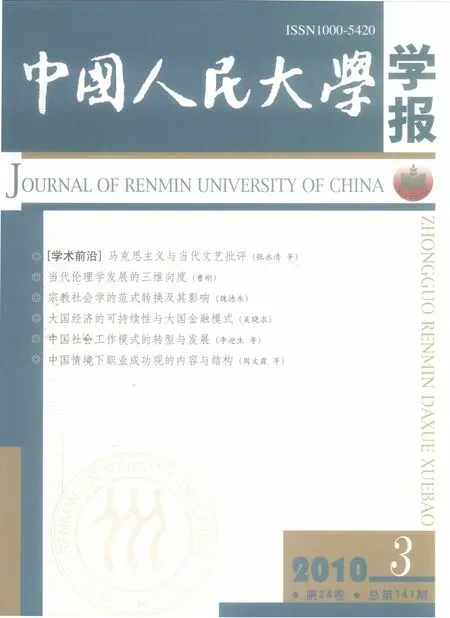凤潭对中国华严思想的批判及其理论意义
张文良
凤潭对中国华严思想的批判及其理论意义
张文良
中国的华严宗和天台宗是中国佛教诸宗派中最具哲理性的宗派,对中国佛教思想性格的形成影响至深。凤潭通过对中国华严宗思想特别是对澄观和宗密的华严思想的批判,试图会通华严思想和天台思想。虽然凤潭对澄观和宗密的批判有失偏颇,但他敏锐地指出了中国华严宗的思想基础由“法性本空”向“真心缘起”的转变,并指出了法藏的华严思想与智者大师的天台思想有相通之处。这对我们准确把握中国华严思想与天台思想的理论特质不无帮助。
凤潭;华严思想;天台思想
凤潭(1659—1738)是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的佛教思想家、文献学家。作为思想家,凤潭宗奉中国华严宗二祖智俨和三祖法藏,对华严思想多有阐扬;同时,凤潭又有很深的天台学的造诣,其弘扬天台教义的热情,甚至不亚于对华严的热情。作为兼通两宗的学者,他站在圆教的立场主张“华天合一”,试图会通华严思想与天台思想。但这种会通不是将两者牵强比附或勉强杂糅在一起,而是建立在他对前代华严学和天台学的批判性考察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对中国华严思想,凤潭虽然宗奉智俨和法藏,但对被后代尊为四祖的澄观和五祖宗密却从多方面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二人的思想背离了法藏开创的华严宗的宗旨,其学说名为“圆教”而实为“终教”,即并非终极圆满之说。在中国华严宗史中,特别是澄观和宗密的祖师地位确立之后,至少在宗派内部就难以见到对二者的批评;而天台宗人虽然对二人有所批判,但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二者在思想上与智俨、法藏的不同,更没有意识到这种不同的深刻意义。凤潭对澄观、宗密的批判,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华严思想的发展、思考中国华严与天台的性格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关于顿教与圆教
教判说是中国佛教各宗派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宗派通过对佛教大小乘经典的序列化和价值评判,树立自宗所奉经典在佛教体系中的至上地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教判说包括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和华严宗的五教十宗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天台和华严的教判体系中都有“顿教”和“圆教”之说,但其含义各有不同;而且即使在各自宗派的内部,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天台和华严诸家也有种种不同的解释。
依据法藏在《五教章》的说法,诞法师最早提出渐、顿二教判。“渐教”指《涅槃经》等经的教理,即先入小乘,再趣大乘,故名渐。“顿教”则指《华严经》的教理,即菩萨不经小乘、直入大乘,故名顿。[1](P480上)法藏在《探玄记》中云“但一念不生 ,即名为佛,不依位地渐次而说,故立为顿”[2](P115下),并举出《思益经》、《楞伽经》和《维摩经》的说法作为经证。在法藏这里,顿教主要是指佛不是遵循由小到大的次第而是直接宣说的大乘之法,同时“一念不生,即名为佛”的说法也包含了从“顿悟”的意义上理解“顿教”的意义。
对于法藏的教判说,特别是对于其“顿教”说,澄观与宗密做了重要修正,即从澄观开始,直接将“顿教”概念与当时兴盛的禅宗联系起来。按照澄观的说法,法华的化法四教中没有“顿教”是因为四教中皆有“绝言”的教义,而华严之所以要另立一“顿教”,是为了满足一类具有“离念”根机的众生,即禅宗的实践者。澄观在《演义钞》中云:“达摩以心传心,正是斯教。若不指一言以直说即心是佛,何由可传。故寄无言以言,直诠绝言之理,教亦明矣。故南北宗禅,不出顿教也。”[3](P62上)以种种方便言说来诠释超越语言名相的真理,即为“顿教”。在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相标榜的禅宗出现以后,如何理解超越语言名相的“禅”与依靠经文表达真理的“教”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佛教诸宗的重要课题。法藏所说的“顿教”虽然言及“一念不生,即名为佛”这一具有禅宗意味的命题,但基本上还是在“教”的范畴内来把握“顿”,“顿”主要是经典中的一种言说方式,即只说大乘而不说小乘。而澄观将南北禅宗纳入“顿教”的范畴之中,意味着他超出了“教”的范围,开始从“禅”和“教”两方面来理解“顿教”,而“顿教”除了是一种言说方式之外,还具有禅宗的“顿悟”法门的含义。这表明澄观试图在华严思想体系中将教与禅相会通。宗密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是佛语,禅是佛意”[4](P399上),奠定了“禅教一致说”的基础。
澄观、宗密引禅宗入华严教判的做法,招致了凤潭的批评。在凤潭看来,如果说禅宗可以归入“顿教”范围内的话,那么禅宗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又何在呢?如果禅的理念和修法也是“教”之一种,则达摩西来,创宗立派,岂不是白费工夫?①《匡真钞》卷三云:“禅宗既为滞教网,达摩西来,倘为顿教者,早被顿网罗了,活底祖意,更何在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73册,370页中。可见,凤潭强调禅宗有着独立于教门的独特价值和地位,并不认同澄观和宗密以“禅宗”解“顿教”的观点。
在禅宗的谱系方面,澄观和宗密都承袭了菏泽神会的禅思想。菏泽神会的禅思想建立在“灵知”论基础之上,所谓“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凤潭评论道:“盖夫北宗姑置,水南菏泽,虽派南宗,出于五叶之外,然清凉、圭山所尚参禅者。故知皆是党乎知解穿凿之过,非关吾宗事也。”[5](P370中)在凤潭看来,将禅宗归入“顿教”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更何况澄观和宗密所宗奉的禅宗即荷泽一系的禅法并非慧能南宗的正统。所以,这样的禅思想与华严宗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华严的“圆教”立场,法藏在谈到天台的化法四教即“藏通别圆”时,将天台的圆教比配于《华严经》等。②《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云:“四名圆教。为法界自在,具足一切无尽法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即华严等经是也。”《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5册,480页上。这对将《法华经》视为圆教的天台宗人来说自然是难以接受的。比如,湛然就认为,包括《华严经》在内的诸大乘经典虽然皆说诸法实相,但比较而言,只有《法华经》的一念三千等教理才是纯粹圆满之法,所以不是《华严经》而是《法华经》才是圆教。③《金刚钅卑》云:“虽则通依一切大部,指的妙境,出自法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785页下。凤潭则引用《探玄记》和《四教义》的说法,认为无论是法藏,还是正统的天台宗人都是将《法华经》与《华严经》一样视为圆教的。④凤潭引《探玄记》“亦华严等是也”而于《匡真钞》卷三云:“亦字等字,亦于法华,等取法华等也。故《四教义》云,诸大乘经论,说佛境界,不共三乘位次,总属此教也。”《大正新修大藏经》,第73册,370页中。应该说,无论是华严宗的法藏,还是天台宗的智者大师,都还没有后来的继承者那里所见到的《华严经》至上或《法华经》至上的意识,这样的意识是随着宗派意识的逐渐强化而出现的。⑤参见菅野博史:《智顗与吉藏的法华经观的比较——智顗真是法华经至上主义者吗?》,载《三论教学与佛教诸思想》,123~141页,东京,春秋社,2000。凤潭主张回到法藏和智者大师,强调圆教既包括《华严经》的教义也包括《法华经》的教义,反映了凤潭“华天一致”的立场。
澄观也承认《法华经》是圆教,但却认为它只是“化法”意义上的圆教,而在“化仪”意义上,它则属于渐教。故澄观称《华严经》为“顿顿”,称《法华经》为“渐顿”。①《演义钞》卷七云:“以化仪取法,华严之圆是顿中之圆,法华之圆是渐中之圆。渐顿之义,二经则异,圆教化法,二经不殊,大师本意,判教如是。又詺圆教,亦名为顿,故云圆顿止观。由此亦谓华严名为顿顿,法华名为渐顿。以是顿义中圆顿,渐义中圆顿故。”《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6册,50页中。宗密则认为《华严经》属于“化仪”顿教,《圆觉经》属于“逐机”顿教,《法华经》、《涅槃经》等则属于渐教②《圆觉经钞》卷二云:“顿者有二:一化仪顿,谓华严经。初成佛时,称性一时,顿说理事本末始终因果,穷理尽性故。二逐机顿,谓对上根具足凡夫顿指绝待中道真性,不同法华、涅槃之类有三可破,有权可会。”《卍新纂续藏经》,第9册,833页中。;又进而认为《法华经》不仅在“化仪”的意义上属于渐教,而且认为在“化法”的意义上也不属于圆教而是属于终教。③《圆觉经钞》卷四云:“终教法华涅槃之类,顿教华严胜鬘之类。”《卍新纂续藏经》,第9册,857页下。
“化仪”四教和“化法”四教本来是天台宗的判教概念,澄观和宗密作为华严宗的僧人直接借用“化仪”、“化法”来论述“顿教”和“圆教”的做法,招致了凤潭的批评:“清凉圭山,尝拟台家,动论化仪化法,迂之甚矣。若以华严属化仪顿者,不如法华独妙,显露非顿非渐超八之圆者,弥已彰矣。”[6](P348中)
虽然澄观和宗密借用了天台的“化仪”中的“顿教”概念,但实际上赋予了这一概念新的含义。在天台宗那里,“顿教”从“部”、“时”,“味”立意,指佛初成道时,未游诸会,直接宣说华严大部,所以名为顿。但因为此时权教与实教、大乘与小乘还处于分离状态,所以还不能称为“妙”。而澄观所说的“化仪”中的顿和渐则是指说法的方式,如果先说空、无常,然后说不空、常,则是渐教,而同时说空不空、常无常则是顿教。④《演义钞》卷六云:“别时说空不空,即名为渐。同时说空不空,即名为顿。故是化仪。”《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6册,44页下。而宗密则将“化仪”顿与对上根顿机所说法的“随机顿”同称为顿教,也使顿教概念的含义背离了它在天台宗中的原意。所以,凤潭认为,澄观和宗密借用天台宗的“化仪”、“化法”概念而又没有遵循其原意是非常错误的。如果严格按照天台宗的说法,华严虽为化仪顿,但因为释尊说华严时,权教与实教各不相即,所以不如法华之摄一切众机。
对华严宗的教判说特别是澄观的教判说,天台宗人进行了激烈批判。湛然在《义例》中就澄观的“顿顿”、“渐顿”说分七条进行了驳斥。⑤《止观义例》卷下云:“一者不识教名之妨,二者不识渐开之妨,三者不识教体之妨,四者抑挫法华之妨,五者不识顿名之妨,六者违拒本宗之妨,七者违文背义之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453页中。其第五条云,华严在“化仪”中属于“初味”之顿,而法华则是“独显”之圆,澄观的错误在于没有正确理解天台“顿教”的意义。其第七条云,《法华经》的圆满具足是从其教义来说的,而不是从经中出现的圣众来说的。不能因为《法华经》中出现了声闻众,而声闻从“渐”而入,就判《法华经》为渐教。
凤潭认为,湛然的批评如果是针对澄观和宗密则有几分道理,但因为二者的教判完全背离了智俨和法藏的立场,所以如果这种批评针对智俨、法藏的华严教判则没有任何道理。凤潭在引法藏的《探玄记》“海印一乘教义开为二门,一者别教,如华严说,二者同教,如法华等”之后云:“谓非遮法华开显,不能纯一无杂,开权显本,独得妙名者,则华严海印一乘,同教之功,弥以妙绝矣。立同教门,意在于此。同教一乘既妙,况复别教一乘,主伴帝网圆极自在法门。如此高判,莫不该摄,一切融通,胡为妄分渐顿之于顿顿,而论其优劣。”[7](P355中-下)在凤潭看来 ,法藏的“同教”说 ,是指《法华经》等与《华严经》一样,是“华严海印一乘”的组成部分,所以将《法华经》归于“同教”,并不是否定《法华经》的“纯一无杂”、“开权显本”,而是承认其“海印一乘”的属性。华严的圆教,从“别教”的立场看,则唯属《华严经》,而从“同教”的立场看,则融通一切教。法藏并没有将《华严经》视为唯一的最高的经典。所以,凤潭认为,澄观划分“渐顿”“顿顿”,进而判定《法华经》与《华严经》的优劣,是不符合法藏的教判思想的。
总之,凤潭在教判上的立场,是主张华严与法华在圆教的意义上的一致,他既反对澄观和宗密贬《法华经》而扬《华严经》,也反对湛然等贬《华严经》而扬《法华经》,并且认为这才是法藏的教判说的本意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澄观、宗密的教判固然背离了法藏之说,但湛然等不辨澄观、宗密之说与智俨、法藏之说的区别,将前者之说视为华严宗的正统之说加以批判,也是无的放矢。
二、关于唯心说
华严宗的唯心说源于《华严经》的唯心偈。由于各家各派对“三界虚妄,但一心作”的“一心”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了各种对于唯心的解释。澄观将这些“一心”说归为十门①《华严经疏》卷四十云:“假说一心。相见俱存,故说一心。摄相归见,故说一心。摄数归王,故说一心。以末归本,故说一心。摄相归性,故说一心。性相俱融,故说一心。理事俱融,故说一心。融事相入,故说一心。令事相即,故说一心。帝网无碍,故说一心。”《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806页中。,其中包括以识解释一心的始教、以如来藏解释唯心的终教以及以圆融无碍解释一心的圆教。在澄观的唯心说体系中,华严宗的唯心说无疑就是圆教的唯心说。
但在关于唯心的具体论述中,澄观的唯心解释受到了凤潭的严厉批评。如关于“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澄观做了如下解释:“心是总相,悟之名佛,成净缘起;迷作众生,成染缘起,缘起虽有染净,心体不殊。”[8](P655上)又云:“法界染净,万类万法,不出一心,故名总相,余染净二缘,各属二类(四圣、六道)。”[9](P322中)在澄观看来,“心”或“一心”是万类万法的“心体”,因为万类万法皆包括在“一心”之内,所以被称为“总相”。但凤潭认为这种解释不仅不符合“唯心偈”的原意,而且违背了法藏的相关解释。心、佛、众生三法无差别,是说从“心”的立场看,心摄佛与众生;而从“佛”的立场看,佛摄心与众生;从“众生”的立场看,则是众生摄心与佛。所以,“唯心偈”既可以表述为“唯心”,也可以同时表述为“唯佛”、“唯众生”。之所以表述为“唯心”,只是为了简要、出于表达上的方便而已,并不表示心法高于佛、众生,或者心法比佛、众生更根本。澄观以总相、别相对三法进行区别,并认为佛、众生分别属于净法、染法,而心则超越染净、一体不变,显然将心看成了超越佛、众生的更根本的存在。
凤潭引用四明知礼对澄观的批评云:“据他所释,心法是理,唯论能具、能造,生佛是事,唯有所具、所造,则心造之义尚缺,无差之文永失矣。”[10](P708下)在四明知礼看来,澄观实际上是把“心”视为“理”,而将佛、众生视为“事”,从而将心与佛、众生的关系视为一种能具与所具、能造与所造的关系。这不仅不符合“唯心”的原理,更违背了“三无差别”的原意。
四明知礼对澄观的批判,凤潭表示赞成。不过,他同时认为,如果这种批判仅仅限于澄观的话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针对整个华严宗则不能成立。因为法藏明确主张心、佛、众生三法缘起相互融摄,随举其中任何一法都摄其余二法无尽,并没有将“心”法视为比佛、众生更根本。澄观之所以招致天台宗的批判,亦是因为他的唯心说背离了华严宗的宗旨。
又如,关于“法相圆融”之原因之一“唯心现”,澄观以“真心”解释“唯心”之“心”,主张一切诸法唯真心所现:“如大海水举体成波者。心能变境,境须似心。心既无碍,境亦无碍。况真心所现,拣异妄心。真法具德,故能即入,重重无碍。言举体者 ,全真成妄也。”[11](P82下)
《华严经》的“唯心偈”之“心”原本是指十二缘起中的“识”,属于“妄心”的范畴,但随着中国佛教思想家对“心”的扩大解释,“心”具有“真妄和合识”、“真心”等意义。“心能变境”之“心”与“境”的关系是能变与所变的关系,此“心”原本的含义是“识”。而“真心所现”之“心”与万法的关系则是所现与能现的关系,此“心”只能是“真心”而非妄心。在澄观看来,这两种关系又是圆融一体的,即“妄心”之“能变”全体就是“真心”之“能现”。
对此,凤潭认为澄观的立场看似融合了真妄,实际上仍然将“真心”视为根本:“清凉曾执灵知真心,故只知真法具德,全真成妄,而不晓即妄而真,性恶本具。是故拣异妄心。岂非深失祖意乎?”[12](P471上)在凤潭看来,“全真成妄”仍然是视“真心”为能造、能现,视佛、众生等一切万法为所造、所现,属于真心缘起的终教范畴,没有达到“即妄而真”,即主伴圆明、相即相入、重重无尽的圆教境地。虽然澄观对圆教的许多论述看似与法藏没有差别,但由于他对灵知真心的执著,所以始终不能超越终教而达到性恶本具的圆教境地。
三、关于佛性与法性
佛性与法性的问题源于如何理解佛性的普遍性问题。受到《涅槃经》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佛教中,强调一切众生皆有成佛的素质或成佛的可能性的主张成为主流,但对于众生之外的山河大地、墙壁瓦石等无情之物是否具有佛性的问题则有很多论争。净影寺慧远将佛性分为“能知性”和“所知性”:能知性即真心觉知性,只存在于众生;而所知性即法性、实际、实相、法界等,不仅存在于众生,而且存在于非情之物。①《大乘义章》卷第一云:“二体义名性。说体有四,一佛因自体,名为佛性,谓真识心。二佛果自体,名为佛性,所谓法身。第三通就佛因佛果,同一觉性,名为佛性。……此前三义,是能知性,局就众生,不通非情。第四通说,诸法自体,故名为性。此性唯是诸佛所穷,就佛以明诸法体性,故云佛性。此后一义,是所知性,通其內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4册,472页上。通过对佛性概念的扩大解释,佛性概念不再局限于有情众生,而是扩大到了非情之物。
在净影寺慧远那里,“能知性”和“所知性”都还是佛性概念的一个侧面,作为“所知性”的“法性”还没有成为一个与佛性相对的概念。而澄观根据《大智度论》和《佛地论》的有关论述,提出“在有情数中,名为佛性,在非情数中,名为法性”[13](P569下),将“佛性”与“法性”对举 ,使法性成为与佛性并列的概念。澄观又从“性”、“相”关系的角度对两个概念做了如下说明:“第一义空,不在智慧,但名法性,由在智慧,故名佛性。若以性从相,则唯众生得有佛性,有智慧故。墙壁瓦砾,无有智慧,故无佛性。若以相从性,第一义空无所不在,则墙壁等皆是第一义空,云何非性?”[14](P280上)即“第一义空”与“智慧”相即一体称为佛性,单纯的“第一义空”则是法性。从“相”的角度看,因为只有众生才有智慧,所以有佛性,而墙壁瓦砾等因为没有智慧,所以没有佛性。但从“性”的立场看,则“法性”普遍存在于一切有情、无情。除了在“佛性”之外又提出了“法性”概念之外,澄观的以上说法与净影寺慧远的说法没有根本不同。
对法藏和澄观等对“佛性”和“法性”的区分,天台宗的湛然、知礼等进行了批判。湛然在《金刚钅卑》中认为,佛性、法性、真如等虽然名字不同而意义没有差别。[15](P783上)虽然从别教的立场看,法性是所觉而佛性是能觉,法性属本有而佛性是修生,但从圆教的立场看,能所相即,修性一如,佛性与法性不可分。知礼认为,虽然法藏在《起信论义记》中讲真如“随缘不变”,但既然真如在有情中名佛性、在非情中名法性,真如早已经“变”为两个概念,“不变”之义已经不存在。法藏的佛性、法性说只是用了圆教的名义,而实际上却是别教的说法。[16](P871中)
凤潭则认为湛然和知礼的批评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法藏本人本来就是从终教的立场而非圆教的立场出发来对“佛性”与“法性”进行区分的,所以,认为法藏之说是别教而非圆教的批评,是无的放矢。在凤潭看来,如果天台宗人的批评针对宗密的观点,还有几分合理性,因为宗密在《圆觉大疏》中直接将终教关于佛性、法性说看成圆教的说法。[17](P351中)但从华严的正统教义来说,佛性与法性的区分,只是一种鼓励众生修行成佛的方便教义而非究竟教义,宗密的错误在于将方便教义错认为了究竟教义。
但在澄观那里,他也试图从华严的圆融无碍的立场出发将两个概念融通起来。虽然从“性”、“相”对立的立场看,佛性与法性不同,佛性仅仅局限于有情众生,但从“性”、“相”不二的圆教立场来看,法性即佛性。又因为境由心变,境不异心,所以既然心有性,那么境亦有性。[18](P281下)可见,澄观认为,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佛性与法性相即不二,佛性遍于一切有情、无情。
虽然澄观也表达了圆教的立场,主张佛性遍于一切有情、无情,但凤潭认为,澄观所说的“性相相即”只是有“相即”之名而无“相即”之实,他虽然欲表达圆教的立场,但并没有理解圆教的真正含义:“问:无障碍宗,法性即佛性,真性不二,心境相即者,应是圆解,岂属终教?答:清凉释中,虽言性相相从不二,但有即名,即义不成。何以知者?彼云,知即心体,灵知真心,异乎木石者,通能所证也。了别即非真知,瞥起亦非真知,心体离念。知之一字,众妙之门。亦是水南之言。以此明知,弃妄心外,别立灵知真心为究竟谈。果是九界永缺性德,纵知正因遍,而不知缘了周遍,将以何可为圆矣。盖是学得菏泽知解来底大患也。哀哉。”[19](P506中)凤潭的批判主要有四层意义:其一,在妄心之外别立真心为万法之体,这是终教的说法,与圆教的真妄不二、即妄全真的教义不相符合;其二,因为将真心与妄心加以区别,并且认为妄心只具有烦恼性,而真心只具有佛界性德而不同时具有其他九界性德,所以澄观只知道性具善而不知性具恶;其三,从正、缘、了三因佛性来说,澄观所说的佛性的普遍性仅限于作为第一义空的正因,而不知道缘因、了因的普遍性;其四,澄观之所以没有坚持圆教的立场,是因为他受到菏泽禅的影响,坚持灵知说。
四、凤潭的中国华严批判的理论意义
从以上凤潭对澄观、宗密的批判可以看出双方基本立场的差异。
首先,在对待华严思想与天台思想的基本态度上,虽然澄观和宗密是联系天台的教义而展开其华严的论述(如澄观与宗密认为天台的“圆教”与华严的“圆教”相通),但他们的核心论述都仅仅限于华严思想,并对法华有所贬低和批判。而凤潭虽然也宗奉华严,但并没有华严至上的思想,而是大胆吸收天台的一念三千、性具善恶、十界互具等思想来论述圆教,并在圆教的基础上会通华严与天台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凤潭打破了中国华严宗与天台宗的宗派界限,试图探求超越宗派之上的佛教的真理,其遵奉的是圆教至上主义。
其次,凤潭对澄观、宗密的批判的重要内容是他们对“终教”与“圆教”关系的理解。虽然在教判中澄观和宗密也承认“终教”与“圆教”之间的差别,但在具体论述中往往将“终教”的内容与“圆教”的内容相混同。如澄观在论述“终教”时,认为此教不仅说空而且还说中道妙有,故称之为“实教”,并且认为实教通“圆教”。正因为如此,澄观认为《大乘起信论》的真如一心二门教义虽然侧重于“一心”而没有讲佛与众生的互摄互具,但还是表达了华严圆教的教义。①《演义钞》卷十三云:“起信虽明始本不二,三大攸同,而是自心各各修证,不言生佛二互全收。是则用起信之文,成华严之义,妙之至也。”《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6册,96页下。在凤潭看来,从华严的教判体系看,清凉、宗密所认为的圆教思想其实都不过是“空有无碍宗”,而非代表法藏所说的“圆明具德宗”,是终教而非圆教。②《匡真钞》卷三云:“清凉宗密,尅为圆教者,皆不出此第九空有无碍宗,此岂非失一家之纲要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73册,382页下。
凤潭对澄观、宗密的批判,无论是对他们的教判说还是对其“唯心”说和“佛性”、“法性”说 ,都涉及“灵知”说。在凤潭看来,正因为澄观、宗密以菏泽一系禅宗所主张的“灵知”来理解“顿教”和“终教”,所以才会将灵知真心与妄心加以区别,视真心为根本,而认识不到真妄合一的道理。凤潭的这一立场与他的禅宗观联系在一起。凤潭批评菏泽一派的灵知说实际上是受如来藏思想的影响,将真心、灵知、本觉视为本体,由此本体随缘而产生无始无明以及一切分别的世界。但从法界缘起的立场看,法性本空,所以它既可以说是“众生本觉圆明之性”,也可以说是“众生无始无明”,当相即是。凤潭认为,华严宗所说的法界缘起,与如来藏的缘起是有天壤之别的。本觉、不觉、始觉是就“修”而言的,即显示修行的进阶、修行的归趣。如果把一个修行论的话题视为圆教的境界,就意味着判“理”法界与“事”法界为两截,它没有契合理事不二之门,更何况事事无碍?
如上所述,在对华严教判的理解方面,澄观与法藏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对“顿教”的重新解释。他将当时势力正盛的禅宗的思想引入华严宗的教判之中,力图将“禅”与“教”加以会通,可以说开了“禅教合一”思想的先河。后经宗密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华严宗的重要思想特征之一。这一思想特征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禅宗的影响力巨大的历史现实,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佛教融合性格的反映。但由于澄观、宗密是将菏泽系的禅宗引入华严宗的思想体系之中,所以这种“灵知”真心说与智俨、法藏的法性本空说能否真正融合,在凤潭看来就成为一个问题。凤潭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排除澄观、宗密对法藏的华严思想的改造,恢复华严的正统思想。但从结果来看,他的批判招致了当时日本佛教界的反批判,其观点也并没有被人们所普遍接受。③凤潭在宝永四年(1707)出版《匡真钞》后,与真言宗宝林学派的灵云寺慧光之间展开了激烈论战。在此前后,围绕着凤潭所著《起信论幻虎录》(1701年出版),凤潭与慈空显慧等也曾展开了往复论辩。尽管如此,他的批判性考察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华严、天台乃至禅宗的发展轨迹和思想特征仍然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5册。
[2]法藏:《探玄记》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
[3]澄观:《演义钞》卷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6册。
[4]宗密:《禅源都诠集都序》卷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
[5][7]凤潭:《匡真钞》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73册。
[6]凤潭:《匡真钞》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73册。
[8]澄观:《华严经疏》卷二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
[9]澄观:《演义钞》卷四十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6册。
[10]凤潭:《指要抄》卷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
[11]澄观:《演义钞》卷十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6册。
[12]凤潭:《匡真钞》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73册。
[13]澄观:《华严经疏》卷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
[14][18]澄观:《演义钞》卷三十七,《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6册。
[15]湛然:《金刚钅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
[16]知礼:《教行录》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
[17]宗密:《圆觉大疏》卷上之四,《卍新纂续藏经》,第9册。
[19]凤潭:《匡真钞》卷七,《大正新修大藏经》,第73册。
(责任编辑 李 理)
Fengtan's Criticism of the Thought of Chinese Huayan School and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ZHANG Wen-liang
(Institute for the Studies of Buddhism and Religious The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Chinese Huayan and Tiantai Buddhist School are the most philosophical schools of Chinese Buddhist Schools,which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Buddhism.Through the criticism of Huayan Buddhist School,especially of the thought of Chengguan and Zongmi,Fengtan attempted to harmonize differences in teachings of Huayan and Tiantai Buddhist School.There are some biased comments on Chengguan and Zongmi,Fengtan observantly pointed ou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Emptiness of Dharma-nature”to“Dependent Origination of True Mind”of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Huayan Buddhist School.Fengtan also marked that there are some connections between Fazang'Huayan thought and Zhiyi's Tiantai thought.All of these will be helpful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Huayan Buddhist School and Tiantai Buddhist School.
Fengtan;Thought of Huayan Buddhist School;Thought of Tiantai Buddhist School
张文良:东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