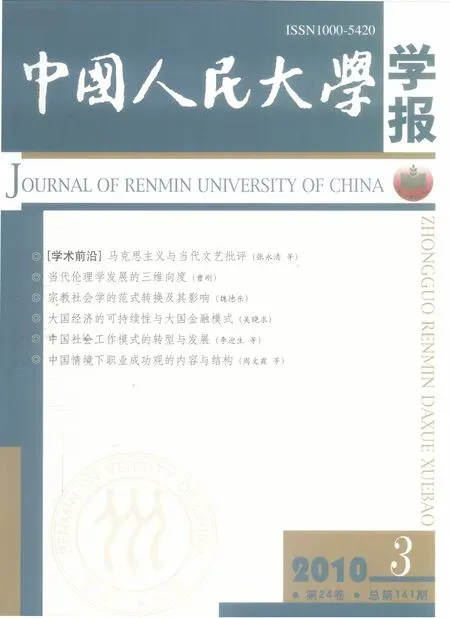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
张风雷
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
张风雷
庐山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理论论争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它反映了东晋末年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学者对当时流行的般若性空学说的深刻反思,为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从大乘般若学向大乘涅槃学的重大转向起到了思想铺垫作用,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庐山慧远;鸠摩罗什;大乘般若学;大乘涅槃学
庐山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理论论争,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研究中国佛教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学者,无不对这一事件给予极大的关注。以《大乘大义章》为中心,详尽地分析和研究这两位佛学大师之间的往返问答和思想差异,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的重心和主流。相应地,在这一研究领域,学术界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尽管在对某一问某一答等细节的具体分析上学者们间或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从总体上来说,前辈学者们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可以说是相当详尽完备了。
不过,相对于对《大乘大义章》等相关文本的详尽丰富的研究而言,学术界对慧远与鸠摩罗什之争的思想史意义的揭示则显得较为单薄。这与慧远和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卓越地位及二人之间理论论争的特殊重要性,显然是不相称的。近年来,这一问题已引起若干中国佛教学者的重视,如方立天的《中国佛教法性实在论的确立与转向》[1]、赖鹏举的《中国佛教义学的形成——东晋外国罗什“般若”与本土慧远“涅槃”之争》[2]、涂艳秋的《鸠摩罗什门下由“空”到“有”的转变——以僧叡为代表》[3]、立人(宋立道)的《般若与实在:“法性”在早期佛教义理学的疑惑》[4]与《法性与涅槃:早期中国佛教学的大小乘对接(上、下)》[5]、刘剑锋的《涅槃“有”与般若“空”义理论争的发展——从庐山慧远到竺道生》[6]及其博士学位论文《竺道生与晋宋佛学思潮转向》[7]等,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慧远与鸠摩罗什之争的思想史意义做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探索。在此,笔者愿就慧远与鸠摩罗什之争与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发展流变问题发表一点浅见,求正于方家。
一、从“般若性空”到“涅槃妙有”——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
大乘“般若性空”之学在中土的传扬,由来已久。早在东汉末年,支娄迦谶即译有《道行般若经》;其后,三国吴支谦对支谶所译的《道行般若经》加以改订,成《大明度无极经》;至西晋中叶,又先后有《光赞般若经》和《放光般若经》的译出。随着《般若》类经典的译出及魏晋玄学的兴起,与玄学关系密切的大乘般若学得到了发展。西晋末叶以后,整个社会特别是处于上层统治地位的门阀士族,忧患之感日益深重,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也更加迫切,而反观玄学自身的发展,则陷于停滞状态,缺乏新的思想创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玄学名士便逐渐把目光转向了佛学。他们发现,佛教般若学的空有之论不仅在义理方面与玄学的有无之辨颇为投机,而且还能为玄学旧义提供补充;同时,佛教的般若学还能提供一种与魏晋玄学相类似甚至是更为超越的精神境界。因此,一些清谈名士开始接受甚至服膺于佛教的般若学思想,中国的学术思潮由此为之一变。
至东晋道安(公元312年或314—385年)的时代,般若学更是声势浩大,形成了所谓的“六家七宗”,在中国佛教义学中基本上确立了主导的地位。不过,由于彼时佛教般若学经典的翻译、讲说与研习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而龙树中观学派的基本理论著作尚未系统地传译过来,因此,这些翻译、研习和解说均难以完全契合大乘“般若性空”的本义。鸠摩罗什的弟子僧叡在论及早期中土般若类经典的翻译时说:“而经来兹土,乃以秦言译之,典谟乖于殊制,名实丧于不谨,致使求之弥至,而失之弥远。”[8](P292)他又评论之前中土佛教般若学的讲说与研习,谓:“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已来,虽曰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即使以道安为代表的“性空之宗,最得其实”,然由于译典未备,“无法可寻”,验之以般若正义,仍未免“炉冶之功,微恨不尽”。[9](P311)僧叡的这种评论,可以说真实地反映了鸠摩罗什入关之前中土般若学发展的实际状况。
以后秦弘始三年(东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鸠摩罗什被姚兴迎请入关的事件为标志,中国佛教般若学的这种“偏而不即”的发展状况才得以根本改观。鸠摩罗什不但是一代译经大师,而且还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佛教思想家,他所宗承的正是以龙树、提婆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因此,他的翻译,是以大乘般若类经论为宗骨的;他的思想,也是以大乘般若学为标的的。对于鸠摩罗什的译经,吕澂先生评论说:“从翻译的质量言,不论技巧和内容的正确程度方面,都是中国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可以说开辟了中国译经史上的一个新纪元。”[10](P88)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评价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义学所作的贡献:其大乘般若学经典的翻译和传扬,对于中国佛教般若学乃至整个中国佛教义学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慧叡在《喻疑论》中曾谓:“既蒙什公入关,开讬真照,《般若》之明,复得辉光末俗,朗兹实化”[11](P235),岂虚誉哉!
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义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不仅表现在佛教经典的传译方面,而且还在于他为中国佛教培养了大批义学高僧。鸠摩罗什在译经时,对于经义常常随即敷扬,释疑解惑,由是参加译场的助手便成为听受义理的弟子。当时的义学沙门,多云集长安,慕名趋于鸠摩罗什的门下。从其受学者据说有三千之众,著名的如道生、僧肇、道融、僧叡等 ,号称“什门四圣”,此外 ,昙影、道恒(常)、慧观、慧严等人,也都是一代名僧。在鸠摩罗什的这些弟子中,助其传扬大乘般若学最有力者,当属有“秦人解空第一”之誉的僧肇。鸠摩罗什在评价僧肇所撰写的《般若无知论》时曾言:“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挹。”①《高僧传》卷六《僧肇传》载:“肇以去圣久远,文义多杂,先旧所解,时有乖谬。及见什咨禀,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后,肇便著《波若无知论》凡二千余言,竟以呈什。什读之称善,乃谓肇曰:‘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挹。’”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2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从这句评语中可以看出,鸠摩罗什对自己的般若学造诣有着充分的自信,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僧肇对般若义理的表述和阐发更胜过自己。不论鸠摩罗什如何地通晓华言,要像僧肇那样用六朝特有的文丽辞章把般若思想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使得中土人士能够充分的理解,还是难以做到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僧肇显示出了其无与伦比的语文与哲思天才的优越性。他所撰写的《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等阐扬般若思想的论文,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堪与庄子的《齐物论》、《逍遥游》相比肩的最优美的哲学文字。在深得鸠摩罗什真传的基础上,僧肇以优美的文字把般若学玄妙的哲理清晰地展示出来,厘清了数百年来中土人士对般若正理的种种滞碍和曲解,把中土的大乘般若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顶峰。
如果以僧肇的去世(公元414年)作为中土“般若性空”之学发展至顶峰的标尺的话,那么,在此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土的佛学思潮却发生了近乎戏剧性的巨大变化。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十月一日至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正月一日,由法显携归的六卷本《大般泥洹经》于晋都建康(今江苏南京)道场寺由佛驮跋陀罗禅师等译出并校定尽讫①见《出三藏记集》卷八《六卷泥洹经记》。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3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唱言“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中土佛学界特别是以“义学首府”建康为中心的南方佛学界引起了道生、慧叡、慧严、慧观等一代名僧的强烈反响,正式揭开了大乘涅槃学兴盛的帷幕。此后,更因道生不为经文所囿而“孤明先发”地主张“一阐提”亦有佛性,而在当时的佛教界引起轩然大波,道生本人也被滞文守经之徒斥之为“离经叛道”而受到“破僧”(开除教籍,摒出僧伽)的严厉处分,被逐出建康。这一轰动性的事件,对道生本人虽不公平,但从另一方面看,却也为大乘涅槃学在佛教界的兴盛和流行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
此后不久,天竺三藏昙无谶又应北凉王沮渠蒙逊之请,于北凉玄始十年(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在姑臧译出四十卷本的《大般涅槃经》。相对于法显的六卷《泥洹》而言,昙无谶所译的四十卷《大般涅槃经》被称为“大本《涅槃经》”或《大涅槃经》。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大本《涅槃经》由凉地传至宋京建康,当时的义学名僧慧严、慧观,因其文言质朴而品数疏简,遂与文学家谢灵运等,依法显的六卷《泥洹》修改文字、增加品目,把原来的四十卷十三品修订为三十六卷二十五品,世称为《南本涅槃经》。经中明确地讲到“一阐提”亦可成佛,从而印证了道生先前的观点。道生不仅恢复了僧籍,而且还被佛学界称誉为“孤明先发”的“涅槃圣”。此一事件,再一次激起了对大乘涅槃学研讨的热潮。
总之,在晋宋之际,大乘《涅槃经》及与此性质相类似的一些佛教经典,如《如来藏经》、《胜鬘经》、《楞伽经》、《央掘魔罗经》、《大法鼓经》等的陆续译出,为涅槃佛性学说的兴起提供了直接的经典依据;而道生等人的极力阐扬,也大大推动了涅槃佛性学说的兴盛和流行。在当时的佛学界,出现了一些专门讲习《涅槃经》的涅槃论师。早期的涅槃论师,在南方以道生、慧观为首,在北方则以曾亲列昙无谶译席并笔受《涅槃》的慧嵩、道朗为始。在他们的门下,造就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涅槃学者,共同构成了涅槃师的主体。在整个南北朝,除了这些专门讲习《涅槃经》的涅槃师之外,其他各家论师如成实师、三论师、地论师、摄论师等,也大多兼研《涅槃》。从南北朝时期的教判学说中可以看出,各家各派尽管对佛教经典的判释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对于《涅槃》却有着一些共同的认识,即都把《涅槃》列于很高的地位,视之为佛陀最重要的教说之一。这充分地表明,涅槃佛性学说在南北朝时期的整个中国佛学界一直居于“显学”的地位而受到佛教学者的普遍重视。直到隋代一统南北,涅槃学仍在当时的佛学“五众”②隋文帝统一南北后,把佛教义学分为涅槃、地论、大论、讲律、禅门之五众,各设众主一名,以司掌教化之职。中名冠群首。
二、慧远与鸠摩罗什之争的思想史意义
自僧肇去世(公元414年)至道生入灭(公元434年),在这短短的20年间,中国佛学思潮由“般若性空”之论向“涅槃妙有”之说的转向,何以会如此急剧迅猛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做认真的思考。
对此问题,学术界通常的解释是:大乘《涅槃经》所宣扬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所宣扬的“人皆可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学说颇有契合之处,故大乘《涅槃经》(最初即法显的六卷本《大般泥洹经》)一经译出,立刻就引起了中国佛学界的极大关注和普遍认同。
不过,事情恐怕并不是这么简单。传统的儒家,不仅主张“人皆可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而且还讲到“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按照这个逻辑,“一阐提亦有佛性,亦可成佛”固亦与儒家思想合若符契,何以竺道生竟毫不见容于当时的佛学界,而受到“破僧”的严厉处分呢?看来在当时的中国佛学界,接受或拒斥一种佛教经典或佛教思想的最主要的标尺,恐怕并不完全在于它是否与儒家等中国传统的观念相契合,而是必有其佛教自身的内在原因。
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其实质是由“般若性空”转向“涅槃妙有”,亦即是由“性空无我”转向“佛性真我”。直接推动这一转向的《大般泥洹经》,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即是以“经”的形式明确提出了“佛身是常,佛性是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当时的中土佛教学者何以会对这个问题如此敏感而普遍地予以特别的关注呢?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既不是因为它与中国固有的传统理念相契合,也不是出于中土佛教学者对新译经典一时突发的冲动和热情,而是因为在《大般泥洹经》译出之前,中土的佛教学者们早已对类似的问题做过较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究,只是苦于缺乏有力的、明确的经典依据罢了。从这个角度再来反观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关于“法身”、“法性”等问题的论争,其价值恐不再限于二者的孰是孰非,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正如学者们所普遍认同的那样,在与鸠摩罗什的书信往还中,慧远提出了许多佛学理论问题向鸠摩罗什请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涅槃相关的法身、法性问题。对慧远提出的这些问题,鸠摩罗什本着般若性空的立场,一一给予了回答,强调“法身”、“法性”并不是什么独立自在的实体,而是以般若智慧悟证诸法实相毕竟空寂,因此,不能把“法身”、“佛身”执以为实体。鸠摩罗什明确指出,所谓“法身”、“佛身”,只是为了适应对不同人的传法需要而做的方便假说,实则“皆从众缘生,无有自性 ,毕竟空寂 ,如梦如化”[12](P134下),即使“诸佛所见之佛,亦从众缘和合而生,虚妄非实,毕竟性空,同如法性”。[13](P129上)总之,“法身可以假名说,不可以取相求”。[14](P127上)对此,慧远则持有不同的意见。在慧远看来,佛经在谈到法性的时候,常说“有佛无佛,性住如故”,这就是承认有常住不变的法性,因此,慧远认为“因缘之所化,应无定相;非因缘之所化,宜有定相”[15](P136下),而“因缘之生 ,生于实法”。[16](P136中)这就是说 ,形形色色的万千事象是由因缘和合而成的,变幻不实,无有定相,但是,使万事万物得以发生的宇宙本体则是非由因缘、真实不变的。从慧远与鸠摩罗什的书信往还、辩难问答中可以看出,慧远一直在追求一个“至极无变”的、绝对的实体性的东西,并以这个实体的存在作为其整个佛学理论的基石。①《高僧传》卷六《慧远传》谓:“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说,但言寿命长远而已。远乃叹曰:‘佛是至极,至极则无变;无变之理,岂有穷耶?’因著《法性论》,曰:‘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2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即使慧远在晚年所写作的《大智论抄序》中对“法性”的论述往般若学的方向上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但从根本上来讲,他仍保留了对“法性”为一“至极不变”之性的基本规定。②参见赖鹏举:《中国佛教义学的形成——东晋外国罗什“般若”与本土慧远“涅槃”之争》,载《中华佛学学报》,2000(13);刘剑锋:《涅槃“有”与般若“空”义理论争的发展——从庐山慧远到竺道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11)。
慧远的这一“法性实在论”思想,如许多学者所共同指出的那样,明显受了说一切有部和犊子部的影响,甚或也还带有魏晋玄学本体论和道安“本无”义的思想痕迹。对此,笔者并无异议。不过,恐怕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值得考虑,即慧远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并不单纯在于纯粹的佛教理论问题,他更为关注的是如何用佛教理论来有效地回答、指导和解决普通信众在日常佛教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相对而言,鸠摩罗什则更为关注般若学理论体系自身逻辑的自洽性和完满性。般若性空的学说,虽能博得风雅文人、玄谈名士的青睐,但对于一般民众而言,这种所谓的“一切皆空”,并不能作为他们的可靠的精神支柱,不能满足他们的现实的心理需求。尽管般若学所宣扬的“空”并非绝对的虚无,但对一般民众来说,所谓的“一切皆空”,甚至于“涅槃亦空”,“诸佛所见之佛”亦“虚妄非实,毕竟性空”[17](P129上),多少会令他们感觉着有些虚无缥缈、难以捉摸。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明晰的、牢靠的、可以把捉的、可以依靠的东西,是一个竖立在他们面前的“精神支柱”,而不是一个使他们茫然无所依寄的玄虚的“空”。慧远之所以一再坚持“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18](P218),或许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吧。
总之,慧远与鸠摩罗什之争,不简单地是一个慧远懂不懂得般若学的问题,更是慧远对当时流行的般若性空学说的一种反思,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佛教思想家对佛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独立思考,而且也表明当时的中国佛教迫切地需要确立一个所谓的“实体”。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佛学界对般若性空学说的这种反思,不仅在与慧远关系密切的道生等人的身上有所体现,而且在鸠摩罗什的弟子中也有所表现。例如,与僧肇、道生、道融并称为“关中四圣”的僧叡,在协助鸠摩罗什译完《妙法莲华经》之后,见经中说实归本、云佛寿无量,便叹曰:“《法华经》者,诸佛之秘藏,众经之实体也。”他还把《般若》与《法华》做了一番比较,认为:“至如《般若》诸经,深无不极,故道者以之而归;大无不该,故乘者以之而济。然其大略,皆以适化为本,应务之门,不得不以善权为用。权之为化,悟物虽弘,于实体不足。皆属《法华》,固其宜矣。”[19](P306-307)
僧叡的这一看法可谓一针见血,因为鸠摩罗什所传译宣扬的中观般若学的确是不承认任何实体的。僧叡朦胧地意识到,似乎应该确立一个“实体”,而不能只在“空”中打转。般若不但是“破”(破除世惑),而且还应有所“立”(建立实体)。但是,这个应立的“实体”到底是什么呢?《法华》虽然讲到如来寿量长远,却并未论及佛身是常,因此,僧叡在《法华》中找不到完满的答案。直到后来大乘《大般涅槃经》译出,人们看到“佛身是常,佛性是我”的经文,问题才豁然冰释。
在大乘《涅槃经》译出之前,像僧叡这样的思想困惑在当时的般若学者中是颇具代表性的。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鸠摩罗什的门下是否曾就类似的问题展开过讨论,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大乘《大般涅槃经》(确切地说,即是法显所携归的《大般泥洹经》)译出之后,曾厕身鸠摩罗什门下的道生、慧观、慧严、慧叡等人成为最早的涅槃师,而这些人同时也是庐山慧远的弟子。这难道只是历史的偶然吗?照我们的推测,道生等人早年即受到慧远法性、法身论的影响,在鸠摩罗什门下研习般若的时候,对法性、法身问题也没有停止过思考,或许还与僧叡等人共同研讨过相关的问题,亦未可知。这虽然只是一种推测,但也并非是绝无踪迹可寻的。慧叡在《喻疑论》中曾追忆当年在鸠摩罗什门下学习、向鸠摩罗什请益的情景,谓:“每至苦问:‘佛之真主亦复虚妄,积功累德,谁为不惑之本?’或时有言:‘佛若虚妄,谁为真者?若是虚妄,积功累德,谁为其主?’如其所探,今言佛有真业,众生有真性,虽未见其经证,明评量意,便为不乖。而亦曾问:‘此土先有经言,一切众生皆当作佛,此当云何?’答言:‘《法华》开佛知见,亦可皆有为佛性。若有佛性,复何为不得皆作佛耶?但此《法华》所明,明其唯有佛乘,无二无三,不明一切众生皆当作佛。皆当作佛,我未见之 ,亦不抑言无也。’”[20](P236)
从《喻疑论》这段追记中可以看出:当时慧叡等所问的“佛若虚妄,谁为真者?若是虚妄,积功累德,谁为其主?”等问题,与庐山慧远的疑惑可谓如出一辙,此可注意者一也。其二,慧叡等问众生作佛义,鸠摩罗什以《法华》“开佛知见”义相答,再一次显示出《法华》在《般若》和《涅槃》中间重要的过渡作用。如前所述,僧叡也正是在看到《法华》开权显实、言佛寿无量之后才开始反思到《般若》“悟物虽弘,于实体不足”的。可见,《法华》“开佛知见”、“佛寿无量”等观念曾给当时的般若学者以强烈的思想刺激,促使他们反省般若学自身的问题,这为后来大乘般若学向大乘涅槃学的迅速转向起到了很好的思想铺垫作用。其三,从鸠摩罗什的回答中可以看出,鸠摩罗什因未见明确的经证,未敢断言佛性之有;然因《法华》有“令众生开佛知见”义,亦未敢遽言佛性即无。这说明鸠摩罗什本人对众生有无佛性的问题还是有过思考的,只是他囿于所传的般若性空义,未敢对佛性问题做决定说。无论如何,在鸠摩罗什的门下,甚至连鸠摩罗什本人,对般若学的未尽之义,多少还是有所反省的。
总之,正是由于慧远及深受其影响的道生等一批中土佛教学者早在《大般泥洹经》译出之前即从法身、法性实有的角度对般若性空学说做过深刻的反思,才有道生、慧叡、慧严、慧观等人在《大般泥洹经》译出之后迅即由般若学转向涅槃学,成为最早的涅槃师。如慧叡,在《喻疑论》中直指非《泥洹》者为“阐提”,极言涅槃佛性为本真。他评誉涅槃佛性义云:“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而复致疑,安于渐照;而排跋真诲,任其偏执;而自幽不救,其可如乎?”[21](P235)慧叡甚至还断定倘若鸠摩罗什在世,得闻此正言,亦必会心府,深加信受。他说:“什公时虽未有《大般泥洹经》文,已有《法身经》,明佛法身即是泥洹,与今所出,若合符契。此公若得闻此‘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便当应如白日朗其胸襟,甘露润其四体,无所疑也。”[22](P236)鸠摩罗什见此《大般泥洹经》文,是否真的会“如白日朗其胸襟,甘露润其四体”,或许难以定论;但慧远见此经文,想必一定会有豁然冰释、如沐春风之感吧。
[1]方立天:《中国佛教法性实在论的确立与转向》,载《中国文化》,2001(17,18)。
[2]赖鹏举:《中国佛教义学的形成——东晋外国罗什“般若”与本土慧远“涅槃”之争》,载《中华佛学学报》,2000(13)。
[3]涂艳秋:《鸠摩罗什门下由“空”到“有”的转变——以僧叡为代表》,载《汉学研究》,2000(2,18)。
[4]立人:《般若与实在:“法性”在早期佛教义理学的疑惑》,载《觉群》,2007(3)。
[5]立人:《法性与涅槃:早期中国佛教学的大小乘对接(上、下)》,载《觉群》,2007(4,5)。
[6]刘剑锋:《涅槃“有”与般若“空”义理论争的发展——从庐山慧远到竺道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11)。
[7]刘剑锋:《竺道生与晋宋佛学思潮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答辩稿(未刊),2006。
[8][9][19]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5。
[10]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20][21][22]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5。
[12]慧远、鸠摩罗什:《次问念佛三昧并答》,载《鸠摩罗什法师大义》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5册。
[13][14][17]慧远、鸠摩罗什:《次问修三十二相并答》,载《鸠摩罗什法师大义》卷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5册。
[15][16]慧远、鸠摩罗什:《问实法有并答》,载《鸠摩罗什法师大义》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5册。
[18]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六《慧远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
Debate between Hui Yuan and Kumārjīva and Diversion of Buddhist Thought during the Jin and Song Dynasties
ZHANG Feng-lei
(Institute for the Studies of Buddhism and Religious The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The doctrinal debate between Hui Yuan of Lu Shan and Kumārajīva w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however,its significance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reveal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This paper is of this opinion:The doctrinal debate between Hui Yuan and Kumārajīva revealed a profound refection of Chinese Buddhist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Hui Yuan on the then popular prajñā-’sūnyatāphilosophy since the end of East Jin Dynasty,which paved the way for the great diversion of Chinese Buddhist thought from the Mahāyānaprajñāpāramitāphilosophy to Mahāyāna-nirvāna philosophy,and was of milestone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thought.
Hui Yuan of Lu Shan;Kumārajīva;Mahāyāna-prajñāpāramitāphilosophy;Mahāyānanirvāna philosophy
张风雷: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 李 理)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成果
——谈谈徐兆寿长篇小说《鸠摩罗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