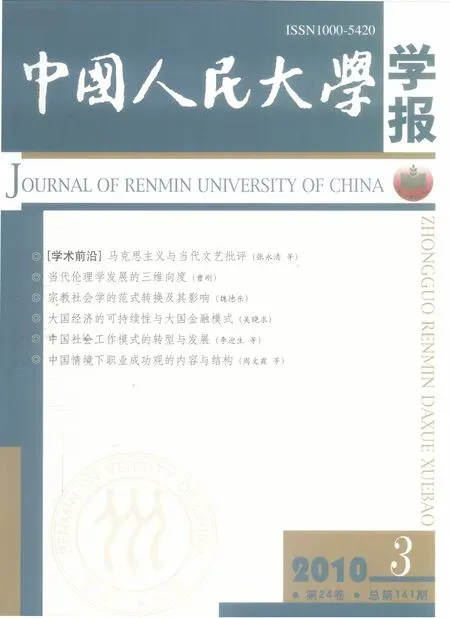论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的多维向度
季水河
论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的多维向度
季水河
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的多维向度包括:从社会生活、人与自然关系、生产论、意识形态四个方面对文学的审视角度;纵向历时比较、横向共时比较、跨越学科比较立体交叉的比较方法;美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批评标准。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审视角度;比较方法;批评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从严格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一本文学理论专著,也没有发表过一篇文学理论学术论文,他们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都是在他们的文学批评实践、在他们对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中表现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学批评论。但是,过去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学理论的这一特点认识不足,对他们的文学批评的重要地位重视不够,其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于对他们的文学批评标准——“历史标准与美学标准”的探讨,缺少对他们文学批评的多维审视与整体把握。
一、灵活多变的审视角度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不是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去研究文学,而是以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的身份进入文学领域开展文学批评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不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去思考文学问题,而是从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更灵活多变的角度去思考文学问题、评论作家作品,从而使他们的文学批评具有变化性的特征。具体言之,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以下四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角度去思考文学问题、评论作家作品的。
(一)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审视文学
从社会存在与社会实践的角度去思考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去评价作家与作品的意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的一个基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特色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一些作家与作品时,都是将其置于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中去考察、去揭示其意义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是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推崇和重点评论的作家之一。从1851年至1889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引用巴尔扎克的作品,评价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肯定巴尔扎克创作的伟大意义。在这个历史时期,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也有了重要转变,但他们对巴尔扎克评价的基点、思考的角度却保持了连续性和一致性,即都是将其置于1816年至1848年法国社会生活之中,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生活之中去思考和评价、肯定其价值、揭示其意义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有深刻理解”,评价巴尔扎克的小说《农民》“切当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的农民生活。他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巴尔扎克,在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农民》里,切当地描写了一个小农为了保持住一个高利贷者对自己的厚待,如何情愿白白地替高利贷者干各种活,并且认为,他这样做,并没有向高利贷者献出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劳动不需要花费他自己的现金。这样一来,高利贷者却可以一箭双雕。他既节省了工资的现金支出,同时又使那个由于不在自有土地上劳动而日趋没落的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高利贷的蜘蛛网中。”[1](P47-48)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也主要在于他正确地处理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杰出地描写了现实生活,“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2](P683)。马克思对英国作家笛福和狄更斯的评价也是将他们放到社会生活系统中去思考和定位的。
(二)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审视文学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关心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和美学问题。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自然既是人物质生产的对象又是人精神生产的对象,既是人的物质食粮又是人的精神食粮,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对自然依存关系的精辟概括。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审视文学,评论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评论原始社会的自然宗教和神话、传说、诗歌的产生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它们都是“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3](P63)等自然现象的反映。比如希腊神话,就是希腊初民“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4](P29)的结果。即使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虽然人类的生产力高度发达,文学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与自然的联系变得更为曲折、隐蔽,但自然与文学的关系却始终存在,而且其表现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或表现为自然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性格、心理的影响,或表现为自然对文学生产、文学风格的影响。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评论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时认为,大自然与人的天性具有天然联系,更符合人性的表现。他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资产阶级生活的锁链脱去了,玛丽花可以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的天性,因此她流露出如此蓬勃的生趣、如此丰富的感受以及对大自然美的如此合乎人性的欣喜若狂。”[5](P217)在《爱尔兰史》、《爱尔兰歌曲集代序》等著作中,恩格斯评价爱尔兰诗歌“大部分充满着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直到今天也还是民族情绪的表现”[6](P575)。而这种忧郁的民族情绪,又是爱尔兰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的产物。
(三)从生产论的角度审视文学
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联出发,将文学视为一种生产活动,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的一个独特角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从生产论的角度,考察了文学家作为精神生产者和雇佣劳动者的区别、文学创作作为非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的界限。他们一方面承认文学生产具有商业生产的共性,文学作品具有商品的属性;另一方面又批评文学的商业化,赞美作家为表现自己的天性而写作、为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个人的生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为资本家赚钱而写作的作者是生产劳动者,其作品是商品;为实现自己的天性而写作的作者是非生产劳动者,其作品是非商品。他们强调文学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更应成为一种天性的表现、自觉的目的追求。他们在评论弥尔顿时,称他为“非生产劳动者”,说他创作《失乐园》是“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7](P432)。他们在评价贝朗瑞时对其“我活着只是为了编写诗歌”的诗句表示高度认同,并强调:“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8](P87)
(四)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文学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审视文学创作,探讨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的显著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就文学本身的属性而言,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同时又是有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审美意识形态;就作家的创作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言,作家一方面受到现存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现存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他们对欧洲几次革命的诗歌的评论、对歌德作品的评论、对巴尔扎克小说的评论等都贯穿了这样的基本观念。
在评价路德《我们的主是坚固堡垒》及其在德国文学史上的作用时,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是坚固堡垒》这首歌是农民战争的《马赛曲》。虽然它的歌词和曲调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可是今天却不能也不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领会它……一般说来,过去几次革命的诗歌(《马赛曲》始终是例外),在以后就很少有革命的效果,因为这些诗歌为了影响群众,也必定反映出当时群众的偏见,所以,甚至在宪章派那里也有宗教的胡言乱语。”[9](P310-311)
在评价歌德的文学成就及其在德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受到现存意识形态的束缚,使歌德向德国现存的鄙俗气妥协;由于同现存意识形态相冲突,又使他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歌德与现存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冲突,主要表现在他“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些方面”,其认同与冲突的结果,导致“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10](P256)。
在评价巴尔扎克及其文学成就时,恩格斯认为,一方面,巴尔扎克受到现存意识形态的影响,使他认同现存意识形态,他“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其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其感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另一方面,与现存意识形态的冲突又使他否定现存意识形态。对现存社会制度“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11](P684)。
二、立体交叉的比较方法
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没有诞生比较文学学科,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世界文学”构想却蕴含着比较文学学科诞生的前提,特别是他们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所熟练掌握和运用的立体交叉的比较方法,是许多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都难以企及的。
(一)纵向历时比较
马克思、恩格斯不管是评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与流派,还是评论一个作家或作品,多是将其放到一个更长远的历史阶段,甚至是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加以考察和定位,而不是局限于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作孤立的评论。
在评论某些特定文学形式产生的原因、某些文学思潮所需的条件、某些文学流派产生的基础时,他们是以文学发展的整个历史为背景,以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体裁、思潮、流派为对象加以比较的,进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如马克思对神话、史诗和法国古典戏剧“三一律”的评论就是这样。马克思通过对希腊人、莎士比亚与现代人的比较,说明神话、史诗这种特定的文学形式只能产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都不发达的阶段。他说:“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12](P28)马克思通过法国古典戏剧与希腊戏剧的比较研究,揭示了法国古典戏剧“三一律”与希腊戏剧的历史关联性,指出法国古典戏剧“三一律”来自对希腊戏剧的曲解以及曲解的原因。他说:“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13](P608)
恩格斯对敏·考茨基《旧人与新人》的评论,也运用了纵向历时比较方法。他通过对从古希腊到18世纪著名诗人如何表现文学倾向性的比较,指出了敏·考茨基在表现文学倾向性方面的不足,揭示了文学表现倾向性的艺术方法。他说:“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14](P673)。
(二)横向共时比较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不管是评论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还是评论一个作家的创作,也多是将评论对象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地域之间或不同的作家之间进行横向共时性比较,在比较中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或突出作家的个性,发现在孤立研究中未被发现甚至无法发现的新观点、新结论。
如恩格斯在研究18世纪德国和英、法等国,19世纪俄国、挪威和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生产与物质生产、文学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时进行了横向共时比较,“通过比较,揭示了在同一历史时期,并非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艺术就越发展,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在文艺上也能够出现繁盛局面,但同时也是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变革的结果”[15](P191)。
马克思的文学批评,也十分善于运用横向共时比较方法,他经常对同一时代的不同作家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揭示不同作家的不同特点。这种横向共时比较方法,在对英国诗人雪莱、德国诗人海涅的评论中体现得最为典型。他对雪莱与拜伦、海涅与倍克等诗人进行了比较,在比较中突出了雪莱思想的革命性、海涅风格的独特性。
关于雪莱与拜伦,马克思评论道:“拜伦和雪莱的真正区别在于:凡是了解和喜欢他们的人,都认为拜伦在三十六岁逝世是一种幸福,因为拜伦要是活得再久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相反地,这些人惋惜雪莱在二十九岁就死了,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16](P136)
关于海涅与倍克,马克思评论道:“情节大致相同的同样的题材,在海涅的笔下会变成对德国人的极辛辣的讽刺;而在倍克那里仅仅成了对于把自己和无力地沉溺于幻想的青年人看做同一个人的诗人本身的讽刺。在海涅那里,市民的幻想被故意捧到高空,是为了再故意把它们抛到现实的地面。而在倍克那里,诗人自己同这种幻想一起翱翔,自然,当他跌落到现实世界上的时候,同样是要受伤的。前者以自己的大胆激起了市民的愤怒,后者则因自己和市民意气相投而使市民感到慰藉。”[17](P236)
(三)跨越学科比较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还十分注意将文学与其他学科、文学创作与其他精神活动、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等不同学科领域的活动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揭示文学的审美属性、文学创作的独特方法、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
关于文学与其他学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学与法律、政治、宗教、哲学等具有相同的一面,都是“意识形态的形式”[18](P33),但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又与法律、政治、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的形式”具有明显的区别,是一种形象化的意识形态、审美化的意识形态,即是一种通过人物的“个性描写”,通过故事“场面和情节”[19](P673)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
关于文学创作与其他精神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学与其他精神活动的相似性表现在,它们都是一种主观性、创造性很强的精神生产;但是,不同的精神生产掌握世界的方式又是有别的,文学创作是以“艺术精神的”方式掌握世界。[20](P19)
关于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学发展受到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发展速度、发展水平的影响,在长时期、广范围内,它们的发展轴线是“接近于平行”的[21](P733)。但是,文学又是一种更高的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离物质生产更远,独立性更强,因此,文学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在某些历史阶段和某些特定范围内又呈现出不平衡现象。
三、美学与历史结合的批评标准
美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批评标准,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是文学批评的“最高的标准”,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实践中始终贯彻的重要标准,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文学批评范畴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美学与历史结合的批评标准在梅林、毛泽东等理论家那里得到了坚持与发展。
美学与历史结合的批评标准,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主张和使用的,由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致斐·拉萨尔》中评论歌德和拉萨尔两位作家及其作品时明确提出。其准确和完整的表述是:“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22](P257);“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23](P561)那么,“美学和历史”批评标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的含义是什么呢?他们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又是怎样运用“美学和历史”批评标准的呢?
(一)美学标准
“美学”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具有丰富的含义:它在学科意义上指美学学科,在对现实超越上指审美理想,在情感愉悦上指审美享受,在文学活动中指艺术方法,等等。美学标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特指对作家创作和文学作品的艺术要求,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人物塑造的典型化。
在对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小说、戏剧等叙事性作品的评论中,美学标准是马克思、恩格斯衡量人物塑造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它的“最高的”要求是在保证“细节的真实”的前提下,“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4](P683)。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实主义有充分与不充分之别,典型人物有够典型与不够典型之分。够典型的典型人物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种典型人物是高度概括性、鲜明时代性和独特个性相统一的人物形象:“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25](P673)。如何塑造符合这种“最高的标准”的人物形象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家要注意两点:(1)不仅要表现作品中的人物“做什么”,而且要着重表现作品中的人物“怎样做”,通过“怎样做”来表现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情感特点和行为方式;(2)要“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26](P558),也就是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人物性格差异,刻画人物独特性格。
马克思、恩格斯用这一标准评论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拉萨尔、敏·考茨基、哈克奈斯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认为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典型化程度很高,多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拉萨尔、敏·考茨基、哈克奈斯作品中人物塑造的典型化程度不够高,还达不到“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条件。
第二,情节安排的艺术化。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中,美学标准还体现为对文学作品情节安排的要求。他们认为,文学作品情节结构的艺术表现的“最高的”美学标准是“莎士比亚化”。而“莎士比亚化”的标志主要是“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27](P558)。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的“生动性”,既表现在他的剧作通过波澜起伏的情节发展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又表现在他的剧作通过人物活动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28](P559),即“福斯泰夫式的背景”[29](P560)。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丰富性”,主要表现为他的剧作的情节一般都不是单线发展,而是双线或多线并进,从而扩大了作品的社会生活容量,给观众以丰富的审美享受。
马克思、恩格斯用这一标准分析拉萨尔的剧作《弗兰茨·冯·济金根》和敏·考茨基的小说《旧人与新人》,认为尽管拉萨尔剧本所体现出的悲剧观念不正确,但还是肯定了其情节和结构的艺术化:“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30](P553),“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31](P557)。尽管敏·考茨基在作品的倾向表现上存在问题,但恩格斯还是称赞了她“对维也纳社交界的描写大部分也是很好的”[32](P672)。
第三,倾向表达的自然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特别关注作家思想感情的表达方式,他们把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思想倾向表达的艺术化——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作者的倾向看做是美学标准的基本内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与哲学、政治等意识形态一样,必然会表现思想内容;由于作家的社会属性,他必然会持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和具有某种思想倾向。文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从古希腊的戏剧家埃斯库罗斯到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席勒,他们的作品都表现了思想倾向。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认为,由于文学的审美属性,文学作品的倾向表达也与哲学、政治等意识形态的倾向表达有所不同,它有着自身特殊的表达方式——自然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诸多作家的评论中都强调了文学倾向表达的自然化特点,视其为文学美学要求的必备条件,这在他们关于拉萨尔的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敏·考茨基的小说《旧人与新人》的评论中表达得最为集中、最为明确。针对拉萨尔在《济金根》中让剧中人物胡登宣传作者“国民的一致”的“主要思想”,“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33](P555)的缺点,马克思告诫他要“更加莎士比亚化”,“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34](P554)。针对敏·考茨基在小说中“公开表明”作者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作者的“信念”,恩格斯告诫作者务必注意倾向表达的自然化,“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35](P673)。
(二)历史标准
与“美学”一词相似,“历史”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也有多种含义:在学科意义上指历史学科,在精神指向上指历史精神,在研究方法上指历史方法,等等。历史标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领域中对历史人物和历史题材作品评论上的具体应用,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求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具有历史眼光。
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里,针对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中用抽象的人的观点去看歌德,评价歌德作品的人物,“不仅将歌德加以抽象化,而且对歌德所描写的人进行理论抽象,概括为一种生理学意义上的、只具有肉体组织的‘纯粹的人’”的非历史主义倾向[36](P140),提出了用历史标准去评价歌德。恩格斯指出:“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37](P254)歌德人格的双重性、歌德作品中人物性格的矛盾性,不是用抽象的人的观点可以解释的,也不是“纯粹的人”的结论可以说明的,而只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将歌德放到他生活的历史环境,将歌德笔下的人物放到他创作的历史背景中去研究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歌德人格的矛盾体现在“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38](P256-257),歌德笔下人物性格的矛盾性,是由当时德国社会的两重性所造就的。
二是要求作家在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中具有历史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时,对拉萨尔在剧本中所描写的以济金根和胡登为代表的骑士暴动歪曲历史事实、违背历史真实的行为提出了批评,指出拉萨尔在剧本中“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39](P555)是一种缺乏历史意识的表现,是一种违背历史真实的态度。这种历史意识的缺乏又进一步导致了拉萨尔错误的悲剧观念,将济金根的覆灭归结为他性格的“狡诈”,而没有看到他覆灭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40](P553-554),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41](P560)。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是一个被许多人谈论过的话题,过去由于惯性思维的影响,许多人都只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批评标准的论述,而遮蔽了他们文学批评实践的丰富性。本文从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灵活多变的审视角度、立体交叉的比较方法、美学历史的批评标准等维度论述了他们的文学批评,但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内容,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11][14][19][21][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9][40][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12][18][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0][17][22][37][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5]季水河:《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6]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6]陆贵山、周忠厚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Marxist and Engels'Literary Criticism
JI Shui-he
(Mao Zedong Thoughts Study Centre;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Marxist and Engels'literary criticism refer to four angles of studying literature:social life,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production theory and ideology,three intersectional and crossing comparative approaches:longitudinal and diachronic comparison,transversal and synchronic comparis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mparison,and the critical criterion of combining aesthetics and history.The above three dimensions compose the main content and basic characters of Marxist and Engels'literary criticism.
Marx;Engels;literary criticism;study angle;comparative approach;critical criterion
季水河: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湖南湘潭411105)
(责任编辑 林 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06BZW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