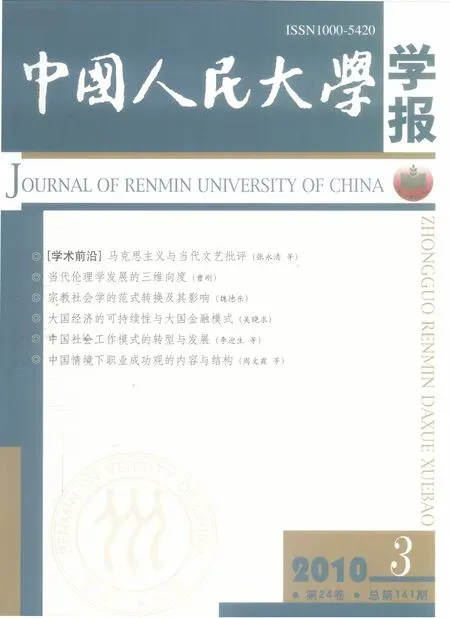古史传说与华夏共同体的文化建构
邹明华
古史传说与华夏共同体的文化建构
邹明华
在近年开展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围绕黄帝、炎帝、大禹、尧、舜等古史人物的文化活动重新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政府的承认,这启示我们重新认识并重视古史叙事的文化意义。通过梳理古史传说中用叙事所创立的部分专名,把它们看做传承群体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的标志和共同体的认同对象,以此理解华夏共同体在起始时期的文化建构。共同体是一个空间概念,但是它必须有自己的时间内涵和时间纵深。共同体的时间深度造就民众的历史感,这同样是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传说时代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文化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古史传说;共同体;专名;时空意识;文化建构
自2000年以来,中国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一方面积极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另一方面在国内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动员各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和公众都注意到一个突出的现象,这就是围绕古史传说人物的民俗活动至今仍然广泛地留存在全国的众多地方,各地群众和地方政府把它们视为自己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并积极申报其为县、市、省、自治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文化部也选择其中一部分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这些近代以来引起真实性非议的人物和叙事,现在同时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政府的承认,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启示我们重新认识并重视古史叙事的文化意义。
一、古史传说:重新发现对于共同体的认同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项关键的制度设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①各个社区、社群或个人所擅长的文化,通过地方政府向文化部提出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申请。文化部组织专家评选并在多个部级机构讨论之后公示,最后由国务院批准并公布。国务院在2006年和2008年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共确认了1 028个项目。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批涉及古史传说的项目,如黄帝陵祭典(陕西省黄陵县)、炎帝陵祭典(河南省炎陵县)、太昊伏羲祭典(甘肃省天水市、河南省淮阳县)、女娲祭典(河北省涉县)、大禹祭典(浙江省绍兴市)、尧的传说(山西省绛县)、炎帝神农传说(湖北省随州市、神农架林区)、洪洞走亲习俗(纪念尧及其女儿与舜的传说、信仰、结社,山西省洪洞县)。
古史传说所关联的文化活动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说明:一方面,古史人物仍然被当今的民众所崇信,古史叙事仍然在民间传承;另一方面,曾经否定这类叙事的真实价值的知识分子现在找到了肯定它们的价值的视角,曾经试图用政治运动清除这些文化活动的政府部门现在转而保护它们的积极作用。在先秦以来的传统社会,古史叙事一直是全民族的共同知识。历经近代以来近百年的分歧,中国的官方与民间、学者与普通民众重新达到了对于这些叙事的文化价值及其活动的认同。这种历史的回归,表明古史传说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重新得到彰显,现在它们成为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华文化自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古史传说出现并初始记录在先秦时期(从上古时代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基本事实。但是实际上它们在后世仍在社会中口耳相传,秦汉以后的文献有的引用先秦相关文字,有的记录社会中的相关传说。先秦时期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奠基期,又是华夏共同体的形成期,也是传说这种叙事体裁的发端、成长期。传说的发生与传说的记录并不是同时进行的,中华文明早期的传说是在华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之中以及稍后时期由继承华夏文明的王朝所记录的。在记录这些传说的时候,古人对于他们的叙述对象并无神话、传说、历史的区分。或许在他们看来,他们讲述的只是代代相传的远古的生活和记忆,是各种可传之事。早期的传说应该是非常丰富的,但是记录传说的时候是依据记录时代的特殊偏好而有所选择的。这种选择集中体现着一个价值,这就是直接或间接地表述正在形成之中的或者已经形成的华夏共同体存在的依据。由大一统的社会性质所决定,那些与华夏共同体形成的历程相呼应的传说更容易传承,更容易被后世重视并记录下来。
文化重构是中国近代以来不断反复的社会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所谓“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从“四个现代化”对汉族生活方式的影响到少数民族通过汉族的传递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都是学术界多学科研究中国文化的重构或再重构的关注点。这些研究主要是关注新的、外来的、西方的、现代的文化如何改变、冲淡、打击、取代传统文化或其要素。最近十多年,民俗学界注意到全国各地民俗复兴的现象,发现各种传统文化重新活跃在各种人群的现实生活之中,这应该被看做新一轮的文化重构,古史传说在一轮一轮的文化重构中都是首当其冲的。反思这一有趣的历史现象,我们不难看到,古史传说之所以在不断的文化重构中不可缺席,恰恰是因为它们在初始的文化建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带给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即共同体的形成与认同机制的问题。一方面,因为发达的交通与通信形成联系紧密的“地球村”,人们关心世界共同体和世界公民的形成;另一方面,人们因为担忧自己所处社会的共同体属性的弱化而希望寻找保持共同体认同的理念与方法。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成员共同体,认识这个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维持的历史与机制都是具有学术与现实意义的。
二、共同体认同:关键在于时空意识的文化建构
中国这个人类最大的共同体,不是一次革命而造就的,而是长期的历史过程的产物。从“夏”、“诸夏”、“华夏”到近代的“中华民族”[1],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压力和文治武功的作用下保持着自己的共同体认同。这个共同体在今天可以用中国的人口和国界来确认,而要追溯它的起始,我们需要回到夏商周的时代。在那个时期,“中国”作为共同体的原型逐渐形成,它有三个核心认同,即作为共居地(领土)的“禹绩”、作为人口同质性的黄帝子孙和作为族称的“华夏”①夏、商、周三族到西周已经融合,主要表现在地域(禹绩——大禹开拓、治理的地方)、祖神(黄帝)、民族名称(夏)的认同。夏朝称“夏”,商周在人和文化上也称“夏”,又称诸夏、华夏。参见陈连开:《论华夏民族雏形的形成》,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3)。。
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视角来研究华夏或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之初就备受关注的课题。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推翻了夏商周之前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从《史记·五帝本纪》以来作为信史的地位,从而使中国文明的起源真正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2]这就是通过考古学之路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努力。这种努力很快就由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济在1926年对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和1928年对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等一系列考古活动所展开。考古学的发掘为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物证,证明在与传说中黄帝时期相对应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黄河流域广大地域分布的不是一种单纯性质的文化,即使仅就中原地区而言,也绝非是一个氏族部落的文化所能包容的,而表现为文化的多元性。用这一事实来观照当时的共同体,可信的结论是当时处于多个族群共同体并存的状态。以此来看古史传说,黄帝只是众多部族之一支的首领,而非所有氏族部落的祖先。[3]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说:“自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疆界日益扩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4]
无论国民的共同体意识可能包含多么繁复的内容,时空意识肯定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框架。像王朝、国家这样的共同体,通常都是远远大于任何个人的活动范围,通常也远远超过个人人生的时间表,于是人们不得不借助想象才能够意识到它的整体;即使它们是一个新生的共同体,也会把它们的来源追溯到一个过去的时期,或者把它们的使命定位于某个将来,总之是保证共同体的时间超过任何个人的时间。王朝、国家是可以靠武力征战建立的,但是要作为共同体被民众所认知、认同,那一定需要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其中,自然形成或者主动铸造便于民众认知共同体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是最基本的内容。
从时空意识来说,共同体是一种有时间深度的空间。对时间的辨识需要刻度,而对空间的想象需要参照物,这就形成了对于符号和标志的公共需要。所以说,对共同体的文化建构的基本使命就是为成员提供公共的符号、象征,以便他们形成相同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古史传说以独特的叙事形成了中华文明传之后世的一批专名,它们就发挥着共同体时空想象的符号和参照物的作用。
传说作为一种对于专名的叙事,是一种落实于具体时空但又可以超越具体时空的叙事,对于想象表述大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传说同时又是一种集体性的叙事行为,单个的传说叙述者和聆听者原本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正是由于大家都参与到说与听这个“传”的过程中来,所“说”之事不再是私人性的,而变为公共性的,个体也就通过这样的集体叙事被纳入一地的集体意识之中;如果叙事所传的专名在意义和抽象程度上是超越一地的,个体就自然被纳入整个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意识之中。当古史传说之叙事从一个族群传递到另一个族群或代代相传时,一方面,它既把人所经历的直观世界传递下来;另一方面,它又以一系列的专名来构筑一个超越直观经验世界的想象的共同体。考古学研究已经证明,周代之前的漫长历史都是众多较小共同体此起彼伏、竞争与融合并存的过程,而在周代才形成一个以分封制来统领广大地域的超级共同体,并逐渐大浪淘沙,把文明发生的叙事集中在较少的一些专名身上,后世之人对这个结果进行整理,才形成五帝及其世系的叙事体系,也为我们今天整理中华文明早期的共同体意识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三、传说专名:想象共同时空的文化参照系
共同体是一个人居的空间,这个空间在物理上寄居于自然空间,但是又需要与自然状态相区隔,因此,它要把自然世界转化为人文世界。即使是当古史传说讲述前人文状态的时候,讲述的意义也在于凸显讲述者在当下已经处于一个怎样的人文状态。综观整个先秦时期的传说,不难发现,其中体现出来的是一个由自然向人文转变的世界。
传说是以专名为核心的叙事体裁,同时又以记忆为中介,口耳相传为手段。当然,这里的记忆往往是一种意象的重建和构联,从而也赋予传说一种重构意象的功能。于是,在早期的传说中,出现了怀想远古生活、追述远古历史的内容,出现了炎黄、尧舜、鲧禹等专名。这些专名不一定代表真实,也不一定代表历史,但是它们能够自然地产生真实性、历史感,能够让传说的叙述者和倾听者相信这些人物开创了(最起码见证了)华夏文明的开端。在这里,传说强调的是意义与秩序,是赋予经验生活以历史维度与人文内涵,至于传说所叙之事是否“信史”,相对来说并不是一个需要考究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有关的传说联系起来解读,可以发现,最初人们生存于一个自然状态下的环境之中,茹毛饮血、穴居野处、不媒不聘,都是对当时人类生活状况的概括表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与其说是适应不如说是依赖。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文化的发明创造逐渐出现,人类生活的环境才渐渐有了人文的因素,人类也才逐步获得越来越多的安全、道德、尊严、舒适。这一人类生活逐步由自然状态向人文状态过渡的经历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留下印象,继而又在民间言传中有所反映。传说以其对远古生活的怀想,阐明、澄清、照亮了人所经验的直观世界。它既深深地渗透着传说发生时人们的经验与感受,又附着了传说记录时人们的思维与情感,人们在口耳相传中生动地感觉和猜测到遥远的过去与现在的维系、区别。人们讲述、追忆一个久远的自然时期,是要彰显当下世界的人文性和道德价值,并传达对于这个人文世界的珍视。
人类早期的衣饰当然是取自大自然,以兽皮、鸟羽、树叶为衣的习俗有相当长久的历史。《礼记·礼运》记载:“未有丝麻,衣其羽皮。”《韩非子·五蠹篇》记载:“古者……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所以在反映人类远古生活的传说中,最早的神和人常常是人面兽身的,或许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人与自然、人与其他动物在外观上并不能完全区分。传说中的上古圣贤就多有非人的异象。如《山海经》中记载的上古之神常有人面鸟身、人面龙身、人面豚身等说法。“人面兽身”之说影响也颇为深远,直到《列子·黄帝篇》中仍然有“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的记载。
人类最古老的饮食习俗是生食,然后逐渐过渡到熟食。与此相关的茹毛饮血的传说和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就叙述了人类饮食由自然向人文转变的过程。《礼记·礼运》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韩非子·五蠹篇》记载:“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随后,人类发明了人工取火,熟食才成为人类的饮食选择,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也因而流传下来,“燧人氏”这个专名的成立,也让这段历史成为可以传讲的“真人真事”。《韩非子·五蠹篇》记载的燧人传说最为经典:“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蛤蜊,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通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班固在《白虎通义·号》中说:“谓之燧人何?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可见这一传说流传的广泛和久远,也可知“燧人氏”已作为一个专名流传下来。
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对上古时代人们的居住状况作了描述,上古之人居住于洞穴之中的传说也进入了文字。《易·系辞》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当尧之时……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礼记·礼运》也说:“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在《庄子·盗跖篇》及《韩非子·五蠧篇》中都出现了“有巢氏”的专名。《庄子·盗跖篇》记载:“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韩非子·五蠧篇》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有巢氏”与初民的生活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生死是自然现象,对待死亡的方式往往是一个群体的文明发展程度的指标。中国在自己的文明兴起之后建立的是“慎终追远”的传统,相比之下,远古的记忆却是相反的。《易·系辞》提到上古之人用树枝包裹尸体的做法,文中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这种记忆凸显的是后世的文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丧葬习俗也有了变化,这样的变化在后人眼中多被视为是进步的,因而,也会将此变化归功于某一文化英雄或者圣明君主。例如《韩非子·难一》载:“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寙,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史记·五帝本纪》也有类似记载。直至晋·谯周《古史考》仍然说:“舜作瓦棺,禹作土堲”①宋髙承:《事物纪原》卷九引。《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一引《古史考》则曰:“尧作瓦棺,汤作木棺。”。可见后世也将发明“瓦棺”——瓮棺一事归于帝舜。
往昔已然逝去,重返不再可能。然而,往事并不如烟,不会随风飘散无迹可寻。人文的世界不会将往昔全然遗忘,往昔可以记忆,可以变化,却不能消失,于是,传说出现了。上述文献在行文中多用“昔者 ……”、“古者 ……”、“上古 ……”、“当 ……之时”、“……之世”等语句来叙述,表明这些关于人类远古时期日常生活各方面的怀想多为对当时传闻的文字记载。这些叙事内容既是历代传承下来的一种集体记忆,也是怀有历史进步观的后人对先人生活的述说,就是这种记忆与述说连接着遥远的过去与可感的现在,叙说与倾听传说的人们以其叙事行为给当时的生活环境注入了历史与人文的因素,人文的世界也以传说为介质在一步一步地被构造着。
发明创造在人类社会由自然状态向人文状态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与发明创造相关的文化英雄传说又是表述这一过程的重要叙事形态之一。文化英雄往往是传说中具有神性的人物,他们创制或是为人类获取了某种作为文明标志的器物,消灭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妖魔鬼怪,教会民众各种生活技艺等。当然,这些文化行为也许并非其所为,而有可能是后人加诸他们身上的。特别是在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进程中,不少民族祖先往往会成为“箭垛”式的人物,他们不仅是本民族的伟大祖先,而且是声名显赫的文化英雄。关于文化英雄发明创造的传说在许多古代文献中都有零星的记载。定稿于秦末汉初的《世本·作篇》较为集中地做了记叙,可能是作者将当时所见的记载和所听到的传闻集中到了一起。其文云:“伏羲作琴,神农作瑟。女娲作笙簧。颛顼命飞龙氏铸洪钟,声振而远。祝融作市。句芒作罗。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伶伦造律吕。诅诵仓颉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尹寿作镜。蚩尤以金作兵器。巫咸作筮。巫彭作衣。巫咸作铜鼓。逢蒙作射。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奚仲始作车。宿沙作煮盐。化益作井。尧造围棋,丹朱善之。鲸作城廓。皋陶作五刑。舜作箫,夔作乐”[5]。
以东南西北为参照感知“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东南西北的方位被用于对“我族”共同体的想象,并与传说中的外族的世界相区分,也是共同体空间建构的一项基本内容和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文明的成就在《楚辞·招魂》中有十分完整的表述。《楚辞·招魂》是这样给人们展现四方地理和风俗的:“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归来归来!不可以托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鯈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归来归来!不可以久淫些。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麋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蚁若象,玄蜂若壸些。五榖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归来归来!恐自遗贼些。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楚辞·招魂》)这里对四方的主要特征的描述都是要衬托“我们”处于世界的中央,只有我们才是一个文明世界。
人们对于共同体的空间意识,一方面包括自然的人文化所构成的人居环境,另一方面包括对于这个已然人文化的空间范围的想象。前者涉及的是这种空间的质的内容,后者侧重的是这种空间的量的内容。大禹治水的叙事及其涉及的山川、地方在空间意识上是最好的想象大共同体的地标。传说大禹有奇才异能。《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鲧死三岁不腐”,“鲧腹生禹”。《归藏·启筮》记载:“鲧死三岁不腐”,“化为黄龙”,“是用出禹”。他的身体也不同于常人。《尚书·帝命验》记载:“禹身长九尺有余,虎鼻、河目、骈齿、鸟喙、耳三漏。”他的丰功伟绩是治水,通过驯化自然的野性,为以水土为生的百姓创造宜居的条件。相传大禹之时洪水猖獗。《庄子·天下》记载:“昔者禹之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记载:“禹通三江五湖。”《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禹“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至名山大川,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史记·河渠书》记载:“然河灾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以入渤海。”无论是“三江五湖”、“四夷九州”的散点连缀,还是从积石、龙门直到渤海的一线贯通,都是百姓想象“禹绩”[6]这个已经非常辽阔的共同体整体的空间构成要素。
人们感知共同体,既要对脚下的土地、山川有体认,还需要对世界在宇宙中的位置有共同的界定。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注意积累宇宙空间的知识和表达方式,往往用人性化的思维来讲述日月星辰,以日月星辰为参照感知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随着传说这一叙事形态的出现,人们开始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述说周围的自然环境,以彼时的思维与情感解释周围的自然环境。一系列的专名——诸如牛郎织女以及更多的地方山川之名——使得人们对天上地下以及遥远不可捉摸的星际有了一个认识的框架,天空渐渐有了人文化的色彩。《左传·昭公七年》说“天有十日”,那么这十个太阳是从哪里来的呢?《山海经·大荒西经》解释说:“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同太阳差不多,月亮为常羲所生,也同人一样要洗澡。《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此始浴之。”《山海经》中还记载了“日出”和“日入”的地方。《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关于星辰的专名如有关牛郎织女的文字可以追溯到《诗经·小雅·大东》中:“维天有汉,监尔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在此后的流传过程中,被逐步赋予传奇色彩,最终演化出了内容复杂、含义深远的牛郎织女传说。
春华秋实,夏雨冬雪,是自然的时序。人要建构自己社会的文化序列,形成人世的时间。世代是人世时间常见的比较朴素的刻度。从自己向上代回溯,一代一代就会追溯到始祖。有的文化是通过《创世纪》来说明人和人世之物的来源。中国文化是通过始祖奇异诞生的传说来确立自己社会的起始时间。在每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一些关于本族来源一类的传说。在传说中,这些民族祖先的出生大多充满神奇色彩,非同凡人,由此也突显了祖先的高远神圣。夏商周三代的先人中,大禹是“鲧腹生禹”,他的后人夏启是石化而生,商人祖先殷契是简狄吞玄卵而生,周人祖先后稷是姜嫄踩巨人足迹而生。
在自古以来的民间传说中,无论是作为华夏民族的始祖,还是作为远古的圣明君主,人们总是将炎帝、黄帝、尧、舜、禹这些专名配以叙事,不仅落实在真实的时空之中,还安排进世系之中,既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帝王谱系,也塑造出一系列可供世人认同的符号。相关的世系文献在司马迁编订“五帝世系”之前就多有记载,这说明这种内容在他之前已经广为流传。《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尧舜在世系上被归于黄帝。《大戴礼记·帝系》:“黄帝产玄嚣,玄嚣产虫乔极,虫乔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大戴礼记·帝系》:“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虫乔牛,虫乔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鲧禹也被安排进炎黄谱系之中。《山海经·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世本》:“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墨子 ·尚贤》:“昔者伯鲧 ,帝之元子。”这种强调同脉共宗的谱系的出现恰好反映了民族和国家逐步走向融合和统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特点。
正是有了传说的存在、专名的使用,时间的流逝对于华夏民族来说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物理运动,而是一个被赋予了人文内涵的历史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时间的延伸具有引起空间扩展的潜力。这是商周的历史所证明了的,承认前朝并把自己与前朝在谱系上联结起来,实际上会有助于旧有版图的占有与新版图的扩张。[7]中国后来的历朝历代都列入在一个文化传承的谱系里,让华夏文明、炎黄子孙一脉相承,对于维护国家的共同体规模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个拥有自身文明的共同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就在反复讲述着自己的各个重要部分的构成渊源,并形成公共认识。共同体形成的客观社会过程与主观的集体意识是一体之两面。没有自我认同的集体意识就没有共同体的完成。因此,一个拥有自身文明传承的共同体不可能从有文字之后才开始自我表述,那么,后世的文明群体在认识这个共同体的时候采用早期的传说就是必然的了。
共同体是一个空间概念,但是它必须有自己的时间内涵,有自己的时间纵深。而且,为了显示自己的共同体是独立自足的,共同体的自我叙事会上溯到文明的初始期,或者说,会用叙事证明自己有一个初始期。那样的话,共同体的时间深度才达到了原点。共同体的时间深度造就民众的历史感,这同样是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所以,传说时代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文化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学术界在认识发展过程中曾经因为偏重“信史”而忽略了早期传说的价值,我们今天的研究应该对此有所弥补。
[1]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2]李伯谦:《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历史文物》,2009(6)。
[3]沈长云:《论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祖先地位的确立》,载《天津社会科学》,1995(2)。
[4]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载《古史辨》(第一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原昊、曹书杰:《〈世本·作篇〉七种辑校》,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5)。
[6]彭邦本:《禹族西兴东渐及其在黄河中下游的活动初探》,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1)。
[7]陈连开:《论华夏民族雏形的形成》,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3)。
(责任编辑 林 间)
Ancient History Legends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mmunity
ZOU Ming-hua
(Institute of Liter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
I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afeguarding movements emerged in recent years,cultural discussion and practice around ancient history characters such as the Emperor Huang,Emperor Yan,Yu,Yao,and Shun have regained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recognition which inspires us to rethink about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ancient history narrative.This article discussed some proper nouns used by the narrative of ancient history,regarding them as symbols of the community's identity and temporal-spatial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so we can comprehe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mmunity in its initial period.Community is a spatial concept,however,it must has its own temporal implication and time depth.Time-depth dimension of community brings up people's sense of history,which is also a sign of the level of civilization.Therefore,the age of legendary is vital for cultural values of a community.
ancient history legends;community;proper nouns;temporal-spatial consciousness;cultural construction
邹明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