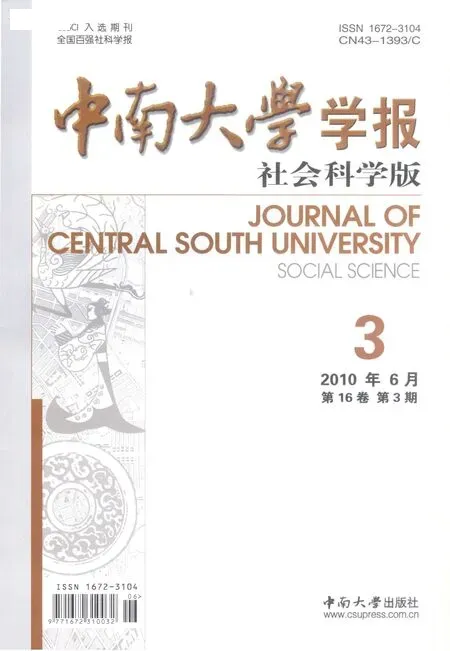精神隐喻背后的“失认”与“失神”
——论《生命法则》中的适应性悖论
毛延生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精神隐喻背后的“失认”与“失神”
——论《生命法则》中的适应性悖论
毛延生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在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生命法则》中,老人不同时期的人生态度划清了自我“精神三变”的原型与流变,洋溢着深切的精神隐喻内涵。老人用自己对于死亡的写实性理解提供了一个适应性悖论纠结于一身的典型,旨在揭示主体适应性悖论不仅存在于物理世界,还延伸至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当中。多维悖论的存在揭示了个体丧失生存空间和精神家园时的困顿与挣扎,更是直指人类面对自然因果律宿命时的一种精神重估,而这正是自然主义文学作品所隐含的现实一般性。
杰克·伦敦精神隐喻;失认;失神;《生命法则》;适应性悖论
《生命的法则》是美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杰克· 伦敦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于1901年由Mcclure杂志出版发行。杰克·伦敦一生著述丰硕,学界把他看作是一个普罗文学家,因为他“取材极广,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他那样把世界上的一切奇丽景色显示给我们看的。他展开北极冰天雪地,荒林野兽给我们看,又将南海的绮丽风光用妙笔写了下来”[1](306)。短篇小说《生命的法则》充分体现了杰克·伦敦身为“镀金时代”作家的艺术才能和独特的生活体验,因为那时的作者正处于充分领悟如何运用写作手法最大限度感染群众的高峰期。作为美国文学史上自然主义小说的典型代表,杰克·伦敦的作品当中洋溢着浓烈的自然主义气息也就不足为奇[2](146)。这主要表现在他是一个近似狂热的“适者生存”理论的信徒与强有力的支持者,因为他从不因为人类控制不了的行为而表扬抑或谴责人类本身,这在单独以他任意一部小说为分析蓝本时均会得以真切体现[3](107)。
小说《生命法则》中的人物设置与描写均精深入微地践行了自然主义的文学范式。例如,小说的背景设在极地,而主人公主要是一个印第安老人,作者旨在将人的社会属性降到最低,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动物本能,而这正是突显作者所推崇的自然主义所需要关照的情结所需要的基本元素[4](17)。杰克·伦敦力求尝试在小说中勾勒单独的个体如何回应自然决定主义的过程,并且当作者摒弃了自己先有的理想主义转而戏剧化地突显深陷物欲藩篱中的个体的勇敢反应时,这一过程显得尤为辛酸[5](92)。在《生命法则》中,作者通过老人精神的隐喻性建构、突显与关联,在多维视角下探寻主体适应性悖论纠结于一身的同时,更在洞察人性的不同层面,提纯了一种淡定的人生态度。本文力求从小说中老人的精神隐喻入手展开小说的主题分析,通过关照其“失认”与“失读”特点,进而挖掘小说主人公在自然主义背景下所必须面对的多维适应性悖论。
一、精神与三变:精神隐喻的原型与流变
隐喻,通常而言,是指不通过指向事物的本体,而通过指向非本体,即喻体来完成意义的建构。“当人们使用隐喻的时候,就把两个不同事物的概念放在一起,这两种思想彼此相互作用,其结果就是隐喻的含义”[6](19)。在小说《生命法则》中,“老人”思绪得以寄托的种种动物以及自我本体都是至关重要的精神隐喻标记,它们一起编织成一个隐喻网络进而整合性地突显小说的主题。确切地说,小说中老人不同时期的认知反应带有明显的隐喻性特点,尤其是参照了当时与之共存共现的动物,这种精神隐喻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小说中与老人精神隐喻具有直接联系的动物是狗与驼鹿,二者同老人一起构建成一个带有隐喻色彩的历时精神化生图景[5](130)。十分有趣的是,老人的精神隐喻之网可以在尼采的“精神三变”中找到原型:骆驼−狮子−婴孩,它们共同描摹一个渐变的、寻找自由的精神之旅。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杰克·伦敦的思想意识和哲学观点深受众多种哲学思想的影响[7](352),其中一位就是尼采[8](99)。据此来看,小说中不排除隐含着精神隐喻的可能性。
杰克·伦敦的小说对于自由有着说不清的眷顾[9](24)。小说中所涉及的动物与尼采本著中提出的本体大相径庭,但是却满足了喻体上的相似性。在尼采看来,骆驼作为沙漠之舟,刻苦耐劳。它是精神之力的负载者,负重的骆驼是传统精神的象征[10](5)。与之相比,在极地环境下,狗可以被看作“冰雪之舟”,这源于它在功能、品性以及能动性上与骆驼的相似性。在能动性方面,骆驼与狗都被赋予了“被动”的内涵——需要主人告知怎么办它们才能做事前进。这种被动性正是小说开头时老人精神的隐喻性体现。此时,之所以说老人同样是被动的,因为他即将被族人所抛弃,而只能毫无选择地独自一人迎接即将到来的死神。此时的老人需要精神上的引导者,而这个引导者就是老人本人,也唯有老人自己心识的张力才可以廓清跨越被动而进入主动的精神顿悟轨迹。
随着小说的发展,老人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看到驼鹿与狼群的抗争。此时,现实中的老人孤零零的,自己还在往火堆里加着象征着希望的柴火。回忆中老人对于驼鹿的反抗和搏斗予以高度认同和赞美,因为它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代表他的生命中流淌着独立性的血液,催促他勇敢地负起应尽的责任,征服自由而主宰自己的世界。老人回忆驼鹿与狼群的搏斗体现出老人对于宿命的精神抵抗,因此具有批判传统而获得创造的自由的主动性特征,而这正是狮子精神的初衷[10](5)。此时,老人渐渐模糊开悟,在变异的狮子精神——驼鹿精神的促动下开始挥舞着柴火,为自己的生存斗争不息。随着柴火愈来愈少,随着狼群越走越近,老人的精神在自然的威逼下再次升华。老人放弃了挥舞柴火,而是双手抱膝、头埋膝盖。这个特定的瞬间是老人命运、思想、生活的关键性时刻,因而对老人精神品格有一种神奇的显相作用[11](102)。老人此时的动作正如同胎儿在母亲子宫内的姿势,象征了尼采“精神三变”的第三阶段——婴儿。老人最终的选择同样象征着生命之轮自转回原点,其向心力轨迹中隐约可辨的就是生命法则对于精神自由的重新界定。可见,杰克·伦敦的小说往往会表现出对于自然逻辑的戏剧化表征[12](191)。因此,读杰克·伦敦的北方小说,不仅不会使读者在大自然面前感到渺小无力的无奈,产生一种屈服于自然、放弃人类战胜自然之主动性的沮丧情绪,反而更使人们增强同自然作斗争的勇气和力量[11](102)。
借助“精神三变”的原型,杰克·伦敦在物性意向安排上表现出卓绝技巧与深厚底蕴。主人公经历了被动、主动与自动的精神蜕变之后,老人最终坦然面对死亡。这种变动不居的复调表达恰当地象似了“自然主义小说中个体意向总是面临一定的挑战与挫败”[5](99)这一变异的景象。死亡意象的嵌入性表征是老人精神隐喻偏离“精神三变”的流变性的又一体现。这突显了个体高贵品质栖息于个体与现实之间的抗争这一事实[5](130),也让小说具备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全息性品格——在不到两千字内,作者带着读者一起领略了俗世凡夫如何完成精神三变的跳跃——从开始的执着于生,进而触发的不舍与恐惧,到后来放弃了生,进而直面死亡,老人对于死亡态度的变化牵动了精神隐喻内涵深化的每一个节点。诚如世界著名评论家 W·T·泼拉斯所言,突出性格的唯一方法,是把人物放入一定的关系中去。仅仅是性格,等于没有性格,只是堆砌而已[13](349)。杰克·伦敦设置这样一个带有隐喻色彩的死神意象(狼),就是这样的一种干预机制,进而微缩地勾勒出个体“精神三变”的心灵历程全景图。没有死亡,老人就不会思考自我,更不会顿悟。顺其自然当中,死神的意象就如同化迂腐为神奇的神来之笔,一切都以它为显性轴心,因为“生”“死”相依,这样自然才能够“在人与自然的碰撞中完成进化”[11](103)。可以说,老人精神内涵的隐喻性颠覆与流变,其实也是折射自己对于死亡态度变化的多棱镜,更是见证老人迈向自由进而完成自我价值重估历程的记事簿,在它背后预示着死亡到来之前必将面临的一种主体失认与失神,二者反过来将精神隐喻推向前景化,进而建构小说主题的强势关联。
二、失认与失神:身份隐喻的突显与关联
从表面上看,自我精神的转变与更替就是如此的简单与偶然,然而实质上,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接受却是绝对的复杂多变,抑或说是异常的艰辛。老人对于死亡理解的跌宕起伏以及他对自我精神的思考说明其精神转变的震撼性。这在小说中老人的主观情态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老人失去了感官中的许多触角,仅剩听觉作为采摄信息的工具,其解读生活中周遭一切的能力大大降低,因此老人是失读的。老人在人际交往中存在诸多障碍,要么是没有交际对象,因为族人已经纷纷离去,要么是交际中词汇单一,因为百感交集之时话语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因此老人又是失语的。自然而然,这种失认的(既失读又失语)老人就必然难逃失神的困顿,走不出自己宿命的“圈”[14](77)。但是不论失认也好,失神也好,都不能代表失意或者失败,因为自然主义关照下的主人公唯有放弃了世俗的恐惧,才能获得超脱般的自由[15](19)。从失认到失神,小说交待了老人精神隐喻的具化层面,同时反过来也指正了老人精神隐喻之网节点间的突显与关联。
小说的开头对于老人的描写是细致的。他看不到什么了,在六识当中相对比较清晰的仅存听觉和意识。就如同忍辱的骆驼或者狗一样,老人默默地、被动地接受了生活中的种种境遇,因为他知道这就是自己宿命的选择。老人在信息识别能力上的退化透露出其主体认知失读的特点。老人头脑中的生活不是文字所描绘的,而是以十分具有质感的图画拼就的现实性生活。他不能全面地感知或理解现实中的信息、符号抑或色彩,周遭一切的解读均因不能识别视觉信号的语言含义而延后甚至损失殆尽。可以说,老人在失读中的信息识别困难是以审视周遭环境上出现困难为特征的定向失能。老人心理上冲突迭起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内性动机,其信息解读上的紧张情绪、怕失败以及独面死亡的强迫性愿望等都可以让老人在心理上产生焦虑、紧张、阻滞。各种心理因素都可能破坏老人主动解读信息的企图,影响了选择性注意、记忆以及认识活动,从而招致被动的失读问题。而这一切的根源均缘起于内心需要同现实条件之间的相互矛盾——生与死的挣扎[11](102),这在老人失语的特点上同样可以找到佐证。
老人在借助词语进行理解和表达时,其语言符号意义的部分功能丧失,时而遇到言语困难。小说中没有交待老人与族人的交际并非偶然,这样可以更好地塑造老人异化的言语表现形式。即便是对老人与亲人的交际做了一些交待,同样也隐含着深层失语特点。最为典型的就是老人和儿子的对话——老人的儿子关心自己的父亲而有所询问。二者之间看似顺畅的话轮交替下面却潜伏着话语功能的错位。尽管从老人的话语来看,老人的语言符号表意功能发挥得很好,但是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看,这回老人的话语实际上侧重的是表情功能——老人无奈的落魄以及对儿子的安慰,但是在儿子那边,这种表情功能却被搁浅——儿子不再回答,继而离去。可以说,这里老人失语不但表现在语言使用层面的单调性上,言语行为上他同样是失语的——要么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要么不能让别人准确地理解自己的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老人单调的语言当中不乏鲜活的隐喻“I am as a last year’s leaf, clinging lightly to the stem”。这个让人耳目一新的隐喻表达是一个美好的创造,因为它形象地表征了老人对于人生的深切体悟,平淡话语中的一个鲜活隐喻揭示了老人在自我失认的世界中存在的一点创造与努力,而这似乎正是老人“狮子精神”在语言层面的化现。加之失语不同于无语,前者并未被推到主动性全部丧失的极限,更可以确定这个隐喻符号所负载的不只是一时的感慨,而是老人精神嬗变的标记。老人隐喻语言点缀于平淡语言之间也象似了老人精神嬗变的细微性,而这也是尼采提出“狮子精神”内涵中的一层[10](5)。
一个人在伴随着失读和失语之后,个体深处一定会有失神的特点。小说中的老人感官上是退化的,因为他唯一能够摄取信息的是听觉,老人对于过去的回忆、表达上的重复等等都说明老人囿于失神之中。但更为重要的是,老人在死亡到来时,读者最后看到的是一种智者洒脱的涅槃般的无畏智勇。这是因为在杰克·伦敦看来,能够直面死亡的超脱能力是人僭越动物的唯一特点,应该为了自己灵魂而不是肉体的归宿担心[16](45)。这里,的确存在精神悲剧性的痕迹[17](148),因为小说渲染的不只是老人对于世俗死亡的恐惧,更关注的是老人在精神上的生存困境,是在精神世界、心理世界以及深层意识中去寻找人的生存困境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老人在初期表现出精神失落的特点,其向度是朝内的,指向人自身,指向自我,涉及自主和自我确定。显然,这是十分切合小说自然主义主题的——老人对于生还是死这样的一个冲突性认识体现了个人的内在真实处境和内在生存的真实性。但是,老人并没有深陷此间而不可自拔。这种精神悲剧性所隐含的真实性恰好成就了自动的婴儿完成凤凰涅槃般重生的基本前提。这种类似逆增上缘式的悟道风格与小说“缩时空性”的精神之变息息相合,它也正体现了杰克·伦敦所推崇的“个人牺牲让人性更有尊荣一些”[5](125)。从作者的创作意识来看,也正好映射出杰克·伦敦所固守的一种创作哲学——整合真实的自己以及非真实但却被感知到的自己于自己的作品当中[18](9)。无论是失读,还是失语,甚或失神,都表明老人无法摆脱“适者生存”的因果律,也无法逃离宿命的死亡悲剧。在一个适应能力至关重要的世界里,任何形式的衰弱和逾越都无法到达安宁的精神处所,唯有真正的看破放下才能跳出自我与自然双重困境之下的适应性悖论交织而成的多维藩篱。此间的纠结是痛苦的,但又是完成精神重估的必经之路。
三、一维与多维:适者生存的纠结与悖论
杰克·伦敦的生活和作品展现了他在现实和幻想之间、在发现真理和否认真理之间永不停歇的斗争,这表现在《生命法则》中老人所遭遇的适应性悖论,其隐遁于字里行间。其中,老人所处的物理世界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受到不同力量之间的纠缠。从本源上来看,这离不开自然主义作品本身所具备的史诗性聚焦特点。回忆是对过去的反鉴,具体延展的时空维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分析视角。就时间维度而言,这种适应性悖论表现为回忆的超现实性。在时间的断裂中,可以更深切地领悟到被永恒迈进的形上时间所遮蔽的生命法则意义。面对生老死别,老人别无选择,但是在自己的记忆中自己依然是年轻的——有回忆为证。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年龄站位是一个十分纠结的问题。小说中的空间既是传统和历史,又是当下现实,具体表征为背景涵义的划定。只有当背景的全部涵义充实并且连贯地体现在个体的内部生命现实与外部生存形态之中时,背景才得以构成为一个与个体融洽统一的完整的现实实体。小说中的老人初期没有坚定的精神立场与追求,并且由于他者的离去而疏离甚至断然消泯了自我与传统背景的关联,因而使得“适应性”被悬置、“适应性”的现实化进程被延期。正是在这种寻找恒定的、可以拥为归宿的根——“死亡”中,适应性的悖论方才体现出生命法则的强大。当老人留恋着火焰,选择与自然抗争时,却无法融入自然的生命法则背景和精神背景之中。老人刚开始无力承受甘认死亡的生命之轻,而只能屈服于最动荡、最恐惧的背景意义——生命法则的统治之中,但这恰是后来精神蜕变的前提与基础[10](2)。到底是以肉体为物理世界的参考,还是游于形骸之间的思考是明显的一个悖论。
作者对个体生存悖论的揭示、对于人性自由的诉说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向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延伸。在社会世界的维度上,老人希望自己是一个至人的同时,还希望自己是一个超人,这都是他自己以别人为参考所提出的理想印象[10](73)。老人本身是向往自由的,可是又常常陷在人为的和自为的种种束缚当中。一方面,老人受到种种人为的、外在的规范的重重裹罩,例如部落将老人抛弃,而老人接受宿命的安排就是一个典范[5](124)。这样,老人与外界的扦格,主体与客体交通的阻塞,进而形成了自我封闭系统,缩限了自我精神的自由活动。同时,老人又希望自己是个超人,发挥潜在的能力,不断地超越自己,进而提升自我。老人在处理自己和部落关系时,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安命的态度就是把死亡贫富都看作命运的流行。诚如庄子所言“死生,命也”。老人认可死和生都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因此采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与此同时,老人又表现出反对这种安命的思想,与狼群的搏斗表明他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并力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去克服所遇到的困难,而创造自己所理想的环境——延续自己的生命。
老人在心理世界上的适应性悖论主要表现在情感维度得以表征。小说中的老人在情感上游离于忘情和激情之间。从心理学角度讲,情绪的困扰,特别是死亡之神的恐惧感,对人有很大的困扰。据此,老人对死亡的恐惧是其悲情的体现。同时,老人最后对于自然法则的遵从又体现出忘情的特点[11](104)。就情感维度而言,老人亲近传统却意味着被传统孤立,而部落发展得以永传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传统的建造和创造。所以,老人的背景化生存注定了是一种自我放逐的过程[14](81),老人的痛苦和空虚也不是在贡献和拼搏之后的怅然若失,而只能是一种伴随着回忆的,表现出经历了精神消费之后的失认与失神特征。这样,在争夺生存权利的热闹场面下,不仅个体求生的欲念愈来愈趋同,个体的孤独感也愈来愈被群体情感共象所强化,个体与群体的界限渐趋模糊,而且无限拥有、无限失落的生存怪圈也日益增大。小说主人公在适应性上存在重重悖论正好暗合了杰克·伦敦对于世界的自然主义属性的独特理解,因为他就是要通过在自己和一个否定自己个性的非人性系统之间建构二元对立[5](120)。
四、结语
关注未能较好适应自然的人们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喧嚣是“镀金时代”作家文学创作的优先主题,小说《生命法则》则从另外一个相反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老人是否具备解除自然与自我的多维适应性悖论的能力和条件已必然地成为老人及其族人所要解决的最首要的精神课题。在反思并有所行动之后,老人有信心找到一条使偏离了的自我回归真正自我的精神纠偏之路,并且在此途中完成精神元婴的价值重估,那就是放下生死、豁然超脱。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老人最后的放弃以及开始对于部落传统的了解注定他是无梦的,因为老人最后对自然界的生命法则完成了通达透解的参悟之道,所以不会再有任何刺激能够勾起他患得患失疲敝,这或许就是自然之子面对生命法则时的最高境地。
[1] 孙丰蕊. 杰克·伦敦小说研究述评[J]. 世界文学评论, 2008, (2): 305−308.
[2] 朱刚. 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二卷[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3] Wilcox E J. The Kipling of the Klondike: Naturalism in London’s Early Fiction [J]. Jack London Newsletter, 1973, (6): 1−12.
[4] Gair, Christopher. Complicity and resistance in Jack London’s novels: From naturalism to nature [D].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1997.
[5] Emmert S. Confined in small spaces: Naturalism in American short stories, 1890−1910 [D]. Purdue University, 2000.
[6] Richards A.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M]. New York: OUP, 1965.
[7] 王桂花. 杰克·伦敦作品中的兽性意识和超人思想[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2008, (3): 350−355.
[8] 斯通·欧文. 杰克·伦敦传——马背上的水手[M]. 褚律元译.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9.
[9] Cooper J G. The summit and the abyss: Jack London’s moral philosophy. Jack London Newsletter, 1979, (12): 24−27.
[10] 陈鼓应. 尼采新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1] 杜进. 在双重撞击中展现人物性格——略谈杰克·伦敦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艺术[J]. 外国文学研究, 2000, (3): 101−103.
[12] Martin R.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Universe Force [M]. Durham: Duke UP, 1981.
[13] 约瀚·霍华德·劳逊. 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伦与技巧[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社, 1978.
[14] 钟吉娅. 一个挣不脱的“圈”——从杰克·伦敦的动物小说探索其内心世界[J]. 国外文学, 2001, (1): 76−81.
[15] Cassuto L, Jeanne C. Rereading Jack London [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 McClintock J I. Jack London’s Strong Truths. Rpt. Of White Logic: Jack London’s Short Stories [M].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P, 1997.
[17] 任生名. 西方现代悲剧论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18] Jack London. On the Writer’s Philosophy of Life. No Mentor But Myself: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C]// Dale, L. Walker, Port Washington. Essays, Reviews, and Letters on Writing and Writers. New York: Kennikat Press, 1979.
The agnosia and distraction behind spiritual metaphor: on adaptive paradox in The Law of Life
MAO Yansheng
(English Department,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In The Law of Life, the old man’s attitude towards life has delineated out the prototype and variants of Tri-transformation of spirit by Nietzsche in different stages. This is further entrenched in the old man’s agnosia and absence, and then constructed into salience and relevance in a network of adaptive paradox the old man is in. With a realistic explanation to death, a model is set where a set of adaptive paradoxes get interwoven and the adaptive paradoxes proceed into the mental and the social worlds. The multi-dimensional paradoxes have betrayed the loss and struggle the individual encounter when losing the worlds at all levels. More significantly, it is directed at a spiritual re-evaluation when mankind is faced with stoical acceptance of fate, which is a norm to be realized in naturalistic works.
Jack London; spiritual metaphor; agnosia; distraction; Law of Life; Adaptive paradoxes
book=16,ebook=23
I106
A
1672-3104(2010)03−0106−05
[编辑:苏慧]
2010−01−13;
2010−01−30
毛延生(1980−),男,黑龙江大庆人,文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副教授,黑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文学语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