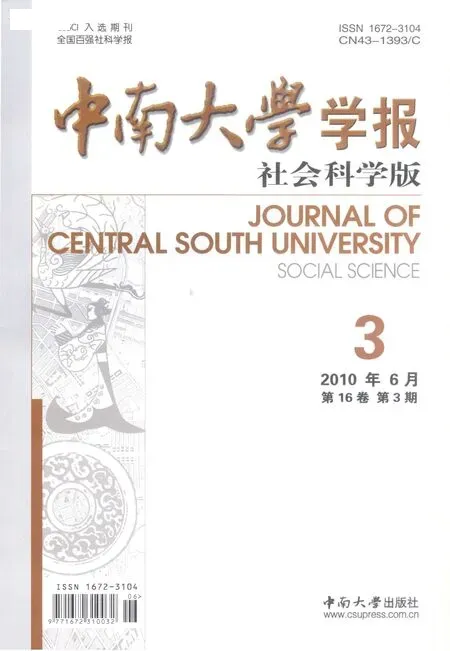建国六十年来中国政府责任的变化与展望
陈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事务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1620)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政府责任的变化与展望
陈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事务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1620)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政府责任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变化:全能型政府时期,政治责任凸现,政府责任越位;经济建设型政府时期,经济责任为中心,政府责任错位;公共服务型政府时期,社会责任回归,政府责任缺位。未来以社会责任实现为宗旨的政府在责任履行方面,不能靠硬性的权力强制推行,也不能靠可视性利益来交换或诱惑,而是靠现代国家作为共同体的权威与公民深层次的认同这二者关系的养成来实现,靠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社会权力三者之间的博弈均衡,因而,要处理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放任之间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结果的分配正义的福利与作为投资的福利之间的关系。
中国政府;六十年成就;中国模式;经济改革;政府责任;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
建国以六十年多年,按中国的甲子纪年法,六十年一个轮回,在重新一个轮回的起点上。胡锦涛总书记也认识到并多次强调中国目前机遇与挑战并存。带着如何认识中国政府责任的变化和如何走出政府责任面临的困境这个问题,本文基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责任侧重点的变化,探寻一个负责任政府执政的一般性规律,以期待政府在面对国内危机和国际风险面前,心态平和、思路清晰、步履稳健、从容面对、积极应对。
一、问题与回顾
针对建国以来政府职能定位与工作重心的转移,国内学界研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林尚立和季卫东两位教授的观点。林尚立教授的观点是“两次转换和三种形态”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的职能形态经历了两次转换,形成了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就是以政治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和社会职能,这种形态出现在改革开放前。第二种形态的出现来自改革推动。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提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求,政府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于是政府的职能形态,就从以政治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社会职能,转变为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府与社会管理职能,从而完成了政府职能形态的第一次转换。第三种形态出现在市场经济发展孕育出充满矛盾的现代社会的时候。为了保障现代社会的有效成长,建设和谐社会,政府的职能形态,就不得不从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和社会管理职能,转变为以社会管理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经济职能。这是中国政府职能形态的第二次转换”[1]。从以政治职能为轴心的全能型政府、到以经济职能为轴心的经济型政府、再到以社会职能为轴心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很清晰,也很有说服力,得到学界基本认同。这对我们分析政府责任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季卫东教授以每十年一个时间节点,再以每 25年为一个分界线概括出每个时间节点的特征,他总结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例,1960年代的主旋律是破私立共,1970年代的课题是走出政治动荡,1980年代的基调是经济体制转型,1990年代的特征是个人发财,而2000年代似乎将以关怀低收入阶层和分配正义为重点。……前25年(1954~1978)的时代性本质在于把个人纳入组织(计划管理),其象征性符号是作为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而默默奉献的雷锋;后 25年(1979~2004)的时代性本质是从组织分离个人(市场竞争),其象征性符号是摇滚乐第一人崔健,他通过震撼灵魂的呐喊使个体都按照发乎自然的节奏而舞蹈唱和”[2]。季卫东教授分析了建国后前 25年是个人被纳入组织的计划管理,后25年是个人从组织中分离的市场竞争,笔者认为在这50年后个人还得回归组织过社会化的“人之生活”,重塑政治共同体与公民的新型关系就显得尤其重要。过去维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任网络日益被商业化浪潮所解构,以利益交换关系维系的日常交往模式又不能给人们提供精神家园的寄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想象的共同体”的政治共识还没有达成,国家整合人们、整合社会不是仅靠硬性的权力和暴力机关就能够整合得住的,也不是靠可视性利益所能够诱惑或迷惑得住的,而是靠共同体的共识和规则的遵从来维系的。
笔者之所以花了很大篇幅来引用和分析这两位学者的观点,觉得他们很有代表性、见解很深刻,也能引起学界的共鸣。当然,还有不少的学者从政府责任的定位角度追问政府是提供安全和秩序、是提高经济效益、还是促进社会公平;也有学者从政府责任内容的“泛经济化”、实现政府责任的手段“泛政治化”的角度来观察政府过程;更多的研究者从行政问责制、高官问责制的角度,尤其是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这方面对于责任政府的研究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这些都为中国责任政府的建设做了很好地经验总结和未来展望。
二、成就与困境
(一) 政治责任与政府责任越位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一化三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形式上完成了人类高级政治形态的过渡,尤其是1954年的宪法和1956的《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性质、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基本任务定位还是非常准确的。可以说,这一时期,定下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安排。
然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在建国初期就摆在了国人面前,盲目的“一边倒”的策略,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惨重教训记忆犹新,告诉人们一个道理: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没有前人的模式可以照搬,一切都靠自己摸索。本应着手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从阶级斗争思维中摆脱出来,也没有从用群众运动和革命方法解决矛盾的做法中解脱出来。虽然国家对私有制的改造在1956年底就已基本完成,但之后的“意识形态”斗争达到白热化阶段,这与当时美苏争霸、资本主义对我国的封锁也有很大的关系,国内政策走向极端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狠斗私自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以阶级标准“划成分”和“扣帽子”搞得人心莫测,“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准备再打世界大战。“以阶级斗争为纲”断断续续地延续了近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靠国家的力量发动一系列的大运动,“一化三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整风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大串联”和“大民主”的“广场政治”或“街头政治”,发动广大底层民众和青年学生“夺权”,使社会充满猜忌、残酷,也使社会极其脆弱、支离破碎,使得社会完全消融到全能国家之中,消融在打乱一切公检法之后毫无章法可循的权力斗争之中。想以“文化建设”的方式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是强化了,但是社会积贫积弱,农村以“人民公社”和城市以“单位制”的形式完全整合到国家的行政控制之下,“政府来办社会”是这一时期主要特征。
从政治绩效看,“十年文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建设二者之间像两张皮,相脱节;从经济绩效来看,尽管在以农业部门为经济主体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三线军工业,但其背后却是以“无实质性的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为代价[3]。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像德国、日本都抓住了时机迅速从战败国重新复苏过来,而中国政府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搞政治斗争方面,对于如何搞经济建设可以说还是一张白纸,那些懂得经济建设的先知先觉者又都被划为政治右派成为被批斗的对象,盲目照抄照搬苏联的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成为这一时期的又一显著特征。一个全能型的政府无所不包的干涉到社会所有角落,甚至人们的精神世界也被模式化了,“样板戏”是其突出表现,什么都要搞个样板出来学习,做人学雷锋,农业学大寨,可见,政府责任的越位现象严重,党政不分的“遗产”给后来的改革留下不知“从何下刀”的难题。
(二) 经济责任与政府责任错位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至20世纪前后,可称为政府强调“经济责任”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开始改善“意识形态”斗争的国际形势判断,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曲折和教训的总结,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要“韬光养晦,自力更生,改革开放”,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认识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首先通过行政性改革为突破口,以经济性分权为试点,使一些地方在经济搞活过程中尝到了甜头,以先富带后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进一步解放思想,胆子更大一些,步伐更大一些,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直到1994年明确了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努力的目标,1995年也成功地实现经济腾飞的“软着陆”,确立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收入分配原则。总体来看在这2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是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渐进式推进的。
从经济绩效来看,由于对原有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新制度逐渐建立并不断地释放能量,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成为“东亚经济腾飞的巨龙”,也使得东太平洋沿岸成为世界经济投资的热土。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具体表现为:第一,市场规律越来越被认识,运行越来越规范。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正在奔往小康的大道上。高档消费的支出占家庭开销的比重越来越大,人们扬眉吐气,对未来的好日子充满信心。第三,与世界接轨方面,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对世界经济做出的贡献越来越突出。东太平洋沿岸的投资热土对于世界经济稳定与繁荣的作用引世人瞩目毋庸置喙,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并不是口号,全球化浪潮已经使中国成为“地球村落”不可分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时段的成就看,经济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政治,“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化为“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各地都纷纷效仿以GDP作为考评的重要指标,甚至享有生杀予夺的“一票否决权”。一方面,中央和上级政府下达的财政任务,另一方面,当地人民提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这双向考核指标使地方政府压得喘不过气来,“唯经济马首是瞻”,开发区、园区建设遍地开花,全民招商、各个机关下达“招商引资”任务,政府商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形象工程”或“豆腐渣工程”或“权钱交易”等丑恶现象屡见报端,部门小金库、个人贪污敛财数目惊人。社会阶层急剧分化,利益集团也开始出现,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经济权力越来越强大,在过去从政治权力的松绑中分得一杯羹的地位,越来越成为“勾结”和“俘获”政府权力的重要力量。一方面是新贵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大量下岗工人过着“颠沛流离”和“食不果腹”的生活,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市场是解决资源有效流动的最佳配置方式,但是决不能保证分配正义、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自动实现。据调查数据表明,经济的增长不但没有带来人们幸福的正比例上升,反而温情脉脉的传统信任关系被冷冰冰的金钱关系冲击和瓦解地体无完肤,市场背后的社会空间永远是人们安生立命的根本,人们可以不参与政治、也可以没有金钱,但不能没有社会关系,否则,脱离社会关系,人就不成其为人。政府责任最终归宿应该是提供公共物品、营造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政府由于其公共性,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并不适用一样的计算方式,我们难道可以考虑金钱而不救死扶伤、而不投资义务教育、而不提供基本的公共设施了吗? 再者说来,政府直接管理经济,更是外行领导内行,政企不分使国业改革举步维艰。政府主要通过法治来打击倾销和市场垄断行为,为市场公平竞争营造法治秩序,不能放任市场等到市场危机不可收拾再去拯救市场,灾难以定,为时已晚,而应该在进入市场的门槛时就引入市场的法治规则来规范市场行为。市场的搞活使得中国的市民社会在夹缝中寻找到生存空间,政治权力的下放和分权成为时代催生的必然,政治权力向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转移,使政治权力紧缩、经济权力整合、社会权力回归也成为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转移而不是放弃政治权力,从而完全听任经济杠杆的指挥,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社会综合实力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这一时期,政府责任的错位现象严重,责任内容的“泛经济化”现象严重。
(三) 社会责任与政府责任缺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朱镕基总理针对社保、医保、住房改革和教育公平等民生的问题,提出一揽子的政府改革方案。21世纪以来,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公平正义的分配、工业反哺农业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更使得社会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彰显了政府的社会责任。
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不够丰富,但收入差别不大,单位、国企、集体提供了大量的基本社会福利保障,社会还保持了相对低水平的正义分配。在城镇,建立了一套以终身就业为基础的、由单位直接提供的、包括医疗、住房、教育、养老以及各种生活福利在内的“统包统揽”的社会福利体系使得个人离开单位难以生存。在农村,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合作医疗制度、五保户制度等集体福利制度。形成乡卫生院、村卫生所、防疫站以及赤脚医生遍天下的全覆盖的医疗保障。“在全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虽然城乡社会福利水平差距很大,形成了二元制福利体系,但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在社会福利提供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居民的基本福利需要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4]。但是,这种福利制度为国企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企的低效率。为配合国企改革,救济从“单位制解体”中释放出来的弱势群体,我国进行了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福利体制改革,开始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体系。然而,国企、事业单位把包袱放得太快、放得太多,以为把这些都推向市场,靠市场自由竞争,就万事大吉,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很明显,这就过于浅薄。因为从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来看,导致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社会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悬殊、贫富差距扩大,下岗失业状况恶化,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接近警戒线,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未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公共领域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不同于市场的场所,是人们追求积极生活的空间。人们在此领域中生活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给人们提供这种条件或者公共物品的不是市场,而是政府。政府正是在市场失灵之处确立了自己存在的空间,也使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具有了合理化的理由”[5]。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数据,用于教育、卫生保健的社会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01年前后,瑞典、丹麦、法国、德国和古巴等国家比较高,约为13%~15%;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次之,约为10%~12%;俄罗斯、巴西、韩国、泰国等国家约为6%~7%;而中国为4.5%,甚至低于印度的 5.0%”[6]。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相当落后,与广大居民实际需要存在较大的缺口。2003年的那次席卷全国的“非典危机”对全国医疗卫生系统提出全面挑战,公共卫生资源都向大城市集中,建国初期乡村还能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覆盖,现在乡镇公共卫生资源流失严重,乡卫生院医疗器械简陋、芳草萋萋、一番衰败景象,“空壳化”严重的农村更是公共设施为零。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获得来衡量的人民生活状况却令人堪忧,繁华背后的浮华,引人深思表面的经济繁荣背后,暗潮涌动的社会危机的隐患正在集聚,政府责任的忽视、甚至熟视无睹,无限期的缺位下去,带来的将是不堪设想的后果。可见,政府面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对社会弊病的整治,不是“国家的退却”,放任治之,推给市场和社会就能解决的。这些社会政策领域可能只有部分层次、某些环节可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引入社会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共同治理,但是很大部分都是需要政府提供扶持、赋予政策、关心和指导的,社会领域是政府管理职能真正目的所在的地方。因为社会投资成本大、见效慢、收益成本小、分担风险大的重要领域,必须由政府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来,还有像社会软环境的投资和建设,市场所不愿、不能、不及的领域,政府都应该责无旁贷的担当起来,最起码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改革成果大家共享的机制。
从以上的发展阶段可以看出,社会从消融到全能国家之中,到从国家夹缝中成长,再到中国的市民社会逐渐强大,如果处理不好,社会权力就会与政治权力形成势不两立的对垒局面。如何走出这个最坏的结局,把市民社会转化为公民社会,使人民把利益与权利统一起来,把自由与责任统一起来,形成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者合作双赢的局面,政府责任的定位得准确与否和贯彻落实得程度怎样,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借鉴与展望
纵观六十年我国政府责任的变化,我们认为,要解决政府责任这一难题,首先是要处理好政府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先追求效率,后讲究公平;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存在不少的问题,能否找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方式,对政府责任提出更高的挑战。
其次,要处理好政府干预与放任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在以政治职能整合经济和社会阶段,高度计划的全能政府,政府控制得过死,管辖得过宽,一旦方向走偏,南辕北辙,离正确的方向越走越远,如集中精力搞政治斗争而使中国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失之交臂,人们生活在一个被鼓动的“口号中国”中,“上山下乡”的“知青的那一代”的理想幻灭以青春被耽搁为代价,发出“还我青春”的痛悔呐喊。在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放了再收,收了再放,一放则乱,一收即死”的怪圈循环,经济性分权太多,就容易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中央权威流失;行政集权太大,就容易出现体制僵化,经济缺乏活力,中央财力不足。在政府的社会责任方面,就不应该以“一放了之”的态度,更多的应该以加强公共服务项目的支出,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为己任。这也早被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管理经验所证明,在自由放任阶段,财富急剧垄断,经济危机爆发频繁,尤其是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促进了其后三四十年的“凯恩斯时代”的兴起,国家的计划干预在收获其巨大成就后,否极泰来,财政赤字带来的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的经济滞胀现象普遍存在,解决它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动力。从国内外的政府经验可见,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是很有必要的,市场的放任并不能带来社会公平正义分配的自动实现,但想实现“结果平等的正义分配”而过度干预的政府也面临困境重重,靠硬性权力的分配,如何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本身也存在难题。政府对结果的关注只能限于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和利益共享机制,更应该把眼光放在前瞻上,即提供更多起点平等的可能性,诸如把福利投放在提供更多教育机会、工作能力培训等方面。
第三,要处理好福利分配与福利投资之间的关系。社会责任是政府责任的根本所在,政府存在就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增进社会发展,提供“人之为人”的社会生活,即免于压迫、免于歧视、平等地受到尊重的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然而,这种社会理想在残酷的社会竞争面前总是以不平等地剥削而存在。处在社会弱势的群体一种是先天性的弱势,诸如先天性身体受障碍者;另一种后天造成的弱势,即体制安排的不合理所导致的,如不公正的分配等。政府对弱势群体必须提供最低社会生活保障和免于排斥、不受歧视的资源共享性社会包容机制。中国政府目前在社会福利方面越来越受重视,诸如农业税的全免、九年制义务教育全免等,还应该加大公共服务支出的费用,使更多的群体成为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群体。然而,福利性支出也要吸取西方发达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传统福利政策所导致的“福利陷阱”;还有一个弊病是这种选择性福利容易带来因严格审查所带来的歧视,使真正需要的群体为免予歧视而被排除在福利范围之外。所以,现在福利保障越来越选择“四金保障”和加入保险等方式。另一种是从“福利再分配的保障”转型到“福利再投资的保障”,即从结果型保障到前期投资型保障,换句话说,就是“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是“输血”还是“造血”,是“直接给黄金”还是“宁可给点金之术”,这样的选择已经很明显了。
[1] 林尚立. 民主的成长:从个体自主到社会公平[A]. 陈明明. 权利、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4辑)[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375−376.
[2] 季卫东. 宪政新论(第2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 2005, 3: 302−304.
[3] 林毅夫, 蔡湓, 李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69−71.
[4] 岳经纶. 和谐社会与政府职能转变: 社会政策的视角[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60(3): 419.
[5] 彭定光. 论政府的道德责任[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2(3): 283.
[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The change of and prospect for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in the past 60 years after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CHEN Y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433, China)
S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 the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has experiered three changes. When the government is all−powerful,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olitics becomes marked and the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becomes offside. When the government is engaged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becomes the focus and the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is misplaced. When the government offers public services,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turns and the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is lacked. The government will regard how to realiz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its purpose in the future. As far a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responsibility is concerned, the government can not rely on its power to execute or the visible benefit to exchange or attract. In fact,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dependent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modern state as a community and the citizen’s recogni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dependent on the game equilibrium of the politic power, economy power and society power. In conclusion,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the market indulgence,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ocial fairness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welfare as the results of distribution justice and the welfare as an investment carefully.
the China’s government; achievement of the sixty years; the China’s model; economy reformation;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politics responsibility;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book=16,ebook=187
D0351
A
1672-3104(2010)03−0069−05
[编辑: 汪晓]
2010−01−19;
2010−04−22
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项目《博弈规则与合作秩序》成果之一(hzf-07010)
陈毅(1979−),男,河南信阳人,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集体行动理论,政治学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