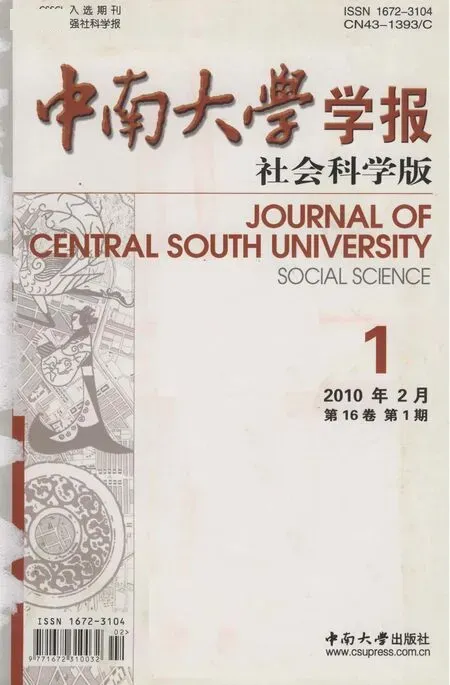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法规梳理与司法实践考察
陈海平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法规梳理与司法实践考察
陈海平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我国确立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十多年来,立法机关积极推进出台了一系列新规范,实务部门抵制过多,导致落实不力。侦查阶段律师帮助的现实是: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分野颇大,立法规范上进步不小,但还需完善;司法实践中执行走样亟待落实;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应有权利于法无据、既有权利难以落实而依然难有作为。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完善,需要从立法规范和制度实践两方面着力推进。
侦查阶段;律师帮助;立法规范;制度实践
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称《刑诉法》)确立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①,其实现程度直接影响着犯罪侦查的效率和人权保障的效果。在我国实现了“人权入宪”、国际上普遍强调人权保障的时代背景下,又值《刑诉法》再修改之际,理应对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进行深入调查和理性反思。十多年来立法上有无进步?侦查阶段律师帮助的现状到底如何?能否满足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需求?本文试图拨开迷雾,从法律规范的文本分析和司法实践的实证考察两个角度入手,全面呈现其现状,客观评价其发展,理性思考其对策。
一、法律规范的文本梳理
关于侦查阶段律师帮助之法律规范,根据制定机关和效力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一)法律
主要有1996年修订的《刑诉法》和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刑诉法》是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原始法源,其第96条集中规定了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其第 75条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申请取保候审和要求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律师法》在《刑诉法》的基础上,扩展了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其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二)行政法规
主要有2003年国务院发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称《法援条例》)。在经历了多年的酝酿之后,我国首部规范法律援助行为的法规——《法援条例》终于问世,填补了侦查阶段法律援助的立法空白。其第11条规定:“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从而使侦查阶段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免费获得律师帮助成为可能。
(三)全国性法律解释
主要有:1998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称《公安规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六机关规定》),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称《检察规则》),2000年司法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以下称《联合通知1》),2000年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以下称《联合通知2》),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以下称《保障规定》),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以下称《法援规定》)等等。
《公安规定》《检察规则》就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做了系统规定,明确了侦查机关对聘请律师权的告知义务,是对《刑诉法》的进一步解释和可操作性说明。针对此前公、检、法出台的解释相互“打架”的情况,《六机关规定》专门就“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用8个条文予以了统一和规范。《联合通知1》首次赋予了公安机关侦办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因经济困难无能力聘请律师时免费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联合通知2》首次赋予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因经济困难无能力聘请律师时免费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保障规定》就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做了具体规定,实现了刑诉法有关律师会见权规定的可操作化,并将听取受聘律师关于案件的意见规定为侦查终结的必要程序。《法援规定》以《法律援助条例》为基础,将前述两个《联合通知》协调统一,自此,所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因经济困难无能力聘请律师时均有机会免费获得律师帮助②,并要求侦查机关对律师帮助提供便利条件③。
(四)地方性规范
省级政法机关联合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具代表性的有:2003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北京市司法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称《北京规定》);2003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河北省公安厅、河北省司法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称《河北通知》);2003年四川省司法厅、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四川省国家安全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称《四川规定》);2004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司法局联合制定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暂行办法》;2004年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辽宁省公安厅、辽宁省国家安全厅、辽宁省司法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以下称《辽宁规定》);2006年山东省司法厅联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检察院、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国家安全厅共同制定的《关于在刑事诉讼中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和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若干规定》(以下称《山东规定》);2007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司法厅《湖南省关于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若干规定》(以下称《湖南规定》);2008年12月天津市政法委员会下发的《天津市关于严格执行<律师法>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天津规定》)。计划单列市或省辖市有关机关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具有代表性的有:2003年大连市司法局发布的《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称《大连规定》),2004年底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珠海市律师执业保障条例》(以下称《珠海条例》),2006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市国家安全局、深圳海关缉私局、深圳市司法局联合制定的《关于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的若干规定》(以下称《深圳规定》),2006年通辽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以下称《通辽规定》),广东、上海等地正在酝酿制定的《律师执业权益保障条例》等等。
纵观前述各地方性规范,相互雷同是其最鲜明的特征。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北京规定》(2003年3月26日)最早发布,当属原创无疑,时隔不久面世的《河北通知》(2003年4月14日)亦属原创,而近6个月后出台的《四川规定》(2003年9月15日)无论怎么看也遮不住《北京规定》的影子,在《保障规定》(2004年2月10日)出台前不久面世的《大连规定》(2003年12月18日)更像是《北京规定》的孪生姊妹。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规定》的基础上发布了《保障规定》(2004年2月10日),主要包括律师会见、阅卷、申请调取证据、听取律师意见、律师投诉处理等方面内容,对于《北京规定》有关律师会见的规定基本全部吸收。就正常的逻辑而言,自此开始,各地的效仿对象应该转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保障规定》,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在《保障规定》出台4个月后,《辽宁规定》(2004年6月14日)发布,依然难掩《北京规定》之风。更为夸张的是,《保障规定》出台2年多后的2006年6月7日,通辽市政府发布的《通辽规定》(39条)以《北京规定》(40条)删节版(仅删除 1条)的形象面世④。时隔近 3年后的2006年11月,以《保障规定》为蓝本的《山东规定》《深圳规定》《湖南规定》等地方规范相继面世,其基调与核心内容与《保障规定》并无二致,基本亦属照抄照搬者。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第一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地方性法规——《珠海条例》,以地方性立法的形式解决侦查阶段律师执业难题的做法,对律师权利保障立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律师法面世后的首个地方性规范《天津规定》,其亮点主要在于:首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除本人外,其亲属、所在单位也可以为其聘请律师;明确强调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但不得干扰律师正常会见;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次数不受限制;创设了律师申请侦查机关调查取证自行调查取证权。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这应当是保障律师帮助最为得力的地方性规范。
基于法律规范的上述考察可见,现行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主要由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受聘律师的权利构成。前者主要包括:获知聘请律师的权利、经济困难免费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向律师法律咨询的权利、与律师会见交流的权利、自行或者通过律师提出控告及申诉的权利、被逮捕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或要求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后者主要包括:介入侦查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的权利、与犯罪嫌疑人会见交流的权利、代为控告及申诉的权利、申请取保候审或要求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了解案情的权利⑤、反映意见的权利⑥。
有关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法律规范,从《刑诉法》到《法援条例》再到《律师法》,从《六机关规定》到《保障规定》再到《法援规定》,从全国性司法解释到地方性保障规范,免费指定律师帮助权的从无到有、反映意见权的从无到有、了解案情权的从小到大⑦、会见权从限制到保障、具体权利从宏观难实现到具体可操作,无不体现着规范层面的进步,无不彰显着规则制定者对侦查阶段律师帮助的态度之转变。
二、制度运行的实践考察
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难是有目共睹的,多重受制下的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实践同样异常艰难。有学者明确指出:“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即使在第一次讯问之后实际上也没有聘请律师;已经接受聘请的律师在法律上无权于讯问时到场,甚至连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都非常困难。”[1]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将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来呈现我国侦查阶段律师帮助的现实。
(一)聘请律师权利告知不理想
虽然《刑诉法》并未规定侦查机关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权利的义务,但《公安规定》《检察规则》《天津规定》都明确了侦查机关的此项告知义务⑧:自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侦查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记录在案。据侯晓焱等 2003年 4月对北京海淀看守所 177名在押人员的调查:75.7%的犯罪嫌疑人表示在侦查阶段被告知过聘请律师的权利,其中52%是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时告知的,23%是在被侦查机关第二次讯问时告知的,20%人是在被宣布逮捕时告知的。71%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从侦查人员处得到有关律师帮助的作用的解释,而且有的侦查人员甚至还表示“你请也白请”[2]。虽然该调查基本能够反映首都侦查人员良好的执法自觉,但调查本身的局限性也决定其只能反应北京一个小区域的状况。即便如此,仍有相当比例的权利告知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李步云教授主持的课题组2006年3~9月对广东、湖南、辽宁、新疆等省的大规模调查:虽然近80%的警察、法官、检察官、律师均认为应该告知犯罪嫌疑人法定诉讼权利,72.6%的警察、89.6%的律师表示,《刑诉法》应当明确规定在侦查阶段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的权利,而且 85.9%的警察、92.3%的检察官表示办案中实际告知了犯罪嫌疑人应该享有的该项权利,但是1159名服刑人员中只有35%表示直接从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那里知道诉讼过程中可以得到律师帮助,18%的服刑人员甚至不知道律师可以帮助他,62.4%的服刑人员表示不知道因经济困难可以免费获得律师服务[3],来自服刑人员的验证或许更能反映权利告知的真实状况。据“南大学生调查报告”⑨:42.31%的公安人员认为侦查阶段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咨询没有必要或者意义不大,有高达88.48%的公安人员认为在侦查阶段律师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或者作用一般;另据有学者对江西检察机关的调查,70%的检察官认为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对保障当事人权利意义不大[4](361)。在侦查机关这般主流意识之下,我们对于权利告知及其质量实在不敢抱以过于乐观的估计。
(二)聘请律师的权利远未落实
虽然相关法律规范明确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利,并将侦查机关的协助设定为义务,但根据侯晓焱等的调查,即便 76.2%的犯罪嫌疑人表示最希望在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包括已决犯和开庭候判的未决犯在内也只有 31.5%的在押人员聘请了律师。[2]78.5%的犯罪嫌疑人向预审人员提出了聘请律师的要求,而 40.1%的预审人员没有反应,只记录在卷[2]。对海淀区检察院的调查显示:自侦案件中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比例也不高[5]:2003年为48%,2004年为53%,2005年为63%⑩,2006年为55%,4年平均为54%。据有学者对几个县级法院的调查[6]: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区法院无辩护人的刑事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为48%,四个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县法院无辩护人的刑事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分别为 66%、69%、71%、74%,一个贫困地区的县法院无辩护人的刑事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竟高达93%,以上平均达 70.2%。虽然这两项调查并不能直接反映侦查阶段聘请律师的情况,但一般的逻辑和经验告诉我们:侦查阶段聘请律师的比例一般只会比起诉阶段低,前述数据作为侧面证据足以得出侦查阶段律师介入比例不高的结论。2004年黑龙江全省侦查阶段律师介入案件平均比例只有 23.4%[7]。河南省潢川县检察院办理的48件自侦案件中,侦查阶段有律师介入的只有7件,比例低至14.6%,而河南商城县检察院办理的21件自侦案件中竟然无1件有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8]。“南大学生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大部分犯罪嫌疑人表示涉嫌刑事指控时愿意聘请律师,但实际情况是侦查阶段律师的介入率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多不超过 20%,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多为 20%~40%。而与某区检察院座谈时有检察人员表示“我们这里70%的犯罪嫌疑人没有请律师”,这也从侧面证明侦查阶段律师介入的极其有限。
(三)会见交流权的行使步履维艰
《刑诉法》规定了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对于通信权并未作规定。处于羁押状态的犯罪嫌疑人除了等待律师的会见外别无他途向律师求助。那么律师会见的情况如何呢?在我国,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异常艰难。来自实证的数据将进一步强化我们对会见艰难的体认:其一,侦查机关经常性拒绝安排会见,北京海淀区全部在押人员中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率约为 14.6%[2];据对北京 700多名律师的调查,经过律师据理力争或向侦查机关的领导或者上级部门反映后,侦查机关安排会见的也只占侦查阶段介入案件的34.3%[9](270)。其二,侦查机关习惯性拖延安排会见。据《六机关规定》可知,对大多数案件应在律师提出会见后48小时内安排,而对江西律师的调查表明,一般在受聘3日内会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会见前一般要等待5至10日[4](367);据对北京700多名律师的调查,侦查机关在48小时之内安排律师会见的只占律师提出会见的22.9%[9](271)。其三,会见经常性派员在场。据对西部某省直律师事务所的调查,“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时侦查人员在场率高达75.4%”[10](176),据“南大学生调查报告”,公安机关有接近半数的人认为无论何种情况下都应派员在场,只有10%的侦查人员认为不需要派员在场。其四,会见限制颇多。侦查机关普遍对会见时间、次数以及会见时讨论案情予以限制。据对海淀区的调查,会见的平均次数为1.3次,人均每次会见时间约为24分钟;[2]据对西部某省直律师事务所的调查,只有 20.5%的案件没有限制会见次数,49.5%的案件只能会见1次,54%的会见被限制在 1小时以内;[10](175−176)另据对北京700多名律师的调查,只安排会见1次的占安排会见总数的49.3%[18],讨论案情占侦查人员干预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谈话全部理由的65.8%[9](272)。“南大学生调查报告”显示:73.75%的侦查人员对律师会见时讨论案件持不赞成态度,“由于法律没有对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次数做出规定,因而一般都默认为只准会见一次。”某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如是说。
(四)了解罪名、提供法律咨询的权利保障不力
律师介入侦查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相关法律规范均将其作为律师的一项权利明确规定。为保障犯罪嫌疑人有效地行使辩护权,向受聘律师告知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是国际通例。但“南大学生调查报告”显示,对于律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的要求,60.77%的公安人员会有选择地介绍或者干脆不予介绍。了解涉嫌罪名尚且如此不易,会见之难前文已有交代,对于以会见为基础的法律咨询敢抱多大期待?据对西部某省直律师事务所的调查:“会见前,侦查人员会明示律师:案件刚刚接触,不该问的不能多问。会见中,侦查人员也常常限制或打断,如规定律师提问范围,控制谈话内容,有的甚至不允许谈论案情;……在会见过程中插话或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示意,不让犯罪嫌疑人翻供等。”[10](175−176)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之下,犯罪嫌疑人和律师到底需要多高水平才能在不涉及“案情”的情况下进行“法律咨询”?犯罪嫌疑人有如此水平又何需律师的“法律咨询”?基于此,笔者以为,在涉嫌罪名都难以确知的基础上提供“法律咨询”根本就是无的放矢,在案情都不能涉及的会见中提供“法律咨询”纯粹就是无稽之谈。
(五)申请取保候审、要求变更强制措施极其困难
相关法律规范均规定了受聘律师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要求解除超过法定期限强制措施的权利。律师因了解罪名权不保、会见权受限导致其难以了解案情,无法提出适当理由,对于侦查机关做出的不变更强制措施决定只能接受,无从提出不同意见。据“南大学生调查报告”: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出的取保候审申请,只有23.85%的侦查人员认为有可能被批准,至于不予批准的主要原因,50%的侦查人员认为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不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39.23%的侦查人员认为取保候审不利于侦查活动的开展。而对律师方面的调查也验证了这一结论,律师向侦查机关申请取保候审,各地侦查机关多以种种借口不予批准,在规定时间内不予答复的情况极为普遍。
(六)代理申诉、控告的权利无法实现
现行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受聘律师代理申诉、控告的权利,而对其具体的操作程序却毫无规定,导致代理申诉、控告权无法兑现。我国的“特殊国情”还在于,即便立法上有明文规定,执法中还是难免会打折扣,既然立法者已经打了“折扣”,执法者自然也不太会把此项“权利”当真。实践中,即便刑讯逼供有恃无恐,即便超期羁押一如既往,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诉、控告的案例还是不多见。“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在立法者与执法者的“共谋”下,代理申诉、控告就只能作为高调宣传而无法实现的“权利”,对犯罪嫌疑人和律师来说,是“当不得真”的“权利”。
(七)律师介入流于形式,实质作用有限
据前文可知,对于侦查阶段律师帮助的作用,抱持乐观估计的态度本身就过于乐观了。根据对海淀区的调查,44名被调查者中:29人从律师处了解了家人近况并通过律师得到了家人送来的生活必需物品;26人的律师为其分析案情、提供法律咨询;13人的律师向嫌疑人询问了侦查人员是否有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违法行为;10人的律师尝试给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均未成功;有6人认为律师在这阶段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帮助[2]。难怪对侦查阶段的律师作用被戏谑为:通知犯罪嫌疑人“家属为你请了律师,家里一切都好,请你放心”,再多就是“你和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转达”。既然如此,也难怪会有侦查人员对想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说“请了也白请”,这或许还可以解释为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制度关怀。
考察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实践,实在是说不完的艰难、道不尽的辛酸。这固然有立法上的原因,但更多是执行中的问题。比如聘请律师的权利告知、了解涉嫌罪名的权利、律师会见、法律咨询……,哪个不是立法有明文规定?哪个不是执法走样变形?十多年来,立法方面的进步可谓不小,而执法方面依然艰难,甚至可以说,“艰难”是现行侦查阶段律师帮助的“关键词”。
三、评价与反思
(一)立法规范上进步不小,还需完善
《刑诉法》确立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六机关规定》的强化与协调,《公安规定》和《检察规则》明确聘请律师权的告知义务,两个《联合通知》和《法援规定》确立免费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保障规定》对律师会见的可操作性规定和创设听取律师意见制度,《法援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免费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律师法》确认律师凭“三证”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北京规定》对会见权的保障,诸多模仿性地方规范的出台,各地有关“律师执业保障条例”的制定和酝酿,无不昭示着立法上的前进,在上位规范《刑诉法》尚未修改的情况下,下位规范事实上已有不少突破性规定。因此必须承认: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在立法上的进步是巨大的。虽然进步不小,但存在的问题也还是不少,这可从规范制定和权利设定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规范制定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规则笼统粗放,可操作性不足。现行法律规范对于侦查阶段律师帮助的规定单从形式而言并不存在很大问题,但是为什么法定权利总是无法落实,原因之一就在于“大量的诉讼程序规则不具有最起码的可操作性,使得这些程序规则根本就无法得到实施”[12]。第二,重复制定规范。有关侦查阶段律师帮助的法律规范的制定,涉及从中央到地方多层次多部门,有些显然不“适格”的部门也参与其中,多属重复性规范,实际意义不大,如各地对《北京规定》的盲目跟风、《保障规定》出台后诸多地方性规定照抄照搬等。第三,位阶过低、难保落实。前述诸多法律规范中,大多是以司法解释和地方办案机关操作规程的形式发布的,不具有强制落实的效力,很难保证彻底执行,例如以司法解释形式确立的聘请律师权利的告知即属此例。此外,有些改革步伐过快,以至于很难执行。如《律师法》确立凭“三证”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其执行效果虽然尚待长期观察,但落实不力的现状至少在目前已经完全暴露;再如《法援条例》将国家救济异化为社会救济、将政府义务转嫁给社会公众义务,招致难以彻底落实的尴尬。第四,部门、地域规范招致不公平。部门性规范主要适用于本部门本系统,地方性规范主要适用于本地方本区域,部门、地方性规范的制定与适用易导致执法的不公平。
(二)司法实践中执行走样,亟待落实
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现有规范在落实上严重走样变形。主要表现有:对于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利,立法虽然明确要求侦查机关履行告知义务,但实践中要么不告知,要么不诚实告知,或者告知的同时又劝导“请了也白请”“白花冤枉钱”。对于聘请律师权利的落实,有关法律解释虽然明确要求侦查机关履行协助义务,但实践中要么不协助,要么不善意协助。如对聘请律师的请求不转达、拖延转达,或者对于符合免费获得律师帮助条件的犯罪嫌疑人答复“不符合条件”。对于律师的会见权,有关法律解释虽然明确要求尽早安排并提供必要便利,但实践中要么不安排,要么不善意安排,如因“领导经常不在”拖延安排,或者限制会见时间、次数,严格限制谈话内容。对于申请取保候审和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有关法律规定虽然明确要求侦查机关履行审查和说明理由义务,但实践中要么不审查,要么不认真审查或者不作合理说明。如对于取保候审和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置之不理,或者带着极端偏见审查,对不批准的决定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笼统说明“不符合法律规定”。对于代为申诉、控告的权利,有关法律解释也明确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必要方便,但实践中要么不提供,要么不充分提供。
执行中走样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是法律规范本身的问题。如权利设定不足、可操作性不强等,前文已有说明,不再赘述。另一方面是侦查人员基于认识误区的抵触。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竭尽所能限制律师介入的认识基础即是“律师介入影响侦查”。如据“南大学生调查报告”,某市公安局工作人员说:“律师的参与并不能使案件事实变得更清楚,很多律师的职业素质低下,他们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帮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的追究,而不考虑犯罪嫌疑人是不是真正犯了罪,他们的介入会增加案件侦查的难度,有时还会歪曲案情。”基于此种认识,侦查人员本能地排斥律师的介入。之所以说是认识“误区”,理由在于:律师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案件事实利于案件真相的及早发现,能够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职业群体,有其行为规范和职业操守,并非是单纯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律师介入对侦查机关形成监督,能促使其文明办案、防止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利于整体提升程序公正。
基于对现行法律规范形式上进步和执行中走样的认识,有学者认为侦查阶段律师帮助问题成堆的原因是现有法律规范未落实,而不在于法律规范本身的不完善,应当通过“落实法律”之路径来推动现有法律规范的修改与完善,并强调这种“逻辑顺序”对于我国司法改革的积极意义。[13]如果将这种改革完善的“逻辑顺序”放在我国司法改革的高度上考量,笔者是赞同的。但回到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改革完善这个具体问题上,笔者则难以苟同。理由有二:首先,所谓“落实法律”应该建立在法律应落实的基础上。无此基础强调“落实法律”,难道也可以通过对“恶法”的“落实”使制度得到改革完善吗?有关侦查阶段律师帮助的现行法律规范,参照国际标准和域外经验可知:虽形式上进步不小,但实质上差距颇大。这种情况下难道就应该不考虑通过修订法律满足最低限度的标准而优先考虑落实现有法律规范吗?其次,所谓“落实法律”,应该建立在法律可落实的基础上。前文亦指出,即便法有明文规定,但在实践中依然走样,究其原因就在于该法不具有可操作性。例如,法律只规定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而对于这个“可以”未作任何解释,侦查机关案案派员在场在法律上难道就不“可以”了?事实上,已有学者,以侦查阶段会见权为例,针对《刑诉法》第96条的不可落实性做过颇为精彩的论述,并得出“律师要会见在押嫌疑人而又不受到侦查机关的无理限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结论[12]。基于这一认识,关于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改革完善路径,笔者的主张是规范完善与实践落实并进:对于不符合国际标准的规定,应尽快修订或增补相关规范;对于形式上完美而实践中无效用的规范,应尽快修订以弥补其立法技术的不足;对于目前有条件落实的既有法律规范,应该加大力度认真落实。
四、结语
我国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现实是:立法上虽然进步不小、授权不少,但过多限制和操作性不高使权利沦为口号,实质性授权并不多;执法中侦查机关任意解释立法上的限制,极力抵制造成执行不力;对于执法机关侵犯律师帮助权的行为,司法上不但没有提供任何哪怕是形式上的保障,而且还对侦查机关的侵犯姑息有余。可以说,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徒具其形不具其实的现状正是拜立法不足、执法抵制及司法姑息三方“共谋”所赐。据此可得出,我国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完善对策:从立法规范和制度实践上双向着力,参照国际标准、借鉴域外经验,修订、增补法律规范,加强可操作性,完善制度设计,确立配套制度,确保法律规范真正转化制度实践。如此将彻底解决规范和实践分野的难题,彻底改变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残酷现状,极大推进我国侦查程序的法治化进程。
注释:
① 《刑诉法》第96条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规定,学界通说认为并非如有学者所言是关于侦查阶段“辩护”的规定,故本文一概称为“侦查阶段律师帮助”。
② 《法援规定》第4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对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或者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③ 《法援规定》第16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支持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开展工作,应当告知律师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依法安排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为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为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等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
④ 《通辽规定》第39条郑重宣布:“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规定发布之日前本市各部门的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笔者实在难以找到通辽市政府能够制定此类规范并约束该市各政法机关的依据。在《保障规定》已然吸收发展《北京规定》,时隔2年多后还这般追求早已过时的“流行”,令人不得不感叹中国治理中上情下达之艰难、不得不承认中国城乡差距之巨大。
⑤ 《刑诉法》第96条第2款规定:“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只规定了了解有限案情(涉嫌罪名)的权利。《保障规定》对这一权利做了重大延伸和拓展,第1条规定:律师可以“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及犯罪嫌疑人的关押场所告知受委托的律师。”第6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况:(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实施和情节的陈述;(四)犯罪嫌疑人关于无罪、罪轻的辩解;(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七)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⑥ 也属于对律师权利所做的延伸与扩展。《保障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案件承办人应当听取受委托的律师关于案件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受委托的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⑦ 对于《保障规定》对反映意见权及了解案情权的延伸和扩展,有学者甚至认为“实质上是明确了律师在这个阶段的实体调查权”。参见:徐鹤喃:《关于律师辩护制度发展路径的思考》,《法学杂志》,2007年第2期。
⑧ 《检察规则》第145条、《公安规定》第36条、《天津规定》第1条。
⑨ 南京大学法学院2005年暑假组织学生在南京、徐州、连云港、淮南、无锡等地进行“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主题社会实践,形成12万余字的调查报告,包括座谈笔录和问卷调查两部分。笔者认真阅读后认为其问卷设计的科学性与数据统计的准确性均无瑕疵,该报告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本文主要参考其座谈笔录、“对无锡、南京、徐州、淮南四地公安机关171份有效问卷的分析”、“对淮南、无锡、南京、徐州、连云港等地律师162份有效问卷的分析”等内容。出于叙述上的简便,行文涉及该报告时一概简称为“南大学生调查报告”,并对相关数据做进一步处理。报告来源:http://law.nju.edu.cn/Print.asp? ArticleID=2007417165200697,2009年7月7日最后访问。
⑩ 该调查中给出的2005年比例为55%,但从“2005年受理自侦案件27件38人,其中聘请律师辩护的20件24人”的表述中可以计算出该比例为63%,而不是55%。
[1] 孙长永. 论侦讯程序的立法改革和完善[J]. 江海学刊, 2006, (3): 112.
[2] 侯晓焱, 等. 什么时候最需要律师帮助—对北京市某看守所200名在押人员的调查[J]. 中国律师, 2003, (11): 14.
[3] 黄立. 诉讼权利告知的实证研究[J]. 法学杂志, 2007, (3): 94−98.
[4] 张志铭, 等. 江西省刑事自侦案件律师辩护问题调研报告[C]// 石少侠, 徐鹤喃. 律师辩护制度研究—以审前程序中的律师作用为视角.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
[5] 庄伟.审查起诉阶段的律师作用—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2003年至 2006年办理的自侦案件中的律师执业为视角[C]//石少侠, 徐鹤喃. 律师辩护制度研究—以审前程序中的律师作用为视角.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 112.
[6] 马贵翔, 倪泽仁. 刑事辩护萎缩看辩护律师诉讼地位的提升[C]// 陈卫东. 中美“律师辩护职能与司法公正”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 198.
[7] 张志铭, 等. 律师辩护的困境与出路——黑龙江省刑事自侦案件的调研报告[C]// 石少侠, 徐鹤喃. 律师辩护制度研究—以审前程序中的律师作用为视角.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 375.
[8] 周洪波. 河南省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情况的调研报告[C]// 石少侠, 徐鹤喃. 律师辩护制度研究——以审前程序中的律师作用为视角.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 401−402.
[9] 陈瑞华. 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0] 左卫民, 等. 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11] 房保国. 当前“律师会见难”的现状剖析[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4, (3): 70.
[12] 陈瑞华. 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技术问题[J]. 法学, 2005(3): 17.
[13] 徐鹤喃. 关于律师辩护制度发展路径的思考[J]. 法学杂志, 2007(2): 104−107.
On lawyers′ aid in investigation in China
CHEN Hai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 series of new regulations have been advanced and promoted by legislature organizations, since having the system of lawyers’ aid in investigation for over ten years, while the effect is unsatisfied because the substantive departments resist to practise. The fact is that conflict between legal standard and judicial practice is still drastic, which should be consummated in the legal standard although a great advances; Awry execution of judicial practice needs to fall into place; Lawyer’s rights in investigation are unwarranted or beyond factitive. Therefore,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lawyers aids in investigation requires to promote the legal norm and system practice.
investigation stage; lawyers aid; legal norm; practice of system
book=16,ebook=50
D925.2
A
1672-3104(2010)01−0065−08
[编辑:苏慧]
2009−07−27;
2009−12−06
河北省教育厅2008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侦查阶段法律帮助制度研究”(SZ080102)
陈海平(1979−),男,甘肃渭源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讲师,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