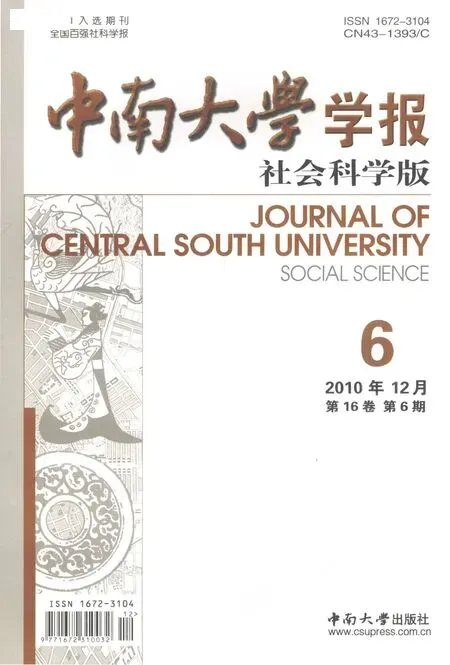徐訏小说中的西方形象——为纪念徐訏逝世三十周年而作
陈娟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421001;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作家,徐訏小说的异域色彩和浪漫情调早已为学界所熟知并广泛论及。在徐訏小说中,出现了许多西方男女形象以及具有西方色彩的物质文化景观,“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1](17)以下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对属于本范围的相关论题进行探讨。
一、爱的港湾:风姿绰约的异国女性
徐訏小说中的异国女性,都非常美丽,不论未婚的单身女性具有超凡脱俗的美,已婚的中老年妇人也都温柔娴静。更重要的是,她们都善良高尚。
我们先看文本中的已婚异国妇人形象。《风萧萧》中史蒂芬太太有很美的身材,长长的颈子,配着挺秀的面庞,声音轻妙低微,表情浅淡温文,在一番交谈之后,“我”发觉史蒂芬太太灵的美丽以及体念感觉的细腻与敏锐;曼斐儿太太有很丰富的笑容,“我从她女儿推论,我想她青年时一定也是美丽的”,[2](44)非常和蔼可亲;《时与光》中萨第美娜太太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虽然头发花白,面孔挂满了皱纹,但她声音的节奏、手的动作与眼睛的表情,都很有风度。不仅如此,即便是对文本中一笔带过的费利普医师的太太和中国人高先生的太太(《风萧萧》)以及兰姆太太(《时与光》)、舍而可斯太太(《犹太的彗星》),只言片语中也都充满亲切情感:费利普医师的太太大方可亲、中国人高先生的太太是一个秀美的美国人、兰姆太太人很和善、舍而可斯太太年青时候也很美过,态度很柔和。在一定程度上,这类温柔娴静的异国妇人形象,寄寓着作者对西方的一种想象。
我们再来看徐訏小说中的单身异国女性。《风萧萧》中很喜欢中国的海伦不仅美丽动人,有明朗的前额,秀长的眼梢,挺美的鼻子,婉转柔和的唇线,而且恬静温柔,具有一颗难以企及的灵魂。《荒谬的英法海峡》中象征着真善美的培因斯,在“我”看来,如在教堂里望着壁画中云端里的圣母。《吉普赛的诱惑》中美好、温柔、宁静、可爱的潘蕊具有一种尊贵高洁与光明的美。《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白蒂脸庞美丽、海兰具有诱人的美,品德崇高。《犹太的彗星》中凯撒玲留给我的印象是矫健,活泼,愉快,勇敢而轻捷,“她是光,是火,星星,是把自己的光与热散布给人类,而自身消灭在云海之中的星球”。[3](39)
无需进一步详述,可以肯定的是,徐訏对美有深情的凝望,爱与人性是其小说的一贯主题。但问题并不到此为止,值得继续探讨的是,徐訏小说中这些单身异国女性,如海伦、培因斯、潘蕊、白蒂、海兰、凯撒玲等等,她们都爱上了一个中国人,而且“我”对她们也都有深情的爱。此一情况,促使我们思索这种异域情爱叙事所潜隐的中国作家对西方的想象和对自身文化的反观。异域情爱既有国别社会历史的投射,也是认识异质文化及了解他者的愿望,更是一种重构自我身份的努力,因为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4](426)徐訏小说中这些中国男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有学识、风度翩翩、有理想。无论是在异国他乡(如《荒谬的英法海峡》《吉普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还是在三四十年代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上海,(如《风萧萧》等),男主人公都在对自我价值不断追寻和确认,但都有一种焦虑:身处异国他乡所产生的文化边缘人感受是不言而明的,而置身殖民都会上海,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所产生的迷茫和失落也可想而知。可以说,异域情爱在某种程度上是文本男主人公们化解焦虑的一种方式,他们想通过与异域女性的爱恋来证明自己,融入日新月异的变动空间。最重要的或许还不在于此,徐訏以其小说中所塑造的这些风姿绰约的异国女性对中国男性的爱,含蓄传达了对东方的眷恋热爱之情,中国男性的魅力在文本中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文本的表达,提高国人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热爱之情,这对当时身处十里洋场和水深火热现实情境中或曾飘荡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激励。关于这点,我们在下文还将说到。
二、 男性:对东方的爱或被中国男性战败
徐訏小说中的西方男性,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东方充满神往热爱之情的男性形象;一类是在与异国女性、中国男性的三角情爱关系中,败下阵来的受挫者形象。下面我们依次进行分析。
在《风萧萧》《犹太的彗星》《期待曲》《荒谬的英法海峡》等小说中都出现了对东方充满神往热爱之情的异国男性形象。《风萧萧》中 C.L.史蒂芬是美国 N舰的医官,爱上了中国式的生活,他与庄严文雅的费利普医师都积极投身于抗战中;《风萧萧》中英国人多赛雷到东方来研究东方哲学,是一个对中国文艺语言有研究的人;帕亭西教授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神,是一个非常淡泊宁静的音乐家,有一颗很容易被人接近的朴素单纯的心,从东欧来到东方三十多年,对于东方文化特别有兴趣。《犹太的彗星》中舍而可斯爱音乐、爱和平,认为中国人比随便哪里的人都美。《期待曲》中“我”认识的美国人,很有兴趣于东方文化。《荒谬的英法海峡》中史密斯魁梧漂亮,对中国充满热爱,他倡导世界和平,自由,平等,快乐,没有阶级,没有官僚,爱上了中国女性羽宁。这类形象和前文所述爱上中国男性的异国女性相得益彰,其寓意亦可作如是观,共同表征了作者对东方的眷恋热爱之情,“‘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1](157)借助他者形象,使生活于特定社会历史氛围中的个体找到自我身份认同感及文化归属感。
此外,徐訏小说还写了一类在与异国女性、中国男性的三角情爱关系中,败下阵来的受挫异国男性形象,这方面的文本有《犹太的彗星》《炉火》等。《犹太的彗星》中凯撒玲爱的不是意大利青年,而是中国人“我”,而且在文本中意大利青年根本没有爱的发言的权力,就被淘汰出局。《炉火》中研究东方美术的法国青年史丹尼斯虽然不过三十岁,但在年长的中国人叶卧佛面前,却依然败下阵来,卫勒从叫叶卧佛为她绘画的那天就爱上了叶卧佛,之后她给史丹尼斯写了一封很轻松的告别的信,把他们的关系看作极其平淡的一个际遇,史丹尼斯因此而自杀。异域情爱“往往体现着性别、种族与政治冲突的内涵”,[5](344)也许我们还应当更进一步,因为这种异域情爱叙事所潜隐的等级化的东西方权力关系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不一致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国内的现实状况,所遭受的民族歧视可想而知,徐訏小说中所建构的这类在与异国女性、中国男性的三角情爱关系中,败下阵来的受挫者异国男性形象所表征的蕴涵也是很意味深长的,在此,我们不得不敬佩周蕾探幽入微的洞见:“‘想象’这一词极富有暗示意义,表明主体在形成的过程中,通过外界客体而认识到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使主体自己受到‘肢解’的那一部分。”[6](348)从此意义出发,我们重复这一点不是没有道理的:通过文本想象来建构强大的东方形象,这对于提高国人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热爱之情,其意义不言而喻。
至此,在下文具体分析徐訏小说具有西化色彩的物质细节之前,我想再就徐訏小说中的美与爱做一补充说明。我曾专文探讨过徐訏小说中的美与爱,[7]认为徐訏之所以这样描写女子超脱尘俗的美,是他通过让人物为这种崇高、圣洁而脱俗的美的全身心倾服而获得一种内思性的感性深化,进而借女性表达对一种完美自由与宁静自然世界的渴望,并藉此展开对自我的寻找。同时认为徐訏小说中的爱,是个体对完满追求的表现,通过爱与被爱,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获得对自我的肯定,找到自身存在的安全感,是人内心对自己精神主体的自觉坚持,对真正实在自我的回归。当我们再次阅读徐訏小说,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来进行探讨徐訏小说中相关主题,并不是对以前观点的否定,而是想指出,同样的文本,当从不同角度来多方面解读时,就可以获得不同内蕴和感受,而这也正昭示了徐訏小说的丰富性。
三、物质细节与殖民叙述
“自从欧洲文化输入以后,各都会都摩登化了,跳舞场、酒吧间、西乐会、电影院等等文化设备,几乎欧化到了不能再欧,现在连男女的服装,旧剧的布景说白,都带上了牛酪奶油的气味;银座大街上的商店,门面改换了洋楼,名称也唤作了欧语……”[8](186)阅读徐訏小说,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文本中出现了很多具有西方色彩的物质文化景观,这些物质细节主要体现在一些中国人身上。以下试图对此现象作一番探讨。
在《风萧萧》《婚事》《犹太的彗星》《笔名》《赌窟里的花魂》《无题》《时与光》《女人与事》《过客》《小人物的上进》《投海》等文本中,我们注意到,人物活动的场所多为咖啡馆、舞厅与西式公寓、洋房;寓所里有电风扇、电话、冰箱、以及用来烧咖啡和烘面包的电炉;他们喝咖啡、葡萄酒、威士忌;吃巧克力、土司;会说英文等外国语言,在中文中还不时夹杂几个英文单词;喜欢看电影,跳探戈、华尔兹;听无线电、留声机、音乐会;会弹钢琴,或者学弹提琴和钢琴;打网球、台球、骑自行车;过圣诞节、复活节等洋节。可以说,徐訏小说充满着琳琅满目的西方文化气息,文本中有迹可循的细节描绘是论证的重要索引,鉴于篇幅,我不打算逐一罗列,而是准备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细节,同时从文本中引用相关重要文字,作为分析的资料,来看看在徐訏小说所体现的历史时空中,这些细节所反衬出来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些问题及寓意。
“自从美国影片广传中国以来,时髦的女孩子都学美国女明星的派头”(《风萧萧》),[2](188)徐訏小说中中国女性的穿着打扮大致如此,如《舞女》中的张小姐,作者是这样介绍她的:
张小姐到底是美国派,短装打扮,长裤衬衫,露着乖诱人的手臂。手腕上是一只精致的游泳表,踏着鹅黄的平底鞋,一付旅行派头。[9](468)
在这里还要提到《妹妹的归化》这个散文文本,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姑娘在去美国之前在穿着言行等方面所做的种种准备,很具有典型性。身在美国的“我”同妹妹分别四年,妹妹要来美国读书,“我”去旧金山接她,一见面几乎不认识了,因为妹妹原来是个天真好玩的孩子,现在是个很成熟的少女,满脸脂粉口红,穿一套时髦的洋装:
“女大十八变。”我心里想。
“哈啰!”她第一声。叫我第二声呢?还是:“哈啰。”
“蓓君!”我叫她。
亲热一番以后,她忽然笑着说:
‘“你怎么不叫我爱立丝?”’[10](609)
这让哥哥“我”哭笑不得,妹妹对哥哥在美国的生活方式也不予理解和奇怪:“谁知道你还是没有美国化。”[10](611)不仅如此,在与妹妹的交谈中,“我”得知她在中国已学跳舞、游泳、网球、汽车、钢琴等,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后来,在舞场,妹妹的跳舞更让“我”目瞪口呆:奇奇怪怪的步子,各色各样的腔调,不用说“我”不会跳,“我”看都没有看见过,舞场里也很少有人看见过,跳完了全场鼓掌。这下子哥哥才恍然大悟:原来妹妹已不是当年的故乡园篱上晒手帕的姑娘,而是殖民地交际场中的小姐了。
小说《笔名》中金鑫一家从穿着到生活都是西化的。他太太穿一套西装,上面是柠檬黄的上身,露着洁白的衬衫,下面是一条别致的花裙,在和金鑫参加的各种“PARTY”中同那些洋太太交际应酬,样样学外国派;他们的女儿咪咪也是穿着西装,红绒绳扎着二角辫子;金鑫他穿一身法兰绒的西装,打一个很鲜艳的领带,头发光亮平滑,上海话、国语与英文,都说得很纯粹。他和太太各有一个英文名字:WILLIAM P.C.WANG和DIANA Y.S.K.WANG。在文本中,有一处细节值得注意,是关于金鑫名片的描述:
这张名片非常讲究,是金边的硬卡印着中华书局的仿宋,上面有:“王褒泉,茂成洋行襄理,浙江”以及一大串地址电话小字,反面是英文,我只看了大字,“WILLIAM P.C.WANG”。[11](314)
在此,我想再列举《风萧萧》中有关白苹居所摆设的相关描述,两段文字如出一辙,蕴含同样意蕴:
客厅四壁有几幅齐白石吴昌硕的字画,落地放着几盆花,一架日本式小围屏,四只软矮凳围着寝室里一样的圆铜盆,上面的洋火,烟灰缸与烟匣,几只灰色的沙发,地上是灰色的地毡,沙发旁边都放着矮几,独独没有一张正式的桌子。饭厅里是一架酒柜,一张方桌,铺着四角有黄花的灰台布,上面一个玻璃的水果缸,装满了橘子。四把灰布坐垫的椅子,角落上有二架盆花,都是倒挂淡竹叶。家具都是无漆的白木,地上是银色的地毡。墙上有一幅画,是任伯年的山水,一面是一只荷兰乡村里常用的钟。[2](113)
这两个细节描写,可以说是对作为文化符号的西方殖民话语对东方文明强势入侵的隐喻:金鑫的名片上除了印着中华书局仿宋的字体在表示“中国”的身份之外,别无其他,更有甚者,即便是仿宋字,其排列却是按照英文顺序:人名、身份、城市。同样的,白苹居所除了几幅山水字画在提醒着寓所与东方的关联之外,房屋的布局和生活物品都使人仿佛置身在一个西洋化的空间。具有东方情调的文化符号俨然已成为摆设,被挂在了墙上,但即便是成为摆设,也还在被收编和侵夺,因为挂在墙上的还有一只具有西方乡土情调的荷兰乡村里的钟,被殖民文化在殖民主义都市与乡村文化的双向侵扰之下,不断被割裂、零碎化。徐訏以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殖民都会里殖民者/被殖民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呈现了在殖民者文化统驭控制之下被殖民者文化的生存图景,并由此昭示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我们需要从西方化的中国主体/读者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现代性”。[6](352)在这种呈现的背后,更饱含着作者深刻的文化焦虑,其表征和寓意所指,令人深思。
四、结语
莫哈提出,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形象有三重意义,“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1](25)我们在这里不拟探讨徐訏小说中的西方形象与真实形象的契合度问题,更关宏旨的,我们是想指出,虽是徐訏个人创作中的西方形象,但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的集体想象,因为个人作为社会的存在,无法超越历史。应该说,源于晚清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的想象,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是徐訏的潜在视野,同时,亦融合了自身的文化特质与生活经验。研究徐訏小说,我们无法回避他所生活的年代与环境,徐訏从小喜欢读外国书籍,其小说的一贯表现主题是爱与人性,以及所接受的教育,在西方留学的经历,与西方人接触等,都渗透融化在了徐訏的小说之中,诚如布吕奈尔在他那篇很有洞见的文章里所指出的,“形象是加入了文化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或集体的表现”。[1](113)
如果说,徐訏小说中那些爱上中国男性的风姿绰约的异国女性以及在情爱关系中被东方男性战败和对东方神往热爱的异国男性,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作者对构建强大东方的一种美好理想,那么文本充满的具有西方文化气息的物质细节则更多地表征了一种潜在真实与文化反思,上海和香港的都市殖民化色彩,在他笔下有深刻的呈现。作为处身西方和东方、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徐訏有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对西方现代文明有向往之情,另一方面,对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强势入侵下的割裂零碎,充满焦虑。通过徐訏的小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回望和窥见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文化情状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路的文化焦虑心理。这种文化焦虑及关怀,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应有品格,对于当今我们社会文化的发展也有反思观照之价值。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徐訏.徐訏全集·第一卷[M].台湾: 正中书局,1987.
[3]徐訏.徐訏全集·第五卷[M].台湾: 正中书局,1967.
[4]赛义德.东方学[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姜智芹.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M].北京: 中华书局,2008.
[6]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C].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1999.
[7]陈娟.美与爱的凝望[J].福建论坛,2007,(2): 80−82.
[8]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四卷[M].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9]徐訏.徐訏全集·第十三卷[M].台湾: 正中书局,1969.
[10]徐訏.徐訏全集·第七卷[M].台湾: 正中书局,1967.
[11]徐訏.徐訏全集·第十四卷[M].台湾: 正中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