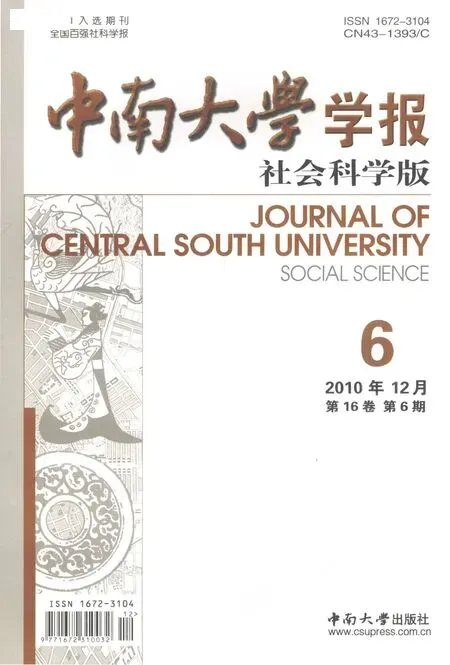再现的政治:历史、现实与虚构——论历史书写元小说的理论特征及内涵
陈后亮
(山东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西方文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趋势,许多作家似乎不约而同地把创作目光从封闭的语言文本再度转向外部世界。历史、政治和现实这些传统内容以熟悉却又陌生的面貌重新出现在小说当中。现代主义所宣扬的艺术自治似乎已失去魅力,更吸引人的却是后结构主义所主张的对语言、现实和历史之间关系的全新理解。像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库弗的《公众的怒火》和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等都是此类小说的典范。在它们问世之初,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评论家都常迷惑不解。一方面,它们拥有历史小说的题材,选取真实历史事件或人物,却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因为它们在自我关注小说的写作、阅读和接受方面明显表现出现代主义元小说的特征,对自身的文本虚构性毫不隐讳。另一方面,它们又和真正的现代主义元小说有很大差别,虽然它们也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却没有像后者那样纯粹沉溺于语言游戏,而是如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又译为琳达·哈切恩)所说“将文本自身及其生产和接受的过程再度语境化,置入它们赖以存在的社会的、历史的、审美的和意识形态的整个情境之中”。[1](40)历史、现实和艺术的话语纠缠在一起,编织成这一类奇特的后现代小说。在这里,历史和小说难以区分,现实和虚构界限模糊,但我们十分清楚的是,这是一类极具影响、特色鲜明的新小说形式。它们既不像现代主义元小说那样曲高和寡,也不像一般通俗小说那样难登大雅之堂,而是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前面列举的几部作品都在获得专业好评的同时登上畅销书榜。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小说,它又有何魅力?
人们给这一类作品起了许多名称,比如叫“超小说”(Surfiction)、“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和“奇幻小说”(Fabulation)等,但最具影响的还是哈琴所命名的“历史书写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她说:“所谓历史书写元小说,是指那些名闻遐迩、广为人知的小说,它们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的宣称与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关。”[1](5)“它不仅是彻底的自我关照的艺术,而且还根植于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现实之中。”[2](29)虽然哈琴将后现代主义小说与历史书写元小说完全等同有值得商榷之处,但由她所点明的这类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不容置疑。我们要想全面深入了解它,就必须将之放入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与西方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文艺思潮和走向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一、历史、现实与再现
一般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科学文化,提倡以理性严谨的方法来认知世界和探求真理。它表现在艺术上就是统治西方近千年的现实主义传统,强调艺术是对真实世界的模仿和再现,协助人们在更高层次上认识世界。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模仿说定下基调后,绝大多数艺术家便把再现现实人生当作首要创作命题。艺术是生活之镜成了人们描述艺术本质时最常用的比喻。尤其是在经过新古典主义的强化以后,有关模仿说的一些基本假设便成为不正自明的前提,即,外部世界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对它的直接经验也是真实可靠的;世界和经验都是可以传达的,作为中介的语言则是透明中立的;现实的表象可能混沌无序,但其深处一定隐藏着不变的真理和意义;历史和文学的目的都是为帮助我们发掘这些真理和意义,尽管它们各自使用的方式不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区分,文学与历史的差别在于“一个叙述已发生的事,一个描述可能发生的事”。[3](64)文学不像历史那样只是如其所是的针对个别已发生的事,而是根据可然率和必然率来描写更具普遍意义的事,因此它比历史更能显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更高的真实性。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曾写道:“一部优秀的创作犹如一面照路的镜子,从中既可以看见天空的蓝色,也可以看见路上的泥塘。”[4](230)这可以说代表了大多数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创作理想。他们力图使小说成为世界的窗户,透过它人们可以了解整个社会的风俗史。按照艾布拉姆斯分析,“现实主义小说就是要带来这样一种效果,即它再现了生活和社会世界,让普通读者感觉那些人物角色真实存在,那些事件确曾发生。”[5]这就要求作者在题材选取、情节组织和写作技巧等方面尽量做到细致贴切,不能有违背常识、不合逻辑的地方。为此,作者经常要在小说封面或序言里加上一条醒目标识,说明本故事源于某人真实经历等。另外,作者一般不能在书中现身,就像福楼拜曾说的:“(艺术家)不该暴露自己,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中露面一样。……至于泄漏我本人对所造人物的意见,不,不,一千个不!我不承认我有这种权利。”[3](210−215)这就是后来批评者所说的“现实的幻象”,好像作者只是客观报道了真实的事情,一切可由读者自主评判似的。
传统历史写作也遵循着同样的现实主义原则。按照一般理解,历史就是过去发生事件的总和,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根据历史遗留下来的档案材料来梳理和发掘其中的意义,为后人总结经验教训,鉴往知来。特别是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和启蒙主义的大背景下,有关历史发展的进步论和目的论成为指导史学研究的不易法则。人们相信,尽管表面看来杂乱无章,但在琐碎的历史事件内部一定隐藏着某种客观联系,它作为整个客观精神运动的一部分,有着开始、过渡和结局。我们常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其中就暗含着这种历史逻辑。历史学家们声称,他们保证客观地还原了历史的原样,尽管受某些限制他们可能无法洞悉全部规律,但只要做到秉笔直书,事实本身自会说话。史学家所作的就是让事实及其联系和意义通过史家技艺展现于史料之上。19世纪法国著名史学家古朗治的一句话颇具代表性,他说:“请不要为我鼓掌,不是我在向你们讲话,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在讲话。”[6](158)
但与此同时,历史小说的悄然兴起又让人们困惑不已。很多作家以艺术的手法演绎真实历史事件,在给人带来乐趣的同时也让人怀疑其真伪。其中最著名的要算英国小说家司各特了。他相信,自己的历史小说虽不能和历史记载完全相符,但在展示事件意义和历史必然性方面却更胜一筹。他常在小说序言里声明在那些地方对史实作了艺术加工,并在后面详细介绍历史原貌,让读者自己在史实与虚构之间作出选择和评判。还有一些历史小说家则会像写学术论文一样为小说添加注释,使其显得真实严谨,其中最夸张的就是布尔加林(Bulgarin)于1830年创作的《冒名顶替的骗子》(Dimitrii the Impostor),书中竟有218个注释。依靠亚里士多德为他们做的辩护,历史小说家们声称他们要揭示的是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而具体人物和事件不过是辅助工具,为此他们有必要对史籍材料做些挑选,清洗掉那些偶然和琐碎的信息,就像当年拉热奇尼科夫(Lazhechnikov)所说的:“历史小说家不应做数据的奴隶。他必须只忠实于时代的人物和它的推动者,那才是他描写的对象。他的任务不是去搜罗一切乌合之众,去费力复述时代和其推动者的生活的所有联系。那是史学家的事。”[7]
尽管历史小说在18~19世纪取得巨大成功,出现了像司各特、雨果和大仲马这样的杰出作家,但同时代的评论家们却对它反应冷淡。根据波恩鲍姆(E.Bernbaum)的研究,我们现在几乎找不到任何当时著名评论家,比如柯勒律治和海兹利特等,对它作出的评论。[8]原因就在于当时人们还是相信文学和历史之间应该有明确的界限,一个是事实,一个是虚构,“历史小说”这个说法本身似乎就有矛盾。就像当年佐伊勒斯(Zoilus)抱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一样,“我越把它当历史,我越发现诗的影子;而我越拿它当诗,却又越发现历史事实。”[8]虽有如此不满,但人们还是有如下共识,即历史和小说都是对事实的再现,只是再现的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虽然有关二者孰优孰劣的争论从古希腊开始就没停息,但这个共识还是一直被保留下来。不过到了20世纪,它将面临根本挑战。
二、语言、文本与自我指涉
著名现代主义艺术评论家格林伯格(C.Greenberg)曾注意到,随着理性主义和市民社会在17世纪的兴起,西方艺术便开始“倾向于试图通过压倒媒介的力量来实现幻觉的现实主义”。[9](12)当模仿说占据统治地位时,人们的兴趣被集中于艺术品的题材和内容而忽略其形式和表现媒介。比如很少有观众会注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使用了何种绘画材质、罗丹的《思想者》若使用花岗石是否会比青铜有更好表现效果等等。但自从19世纪末印象主义开始,“各门艺术之中都有的一个共同倾向是扩充媒介的表现潜力,不是为了表现思想和观念,而是以更为直接的感受性去表现经验中不可复归的因素。”[9](13)格林伯格称之为“从精神向物质的逃离”,其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在波洛克的《薰衣草之雾:第一号》中,观众再也找不到传统绘画中熟悉的形象、题材和思想,满眼只是质感极强的颜料、花布和线条等。
文学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作家们也逐渐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文学艺术的媒介——语言——上。从象征主义开始,语言日益跳到文学表演的前台,强烈要求读者注意到它的存在。适时而生的索绪尔语言学又为艺术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于是在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推动下,现代主义文学率新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语言学转向。人们开始强调,“艺术就是各种手法的总和”,[10]语言与现实之间也不存在指涉对应关系。语言的运作靠的是符号之间约定俗成的系统差异,而非有赖于外部世界的授权,因此作家再也无需迁就于客观现实。特别是在布莱希特、马尔库塞和罗兰·巴特等先锋理论家的鼓动之下,现代艺术家开始激进地宣称现实主义是一种不健康、不道德的写作,它掩饰了自身的虚构性,妄称它所再现的就是客观现实,这客观上也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当作既定前提保留下来,成为现实体制的粉饰和附庸。它以简单手法将艺术内容加工成易于消化的庸俗制品再提供给急需排解无聊时间的大众,在给他们带来廉价愉悦的同时,也使其日益变得被动麻木,对艺术的感受力也愈加降低。
巴尔特对“可读的(lisible)”与“可写的(scriptible)”文本所作的区分颇具影响力。前者基本上指现实主义作品,它把读者当消费者,同时它对再现现实的要求也暗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逻辑。后者基本指现代主义作品,它把读者当成生产者,在拒绝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也拒绝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前提。作者/读者、生产者/消费者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区分具有某种内在的结构对应关系。巴特认为,“现在文学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把读者从文本的消费者变成生产者。”[11]德里达也区别了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一种试图并梦想对处于自由游戏之外的真理或本原进行解码,……另一种则再也不向本原寻求安慰,而是肯定自由游戏,并试图超越人类和人本主义。”[12]阅读和阐释不再是对文本探本求源,而是要从根本上认识到在文本的迷宫中心只是一个空洞,就像一个洋葱头一样“有许多层构成,里边到头来并没有核心,没有隐私,没有不再简约的本原,唯有无穷层的包膜,其中包含着的只是它本身表层的统一。”[2](466)文本成了能指的海洋,每一个所指都不过是另一个能指而已。这在乔伊斯的《芬尼根的觉醒》中得到最形象的说明。
元小说正是这种新的写作和阅读意识的产物。这种小说的特点被帕特里夏·沃(Patria Waugh)概括为:“对创作想象力的颂扬和对自身再现能力的不确定;对语言、形式和写作行为极度的自我关注;对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无所不在的踌躇;戏仿、游戏或过度故作幼稚的写作风格。”[13](2)与现实主义作家不同,元小说作家不再妄称其作品是对现实的真实再现,而是干脆坦白自己不过是虚构,并对前者声称语言可以指涉、通达现实的信念深表怀疑,同时还将这种怀疑清晰展示给读者。他们打破传统小说的一切惯例,将情节安排、人物塑造和艺术理想这些传统创作语汇全部抛弃,就像费德曼(R.Federman)曾说的:“在未来的小说中,一切对真实与想象、意识与无意识、过去与现在、真实与非真实所作的区分将被废除,……小说的首要目的将是暴露自身的虚构性。”[14]现实主义作家愿做小说中隐身的上帝,元小说作家却更愿直接现身。他时而与小说人物商讨未来情节发展,时而邀请读者一同决定某个人物命运,时而又变成评论家对自己刚刚完成的某段文字评头论足。他将自己在创作中的每张牌都摊开在桌子上让读者一目了然,知道作家也并非如以往设想的那样无所不能、洞察秋毫,也并非对世界和生活有超乎寻常的把握,他们在写作中也无时不和普通人一样犹豫不决、前后矛盾、左顾右盼、自暴自弃……。在如此破除现实主义的幻象的同时,他们还希望一并破除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留恋和容忍。
然而正是在这种文化政治的层面上元小说又表现出了某种悖论。一方面,作为整个现代主义先锋运动的一部分,它把传统现实主义看作是“虚假的、服从的、舒舒服服接受和创造的艺术,是艺术与现存状态的虚伪结合,对压迫条件的美化与粉饰”。[15](97)它渴望通过激进的艺术实验来对抗资本主义庸俗文化,有意让艺术变得艰深晦涩、不落俗套,以此来唤起观众的“新感性”。他们相信:“艺术在文化革命的社会远景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绝非那种政治鼓吹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角色,……激进的变革要求粉碎现实主义的感觉形式,……通过拒绝做自然之镜,摧毁对稳固自然的观念本身,艺术打击了统治制度在心理上和经验上的基础。”[15](66)艺术由再现的现实主义到非再现的现代艺术的发展是一条通往主体解放之路,“通过一种新的感性和感受性使灵与肉获得解放,彻底抛弃支离破碎的经验和残缺不全的感性。”[15](93)但另一方面,对艺术形式的极端关注又使他们的小说变成高度自闭的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被切断。在这里没有政治斗争和阶级压迫,只有无休止的能指游戏。马尔库塞会说单纯艺术形式的革新就足以保证其文化政治上的反叛性,但完全非再现的艺术还是让人怀疑它到底是在批判现实还是在逃避和否认现实。就像梅塞尔(P.Meisel)所宣称的:“语言之外不存在作为真实客体的事物,文学文本之外也不存在自然或真实的生活,批评阐释的背后也没有真实的文本,在人们生产的信息多样性背后也不存在真实的人们或机构。一切都被吞没在无限后撤的文本性之中。”[16]元小说作家们虽然也曾邀请读者参与文本游戏,但后来又明显展示出反沟通主义的倾向,其过快的先锋步伐只能让读者选择放弃。就像《芬尼根的觉醒》这样的作品,除了极少数研究专家外又有多少人真正读过?
三、话语、建构与历史书写
从象征主义一直到元小说,整场现代主义运动可以说就是一场形式对内容的反叛。或许是现实主义统治的时间太长,给文学加载了太多政治、道德和历史的责任,才导致这场对内容的叛离持续近百年。世界、现实和历史成了文学研究和写作中受冷落的灰姑娘,语言、修辞和文本占据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心灵。但是时过境迁,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一场新的转变又开始了,正如米勒(J.H.Miller)所观察到的,“过去几年,文学研究经历了一次突变,……即不像以往那样关注语言文本,而是相应的转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和性别局限、社会背景以及物质基础。”[17]
然而有趣的是,当文学研究由语言转向历史的时候,历史研究却在由历史转向语言。历史学家一般称之为“叙事的转向(the narrative turn)”。许多史学家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考据史实或收集史料,而是去探究语言在历史研究和书写(historiography)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毕竟,“历史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接触得到,我们的历史经验与我们的历史话语是分不开的。”[18](292)叙事和修辞是否像传统史学所辨称的那样只起润色和修饰作用,不会干扰真实内容? 历史抒写和文学书写之间到底有无根本差异,是否如同以往所说的一个是事实、一个是虚构? 史学家是否单凭自己的意愿、信念和良好的职业素养就能保证研究的客观公正? 是否还存在一些他自己根本意识不到的结构规则在左右着他的工作? 这些问题在海登·怀特看来远比去弄清一两个史实更值得讨论。而他的回答更是让传统史学家震惊不已。他说:“每一部历史都首先和首要的是一种言辞制品,是某种特殊类型的语言使用的产物。如果说历史话语所生产的是某种特定知识的话,那就首先必须将其作为一种语言结构进行分析。”[6](6)
如前所述,受黑格尔历史哲学影响,传统历史研究把整体论、因果论、目的论和进步论作为根本原则,把“秉笔直书”和“让事实说话”当作职业信念。但就像卡尔所言:“事实本身要说话,但只有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的独立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6](140)在后现代历史哲学家看来,历史中根本没有什么“事实(fact)”,而只有杂乱无章的“事件(event)”。只有那些被史学家按照一定的逻辑刻意挑选出来并编写进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比如喜剧的、悲剧的、浪漫的或反讽的等,这取决于从哪个角度来看)内,从而被赋予某种意义或重要性的事件才会成为事实。因此“一切过去的‘事件’都是潜在的历史‘事实’,但真正成为‘事实’的只能是那些被挑选出来并得以叙述的。……哪些成为事实就要看历史学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文化语境而定”。[19](75)由此看来,叙事和修辞绝非历史书写中可有可无的配角,而是像盖伊(Peter Gay)所说:“没有分析的历史叙事是琐碎的,没有叙事的历史分析是不完整的。”[20]如果我们直接去阅读最原始的历史文献,比如那些年鉴或宫廷档案,便很难从中发现事件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它们似乎只是一件“接着”一件的发生。但到了经过历史学家修撰的史书里面,事件却变成一件“导致”另一件发生,因果关系使得一切变得一目了然,本来微不足道的某个“事件”突然变成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事实”,它的意义也就被神奇显现了出来。怀特认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些因果和意义本来就隐含在事件之中,是史学家把它们发掘了出来;相反,“任何历史再现都必须被视为语言、思想和想象的建构,而非是对假定存在于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结构的报道。”[21](483)
由此看来,历史与文学之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相隔遥远。前文曾提到,历史小说家常公开承认自己对史实所作的艺术加工,去除了某些不适宜的“杂质”。既然史学家同样也对史料去芜存菁,就像文学家一样虚构了事件的起因、发展和结局,那他为何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呢? 其实,文学和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同根所生,不然我们怎么会有“史诗”呢? 只是随着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兴起,历史日益被划为客观知识的领域,文学的因素便被压制下去,“史学中的讲故事长期以来就被剥夺了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的传统功能,而只起到比较谦逊的解释和说明作用。”[18](345)怀特认为,现在我们重新认识到历史中的文学因素并不是贬低了历史学的地位,而还原历史学对事实的建构本质只是要告诉人们:“历史,作为在时间中出现的现实世界,对于历史学家、诗人及小说家来说,理解它的方式都是相同的,既赋予最初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和神秘的事物以可辨认的形式,……到底世界是真实的或只是想象的,这无关紧要;理解它的方式是相同的。”[18](190)中国自古就有文史不分家之说,想想二十四史中有哪一部不是身兼两任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书写的?所谓的“春秋笔法”又是什么意思?
如此一来,历史小说这种一度不被评论家所待见的文学体裁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相比之下,它甚至比历史文本更直率可取,因为后者一度宣称自己只讲述和再现史实。历史学家对现实主义的承诺掩盖了在历史实践中原始史料是如何变为证据的,以及历史是如何被组合成文本的。按照巴尔特的看法,他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故意隐去叙述主体,把事件按照特定顺序排列,似乎一切都是在按照某种客观必然逻辑在自主展开,“似乎历史在自说自话。”[22]所以伯克霍夫(R.F.Berkerhofer)才会谴责说:“历史现实主义的文字工作是使阐释的结构看起来就是事实的结构。它想使读者产生一种印象,即,事实的结构就是表现的结构,……这种表现和指涉性的融合的目的就是为了传达现实主义的幻觉。”[23](100)清代文学家方苞尝说:“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其行也。”[6](122)既然历史学不可能纯然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那它就不单是一个探讨有关过去知识的领域,更是一个为争夺历史意义解释权的政治角斗场。刘震云在《故乡相处流传》如此描述“我”和袁绍的一段对话,我说:“……历史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袁绍说:“……什么涂抹,还不是想占人家小姑娘便宜!”[24](29)
四、现实主义、元小说与历史书写元小说
国内外有许多研究者都把元小说看作是后现代主义,这种观点颇有不妥。就像詹克斯(C.Jencks)曾说的:“戴维斯(Davis)、古德博格(Goldberger)、福斯特(Foster)、詹姆逊、利奥塔、鲍德里亚、科洛斯(Krauss)、哈桑以及许多其他人所说的‘后’现代主义都不过是‘晚期’现代主义(Late-Modernism)。”[25](49)相比之下,笔者更认同哈琴的观点,即元小说仍属晚期现代主义的范畴,它把后者对自我形式的关注发挥到了无以附加的地步,比如美国的超小说派和法国的新−新小说派。元小说最常见的定义是“关于小说的小说”,[26](25)“它将小说的创作、阅读和批评视角融为一体,提醒读者注意其语言虚构本性,从而与那种对小说人物和情节缺乏自我意识的认同拉开距离。与此同时,它也使读者意识到自己在阅读和参与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的积极角色。”[27]这种小说也常被叫做“自我意识小说(self-conscious novel)”,哈琴则更形象地称之为“自恋的小说(narcissistic novel)”。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少年一样,由于过度迷恋自己的身影而导致死亡,不过在他死后其灵魂却化作美丽的水仙花活了下来。在哈琴看来,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历史书写元小说——正是这死而后生的水仙花。
詹克斯在总结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失败的原因时,认为“部分在于它没有跟使用者进行有效沟通,部分在于它没能跟城市和历史建立有效联系。”[25](33)而这也正好说明晚期现代主义元小说的根本问题,即它对待历史、现实和接受者的态度和方式。对现代主义者来说,历史是他们亟待从中醒来的梦魇,就像《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戴德勒斯一样,他们恨不得能肋生双翅,把可恶的历史远远抛在身后。革新和前卫成为刺激他们不断向前的动力,使其很快便耗尽了几乎所有可能的艺术形式。概念艺术的出现似乎便预示着再无形式花样可以操作。另一方面,在对待现实上,由于他们坚持语言的自我指涉和艺术的非再现性,便只剩下不及物(intransitive)的能指符号可以使用。现实的一切成为唯恐避之不及的病毒,一旦沾染上便会被指责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同谋。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芬尼根的觉醒》了。在这部长达六百页的小说中除了语言无穷尽的自我指涉、自我增殖和自我游戏外,我们找不到任何现实的影子,小说成了谁也难以走出的语言迷宫。最后,这样的元小说也就冷落了读者。如前所述,元小说最初曾以积极的合作意愿标明自身,但到了《芬尼根的觉醒》这样的阶段,读者恐怕是想参与也参与不进去了。难怪人们很快就将它打入冷宫,遗忘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
也正是在这三个方面,历史书写元小说与纯粹的元小说有了明显差异。首先是它对待历史的态度。沃曾指出:“小说的未来将有赖于对传统惯例的转换而非抛弃。……当代激进元小说写作对有关小说本性的教谕是:不管是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教训,都不能被轻易忘记。”[13](148)于是在历史书写元小说这里,我们看到一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风格和技巧都被再度启用,熟悉的形式频频出现。当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乍一面世时,许多读者和评论家都欢呼现实主义的复兴。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它在仿效现实主义传统时也在肆意对其提出质疑,随处可见的元小说痕迹又在提醒人们它既非那种简单再现世界的窗户也非自我指涉的迷宫。但它也没有简单否定二者,而是“既沿袭又妄用小说语言和叙述的传统,借以对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观念和现代主义再现论提出疑问。”[2](24)用巴斯(J.Barth)的话来说,这是在“沿着传统的脉络造反”。[28]而在文丘里(R.Venturi)那里就成了“非传统的运用传统,……利用传统部件和适当引进新的部件组成独特的总体”。[29]
其次是它对待现实的态度。现代主义对待现实是虚无主义的,其登峰造极的自我再现观认为没有什么在场之理,也没有什么外部真实能够验证假设,有的只是语言的自我指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本主义(textualism)或泛语言论(pan-linguisticism)。历史书写元小说却没有这样否认现实,因为它知道:“一部小说绝不仅仅是语言和叙述的一个自律的结构,它还自始至终受到它的语境(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制约。”[2](104)它只是对我们以往声称的现实的给定性、直接性和明晰性以及语言对现实的再现能力提出质疑。现实无论如何也不是抽象语言的织体,但却是物质的语言——话语——的建构。历史书写元小说的作家们之所以要在小说中既树立现实主义的幻象,又着意以清醒的自我意识将之戳破,就是要引导读者去一同反思话语和权力在构造我们的日常现实时所发挥的作用。就这样,“恰恰由于这些元小说的策略武器——初看起来像是把文本牢牢包裹在远离当代现实的封闭世界里——反而使它与那个现实有了更贴近的联系。”[30]
再次是它与读者的关系。沃曾指出:“当作为创造性或实验性的形式或语言被提供给观众时,它们不应该显得如此陌生以至于完全超出了既有的交流模式,否则这种小说便会被视为不值一读而遭到拒绝。其中必须要有某种层面的熟悉度才行。”[13](64)这正是历史书写元小说从晚期现代主义元小说那里得到的启示。它不再一味沉溺于文本的自我迷醉,而是时刻不忘把目光投向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把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语码——不管是主流的还是边缘的、高雅的还是通俗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统统纳入其中,以照顾到各种欣赏口味。批评者可能会说这是变相的剽窃,“从世界文化中取材,向诺大的、充满想象生命的博物馆吸取养料,把里面所藏的历史大杂烩,七拼八凑的炮制成为今天的文化产品。”[31](45)但其辩护者却认为这是在以反讽和戏仿的方式向传统表达敬意,是通过赋予旧形式以新意义来显示其对历史的批判性继承。多倾听来自大众的、地方的和边缘人群的声音,以一个生活的积极参与者的身份融入周边环境,而非像现代主义者那种傲慢的精英主义姿态,把普通读者看作庸俗的、无法自救的芸芸众生。于是,像《芬尼根的觉醒》那样只合少数人口味的阳春白雪少了,而像《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这种雅俗共赏的作品多了。埃科(U.Eco)的这部历史书写元小说自1980年问世至今,在让无数专家学者为之着迷的同时,也已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创造了1600万册的销售奇迹。
五、关于历史的问题学:走进历史还是思考历史?
以历史书写元小说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学虽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也招致各种批评,最主要的就是对其反历史、反现实、因而也就是逃避政治的倾向的谴责。其中詹姆逊最有代表性,他说:“后现代给人一种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一方面我们跟公众历史间的关系越来越少,而另一方面,我们个人对时间的体验也因历史感的消退而有所变化。”[31](433)在他看来,历史书写元小说正体现了后现代文化无法应对历史的危机。它不能反思历史,便只好拿历史的幻象来应付,“它已经不再以重现历史过去为己任;它所能承担的任务,只在于把我们对于过去的观念以及观念化的看法‘再现’出来。”[31](468)他还点名批评了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认为其“精神分裂式的”叙事风格让读者根本无法获得完整的阅读体验,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完全是一堆凌乱不堪的叙事链条,形不成连贯的意义。因此“读者在阅读时实在无法体验到具体的历史境况,主体也实在无法稳然屹立于扎实的历史构成之中。”[31](466)而来自艾伦·伍德(E.Wood)的批评声音更为严厉,他说:“后现代主义者们心里只有语言、文化和论述。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似乎就是说人们及其社会关系完全是由语言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构成的”[32](6),“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们暴露出了他们是群根本不顾历史事实的人。”[32](11)
然而,所有这些指责都是混淆了作为晚期现代主义的元小说与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书写元小说的缘故。就像哈琴所说:“后现代小说并没有切断与历史和世界的关系,它只是凸显并以此来挑战那种有关(语言再现与世界和历史之间)无缝对接的设想的惯例性和未被招认的意识形态,同时要求读者去反思我们籍以对自身再现自我和世界的过程,从而认清我们在自己的特定文化中对经验加以理解并建构秩序的那些方式。”[19](53)对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一切再现的方式——不管是文学的还是历史的——都是深深植根于意识形态的,他们不可避免地与现实社会的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盲目迷信再现的纯洁性或许正是导致受压迫者难以摆脱对自身不利的环境的根本原因。通过质疑历史、现实和再现这些以往被人们想当然的接受的观念,就可以将看似自然的东西去自然化、将看似神秘的东西去神秘化,从而“使那些受压迫的人和被剥削的人通过对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利地位与那些有权力的人的地位的理解而获得力量”。[23](342)
詹姆逊认为历史无论如何也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因为“历史既不是文本也不是叙事”,相反,“历史是痛苦之根源”,[33]它的血腥与凝重只允许我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回漱和总结,去探究历史规律和学习历史经验,从而更好地指导现实。他感慨于后现代主义不断侵蚀着人们日渐淡薄的历史感,所以才呼吁人们要“永远历史化”![34]惟如此才能走出历史的失重状态再度走进历史。但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在人们再度走进历史之前最好先对历史观念本身提出疑问:历史是什么? 是过去的事实还是对事实的话语建构? 是谁出于什么目的而讲述的谁的历史? 历史书写元小说就是这样一股反思历史的力量,一种关于历史观念的问题学。它的信念就像多克特罗所指出的:“一本书可以影响意识——影响人们思考、进而去行动的方式。”[1](200)
[1]Linda Hutcheon.The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theory,fiction [M].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1988.
[2]琳达·哈琴.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M].赵伐,郭昌瑜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4.
[3]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下卷)[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4]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Weyer H.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260.
[6]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Dan Ungurianu.Fact and Fiction in the Romantic Historical Novel [J].Russian Review,1998,57(3):387.
[8]Ernest Bernbaum.The Views of the Great Critics on the Historical Novel [J].PMLA,1926,41(2): 424−441.
[9]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走向更新的拉奥孔[J].世界美术,1991,(4): .
[10]Roman Selden.A reader’s guide to com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31.
[11]Roland Barthes.S/Z[M].Paris: Editions du Seuil,1970:11.
[12]Jacques Derrida.Structure,sign,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C]// Richard Macksey,Eugenio Donato.The Language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1970:264.
[13]Patricia Waugh.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 [M].London: Methuen,1984.
[14]Raymond Federman.Surfiction: fiction now…and tomorrow[M].Chicago: Swallow Press,1975.
[15]马尔库塞.作为现实形式的艺术[C]//王治河.艺术的未来.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6]Gerald Graff.Literature against itself: literary ideas in modern society [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61.
[17]张中载,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596.
[18]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9]Linda Hutcheon.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M].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1989.
[20]Hayden White.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J].Critical Inquiry,1980,7(1): 9.
[21]Hayden White.Historical Pluralism [J].Critical Inquiry,1986,12(3): 483.
[22]Roland Barthes.Discourse of history [J].Comparative Criticism,1981(3):10.
[23]罗伯特·伯克霍夫.超越伟大故事: 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M].邢立军译.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4]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9.
[25]Charles Jencks.Postmodern and late modern: The essential definitions [J].Chicago Review,1986,35: 4.
[26]William Gass.Fictions and figures of life [M].New York: Alfred A.Knopf,1970:25.
[27]Linda Hutcheon.Narcissistic narratice: The metafictional paradox [M].New York: Routledge,1991: vii.
[28]John Barth.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 [C]// Mark Currie.Metafiction.New York: Longman,1995:163.
[29]罗伯特·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M].周卜颐译.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42.
[30]Martin Butler,Jens Gurr.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etafiction:Reading paul auster’s travels in the scriptorium [J].English Studies,2008,89(2):205.
[31]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 三联书社,1997.
[32]艾伦·伍德.导论: 何谓“后现代主义”?[C]// 艾伦·伍德,约翰··福斯特.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3]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芬·贝斯特.后现代理论: 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241.
[34]Frede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2: 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