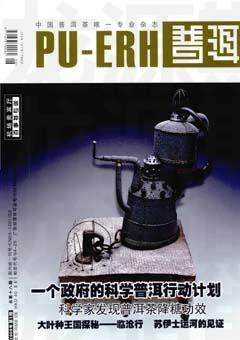宴席厌食症候群
敢于胡乱
遇上不可不去的宴席,准备好拿得出手的红包以外,至少我还要有两手准备:一来,找地方预先铺垫一下,比如来上碗汤汁浓厚的牛肉面;二呢,事毕以后再去填补空白,比如随便找个地方去喝碗米线。
采纳第一手方案,相对比较稳妥,即便宴遇高密度的酒精攻击,多少也还有点底气,不至于出现胃拒现象。这样说或者干脆这样做,并不是故意要对宴席的举办者不恭敬,以目前城里的形势来看,不论事主如何舍得怎样努力,整个宴席中,最提不起兴趣和胃口来的,恐怕就是那一桌子饭菜,处境甚至还不如同在案上的酒水饮料。
一面饥肠辘辘一面心有旁骛味同嚼蜡,这种症状发生的概率,和宴席的规模,往往还成正比。气氛宽松的小型宴席,情况会有所改善,大约是厌食 的“气场”有所收敛,不那么浓烈。如此看来,宴席的表象没有多少变化,仍旧杯盘罗列酒菜堆累,但是骨子里面的精气神,恐怕已经和“吃”渐行渐远,越来越例行差事流水作业。
多年前物质匮乏,宴席却是捞油水吃肉喝酒的好去处,一旦落座,心手相通口齿呼应,不管三七二十一,条条筷子向酒菜,这样的情形,在一些边远山区,目前依然保留完好。前几年跑弥勒山区,晚饭正赶上寨子里的婚宴,还是地席,也就是没有桌椅板凳地上铺垫点松毛酒菜置于上面人员蹲围四周的宴席,风格极其粗犷。上来酒菜也非常粗犷朴素,酒是土瓷大碗装的,菜有七八个,锋芒毕露的一碗扣肉,有肉八片,每片白多红少厚度和拇指相仿。环顾四周,众人面无惧色应对从容,吃气冲天。
而我们这一席城里来的,除了面面相觑以外,不敢有所作为。如此扣肉,如果不是在山里啃上几天的压缩饼干,我也断不敢下手。主人看出问题所在,单独为我们炒了盘大葱瘦肉,立刻峰回路转收到效果,筷子马上密集运作起来:山里的猪肉,滋味的确不同凡响。
坝区的情况,大约介于城里和山区之间,做工比山区精细,材质却一样鲜活。两年前我跑到石屏宝秀吃了台“八碗”,深感滋味非常鲜香难当,通俗的一碗炖排骨都非常耐吃,尤其是那碗清炖乌鱼,让我记忆深刻至今难忘。“八碗”也就是宴席的地点,也相当舒服,专门设了个公共大院落操办,院子周边竹木不少,不时鸟雀也会下来分几颗食。席间客人自由吃喝,主人并不客套敬酒,气氛宽容。后来听说,石屏一带,宝秀的“八碗”水准,排名只靠后不朝前。
据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家里面再是挑三拣四这不吃那不吃的一个,一进幼儿园,连干粑粑都会抢着吃,集体主义的伙食,确实可能激发出旺盛的食欲来。可是一旦坐在城里宴席上,我不但胃口没有带去,恐怕连吃的心情,也抱憾缺席不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