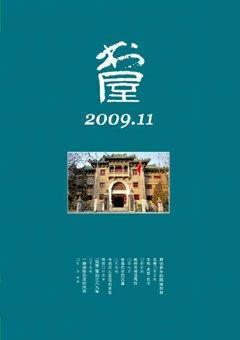胡适梦想进牢狱
房向东
1932年岁末,《东方杂志》社记者采访胡适,问他:1933年的新年即将到来,在新的一年里,先生个人的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胡适的“梦想”竟是进牢狱。他说:我梦想有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可是,我可以读书,可以向外面各图书馆借书进来看,可以把自己的藏书搬一部分进来用。我可以有纸墨笔砚,每天可以做八小时的读书、著述工作。每天有人监督我做一点钟的体操或两点钟的室外手工,如锄地、扫园子、种花、挑水一类的工作。最后强调说:如果我有这样十年或十五年的梦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做出,岂不快哉!
归纳起来,就是有安静的、不受干扰的读书、写作的场所和时间。胡适说过,“宁可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用在这里倒是恰如其分,宁可失去世俗的自由,进到牢狱中,从而获得精神的、心灵的自由。牢狱,竟是胡适之先生“梦想”的世外桃园!
我相信,这是胡适的真心话,是他渴望实现的梦想。这是因为,他一生都被朋友簇拥着,被政治捆绑着,他是场面上的人物,为热闹所苦。
胡适是一个大名人,名人的朋友自然就多。“我的朋友胡适之”是当年场面上的人物不时挂在嘴上的话,大约上个世纪末吧,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了一本回忆胡适的文章,就是用这句话做书名。有人说,胡氏生前真可说是交游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台、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一书中说到这样一件事:一次餐毕,唐德刚从洗手间出来发现胡适失踪,他到店铺内外乱找一通,原来,胡适为了等他,跑进厨房内和一些工友们大聊其天。胡适是连伙夫也谈得来的人。
唐德刚的回忆,我可以加一则佐证,晚年胡适在台湾还结交了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甚至煞有介事地与之探讨英国的君主制和美国的民主制。胡瓞的鼻孔里长了一个瘤,疑是癌症,因治病太贵,治不起,胡适一听,立即握笔疾书,写了一封信给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要袁瓞去治病。信中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其后,袁瓞携函去访高天成院长,虽经检查并非癌症而未加留医,但袁瓞每想起胡博士的这份人情,不禁要流下泪来。袁瓞送给胡适的,通常也只是几个芝麻饼。
胡适的名流朋友,看客耳熟能详,就略去不表了。胡适与伙夫和小贩都能成为朋友,所以,“我的朋友胡适之”遍布天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朋友打扰胡适的时候多,但胡适不甘寂寞,喜欢热闹,也是事实。
1930年12月17日,胡适过四十岁生日。当天,胡适家的门口车水马龙,家内宾客满座,先后到者有陈大齐、陶孟和、余上沅、陈衡哲等百余人。幸好胡宅宽敞,不然如何容纳!虽然很大程度上是朋友来为他捧场,但主要还在于他的呼朋唤友。试想,按中国人的习俗,是五十上寿的,胡适方才四十岁,贺什么寿?如果不是胡适自己的宣布,谁会知道他老人家已经高寿四十?很多人已经指出,胡适是喜欢热闹的,陈翰生与他是北大老同事,一直有交情,就指出胡适喜欢人家捧他,他也喜欢捧人家。这是大抵不错的事实。
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书提到,胡适平均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用在应酬上了。谈得来的朋友,倾心交谈,固然是人生一大乐事,而一些不甚喜欢的朋友,胡适也来者不拒。何炳棣曾在胡适家中住过一阵子,他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某日上午九时左右,何刚要进城,厨子向胡适递上一张名片。胡适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此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当何炳棣走出门时,正听见胡适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有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带说带笑的声音。与不喜欢的人也能打得火热,这是鲁迅绝对做不到的,鲁迅碰到这样的人,是连眼珠子也不转过去。在这一点上,胡适颇有薛宝钗一样的性情或修炼。何炳棣对胡适的这一作派是欣赏的,他说:“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此外,作为“政治票友”,胡适一生中还把很多精力用到了政治上。他留学美国,心中有了一杆美国的秤,用美国的标准秤这个,秤那个,每每不爽,“对执政党的诤言固多,闲话也不少”(唐德刚语),怪论连连,搞得当权者也一样每每不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胡适在政治上惹的风波可谓不少,几乎成了当权者的敌人!这些为读者所熟知。政治上的纠缠,确实费去了他不少时间。他还出任驻美大使等,这是实际地涉足政治了。
胡适一生把不少时间用作应酬和充当“政治票友”,当然是有得有失。如果胡适是一个交际花之类则罢了,如果胡适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也罢了,问题是,他是一个大学问家。交际,固然让他感受到了周遭暖融融的快乐,可是,不能潜心于学问,又让他在享受这种快感的同时或是之后,有了无边无际的烦恼。入世交友的快乐,与出世潜心学问的渴望,成了一对矛盾。胡适多次声称远离政治,不搞政治;可是,不搞政治,政治却来搞他,蒋介石甚至让他参选总统等,就是实例。用唐德刚的话说,他搞的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我想,胡适是快乐时却痛着,不情愿却周旋着。
胡适有一雅号,似乎是叫“半部书先生”,就是说,他的书常常是写了上半部,下半部却难产,直至流产。这罗列起来,有一串哩,比如,他的《白话文学史》是有上部而没有下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只有“半部”,就是他极力提倡的“自传”写作,也只写到四十岁为止,勉强凑成一本单薄的《四十自述》。我印象中胡适还有一些想写而只写了一半的东西。
据称,读者对他的“半部书”既有不满,更有期待,不少人给他写信,希望他丢开其他事情,专心致志,把“下部书”做完。他的朋友汤尔和在他四十岁生日那天,曾在寿联中劝他:“何必与人谈政治,不如为我做文章。”周作人则有奇想,他说,要胡适之把哲学史大纲等写成,非得派一连士兵守住他,不许他下山,不许他会客,不许他谈政治,这样一年两年,哲学史大纲等可能完全写成。可见,大家都希望他集中精力把“下部书”写出来。周作人的派兵把守,与胡适梦想进监狱,已经有异曲同工之妙了——都是有来由的奇想。
对于这些“半成品”,胡适也是心下耿耿,多次表示要将其做完,有的时候似乎真的下了决心要做完,然而,终因种种困扰和自家爱热闹的毛病而留下了残缺之憾。
热闹之后是枯寂,是遗憾,胡适如何不知道呼朋唤友与政治上的表面风光是过眼云烟?晚年,胡适经常说的话是,老鼠之类都是成群结队的,狮子和老虎则独来独往。胡适这样的智者,肯定能感受到热闹中的虚空和孤独。他梦想、渴望有独立的空间,不受外界干扰地做完他的“半部书”,还有其他他想做的一切。
陈独秀与胡适是老朋友,胡适进北大,是陈独秀向蔡元培举荐的。然而,陈、胡后来政见不合,车走车道,马走马路,各行其是,但这一切并不影响他们的私谊。1919年6月29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发表文章,题目叫《研究室与监狱》,全文只有一段话:“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录:‘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的话,是他生命感受的结晶,他自己正是进出如斯之人。胡适引用陈独秀的话,表明了他对这种生存状态的肯定。1920年冬,陈独秀结婚时,请胡适做证婚人。喜庆场合,喜庆之事,胡适却书生气大发,不管三七二十一,作了一幅“未团圆先离别,出监狱入洞房”的对联,这虽然是陈独秀真实生活的写照,也实在大煞风景。后来,章士钊劝他,“我们祝贺人家的新婚,同时隐射人生中一段挫折,怕的是出误解”,也不知胡适是不是听从了。胡适在证婚时是说陈独秀“出监狱入研究室,出研究室入监狱”,这既是陈独秀生活的真实,也是胡适心向往之的境界吧?!陈独秀的经历是实的,胡适的梦想是虚的,这虚的梦想,或是从陈独秀实的际遇中得到启发?也未可知。
“我的朋友”龚明德的书房叫“六场绝缘斋”,据龚明德散文《寂寞书斋》以及他的老朋友、老同学毛翰的文章,“六场”是官场、商场、情场、赛场、赌场、舞场。“六场绝缘”,当然是不当官不与当官的人勾搭、不做生意不与生意人来往、不搞婚外恋、不与人斗智较力等等,是一个近乎愚直的文人的宣言。“六场绝缘”之所,近于牢狱。胡适一生没有进过牢狱,基本上在热闹中度过。因为没有进“牢狱”,文章也浅,书只半部,热闹固然热闹了,遗憾也真是遗憾。
心远地自偏,大隐隐于市。无陈独秀一样的牢狱之灾,是不是要为自己筑一座牢狱,让“六场绝缘”,实在不行,也可考虑请一个连的大兵把守,“宁可不自由”,从而在精神的王国让灵魂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