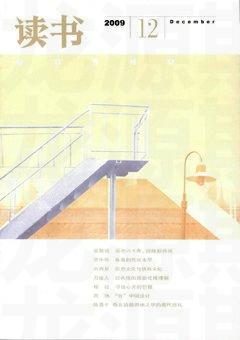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
刘再复
笼统地讲四部古典名著,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上说,其错误是没有分清一个民族的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我想要郑重地说明:四部典籍中的《红楼梦》与《西游记》属原形文化;而《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则属于伪形文化。
原形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原质原汁文化,即其民族的本真本然文化;伪形文化则是指丧失本真的已经变形变性变质的文化。每种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历史风浪颠簸中都可能发生蜕变,考察文化时自然应当正视这一现象。
把文化划分为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首先是受到斯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启迪。此书的第十四章《阿拉伯文化的问题之一:历史的伪形》和第十五章《阿拉伯文化的问题之二:马日的灵魂》,讲的正是文化的变形,也就是文化如何发生“伪形”现象。斯宾格勒在论述阿拉伯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发生“伪形”的原因时,强调的是外因,是外来文化的入侵与影响。《西方的没落》台北中译本的译者陈晓林先生把斯宾格勒的伪形文化思想做了如此概说:
阿拉伯的宗教与文化,一直错综复杂,迷离恍惚,为历史学家所不敢问津。可是斯宾格勒却以两个概念,“历史的伪形”与“洞穴的感受”,一举澄清了阿拉伯文化种种的迷雾。“伪形”本是一个矿物学上的名词,意指:一个矿坑中原有的矿石,已被溶蚀殆尽,只剩下一个空壳,而当地层变化时,另一种矿质流了进来,居于该一壳内,以致此矿的外形与内质,截然不同。所谓“历史的伪形”,即是指在阿拉伯文化尚未成形时,由于古典文明的对外扩张,武力占领,以致整个被古典文明覆压于上,不能正常地发展,故而其文化型态与宗教生命,皆一时被扭曲而扼抑,但古典文明其实已经血尽精枯,只剩下一个空壳,故而一旦阿拉伯文化在重荷之下脱颖而出,其基督教便立刻征服了整个的希腊世界。这同时也完满解释了伊斯兰教,何以能以一个沙漠中的小派,倏忽兴起,如飙风骤雨,席卷了偌大的领域。
二○○一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再版齐世荣等六位先生的中译本。关于“历史的伪形”这一重大概念,此译本则用“历史上的假晶现象”来表述。且看定义“假晶现象”的一段文字:
一种矿石的结晶埋藏在岩层中。罅隙发生了,裂缝出现了,水分渗进去了,结晶慢慢地被冲刷出来了,因而它们顺次只剩下些空洞。随之是震撼山岳的火山爆发;熔化了的物质依次倾泻、凝聚、结晶。但它们不是随意按照自己的特殊形式去进行这一切的。它们必须填满可填的空隙。这样就出现了歪曲的形状,出现了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矛盾的结晶,出现了一种石头呈现另种石头形状的情况。矿物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假晶现象。(齐世荣等:《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二○○一年版,330页)
大陆译本第一版问世于一九六三年,台湾译本问世于一九八五年。尽管从矿物学上说,译为“假晶现象”十分准确,但我得到启迪的则是台译本的“伪形”概念。因为事关重大,我们不妨把陈晓林先生关于“假晶现象”的另一种译法,也录示于下:
在岩层中,本已嵌入了某一矿物的结晶体。当裂缝与罅隙出现时,水流了进来,而结晶体逐渐洗去,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后,只剩下了晶体留下的空壳。然后发生了火山爆发,山层爆炸了,熔岩流了进来,然后以自己的方式僵化及结晶。但这些熔岩,并不能随其自身的特殊形式,而自由地在此结晶,它们必须将就当地的地形,填入那些空间中。故而,出现了扭曲的形态,晶体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形式互相抵触,明明是某一种岩石,却表现了另一种岩石的外观。矿物学家称此现象为“伪形”或“假蜕变”(Pseudomorphosis)。(陈晓林:《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尽管两种译法使用不同的概念,但都没有离开原著的一个基本信息,这就是矿物的晶体在某种外部条件下会发生“假蜕变”现象,即出现歪曲的形状,内部结构与外表形式相矛盾的现象。这种现象无论是称作“假晶”现象也好,“假蜕变”也好,都是原晶体的“伪形”。斯宾格勒把矿物学上的“伪形”现象引申到大文化的考察之中,用这一视角说明世界上多种文化变异现象,的确精彩而令人信服。
斯宾格勒论述的重心是异质文化介入之后使原质文化发生“伪形”。中国文化也经受过异质文化的介入与冲击。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古代佛教文化的传入,一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两次都使中国文化发生某些变形,但是不是已造成“伪形”,则需认真研究后才能下结论。笔者现在可以说的是,第一次虽发生某些变形,但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巨大的同化力,并没有造成伪形。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后演化成中国的禅宗,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存在,并没有导致儒、道这一主流文化的瓦解与彻底变质。至于边陲少数民族文化(如蒙、满文化)的入侵并在政治上获得统治地位,更是被汉文化所同化。第二次异质文化的介入,以“五四”为大规模的起点(之前严复、梁启超诸子的引介为小规模),至今虽有九十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冲击,猛烈空前,但如何估量中国文化的变形变质,还需要时间。
应用原形、伪形文化区分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化,我们会发现一点,不仅是外来异质文化的冲击会产生变动力,而且民族内部的沧桑苦难,尤其是战争的苦难和政治的变动,也会使文化发生伪形。以儒家文化而言,孔子的《论语》属于儒家原形文化,但是经过汉代帝王的“独尊”之后,变成统治阶级思想之后便发生了第一次变形。到了宋明,经过几派大儒的阐释与发现,儒家文化进一步制度化,并发展成许多严酷的行为规范模式,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尽管其中有王阳明伟大心学的出现,但儒家原典(原形)已经发生“伪形”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本意应是批判儒家的伪形,但在打倒孔家店的笼统口号下,有时分清,有时则没有分清。分清时批判了妇女节烈观和二十四孝图等等,反而使儒家原典的本来面目更清楚;分不清时则把孔子揭示的真理一起付之斧钺。今天我们有了原形、伪形区分的意识,倒是可以继续清除儒家伪形部分而重新开掘儒家原典的丰富资源。
如果说《论语》是儒家文化的原形,那么《山海经》则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原形原典。它虽然不是历史(属神话),却是中华民族最本真、最本然的历史。它是中国真正的原形文化,而且是原形的中国英雄文化。《山海经》产生于天地草创之初,其英雄女娲、精卫、夸父、刑天等等,都极单纯,她(他)们均是失败的英雄,但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她们天生不知功利、不知算计、不知功名利禄,只知探险、只知开天辟地、只知造福人类,她们是一些无私的、孤独的、建设性的英雄。她们代表着中华民族最原始的精神气质,她们的所作所为,说明中华民族有一个健康的童年,所做的大梦也是单纯的、美好的、健康的大梦。关于《山海经》所体现的中国原形文化精神,笔者在二○○二年就说过:
《山海经》所凝聚、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精神是什么呢?这里,我必须用非常决断的语言说,它体现的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等等,全是这种精神。天可以补吗?海可以填吗?烈焰可以追赶吗?太阳可以射落吗?都不可能。但远古的英雄却偏偏说:能!偏偏把不可能的事当做可能去争取,去奋斗。这就形成一种大精神。精卫是一只小鸟,它嘴上所噙的树枝那么细微,而沧海却那么深广浩瀚,这是何等巨大的反差,但是坚韧的生命不在乎这种反差。因为他们有一种原始的天真,不知计较成败,不知计较得失,只知一往无前的进取。进取的过程是最重要的,结果倒在其次。生命的精彩全在争取另一可能发生的过程之中。我国古代的神话英雄,不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且其所作所为的一切都是建设性的,都是为人间造福的。要么是为世界填补空缺,要么是为生民创造绿洲,要么是为天下赢得安宁,要么是为百姓治理洪水。这与后来《水浒传》、《三国演义》中那些杀人英雄和玩弄权术阴谋的英雄完全不同。……其实,真正的英雄是救人。而鲁迅先生在《拿破仑与隋那》一文中批评过英雄崇拜的混乱与颠倒。隋那是牛痘疫苗的发明者,救活了无数孩子,而拿破仑则侵略了大半个欧洲,杀了无数人,也把自己的国民当做炮灰,但人们总是不断地赞颂拿破仑而忘记隋那。所以鲁迅批评说:“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是敬佩他的英雄,甚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还在恭维成吉思汗。”“自从有了这种牛痘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虽然有些人大起来还是去给英雄们做炮灰,但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火资格的诸公,却总是在恭维杀人者。”《山海经》中的女娲、精卫、夸父、后羿等都是世界的“修补者”,全是救人英雄。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全是修补世界的创造行为。(参见拙著:《沧桑百感》,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二○○四年版,216—217页)
我们说《红楼梦》是中国的原形文化,不仅因为这部小说一开篇就紧连着《山海经》(故事从女娲补天说起,主人公乃是女娲淘汰的石头),而且因为《红楼梦》中的主人公和他心爱的诸好,以及浸透于全书的精神,都是《山海经》的精神与赤子情怀,都远离《山海经》之后的泥浊世界,特别是巧取豪夺的世界。贾宝玉这个人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用他的天真挑战着一个庞大的泥浊世界,与夸父、精卫一样呆傻。《山海经》所呈现的中国原形文化精神是热爱“人”、造福人的文化精神,是婴儿般的具有质朴内心的精神,《红楼梦》连接、呈现并丰富化了的正是这种精神。《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及唐僧所呈现的也是这种精神。孙悟空与唐僧所形成的心灵结构,是童心和慈悲心融合为一的结构。孙悟空如同不死的刑天,而唐僧则给他以慈悲的规范,只能保护人、不可杀人的规范。唐僧所要造就的英雄是造福人的英雄。这一基本精神与《山海经》完全相通。因此,《西游记》完全属于中国的原形文化。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则不同。以《山海经》为坐标和参照系,我们便可发现这两部小说发生了严重的“伪形”。其英雄已不是建设性的英雄,而是破坏性的英雄,其生命宗旨,不是造福人,而是不断地砍杀人。他们不是要去“补天”,而是自己想成为“天”(《三国演义》)或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无法无天(《水浒传》)。他们已失去《山海经》时代的天真,或把天真变质为粗暴与凶狠(如《水浒传》的李逵与武松),或埋葬全部天真与全部正直,完全走向天真天籁的极端反面,耗尽心术、权术与阴谋(《三国演义》)。《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这两部书有袭用传统的“忠义”理念,但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指向。鲁迅用“三国气”与“水浒气”来描述,实在是太恰当了,两书中只有气,没有灵魂;只有情绪,没有信念;只有政治沙场,没有审美秩序。中国文化的原始精神,走到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便走到了“伪形”的高峰。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一方面是中国英雄文化的伪形,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女性文化的伪形。中国文化大系统中,它的早期有一个女性文化的原形。在此原形中,女性具有创世的崇高地位。这里有上文已提及的《山海经》中的女娲,这个既补天又造人的创世者是女性。这是中国文化原形的伟大象征。在《山海经》中另一女性是填海的精卫,她原是炎帝的女儿,化为精卫鸟之后以填海为自己的目标,是“补天”的对应性行为。这说明中国女性在远古时期地位非凡。而在西周时期,周人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又是神似的偶像。传说她于郊野践巨人足迹怀孕生稷。《诗·大雅·生民》载:“厥初生民,时惟姜。”《史记·周本纪》又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这一传说,与《圣经》中的耶稣诞生的故事相似,耶稣的母亲也是因神迹而受孕,后来成为圣母。可见在周代,中国生民只认女性为真正的创生者。到了战国时期,最早出现的由老子创造的伟大哲学著作《道德经》,更是崇尚柔性、崇尚雌性、崇尚牝性的文化。其中“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以天下之至柔克天下之至刚”的思想,早已为众所知,而“知其雄,守其雌”(第二百八十一章)和“牝常以静胜牡”(牝,雌性动物;牡,雄性动物。参见第六十一章)的“雌性优胜”理念则容易被忽略。老子虽然没有直接谈论妇女,但《道德经》的哲学整体的精神指向是重“水”性、重柔性、重雌性、重牝性则极为明显。这位伟大哲学家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提出牝能胜牡,雌能制强,柔能胜刚,这就为女性能站立于大地而立下根本的哲学基础。这一哲学启迪我们,英雄文化不等于就是雄性文化。真正的英雄必须把握柔与刚、雌与雄、牝与牡的合情合理合势关系,作为男性英雄,更应当充分尊重女性,看到自己往往不如女性。这种雌性优胜的哲学,是中国的原形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真正的精华。而《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则是这种哲学的变形变质。两部经典都在崇尚雄性暴力的同时蔑视、仇视雌性,砍杀和利用女性,从而展示中国文化中最黑暗的一页。
区分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之后,想起了我所崇敬的著名诗人作家聂绀弩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假设。这一假设他多次对我表明。他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是高举《红楼梦》的旗帜就好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点是批判的──批判非人的社会与非人的文化,但是,缺乏正面的旗帜(只好把尼采、易卜生等当旗帜)。其实,《红楼梦》就是产生于中国土地上的关于人的伟大旗帜。他说:“《红楼梦》是人书,人的发现的书,是人从人中发现人的书,是人从非人(不被当做人的人)中发现人的书。”(参见《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碧森的文章:《老幼情深》)聂绀弩这一见解是极其深刻的。“五四”高举人的旗帜,以空前的力度揭露中国标榜仁义道德的旧文化乃是吃人的文化,但是,“五四”的思想先锋忘记了,自己的文化系统中却有一部高举“人”的旗帜的大书,可以作为正面的旗帜和参照系,这就是《红楼梦》。聂绀弩晚年体弱难以走动,背靠小床只读几部古代小说,正如他的“自遣”诗所说的“自笑余生吃遗产,《聊斋》《水浒》又《红楼》”(罗孚:《聂绀弩诗全编》,上海,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113页)。聂绀弩对《红楼梦》和《水浒传》均有许多精辟的、独到的见解,而发现“五四”这场批判“非人”、“吃人”文化、以人为主题的文化大变革却未能把《红楼梦》这部人书作为旗帜的缺陷,更是了不起的极其深刻的见解。这一见解从根本上启发了我。所以我写了《红楼四书》,把他的思想贯彻其中,期待《红楼梦》虽不能成为“五四”旗帜但能成为中国人永远的心灵旗帜。
把《红楼梦》这部人书作为“五四”的正面旗帜,这是聂绀弩的假设。被他的假设所启发,我则做了第二假设: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把孔夫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是把《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五四”作为一个发现人的运动,包括三个层面的发现,即发现人、发现妇女与发现儿童(这是周作人的概说)。而《水浒传》恰恰是不把人当人,无论是官府还是造反者均如此。水浒英雄直接吃人肉的有王英、张青和孙二娘等,更不要说官府间接“吃人”了。至于妇女,无论是《水浒传》还是《三国演义》,她们要么是政治马戏团里的动物(如貂蝉、孙尚香等),要么是被杀戮的对象(如潘金莲、潘巧云、李巧奴等),要么就是哑巴工具和武器(如扈三娘,只是打仗工具,没有语言)。至于儿童,连四岁的无辜小衙内,也被李逵一斧砍成两段。
因此,如果说,《红楼梦》是真正的“人”的文化,那么,《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则是“非人”的文化,是人任人杀戮的文化。“五四”新文化的价值核心,用一公式表述是“人=人”,而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我们则看到“人≠人”的公式,公式里包括集团之外的人不是人,女子不是人,儿童不是人。“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是人的旗帜,而且还突出个人,尊重每一个体生命,是一个很伟大、很了不起的运动,它如果在树立对象与打击对象上做一转换,以曹雪芹取代尼采,即以《红楼梦》作为正面旗帜,而以《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代替孔子而作为主要批判对象,那么,它同样会有震撼,而且能严格地分清中国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原形与伪形,其张扬的核心价值(人——个体价值)和打击的核心观念(人变成非人)都将更为明确而无可争议。
我做这样的假定,并不是想入非非。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展开的前夕,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已和康有为论辩过。在康有为看来,中国风俗人心的颓败,是“不尊孔”之故。陈独秀不同意,写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驳斥他。有意思的是,在驳难的文章中他透露出一个信息,认为风俗人心败坏,莫大于淫杀,就是黄巢、张献忠之辈的淫杀。只是这种淫杀属于过去,在文明社会的今天已不再发生。他这样写道:
康先生与范书曰:“夫同此中国人,昔年风俗人心,何以不坏?今者,风俗人心,何以大坏?盖由尊孔与不尊孔故也。”是直瞽说而已!吾国民德之不隆,乃以比较欧美而言。若以古代风俗人心,善于今日,则妄言也。风俗人心之坏,莫大于淫杀。此二者古今皆不免,而古甚于今。黄巢、张献忠之惨杀,今未闻也。有稍与近似者,亦惟反对新党赞成帝制孔教之汤芗铭、龙济光、张勋、倪嗣冲而已。古之宫廷秽乱,史不绝书。防范之策,至用腐刑。此等惨无人道之事,今日尚有之乎?古之防范妇人,乃至出必蔽面,入不共食;今之朝夕晤对者,未必即乱。古之显人,往往声妓自随,清季公卿,尚公然蓄男宠,今皆无之。溺女蛮风,今亦渐息。此非人心风俗较厚于古乎?(《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版,156页,原载《新青年》二卷四号)
关于世道人心,是今不如昔还是今胜于昔?暂且不论。但陈独秀既然认定“风俗人心之坏,莫大于淫杀”,并认为黄巢、张献忠属于淫杀惨杀之名手(只是“今未闻”),那么,把《水浒传》中的“淫杀”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便不是奇想天开。陈独秀拒绝康有为“尊孔”的妄说可以理解,但走向另一极端把孔子作为风俗人心败坏的总根而放过黄巢、张献忠等,则大可商榷。
聂绀弩“假设”虽然没有使用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的概念,但他作为一个热爱《资本论》(其读本至今还保存在笔者手里)、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实际上是信奉一个民族具有两种文化的观点(列宁提出过两种文化思想)。也就是相信,中国在自己的传统中具有最优秀的文化资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勋不可抹煞,但它对传统文化缺少真伪的分辨却是巨大的缺憾。如果当时的新文化先觉者能用“原形”与“伪形”的视角去观察传统,那么,他们一定会发现,不仅上述的中国的英雄文化和柔性文化发生了“历史的伪形”,而且中国的道德文化也发生严重的伪形。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在先秦时期创造的道德文化是这一文化体系的“原形”,到了宋明,则有一部分发扬了原形,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有一大部分是孔孟伦理学的发扬光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发生“假蜕变”,例如“存天理、灭人欲”观念,“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行为模式等等,就属伪形,至于后来所形成的妇女节烈观(包括立牌坊的反人性的行为)以及“二十四孝图”等愚孝行为语言,更是拙劣的变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衷,打击的其实是伪形的孔子和伪形儒家伦理,并非孔子的原典(《论语》原形),可惜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只能笼统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从而把儒家的原形与伪形一起扫荡。《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及枭雄们不像后来的太平天国革命,公开打击儒生,摧毁孔庙,他们倒是纷纷高举忠义的伦理旗帜,但是,其伦理文化却全面变质,无论是《水浒传》的“聚义”、“忠义”,还是《三国演义》的“结义”,都是“义”文化的伪形。当然,聂绀弩的假设和我的补充假设,只是假设而已。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我的假设也超越了“五四”,而从广阔的角度说明正在进行的(对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双典批判”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