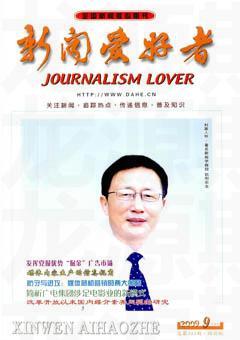从“框架理论”看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框架的转型
程 晟
恩格斯说过:“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由此可见,娱乐是人的天性。我国的电视娱乐节目经历了晚会时期、娱乐时期、竞猜时期、真人秀时期、后选秀时期5个阶段,电视荧屏呈现给我们的娱乐节目转型速度之快、力度之大是毋容置疑的。从框架理论出发,节目理念和形态的框架转型是由社会和大众文化框架以及受众个体框架的转型所共同促成的。这样的转型带给我们的积极意义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不彻底的框架转型也警示我们要为电视娱乐节目的可持续发展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
关于框架理论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1955),由考夫曼(Goffman,1974)将其引入文化社会学,再被引人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定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考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框架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高姆森(Gammson)认为框架定义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显示意义的结构。因而框架研究也被称为“研究媒介与民意关系的新典范”。
框架理论的假设来自两方面:宏观层面的社会学和微观层面的认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从个人层面分析人手,认为框架是个体处理和建构信息的方法。舍瑞夫(sherif)的参照框架理论假定个体的判断和认知不仅受到认知或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且是发生在一个恰当的参照框架下的。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这就说明,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存在着一种个体层面的框架会影响到媒介框架的效果,而这种个体层面框架的构建又源自过去的经验,并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电视娱乐节目通过各种样式所展现给我们不同时期的媒介框架必定是处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技术的社会框架下,受到社会大众文化框架变迁的影响,并且很大程度上由受众这一个体框架的认知作用而发生着框架转型。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和转型
20世纪80年代末,《综艺大观》和《正大综艺》的开播,填补了电视娱乐荧屏中春节联欢晚会“一枝独秀”的境况,“明星+表演”的综艺模式使主持人以绝对领导者的角色调控节目进程,明星嘉宾则是吸引收视率的砝码。1997年,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以其青春、快乐、贴近生活的风格在中国电视娱乐版图中迅速扩张,动作游戏和观众参与是节目的两大新内涵。它带动的明星效应和倡导的快乐理念使电视娱乐节目形态向“明星+游戏+观众参与”转变。1999年,《开心辞典》《幸运52》等博彩类节目的开播实现了将普通观众拉人现场,而明星基本退出舞台的娱乐节目新样态。“观众+答题游戏+巨奖”成为新的电视娱乐节目模式。2004年,《超级女声》《非常6+1》点燃中国真人秀节目的燎原之火,这场包装造星的游戏随着节目的升温达到白热化阶段。当我们还沉醉其中时,“丑小鸭变天鹅”的神话已不再被热捧。《舞林大会》等明星电视真人秀节目又一次将被遗忘的明星们拉上了舞台。“电视模仿秀+电视真人秀”成为这一时期的娱乐节目新模式。2008年,《我爱记歌词》借鉴了国外节目的理念,有机融合了“超女”走红的经验,并做了更具吸引力的本土改良,创造了娱乐节目的收视神话。从南昌唱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唱到全国,从全国唱到莫斯科,《中国红歌会》应运而生。这标志着我们已经迈入了“全民娱乐+本土改良+品牌打造”的娱乐节目多元化时代。
电视娱乐节目框架转型的原因
基于考夫曼“框架源自过去的经验,并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的观点,并从框架“架构”的定义出发,我认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框架转型是社会框架、大众文化框架和受众框架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
社会框架的转型。首先,娱乐节目从属于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文化变迁都有一个现实基础,即当生产力的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与它不相适应时,就会发生变革,它是隐藏在社会历史背后的真正动力,是一切精神力量的最终原因,是动力的动力。娱乐节目转型的20年正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20年。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经济条件有限,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为定位的《正大综艺》满足了受众的好奇心。相对落后的经济状况也使得当时的受众对极致的“美”有一种强烈的向往。因而有着优雅的舞美设计、精湛的表演技艺,以及大牌明星助阵的《综艺大观》受到了追捧。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父母们可以为子女参加选秀活动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这为“超女”的走红奠定了经济基础,另外,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层次化、区域化使传媒的发展出现差异与鸿沟,因而娱乐节目的转型总是率先出现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或是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媒介技术的进步,使得之后一些娱乐节目的实现成为可能。移动电话的普及,为短信参与节目打下了基础;网络的引入,使得节目及时互动成为可能;电视节目制作技术的发展,给受众带来了一种视听娱乐新体验。再次。社会政治框架在这20年也经历了从“集中”向“民主”的转型。“民主意味着每个人不仅享有充分的政治上的公民权,而且每个人一般的文化偏好都潜在地像传统精英们的偏好一样有价值、一样值得尊重并应当实现。”在娱乐文化中,平民大胆地参与正是这种心理的外化,以“超女”为代表的选秀节目的出现使得普通人“受关注”和“受重视”的潜在欲望得到了满足。
大众文化框架的转型。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推进文化走向产业化、市场化,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大众文化自身的娱乐性、广泛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程度。大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复苏与扩展,是在电视真正被视为娱乐手段后,电视文化的繁荣造就了新的娱乐观念,也扩大了人们的娱乐选择,电视是最受欢迎的“娱乐表演家”一
我国的大众文化正从娱乐精英向娱乐平民转变。以往娱乐的主角是专业演员,而受众只是“局外人”。“电视逐渐从对公众的训导和启蒙转向了娱乐和消遣,但这娱乐和消遗却是由原来的精英来承担的,大众仍然将电视看成是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另一个世界。”当普通人成为舞台的主角,他们通过一种“自娱”和“娱人”式的“作秀”,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快乐。“作秀”本身不在于你有多优
秀,而在于你有没有“自我欣赏”的“勇敢”,每一个“超级女声”正是在“想唱就唱”的感召下,“勇敢”地走到镜头前展现自我的。真正的“秀时代”的来临使得一种被动观看式的娱乐模式转向一种主动参与式的娱乐模式。优秀的电视娱乐节目能很快地适应特定的社会状况,同时也承担着沟通电视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桥梁作用。
受众框架的转型。“受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反馈者。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主义盛行,物质生产由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泛化为满足生产的需要,并把它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沉淀到人类的文化思维中,成为人们日常的生活理念,也影响着受众的认知框架。
电视娱乐节目匮乏的时代,受众饥不择食。在电视节目只强调宣传、教育、认知功能的时代,受众娱乐的本能无法得到满足。随着电视娱乐节目竞争愈演愈烈,受众的选择余地逐渐增大,电视娱乐节目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娱乐节目带给受众的首要精神享受必然是“乐”,这也是《快乐大本营》成功的关键。受众压抑的心境、疲惫的工作在游戏精神的激励下可以遗忘,这使得长期处于教化式娱乐节目压制下的受众眼前一亮,有人比喻说:电视娱乐节目提供给了观众一张舒适的“床”,在这张床上,精神负担可以得到缓解,心理压力可以得到释放。随着受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从节目中“找乐”,于是寓教于乐成了下一个时期的主题。首先,轻松愉快的制作方式使这类节目更容易被受众接受。其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重教育、重知识,受众渴望在娱乐中有所收获。而正处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受众,可以从这类节目中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在轻松休闲中得益于个人的发展,这也促使益智类节目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随后兴起的真人秀节目很快取代了益智类节目一统荧幕的局面。此类节目满足受众的窥视欲,通过镜头能直击人性的弱点。“超女”让普通人有可能实现艺术梦想,乃至踏上星途,这是其卖点所在,但是在节目的运作过程中,我们发现“权威对普通人的毒舌”成了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噱头和卖点,活生生的人的梦想被毁灭后的真实的形象的展现使得受众在感同身受的同时具有一种“窥视”的快感。在真人秀节目中,PK既是节目基本的构成环节,也是用来抓住观众的有效手段,它使节目充满了竞争、选择、淘汰的激烈和残酷。这个过程宛若现实社会的缩影: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竞争无处不在。然而真人秀节目的成功之处绝不止于它与现实社会的零距离,更重要的是它让观众领略到了竞争中的情感与知性。
电视娱乐节目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社会框架、大众文化框架以及受众框架的转型势必带来电视娱乐节目的转型,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首先应该肯定这样的转型是一种积极的改良和提升,但是我认为转型力度不够大、范围不够广、内容不够彻底。今天的电视娱乐节目出现的片面追逐商业利润、以收视率论高下、以低俗为卖点、用娱乐来淘金等商业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同时,广大受众对选秀节目产生审美疲劳后,期待欣赏到更具审美价值的娱乐节目。面临这样的困境,路在何方呢,我认为,电视娱乐节目必须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健康道路,进行更全面彻底的框架转型,可以从节目理念和节目形态两方面转型着手。
在节目理念上,实现从浅表娱乐向深层愉悦的框架转变。康德曾经把人的愉快归纳为两类:一是经由感官或者鉴赏获得的“感性的愉快”,二是通过概念或者理念表现出来的“智性的愉快”。如何处理市场领域与公共领域、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的关系,这是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不可回避的问题:2007年,已有娱乐选秀节目被管理部门“叫停”,这提醒我们,必须把对社会责任的考虑变为一种自觉,并认真思考在广告得到市场、制作方得到利益之余,节目给了观众什么、给了社会什么。
在节目形态上,实现从内容拷贝向内容创新的框架转变。在电视娱乐领域,“北欧→美国→日韩→港台→内地某台→各台遍地开花”的模仿路径早已尽人皆知。其实,模仿本身并没有过错,问题是复制过后,节目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核心创造力?是否拥有不可或不易复制的核心内容?创新应该是全面的,包括内容、形式、手段、结构等方面,一档电视娱乐节目的持久生命力依赖于其整体创新能力。精神产品市场也存在优胜劣汰,“以质量求生存”这个工业生产领域的根本法则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上同样适用。
面对社会框架、大众文化框架以及受众框架的转型的碰撞,电视娱乐节目的框架必将面临着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节目理念和形态观念的多元性、开放性和灵活性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电视娱乐节目的主要特点。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代的电视娱乐先锋也势必在两极空间的游走和价值取舍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