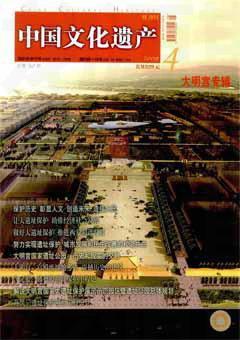万国来朝岁 五服远朝王
周伟洲
有唐一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兴盛时期,长期的政治统一、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对外开放,使唐朝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亚洲乃至当时世界之强国。其国都长安更是繁荣富庶,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呈现出国际大都会的风貌。唐朝京师长安的政治中心,即唐帝国的政治中枢,长时期又在长安的大明宫。作为唐帝国政治中枢的大明宫诸多政治功能中,皇帝接见、宴请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及国外一些民族首领或使臣,是其中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而此,也是唐代对外关系的重要体现。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民族观,将凡是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及国外一些民族、国家,一律视之为臣属于天朝的臣民,称之为“四夷”;其国主、首领或派遣来的使臣至京师,则称之为“朝贡”或“朝献”。这种政治观和制度源于先秦时期的“服事制”,也就是在王畿、诸侯国等华夏族之外,众多的周边民族或国家被名之为“要服”“荒服”,他们要向华夏天子每岁朝贡,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事实上,凡来朝贡、朝献的民族或国家,大部分的确在政治上不同程度附属于当时中国的封建王,他们的朝贡有政治依附关系的性质。但是,也有一部分距中国遥远的外国遣使,他们与当时的中国封建王朝并没有政治上的臣属关系,其朝贡实质上属于一种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性质。唐朝历太宗“贞观之治”和玄宗“开元之治”,国力昌盛,经济繁荣,吸引周边民族及亚洲、欧洲等国纷纷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朝贡即是最正式、最重要的交往之一,也是唐代中外关系的集中体现。《册府元龟》中《外臣部·朝贡》详细记载了各国朝贡的情况。如至京师长安“朝贡”的外国,在今欧洲的有拂菻国(东罗马帝国又称“大秦”),即当时欧洲强国东罗马帝国,从贞观十七年(643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先后6次遣使朝贡,献方物。在今西亚、中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今伊朗等地),与唐关系更为密切,数遣使朝贡。高宗时,波斯渐为大食(阿拉伯)所侵,求援于唐,其王卑路斯逃至长安,后为大食所灭。但其国犹存,“自开元十年(723年)至天宝六载(747年),凡十遣使来朝”。至大历六年(771年)前,仍朝贡不绝。又有原波斯所属陀拔萨惮国(在今里海南岸)也遣使至唐朝贡。此外,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大食国,即阿拉伯帝国,唐代称之为白衣大食(即倭马亚王朝,611年~750年)和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750年~1258年),曾派军助唐平安史之乱。总计文献所见,自永徽二年(651年)起,大食共约有39次遣使入唐。在今中亚地区,唐代有“昭武九姓”诸国,即康国、安国、曹国、米国、石国、何国、火寻国、史国、戊地国,他们与唐朝关系更为密切。据《册府元龟》中《外臣部·朝贡》记载,从贞观八年(634年)至大历七年(772年),九国遣使达60余次,其人人居长安者亦甚众。又居于中亚阿姆河南的吐火罗国、挹怛国(即噘哒)、谢口国、帆延国,居于帕米尔高原的大小勃律国、识匿国、俱密国、护密国、骨咄等国,均时有遣使入唐朝贡。在今南亚地区的印度,唐代以前分裂为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国,后中天竺并其余四国,但不久又分裂。五国先后均有遣使入唐者。印度南的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及印度北边的厨宾国(今克什米尔),西边的尼婆罗国(今尼泊尔)等,也都不时遣使入唐朝贡。在今东南亚地区,唐代称为“南海”的诸国,见于记载的朝贡情况,有邻近唐安南都护府的林邑国(环王国,在今越南中南部)朝贡达35次、真腊国(今柬埔寨等地)16次、诃陵国(闽婆,今印尼爪哇)约13次、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占碑)6次、堕和罗国(在今缅甸那沙林至泰国湄南河下游)4次、盘盘国(在今泰国万伦湾)4次、骠国(今缅甸北部)3次、陋洹国(在今马来半岛北部)3次、丹丹国(在今马来西亚吉兰丹)2次、参半国(在今老挝西北)2次等。此外,在唐朝东面的日本及朝鲜半岛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与唐朝关系更为密切。其中,日本和新罗遣使次数最多。以上大致是属于中外关系范畴的外国朝贡情况,还有被唐朝同样视为“四夷”或荒服的周边民族或政权,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范畴,如东北的靺鞨、契丹、奚、霫、室韦、渤海,北方的铁勒诸族,东、西突厥和薛延陀、回鹘、黠戛斯、沙陀等,西北方的西域高昌、龟兹、焉耆、疏勒、于阗,以及吐谷浑、党项等;西南方的吐蕃、南诏等国。他们在唐代统称为西域胡人或“蕃”,蕃主或其派遣使者赴京师长安朝贡,史籍记载颇多。唐朝沿以前历代传统朝贡体制,设有专门接待朝贡蕃主、使臣的机构——鸿胪寺及尚书省礼部下属之“主客郎中”,并制定了有关朝贡的一系列制度,以及主要国使、蕃主住鸿胪客馆后,怎样迎劳、宴请、接受表章等礼仪。然而,其中最重要、最隆重的仪式,是唐朝皇帝亲自接见和宴请朝贡使臣、蕃主。这是集中体现唐帝国与朝贡诸国或民族政治关系的象征仪式。这种仪式进行的场所,即大明宫内的主殿含元殿,它与殿外的丹凤门一道为举行“外朝”的地方。每岁至元正、冬至,皇帝举行大朝会,各国使臣、蕃王也齐集含元殿,朝觐天子,盛况空前。唐朝诗人张莒Ⅸ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大历十三年吏部试)诗云:“万国来朝岁,千年觐圣君”。诗人崔立之《南至隔仗望含元殿香炉》诗亦云:“千官望长至,万国拜含元”。大诗人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亦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所谓“万国”是形容朝贡各国数量之多,朝贡蕃主及使臣规定“服其国服”,故有“万国衣冠”之说;冕旒,即皇帝所戴冠冕,此处指唐天子。正、冬含元殿大朝会,有诸蕃国各献方物,“列为庭实”;往往还举行宴会,伴以乐舞百戏。郑锡撰《正月一日含元殿观百兽率舞赋》云:“开彤庭执玉帛者万国,发金奏韵箫韶而九成。祥风应律,庆云夹日,华夷会同,车书混一”。除大明宫含元殿外,皇帝有时也在大明宫宣政殿、麟德殿、紫宸殿、延英殿等处,接见或宴请朝贡诸国使臣、蕃王。如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在大明宫芳兰殿(紫兰殿)宴请回纥等铁勒诸部首领;至德元年(756年),肃宗于宣政殿接见回纥叶护等;唐德宗曾在大明宫延英殿接见过南诏王异牟寻之子寻阁劝。贞元十年(794年)三月,德宗于麟德殿接见南诏使,“赐赉甚厚”。唐代诗人宋若宪《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诗云:“端拱承休命,时清荷圣皇。四聪闻受谏,五服远朝王”。诗人卢纶《奉和圣制麟德殿宴百僚》诗也有:“蛮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之句。总之,大明宫作为唐代的政治中枢,由皇帝亲自接见、宴请朝贡诸国使臣、蕃主的大朝会隆
重仪式,表明了大明宫在有唐一代中外关系和与周边民族关系中不可替代的最高地位和作用。唐代外国及周边诸民族政权至唐京师长安的朝贡、朝献,主要是一种政治关系的体现,同时,也具有经济交往的性质和意义。朝贡诸国的朝贡使团往往带有一批“商胡”,沿途及在京师贸易,并向唐朝献其国特产、方物。诸朝贡国在大明宫含元殿等处朝见之时,各献方物。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新乐府》就记述了贞元年间林邑(环王)献犀牛事,诗云:“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一朝得谒大明宫,欢呼拜舞自论功。五年驯养始堪献,六译语言方得通。上嘉人兽俱来远,蛮馆四方犀人苑”。至于文献所记朝贡诸国所献方物就更多。如欧洲拂菻国献赤玻璃、绿金精、底也伽(药物名)、狮子、羚羊等;波斯国所献方物有玛瑙床、火毛绣舞筵、无孔真珠、琥珀、狮子、香药、犀牛、象等。大食国所献方物有狮子、良马、豹、金线织袍、毛锦、宝装玉、洒池瓶、龙脑香等。中亚昭武九姓国献方物中,有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献金桃、银桃、狮子、豹、毛锦、青黛、锁子甲、水晶杯、玛瑙瓶、驼鸟卵、越诺布,安国献豹、马,米国献拓壁舞筵及蝓石,史国献蒲萄酒等。印度五天竺国所贡方物有豹、五色鹦鹉、问日鸟、质汗等药、胡药等,屙宾国献方物有善马、波斯锦舞筵、红盐、黑盐、白戎盐、质汗、千金藤、琉璃、金银等。狮子国贡方物有大珠、钿金、宝璎、象齿、白氍等。泥婆罗国献波棱菜、浑提葱。南海诸国贡方物则有驯象、鍮锁、朝霞布、火珠、犀牛、象牙、珍珠、花氍、沉香、婆律膏、五色鹦鹉、玳瑁、频伽鸟等。唐周边民族和政权朝贡方物则更多,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则贡马、麓牛等牲畜及畜产品,西南吐蕃、南诏多贡金银器皿、犀牛、马等。东北各族则贡名马、丰貂等。唐朝皇帝对上述朝贡蕃主、使臣,往往敕封朝贡国蕃主或使臣以官爵名号,赏赐或回赠大量的金帛、服饰、财物等。《册府元龟》中《外臣部·褒异》有详细记载。如开元十三年(725年)三月“丙午,大食遣其将苏黎等十二人来献方物,并授果毅,赐绯袍银带,放还蕃”;同年七月,“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授折冲,留宿卫”;“开元十五年(272年)二月,罗和异国大城主郎将波斯阿城来朝。赐帛百匹,放还蕃。因遣阿拔赍诏宣慰于佛逝国王。仍赐锦袍钿带及薄寒马一匹”。由此可知,唐代外国和周边民族政权遣使朝贡方物及唐朝回赐金帛,也带有经济贸易的性质,特别是距唐朝较远和未直接或间接管辖的诸外国的朝贡,其贸易的性质更为突出。朝贡方物和回赐金帛,虽然并非中西方经济贸易的主流和主要途径和形式,但是,却是一种在政治关系之下的最高级的贸易形式。它不仅使唐朝从朝贡的各种珍奇、罕见的方物中,扩大了对世界各地的感性认识,丰富了内地稀有的动、植物品种,而且开启和扩大了中外民间经济交流的大门。而这一切大多是在唐京师长安的政治中枢大明宫内进行的,大明宫在中外经济交流、贸易的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无可替代的。在中外文化交往方面,大明宫也有其特有的、突出的作用和地位。中外文化交流,首先应提到的是在外国及周边民族政权朝贡所献方物中。除上述动、植物及各种异香名宝等物品外,还有乐人、幻人、奴婢等具有特殊技艺之人。如“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中亚康国献胡旋女子及豹。史国献胡旋女子及蒲萄酒……七月,史国王阿忽必多遣使献胡旋女子及豹……开元十七年正月,米使献胡旋女子三人及豹、狮子各一”。胡旋女子,即善长胡旋舞的女子。众所周知,唐代开元、天宝年间,胡乐、胡舞大盛于宫庭及民间,胡旋舞即其中最流行的胡舞之一。据载,杨贵妃、安禄山均为胡旋舞之高手。大诗人元稹有题为《胡旋女》诗,内云:“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因此,中亚胡旋舞之所以能盛行于长安等地,与中亚诸国献胡旋女子有关。又如南海诸国的室利佛逝国,开元十二年(724年)七月,曾献杂乐人一部;诃陵国于咸通时期(860~874年)献女乐等。特别是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王子舒难陀来朝贡,“献其国乐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此即著名的“骠国乐”。大诗人白居易有《骠国乐》诗,内云:“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王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以上是中亚、东南亚乐舞通过朝献形式,在大明宫内演绎,而传播于内地的情况。同时,在大明宫朝献时,唐朝宴请外国及周边民族政权首领、使臣,往往也有大型唐乐舞表演。如“开元八年九月,初,正冬朝会。宴见蕃国王。临轩,设乐悬”。上引郑锡撰《正月一日含元殿观百兽率舞赋》亦云:“开彤庭执玉帛者万国,发金奏韵箫韶而九成”。不仅如此,开元二年(714年),玄宗在蓬莱官侧东内苑还设置“内教坊”,教授男乐300人,内有小部音声30人,此即所谓“宫内梨园”之一。因此,大明宫也是中外音乐舞蹈交流的重要场所。同时,上行而下效,外国乐舞很快就传播于民间。在外国及周边民族政权使臣和朝贡所献方物中,还有与外来宗教传播有关的内容。如欧洲的拂菻国景教僧阿罗本于贞观九年(635年)至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后景教(亦称聂斯托里教,基督教的一支)在长安大为流行,建大秦寺。又开元七年(719年)、天宝元年(742年)拂菻国曾遣“大德僧”来朝贡。大德僧,又可译作总主教(Archbishop),即是罗马基督教的主教。南亚印度五天竺国朝献时,其使臣也多有佛教高僧,如开元十七年(729年)六月,“北天竺国三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药”,开元十九年(731年)十月,“中天竺国王伊沙伏磨遣其臣大德僧勃达信来朝,且献方物”等。此“大德僧”,当指佛教高僧。此外,中亚昭武九姓国信奉祆教(拜火教),其使臣到长安大明宫朝献,对祆教在长安的传播也有一定的关系。此外,外国及周边各族首领、使臣及贡献方物中,也带来了各自民族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风俗和一些科学技术,对中国内地也有一些影响。诸如良马的朝献,印度天文历法、药物的传人等。据史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东天竺国三藏大德僧达摩战来献胡药、卑斯比支等及新咒法、梵本杂经论、持国论、占星记梵本诸方”。厨宾国于“开元七年,遣使献天文及秘方奇药”。最后,还值得提及的是大明宫内宣政殿前还设置了门下省、中书省和御史台等机构。在中书省属下设有“四方馆”,通事舍人主之,掌职是接待四方使客。御史台也不时审理在长安居住胡人及其他民族的案件。这说明大明宫内有些机构也有接待和管理外国和周边民族一些事务的职能。综上所述,有唐一代的中外交往中,大明宫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是文化的交流中,均占有十分重要和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说:唐代的中外交往和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中心在长安。而大明宫则是京师长安内的政治中枢及起点;西市是中外经济贸易的中心和起点;而长安西面开远门,则是中外交往和丝绸之路行程的起点。
——明清朝鲜使臣汉诗整理与研究(20BWW023)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