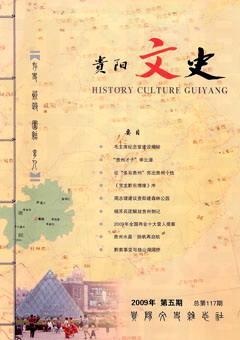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乐无穷
罗 紫
1981年元月,我奉调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工作,任编辑、副主任,1987年元月离休,前后工作只有七年,时间不长,做的工作不多。但我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有兴趣、有感情、印象深刻,体会较多。
省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1959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倡仪开始的,“文革”前,只出了两辑,“文革”后,1979年出了第三辑,1980年出了第四、五、六、七、八辑,我调文史办后,老主任刘毓华同志便交给我编辑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专辑的(第九辑),这是一本革命史专辑,是根据1979年3月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征稿范围的决议编辑出版的。用专辑比较集中的方式编辑出版文史资料选辑,贵州是开始得较早的。当时,省委的党史研究部门尚未成立,党史与文史的分工、界限等诸多问题尚未出现,我们是以政协文史的特色,以三亲资料征集编辑出版革命史的,这也是我到政协后接受的第一个陌生的无现成资料和稿件的一项工作,边学习边摸索,艰难地完成任务。这一辑发表的文章有《红七军在黔东南》《从红军之友到黔北游击队》《忆滇黔边播乐中学特别支部》《忆贵州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记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等篇目。专辑虽还不是很丰满,但我是尽了全力的,收获和体会是很大的。
征集建国前后当地解放史料的工作,贵州也是进行得较早的,《回顾贵州解放》专辑是我接受的第二个任务。共编辑出版四辑,历时三年,共发表史料价值较高的三亲史料160余篇,113万余字,珍贵历史照片多幅。
《回顾贵州解放》专辑是同省军区军史征集办公室紧密合作进行的。由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惠世如、贵阳师范学院院长、原五兵团宣传部长康健、省军区副政委薛光、省政协副主席、原五兵团干部部部长王乐亭等四人向各方发出邀请函,军事方面的稿件由军史办的同志负责征集,地方史料由省政协文史办完成。
贵州解放是解放大西南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全局性伟大战略部署中,占有重要位置。专辑较详尽地回忆记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由湖南插入贵州,切断国民党军之退路,大迂回、大包围,歼灭垂死之敌。贵阳解放后,五兵团兵分两路,十六军北上入川,参加成都战役,配合二野兄弟部队作战,打垮胡宗南,活捉宋希濂,全歼川境诸敌;十七军驰援昆明,粉碎李弥、余程万新八军、二十六军,援救已起义的卢汉部队,胜利完成解放大西南的历史任务。专辑回忆记述了比大军解放更为艰苦复杂的历一年半号称“第二淮海战役”的剿匪斗争。其中既有全貌概述,有重大战役,有创造性的运用铁壁合围、梳篦战术等成功的战例,有种种惊心动魄、抢险激战、曲折斗争的剿匪场面。
专辑还回忆记述了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较顺利、彻底地完成了城市接管、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执行五大任务,实行土地改革,以及国民党军起义的经过,党报的创建,解放初期的妇女运动,中心县和边沿县的解放,地下党、地下武装的配合。青年学生运动迎接解放的种种历史事实和场面。
撰写回忆文章的作者,有参加贵州解放的军政高层领导,有军师团以上的指挥员,也有普通的参谋、干事和文工团员:有白发苍苍的老将军,也有参加战斗和斗争的各级干部、一般工作人员,有当年的县委书记、少数民族干部和民兵战士。
专辑的史料征集工作的过程。是一个艰苦细致的抢救过程,稍晚一步,便会丧失很多不可挽回的珍贵史料。在专辑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组稿编辑往往比文字编辑更为重要。
参加专辑的编辑出版的经验和体会很多。组稿编辑出版工作的核心基础。是很艰苦而又十分细致的。《回顾贵州解放》专辑的组稿工作,领导重视和牵头密切配合支持组稿人员的作用很大,没有领导的亲自出马,几位兵团和地方领导同志的三亲稿件是组不来的。书名的题字也是省军区副政委薛光同志亲自到北京找到潘焱同志才请小平同志签题了书名。有的掌握丰富史料的组稿对象,种种原因,亲自动手撰写有困难,要适时组织人员帮助记录整理或代笔撰写。记得拟请原省委副书记申云浦撰写回忆解放初期的全省的文教工作,云浦同志年老写有困难,需要有人帮助记录整理,推荐了几位乐意为他效力的老部下和阳谷老乡。他都不满意,最后选中曾任原报社总编辑的侯存明同志。完成了一篇很全面很具体史料价值很高的史料。
组稿工作是很艰苦的。往往在上班前后;清晨或夜晚,也无节假日,不论天晴下雨,只要需要立即前往。组稿还需做好充分准备,对组稿对象的基本情况,他掌握的史料的轮廓和时代背景、历史作用等等都要有个基本了解。组稿也是一个耐心的交友过程,反复思想交流,获得信任,才能完成。
印象深刻的是我刚调入文史办,老主任便交给我编辑革命史专辑的任务。没有存稿,只好从组稿开始,边学习边摸索边独立工作。记得当时市政协文史办的朱崇演同志给了我一个线索,1940年至1947年间的地下党的历史尚是一个空白,可向当时小河电机厂离退休支部书记杜守敦同志约稿。他是那个时期临工委的大管家。但说明此人稿件不太好组。看样子。他是碰过钉子的。我做了一些准备,通过友人王觉非的夫人也是小河电机厂的离休干部朱立彬找到了家住青云路一座老楼二楼的杜守敦同志,谈了几次,他虽客气,但仍有距离,似对我有一种警惕性,实际上几次谈话都是对我的考试,反复考察我组稿诚意和处理稿件的态度。每次我都在约定时间骑着我那破单车从北到南爬上他家楼梯吱吱作响的二楼向他约稿。有一次,出门不久,阴云密布,看样子要下大雨。我犹豫片刻,还是下决心骑车快速赶过去,到青云路口,暴雨来临,我奋力骑到他家时,全身湿透,落汤鸡似的,头发和衣服上都滴着水,这次按时赴约,大概对他有点感动,转入组稿正题,他先给了我一篇以故商学礼同志撰写的回忆肖炳坤烈士的遗稿。我读后谈了我的意见。并表示准备发革命史专辑,不一会,他拿出他撰写的一万余字的《临工委纪事之一》,名不虚传,这确是一篇很有气势的高质量的三亲史料,杜老不愧大手笔,文笔也很好。他告诉我,史实已初步展开,发表后在写之二之三。当然,我编入第9辑(革命史专辑),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开会通过,交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9辑已编排出大样,即将付印时,省委原地下党的某秘书叶某突然来到省政协通过省政协机关党组书记、副秘书长指令文史办将这篇稿件撤下来,而又没有说明任何理由。无可挽回的是这段历史仍是一个空白,直到后来公开展览南方局地下活动史料,公布了临工委系列时。仍然是一片空白。之二之三自然也险死腹中了。这也是我的终身遗憾,愧对杜老,充满歉意的一件事。
我在省政协文史办离休后,我对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仍然很有感情、很有兴趣,一直关心支持文史工作,尽可能作些力所能及的奉献。
责任编辑:熊源李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