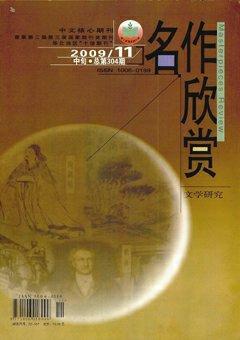遇人不淑与名士风流
关键词:《小团圆》 《今生今世》 名士 现代女性
摘 要:胡兰成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今生今世》披露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段著名的情爱史——张爱玲胡兰成情爱史,时隔四十年之久张爱玲《小团圆》的面世,又给了世人印证、修改乃至颠覆胡兰成之说的可能。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创作主体家世渊源、文学素养、性别意识、婚姻观念的不同,以及传统意识与现代观念的纠葛,导致两部文本对一件情事的不同文学性表述,最终体现为一为一介风流名士的才子佳人梦,一为一位现代女性遇人不淑的婚恋悲剧。
无论我们如何界说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情爱史,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都使这一段或是佳话或是孽缘的恋情成了触目的存在。胡兰成于20世纪60年代即出版了《今生今世》,首次全面披露与张爱玲的情感历程。而张爱玲却对这段情事只字不提,以至于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读者一直以来只能把写成花团锦簇的《今生今世》当成了解、研究张爱玲爱情史的唯一渠道,其中当有很大遗憾与不解。《小团圆》的出版终于让众多张迷们松了口气:却原来张爱玲自己也无法抛开这段情缘,无法不用自己作家的想象在时隔三十年后再次重温旧梦,为主宰自己青春时代甚至是一生命运的一段情感画上一个休止符。
《小团圆》之世俗与《今生今世》之纯情
《小团圆》以女主角盛九莉的视角展示了她的家庭环境、求学生涯和情感历程,与男主角邵之雍的情感纠葛占据了全书大部分篇幅。主人公盛九莉的家世、生活、情感几乎全盘脱胎于作者张爱玲本人,甚至连生日、星座都直接照录。以张氏不可多得的过人颖悟及文学才识,这种直接取材当是刻意为之。
《今生今世》出版于1960年,张爱玲曾得胡兰成赠书,而《小团圆》则开始写于1975年。且从《小团圆》对《今生今世》涉及张胡之恋的各种细节印证、补充或者改写来看,张氏之作似乎颇有一一对证之意。无论从成书时间还是内容上,《小团圆》与《今生今世》的核心情节当为同一件情事的不同文学化表述。在此,笔者不拟对两部著作所涉各种细节的真伪一一求证,而只想以一种文学批评的角度细查二者对张胡之恋这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剖析文本体现出的不同的文学传承、性别意识、婚姻观念、传统意识与现代观念等。
《小团圆》与《今生今世》对男女主角相识的描述基本一致,二者之间大致是由才识互相吸引,共同促成了相知、相爱。胡偶然被张的小说强烈吸引,急欲一睹写下如许美丽文字的佳人真面;张从杂志上看到胡评论的文章,知道胡对自己文章的喜爱,知道胡的入狱及出狱,胡在她心目中俨然是一位因文入狱、恃才不羁的落魄才子。于是二者之间在互相拜访之后迅即开始了热恋。对于张来说,胡的汉奸身份、已婚身份、年长身份(二者相差十四岁)都有一定的障碍,但对胡的才情、聪慧甚至居高临下地位的倾慕,都使大部分成年阶段都处身于二战之中孤岛上海的张难以推却胡的殷勤、热情。
《小团圆》大肆描写恋情之外的世俗琐屑:吃饭、性、金钱等。如对胡一坐经久自己却囿于不会做饭而无法留其晚饭的窘境,对初吻的生理性厌恶、对二人耳鬓厮磨时胡生理反应的敏感——舌头是“软木塞”,下体是“狮子老虎掸苍蝇的尾巴”、“包着绒布的警棍”。对金钱更是不惜笔墨:要还母亲债的誓言,胡提出离婚时需要多少钱的担忧,胡带给她钱的欣慰以及胡逃难之时无法及时资助的困窘等。张爱玲生于贵族之家,本无金钱之虞,但后来逃离父亲的家之后,母亲对她带有功利性的培养让她背负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再加上独立负担自己、卖文为生的艰难生涯,以及同住姑姑的独身与自立,使她形成了一种锱铢必较、互不相欠的金钱习惯和经济头脑。
这些世俗琐屑几乎都难入胡兰成的美文,《今生今世》里丝毫看不到《小团圆》中陌生男女一坐经久的尴尬、社交礼仪的障碍、世俗男女的饮食人生,只有谈文论艺、互诉衷曲、男女相悦的知音流水式唱和。张爱玲的锱铢必较,在《今生今世》也蒙上了一层不食人间烟火般的潇洒与调侃:“我在人情上银钱上,总是人欠欠人,爱玲却是两讫,凡事像刀截的分明,总不拖泥带水。她与姑姑分房而睡,两人锱铢必较。她却也自己知道,还好意思对我说:‘我姑姑说我财迷。说着笑起来,很开心。”张对金钱由衷的忧虑在胡兰成纯情、浪漫的文笔下潇洒为小个性甚至小怪癖。
表面上看来,张处处以食、性、金钱、婚姻等各种世俗琐屑掺杂于情感描述之中,似乎是庸俗甚至是贬低了张胡之恋。事实上,张对胡的情感更纯粹,如小说中表述自己对胡的倾慕时比喻为中世纪骑士对贵妇的无目的的爱,胡的一切在她心目中都值得珍视,甚至于胡留下的烟蒂。她困窘于告诉胡自己要还母亲债,深恐被误会为向他索取钱财。胡给她钱,她很高兴,这种高兴更多是为在外人面前坐实了一家人的名分:“……这才觉得有了借口,不用感到窘了,也可以留他吃晚饭了。”“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也有一种终身有靠的女性传统意识作祟,毕竟“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逻辑已经盛行了几千年。她对胡写下婚书这一形式之举表面上不以为意,事实上一直郑重其事地珍藏在箱底。反倒是似乎纯情得不忍用任何世俗杂质掺杂的胡,婚后两个月即背叛了这段情感。对于胡结识自己之前的滥情,张解释为:“他从前有许多很有情调的小故事,她总以为是他感情没有寄托。”认为“他对女人太博爱,又较富幻想,一来就把人理想化了,所以到处留情。”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他“与小康小姐(即小周)也只能开开玩笑,跟一个十六岁的正经女孩子还能怎样?”这些显然都只是一位陷于爱情中的纯情少女对意中人一厢情愿的理想化想象。
应该说,胡对张才华横溢的倾慕是真实的,对她的爱也并无虚假。只是,他可以把高山流水式知音的美称冠给张,但同样庆幸能与小周为知音。再后来,这一知音美誉又先后给了斯家姨奶奶范秀美,给了寄居日本时的房东妻子一枝,给了后来的妻子佘爱珍……胡兰成一直做着数美并陈的美梦,他对身边每个女性都会纵情夸赞其他爱人:与张爱玲诉说小周的好,又与小周谈论爱玲的好,到了范秀美,又开始谈及张、周二女的好,及至到了日本与佘爱珍,又毫无隐瞒地倾诉众女之好。风花雪月、诗词歌赋、两心相知是胡兰成美文所好,《今生今世》里恣意流荡着一时的小感动、小慰藉,被忽视的却是一桩桩艳遇的另一主角的喜怒哀乐。
在《今生今世》里,胡一味拔高二人的相恋,像放进蒸馏器里过滤过似的,杜绝了一切杂质、尘埃,文笔雅洁,不涉淫秽,重才、重情、有胆识、弃绝欲望,似乎二者俨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生绝配。张的才情、张的家世、张的习惯似乎都成了举世无双的千年偶遇,而他,就邂逅了这么一位红颜。连他后来一而再、再而三明目张胆的背叛,也成了理直气壮:“在我眼里,爱玲就如同我自己,我只能让自己委屈,断不能让旁人委屈”;对张爱玲忍无可忍给他的选择,他毫无同情地辩白“‘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我就这样呆,小周又不在,将来的事的更难期,眼前只有爱玲,我随口答应一声,岂不也罢了?但君子之交,死生不贰,我焉可如此轻薄。”俨然已成了君子坦荡的楷模。
胡之名士风流的传统文化根基与张氏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
中国南方的山山水水滋润了胡兰成的心田,母亲、义母、妻子、侄女一干贤惠女子给了胡兰成无私的爱,民谣、山歌、佛经故事、笔记小说以及如《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乃至目连救母等民间戏文启蒙了胡的文学素养,与他后来系统接受的《诗经》、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传统哲学共同滋养了胡的哲学、文学理念。他的为文乃至立身行事都可见一位中国传统文人的选择与应命,只是胡多吸收其落花流水的潇洒和落魄,少有其坚持与正直。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推许、对自己诸色知己的赞美,以及对此的坦然、当然,撇开其人格低劣乃至近乎变态的自恋不论,这番言行举止、思想情感乃至落笔行文在中国文学里颇有传承,似乎正是一位流落江湖的现代风流名士,其情感历程也恰似中国文学传统中才子佳人故事的再版。
才子佳人故事原型最早即可追溯到《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是体态优美、颇有家世的佳人,君子自是识得诗文、懂得温情、满脑子春梦的才子了。这种故事模式经唐传奇、元杂剧到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逐渐形成一种成熟、完备又难免千篇一律的故事模式。就佳人形象而言,佳人往往是集财、势、才、色、胆识等为一体,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追随。才子则风流倜傥、才识过人,既重视男女相悦之情,又确有辅国才干。在二者之间相识、相爱的过程中,品貌才情是为钟情前提,诗词歌赋是为传情渠道。故事结局大都不脱婚姻事业双丰收、温柔乡功名场二者得兼的大团圆模式。
胡对张的恋情无疑烙下了这一传统爱情故事的俗套,胡看重张的才情不假,但对其曾外祖父是李鸿章、祖母是李鸿章之女、祖父是贵为举人之子名重一时的张佩纶、母亲又是曾留学西洋的现代女性这一显赫家世同样称羡不已。写作《今生今世》之时,胡已成寄居日本的寄人篱下之客。从在汪伪政权中短暂的显赫一时堕入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落魄汉奸路,这种境遇无疑让他倍加感慨。功名之心已注定是一场无法实现的黄粱美梦,与家世显赫、才情卓绝的张爱玲的恋情倒成了一生中可资炫耀的情感资源,于是乎,胡兰成当然要大书特书之了。但出于自命风流的民间文学中三妻四妾“油头小光棍”的风流脾性,他没有不顾事实地把自己写成对张一世钟情的痴情男子,而是在尽可能遵从才子佳人故事模式不涉淫秽、色情的前提下,展现了自己一生中其他几段恋情。
有一个整日缠绵烟榻、抽大烟、娶姨太太的父亲,母亲又是留学西洋、开一代离婚先河的现代女性,这种一半是晚清一半是西洋的家庭不但有新与旧的交锋,也夹杂中西文化的冲突。如斯敏感早慧的张爱玲,很早就对家庭的疏离和骨肉亲情的算计有刻骨体会,从小即学会察言观色,害怕丢别人的脸,成为别人的负担,无论在金钱还是情感上都竭力快刀斩乱麻、两不相讫。如果说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得中国古典文化造诣深厚的父亲之幸,她已经萌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慧根;那么跟随母亲生活的几年以及在香港读书的青年时代,她则系统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教育,以此得以居高临下地鸟瞰曾经生长于斯的旧时大家庭乃至传统中国。对混杂中西、纵贯传统与现代精神的孤岛上海寻常巷陌中的传统家庭、传统婚姻乃至现代女性、两性关系都拉开了距离,用一种陌生化的眼光去阐释、解读。在她的文学创作中,意象、语言、人物、素材几乎都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学,但情节构思、哲理思考、对人性的体察以及一些人物形象则有西方哲学、文学文化做骨架。
作为一位接受过现代教育,熟谙西方现代教育精神和体制的知识女性,张爱玲对女性的传统地位有着现代性醒觉,对那些有一定自我意识但又无法真正自立的女性的现实处境也有切身体会。这种超越年龄的识见在文学创作中结出了累累硕果,诞生了《金锁记》《封锁》等表现两性关系、女性社会地位、女性细腻心理的名篇。在恋爱现实中,这种极强的女性自我意识、敏锐的观察力和极度的敏感,使她即便在沉浸于与胡的男女相悦时也意识到那些抵触的东西。跟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似乎没有丝毫人间烟火味不同,张爱玲时时刻刻要说到现实里去,“欲仙欲死”的爱情背后的种种猜忌,有关金钱、有关饮食、有关离婚事件等种种不快与龃龉,对生理反应近乎自然主义的描述,似乎拼了性命一般要把这段才子佳人两相欢的黄钟大吕拉回到形而下之下里巴人的肉体之欲与琐屑人生。
看《今生今世》与《小团圆》,一件情事的两个版本,颇有日本小说《罗生门》那种各执一说、真相难觅的效果。一个是自命才子风流、一生艳遇无数、邂逅绝世才女的一代佳话,一个却是遇人不淑、无法自我排解的现代女性的婚恋悲剧。男女作者不同的文学素养、个人性情、经历乃至性别立场使得笔下的情缘纠葛除了一定程度的才情相知,大都是将对方当做道具,上演独角戏。一边是陶醉于金童玉女的相知相契,大做数美团圆、和谐相处、共侍一夫的黄粱美梦;另一边却是痛彻心扉的苍凉,无法驱遣情感被玷污、遭背叛的人生噩梦。张的苍凉之感来源于她看透世情的通透,得西方现代教育之幸,古中国的丰厚土壤中生长出了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胡大有中国旧时狎妓士大夫之风,顾盼张致,对一众女性来者不拒,似乎满怀平等之心与博爱之情,骨子里却是三妻四妾的中国传统婚姻,以懂得女心、爱护女性自居,实则从不曾深入如张爱玲般现代女性的内心世界。抛开二者生离死别的社会大背景,单是这样时空相错的心理距离,也注定《今生今世》与《小团圆》只能是一段文学佳话、人生悲剧,这一才子佳人故事到头来不过是又一次落入了痴情女子负心汉这一中国传统文学的俗套,所谓始乱终弃是也。
作者简介:张艳蕊,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是比较文学与英美文学。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小团圆[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版。
[2] 胡兰成.今生今世——我的情感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
[3] 夏世清.色戒[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版。
[4] 谢真元.才子佳人模式及其文化意蕴[J].明清小说研究,1999(4).
[5] 李劲松.才子佳人小说的产生及其结构特点[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5).
(责任编辑:赵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