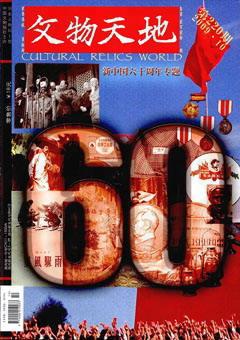杭春晓:如何欣赏一幅中国画
一幅中国画该怎么看?这个话题非常简单,但往往最简单的话题却最有探讨价值。原本在中国语境下根本不应该谈中国画怎么看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习惯了中国的方式,不需要再淡。但问题恰恰在于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和每个人存在的方式、生活经历和视觉体验都与印象中如何看中国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今天在中国有一种情绪已经消逝了——乡愁。民国时期的齐白石等一大批民国画家,在落款上经常有一个“客京华”,意思是在北京生活却并不以此为根,始终是以一种客人的方式生活在北京。再看古代文人,他们离开家乡只有一种情况,就是通过科举外出为官,所谓的出仕。当出仕离开乡土以后,我们注意到古代文人在各种各样的笔记、诗歌中,一旦在外地不顺心的时候,就会产生“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情绪。翻开历代文人写的作品,会看到大量的思归的主题。可是在今天这样的紧张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很少会把自己当作这个城市的客人,也就没有了一种诗的主体——所谓故乡。为什么今天没有思乡?因为今天的乡土缺少了一个余英时先生所讲的半社会结构,也即过去由文人构成的半社会组织结构。在那种结构中,游离于外的人之所以会思乡,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而且真实存在的文人交流的文化环境。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承载着士族社会中很多责任,比如说编写家谱、教育下一代,同时他们可以通过外出为官身份转变而衔接于庙堂。这样一种结构构成了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阶层,这个阶层成为了中国的文化生态。因此古代的文人回到故乡,一定会有一个与他具有共同价值属性的社会史化阶层。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乡土社会阶层,才有一个社会结构承载的文化传承。但是今天,20世纪的中国文化以激进取代渐进、温和的发展,使得这种文化环境消失了。这种激进有两次,一次是“五四”时期完成的,带有形而上的讨论性质;一次是形而下的非常务实的文化传统的推翻,在“文革”中完成了。
今天当我们回到故乡的时候,会发现乡土无处可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状态下,在面对一幅中国画时,我们没有那种发自本性的、理所当然的底气来说“我天然可以读懂一幅中国画”。暂且不谈一幅中国画承载的文人理想方式,这在今天的社会中不存在。单就笔墨材料而言,如果连毛笔都不会拿,甚至看不出来毛笔笔痕的差异性的时候,我们很难说自己能够真正欣赏一幅中国画。这样的一种审美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渐行渐远,我们习惯的视觉方式是20世纪西学东进的成果,是一种西方的视觉体验。达芬奇画鸡蛋,把鸡蛋画得很像,是一种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形成的求真观念和再现观念,而绝对不是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方式中的一种图像经验。
应该说,这种真实再现性的图像视觉体验,是我们判断很多绘画的一个潜移默化、不由自主就会使用的方法,甚至在判断中国画的时候,特别是判断一幅工笔画,习惯看这个东西画得像不像,再加上“五四”以后所谓新传统的呈现,把写意与西方造型结构方式结合。于是,今天我们看一幅画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东西画得真像。徐悲鸿在中国画中实现了一种再现性,但是他并不代表中国画的审美方式和欣赏方式。今天我们延着徐悲鸿的方式来看中国画的时候,已经是拿着类似看《蒙娜丽莎》的方式来看中国画,这是古典西方画对我们的视觉培养。
还有一类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在行为方式上有一种腾挪转换,在这种腾挪转换中呈现出一种当代的观念感,是一种恰当的观感表达、观念表达、思想艺术形态的表达。这种观念表达、思想意识形态的表达,有一部分是可以生活化的;有一部分可以涉足政治化,就是所谓的批判精神;有一部分可以哲学化,可以具有反思精神;还有一部分可以荒诞化,有戏谑的诉求。于是在当代艺术中,我们看到大量各种各样的载体,承载了各种各样的观念的描述。其中对于精英知识分子来说,最有价值的是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所以,在当代艺术的审美判断和批评的语境中,经常会有当代艺术如果丧失批判性就丧失其价值的观点。
以上所讲的是人们习惯的视觉体验中的几种标准,可以总结如下:建立于再现性的空间呈现方式;建立于表达这个客观物体的细节描绘;建立于描绘一个真实场景的色彩观与氛围。这是我们脑海中的一种习惯。比如我们今天看徐悲鸿的某些画时,也许它没有这样的色彩观,但是“马”的形非常好、非常真实,我们就认为这幅画好。另外我们还习惯的一种判断方式,是当代艺术借助某一类载体的应用,表达一种恰当的思想观念。对于这种思想观念的恰当阐释是欣赏当代艺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方式,如果这种阐释中具有一个社会宏观性的、当下性的价值反省与批判精神的话,我们会认为它更具价值。其实,在我们的脑海中,无非就是这些尺度与手段影响着我们对绘画的判断。这是在正式谈如何理解一幅中国画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的:我们今天观看一幅绘画作品时通常所采用的一些思维方式。
中国画的意象审美
在谈欣赏中国画的问题之前,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怎样欣赏一幅中国画,绝对不是单一和僵化的标准,而是伴随着中国画审美方式的历史形成而逐渐形成的,并非有一个人突然拍着脑袋说要这样欣赏中国画。通过呈现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形成一个中国画的语境,才能欣赏中国画。
怎样欣赏一幅中国画?答案很简单,就是回到中国画的语境中。怎样回到中国画的语境中?就是回到中国画的历史发展来看。现在呈现给我们的中国画,最早的在彩陶上就有了。彩陶上有图案性质的绘画,也有《鹳鸟石斧图》这样的具有图像性质的画。元代画家赵孟頫的夫人管夫人善画竹,就是取其倒影来描绘竹的。当一个实际的物体通过光形成一个侧面的最有特征的投影,我们就取得这样的形,这就是中国人特殊的造型观。
洛阳朱村汉墓中的一幅墓室壁画描绘了墓主人餐饮的过程。在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画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空间形成的方式。
在这幅壁画中的棚子下面,有男女墓主人坐在案子前准备吃饭,边上有男女侍从。我们首先看到的空间,绝对不是一种再珊陛空间,而是选择每个物象最能暗示或是交代这个物象的一个平面特征,然后把这些平面特征重新组合起来,构成一幅画面的所谓主观空间,于是这个主观空间就具有了意象表达的能力。
以此方式来看画中人物的比例关系,我们发现,男主人是跪坐的,他边上的侍从却和他一样高,但从侍从们的形态来看,绝对不是侏儒或童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处理方法,是因为中国画在表述空间的时候不是以再现性来诉求的,而是以表达意义形态为诉求。为了使形态更具有特征的描绘性,可以忽略掉所谓的尺度感。中国画是具有一定写实性的,中国画的头与身的比例在画工中都有流传,但是为了仪态的表述,可以省略掉真实。这有点类似于当代艺术
的意义,但是中国画的意象具有抒情性,而不是具有批判、反省、哲学化的观念性,是一种轻松的抒情化的东西。为了使这种轻松抒情意象成立,它可以破坏真实的存在,可以不考虑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于是,画家在取形时,关注侍从和男主人的时候是站在不同角度的,每个视觉取一个特征,然后用线条的疏密、空间组合以及结构关系使画面重新平衡起来。这种疏密的组合构成了绘画自身的一个具有节奏感的空间,进而形成了中国画自身的一种抒情性的空间。元明清绘画讲究浓淡,也等同于这种形态的疏密浓淡的节奏关系。中国画因为一种自身语言的结构关系,解决了在不同角度下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画面感受,使它重新在绘画自身的语言和空间中获得了统一。这是中国画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不是再现于真实性,而是再现于真实背后的一个主观的绘画空间的一种自我的、内在的结构关系。
由此而言,徐悲鸿的作品,如果以中国画的品格来定,充其量只能是神品,甚至只是能品而已,绝没有到“妙逸之品”这样的高境界。妙、逸的高级是语言的抒情,不是那种真实再现的自然,这是中国画的特质。
中国画对于形的描绘是具有特征性的夸张描绘,而不是对局部细节的描绘。中国画取形一般都会形成模式和样式化,有人说都画得差不多,我们欣赏什么呢?欣赏的是对这种模式化、样式化形成过程中语言的描绘。同样是模式化、样式化,恰当地把这个形态特征呈现出来的经过和语言的呈现方式,才是审美的根本。
在中国画中,每一根线就是一个空间,画得好的中国画的线条不是僵化的平面,一根线暗示出了三维转换上的所有变化。有些中国画在画某些形态特征时,行笔的过程中稍微顿了一下,就交代了一个很丰富的空间。但是不会看的人会认为这只是一个线条。其实,线条的变化是非常细腻和讲究的。
看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人们会被一个绚丽、浪漫、想象的世界所吸引,这一个世界不在于它是否具有真实性,而在于它是否具有主观的抒情性,能否营造出一个神异世界。所以空间和形态在这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描绘出这样的一个意象。所以中国画是以意象审美为中心的,而不是再现性或观念性。
看细部和局部
魏晋时期的绘画有一种神仙气,隋唐的绘画有一种富贵气,宋以后的绘画则有一种荒寒气。我们看顾恺之的画,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气。到了唐代,宣扬一种士族华美的审美,我们从《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中看到的是一种华美的宫廷审美。
而到了宋代,义人时代开始崛起。宋代文人清淡为尚的审美方式呈现以后,迅速占据了文化话语权。而北宋时期文人的代表苏东坡、米芾则将这种方式引入绘画,确定了中国画以语言为中心的审美方式。一种是苏东坡戏笔的疗式,另外一种是米氏云山。
宋代文人画不再关注所谓的物象特征,更多的是关注笔墨自身的转变与变化。米友仁的《云山图》不在于它画的山像山,树像树,而是在于它的局部。把带有水分的毛笔在纸上流出既有毛涩又有苍润的痕迹,成为了中国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审美感受。中国画这种笔触的质地,干燥中具有湿润,湿润中具有干涩,所以毛、涩、苍、润所形成的清淡的语言体系是中国画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特征。
一笔下去,既有毛涩又有苍润,这是一种极度的笔墨技巧。重墨处的墨是极度透气的,是好几遍积攒而成的,每一遍形成的叠加关系形成了墨色的微妙的层次和丰富的变化,强调了这种清淡的节奏。这就是运笔,要靠一个画家对笔性、墨性、水性、纸性的功力。一幅好的中国画在强调一个形态特征时,他的笔墨运行果断、肯定,毫不迟疑,但是又恰当地表现出了形态特征。
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是中国山水画中不可回避的一幅图。“鹊”是指赵孟頫的朋友周密老家济南的鹊山,“华”是指华山。鹊山和华山相距数十里,不可能人一幅画。这就涉及到中国画的一个审美特质,即文人画超世俗、超功利的审美体验。
从后世来看,《鹊华秋色图》的左侧江渚处理得过于平行,黄公望的江渚绝对不会是这么平行的,一个圆包包的山和尖山放在一起未必就美。但在“鹊华秋色图》中,物象本身的组合并不重要,它的美在于与客观无关的笔墨。画笔变化的幅度极其微妙,可能有笔尖,然后有笔沟,再到笔锋,再到笔肚带一点擦笔,这种极其微妙的运笔变化形成了《鹊华秋色图》重要的审美基础。怎样欣赏一幅中国画?就是天天看好的中国画,看好的中国画的细部和局部,看的时间长了,慢慢就学会怎样看中国画了。
《富春山居图》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和《鹊华秋色图》有类似的运笔特征和笔墨感觉,苍、湿、毛、枯、润都统一在一个清淡的、超验的、非世俗审美中呈现出来。
徐渭的《墨葡萄》,绝对不是画一个所谓的葡萄,而是借助笔痕的节奏、笔墨的关系,形成一个所谓的“墨点不多泪点多的抒情”。徐渭一生比较苦涩,一直有一种怀才不遇的凄美。他与其是在画墨葡萄,不如说在画葡萄老了,无人采摘,所谓明珠无人赏识,正是徐渭的自我的期许。这一幅画不是描绘真实世界,而是描绘一个非世俗的精神世界,是郁郁不得志的一种抒情,才华无人可赏识的落寞与凄美。
20世纪,黄宾虹是文人画笔墨集大成者。我们看他的画根本没有什么真实的物形可谈,所有的东西都是乌塌塌的一团,但是却形成了每一笔微妙的变化,又和《鹊华秋色图》《富春山居图》这种伟大的山水画的传统有着连结。所以看黄宾虹的画就是看满目华章,满目华章不是在于一个真实的物像的华章,而是在于里面细腻的笔触的华章。这个华章一方面有笔触自身的质量和运笔等等的体验,同时还有整个笔墨形成过程中的一种整幅的节奏和气息。所以,即使他眼睛瞎了,画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具有这种特质,因为他根本不在意真实的所谓的世界。
回到中国画的语境
看中国画一定要回到中国画的语境中,而不是在西方画的语境。第一,中国画的空间是一种主观抒情性的空间,营造的是一种文人的、主观的非真实世界的空间。第二,中国画对物像的描述是多侧面、平面的、特征化的形态描绘。第三,中国画的语言更多靠浓淡枯涩等等一系列的语言对比形成的绘画语言自身的节奏,来统一多元化的取景和多元化的笔墨关系、表现方式。除了这三点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元、明、清以后,中国画进入到一个以语言自身审美为中心的审美方式,以局部的笔触审美取代了整体审美,而局部的笔触审美中的清、淡、毛、涩、枯、润,统一到了以淡为宗、以清洁为高尚的文人的理想,是一种超世俗的诗性的审美和抒情方式,这种诗性的抒情不带有功利性和世俗经验的审美体验,共同构建了中国画华美的篇章。
怎样欣赏一幅中国画?绝对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只有通过欣赏更多的中国画的优点和中国画所谓的价值,有了充分而细腻的体验之后,才能真正理解它。也就是说,通过这些体验,真真切切地构建了一些非常细节的关于中国画的审美体验,用这种审美体验才能欣赏一幅中国画,而不是用我们习惯的20世纪积累的图象经验来看中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