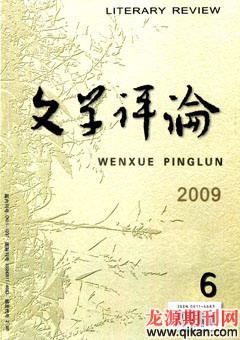论曹禺戏剧的深层剧场性取向
刘家思
内容提要:曹禺戏剧的剧场性已经融入了主题意蕴的深层。他以现代性的艺术视野来对人进行探寻,对人性进行解剖,对人类终极追求进行审问,将道德的张扬与背叛,对现实人生的哀悯与怨愤悖谬性联系在一起,这就在主题上形成了复调交响的艺术张力,在戏剧的深层预设上生成了强烈的剧场性。一是在表现爱的甜蜜与痛苦、追求与逃匿、理想与失望的复调交响中深层预设剧场的呼唤力,二是在生的坚韧与死的决然的现代性审视中蕴藉剧场的感染力;三是在反抗与复仇的二律背反的艺术表现中生成剧场的向心力;四是在表现世俗人生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谋求剧场的裹挟力;五是在表现家的归宿与心的期待、家的桎酷与心的漂泊的世俗人生状态的深层灌注剧场的感应力。
于是,曹禺的剧场性是戏剧的主要特征,它是剧作家预设的戏剧对受众的交流域与磁力场,也就是戏剧对受众所拥有的现场审美裹棼力和剧场感知度的规定性,是一种支配受众的艺术强度。因此,剧场性强,艺术效果就好,戏剧的生命力就强。一个优秀的戏剧家,不仅会在表层上追求剧场性,而且会在戏剧的深层预设着剧场性。曹禺的戏剧之所以吸引人,关键一点就是预设了强烈的剧场性,这不仅表现在艺术技巧等表层因素上,而且融入了戏剧主题意蕴的深层。曹禺的戏剧始终是“写人”。他总是立足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审视现实人生,尤其注视着中国家族社会中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对人类许多问题进行了独特而深入的思考,但他最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的基本问题,焦点是人活着的价值及其终极取向问题,进而传达的是对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问题的观照。这是他“深刻观察体味人生的结果”。于是,曹禺戏剧的主题总体上便形成了道德评判与现实关怀的复调交织的模式。从《雷雨》到《王昭君》,爱与恨、生与死、善与恶、强与弱、理想与现实、苦难与救赎、压迫与反抗、残害与复仇、牺牲与索取、奉献与期望、道德与情感、婚姻与家庭、归宿与飘零、个体与国家等融现实性主题和现代性指向始终交响着。在这里,个体道德的审视与人生状态的关切交相统一,对传统道德既悖逆又张扬,对现实人生既同情又批判。中国是一个道统的家族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规范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主体诉求,“道德”的行为受人推崇,“不道德”的行为也受人关注,戏剧表现这种内容,这就有了共同的关注点。曹禺的戏剧以现代性的艺术视野来对人进行探寻,对人性进行解剖,对人类终极追求进行审问,将道德的张扬与背叛,对现实人生的哀悯与怨愤悖谬性联系在一起,这就在主题上形成了复调交响的艺术张力,在戏剧的深层预设上生成了强烈的剧场性,拥有了广阔的接受空间。
一
爱的甜蜜与痛苦,爱的追求与逃匿,爱的理想与失望,是曹禺戏剧中主题意蕴复调交响的一个突出表现。在这里,主体的疯狂与坚毅,情感的炙热与挣扎,心灵的迷茫与困惑,通常都是因爱而起,以爱而终。爱腈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人们格外关注的人生话题,人们始终不能忘怀。这个多昧豆,总是让人期待,让人遐想,既让人们义无反顾,也让人们饮恨终生。它包容着丰富的社会蕴含与人性深层的密码,储存着艺术的原始张力。正是这样,爱情成为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中不断置换变形却又言说不尽的母题。纵观曹禺的创作,他突出表现情爱或曰性爱的人性张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曹禺的笔下,男女情事都是超现实的畸形的悲剧性的。无论是《雷雨》《日出》《原野》还是《北京人》《家》《王昭君》,其中的爱情故事都是非常态的。他总是通过这种故事来对特定历史时期的道德形态进行观照,对现实人生表现了一种人性化的道德理想。在这里,爱与恨交织,对生命的自卫与对伦理的颠覆杂糅统一在起来,将传统道德的撕裂、坚守与现代人性的呵护和高扬做了理想化的主体性探索。这样,曹禺戏剧便有了深厚的人陛基础,在深层预设了剧场的呼唤力。
如果将曹禺戏剧中的爱情故事按照人物对爱情的态度简单归类的话,可以将它概括为三种主要形态,即占有式、奉献式和理想式。所谓占有式,是指情爱中的男女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追求为内核,以自我需要和自我占有为出发点的畸形形态,基本表现就是不择手段地要使爱情对象从属于自己。例如蘩漪对周萍的爱是疯狂的、曾思懿对曾文清的爱是尖刻的,但都是一种自主性的爱,是以自我为主导的。所谓奉献式,就是指爱情的一方或双方都为对方着想,不考虑自身利益的情状,具有超现实的特点。例如鲁侍萍对周朴园的爱、愫方对曾文清的爱、鸣风对觉慧的爱,都是自由的恋爱,但都是利他的,奉献性的,是以自我牺牲为代价的。所谓理想式,是指情爱中的一方和双方都是怀着一种预设的期待进入爱河,但都经受着或平庸或磨难或痛苦的情感折磨或失望的情状,具有浪漫情调。陈白露对诗人的爱是充满着浪漫遐想的,婉儿屈从冯乐山也是充满着期待的,王昭君远嫁匈奴更是充满着期待的。对这些爱情故事,曹禺并不是从传统的道德理念来显明自己的主张的,而是以一种悖谬性的眼光来审视和表现,往往让爱与恨交织在一起,甚至不置“是非”。所以,在一部戏剧中往往既有对传统的张扬,也有对传统的否定,既有对现代的体认,又有对现代的存疑。正是这样,扩张了戏剧接受的适应度,拓展了戏剧的接受空间,剧场性无形中得到了强化。
在曹禺笔下,占有式的爱是自私的,与道德疏离甚至是对立的,但是又合情合理,既让人不认可,又使人可以理解。奉献式的爱显示了人物高尚的道德感,但在自身的道德之中又夹杂着这样那样的不尽然,所以他们让人敬重但又会使人有所保留。《雷雨》中蘩漪自主占有式的爱是受到作者袒护的。她爱周萍既不应有更多的非议,但人们往往又很难不非议。她爱周萍,也恨周萍。她对周萍由爱而恨,由爱而仇,及至全力报复,令人胆颤心惊,难以认同。但她这样做只是处于对自身生命的护卫,对本能的爱的追求,并不是要将周萍推向绝境。戏剧最后周萍与四凤的兄妹身份暴露,一切都难以收拾的时候,她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悲剧的结局:“(笑向萍,悔恨地),萍,我万想不到是一是这样,萍——”这种歉疚与悔恨是诚挚的真心的。正是这样,她在看完周冲的尸体之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心理自责:“(狂笑)冲儿,你该死,该死!你有了这样的母亲,你该死!”听到周萍自杀的枪声狂喊着跑过去。应该说,她爱周萍是自私的疯狂的。这种疯狂的爱将中国社会乱伦的事件推向了极致,然而谁又能过多地去责备蘩漪的不是呢!侍萍的爱无疑是利他的、奉献的,然而也是爱与恨交织在一起的,她对周家将她赶出周公馆,周朴园屈从父母抛弃她,是怀着怨恨的。但对周朴园是爱的,旧情难忘的。当他们重逢之后,鲁侍萍一再去试探周朴园,充分展示了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真实。可以说,人们敬佩侍萍的人格,然而谁又能举起他的双手对她的爱情选择表示赞赏呢!《北京人》中的曾思懿的爱是尖刻的、自私的,然而谁又能不理解她的行为呢!而愫方的爱是利他的奉献的,然而谁又能赞赏她的行为呢?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矛盾和撕裂感,是因为曹禺的创作并不是
要简单地进行一种道德评判,而是要写人,是要对人性的复杂面进行检视,要探索人在现实的社会与生活中的可怜境状。因为是人,就绝对不是纯然的,人陛的本色就是复杂的,丰富的深邃的甚至神秘的。是人,他的七情六欲就不以别人为转移。在逼窄的生存空间中,人的选择往往是无奈的。在曹禺这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对道德伦理的关怀紧密结合在一起。当道德、伦理与个体生命发生冲突时,曹禺主体心灵中始终看重的是个体生命。这样,曹禺戏剧的二律背反的复调就形成了。正是这种是与不是所产生的二律背反形成了很大的接受空间,感应着不同受众的审美心灵,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道德水平去把握其中的是与不是。因此,曹禺的戏剧便产生了强烈的剧场性。
二
对人的生与死的评判是人类一种常见的行为表现。人对生与死的态度和方式总是显示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这种人的命运的两极,原本是生命的自然旅程所成,但在文学作品中往往融注着个体的主体性抉择或主体性表现。曹禺在戏剧中,始终将生存与命运作为艺术表现的重心。一方面,他“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展示天地间的残忍与人物命运的悲惨,描写他们对于生的挣扎与坚韧,张扬人的生存权-另一方面,他又始终流着眼泪赞美那些驮负人间酸辛的伟大的孤独的心灵,憎恨冥顽不灵的自命为人的动物,展示一种对于死的决然和生的苟且的理想抉择。从《雷雨》开始,一直到《王昭君》,曹禺始终高扬人的尊严,护卫主体人格。这里既有对传统道德的传扬,也有对它的撕裂;既表现了对现实人生中主体命运的关注,也表现了对理想人生的期待。于是,在人物的生命旅程中突出对于生的坚韧与对于死的决然始终是贯穿曹禺戏剧的思想主线。这种二律背反式的艺术表现,彰显了道德评判与现实关怀的复调性。正是这样。它形成了给人关注与品评的基点,蕴藉着一种吸引人、感染人的艺术力量,强化了剧场性。
生的坚韧是一种主体生存意志的艺术表现。在人的意志力中,求生存的意志力是一种基本的意志,它以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生命追求体现出来。曹禺在戏剧中以近乎夸张的艺术描写进行了深刻的表现。他展示了三种生存的方式:生的自尊、生的苟且和生的卑劣,对人的尊严与道德进行了理性审视。显示了现实人生的复杂性。生的自尊是指主体的人在人生旅程中保持着自身的主体性和人格尊严,如鲁侍萍、鲁大海、陈白露、小东西、金子、仇虎等等-生的苟且是指主体的人在人生旅程中没有主体意识、忽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如鲁贵、翠喜、黄省三、王福升、李石清、白傻子等等都是这样的,生的卑劣是指主体的人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中虽然主体性异常强,但人格尊严忽存忽失,一切以利害得失为转移,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自然,他赞赏的是前者,否定的是生的苟且和卑劣,但更重要的是,曹禺通过张扬人坚韧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意志来营造剧场感应力。鲁侍萍是曹禺对于生的坚韧有力表现,展示了一种道德美:为了孩子,她活下来了,这怎能不对受众产生一种感召力呢?翠喜是苟且偷生的。虽然她染有在那地狱下生活的各种坏习惯,而且认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并以她的公平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一分钱买一分货”,
自然是令人可怜和同情的,但她“为着家里那一群老小,她必需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挨下去”,这种自我牺牲,怎能不使人感动呢?她那颗金子一样的心,那副好心肠,那种对那更无告者的温暖的关心,怎能不令人敬佩呢?这样的人生状态怎能不裹挟剧场受众的心魂呢!
曹禺往往将人物的生命追求给予高度的变形,写出了人生的一种幻境,产生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力,产生了强烈的剧场性。如果说鲁贵在剧中基于他的“三点主义”面临困境所爆发出的“骂街”式行为,黄省三为养活一家大小而求生不能由此绝望地发出的血泪控诉、李石清因为他一心往上爬的不顺和艰难导致内心积聚强烈的不平和愤怒,都是一种明确的求生意志主导的话,那么《王昭君》中的孙美人几十年来每天沉醉在等待的幸福和美貌的满足则是生命意识被异化的结果,是主体性被封建伦理道德损害后的变态性表现。但他们都显示了一种生存的坚韧品格,产生了强烈的剧场性张力,诱惑着受众。孙美人的描写是神来之笔,更具代表性。她是为陪衬王昭君而设计的,但生成剧场性十分突出。她母亲生她的时候,梦见日头扑在怀里,才生下她来,后来选进了后宫,被皇帝召见和宠幸就成为她的生命追求。于是,她天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等待皇帝宣召。这种愿望支撑了她的一生。鹦鹉的一句“皇帝驾到,美人接驾!”她就信以为真,让王昭君为她仔仔细细打扮,准备接驾;当她听到黄门的一句“去见皇帝”,竟让她欢喜过度,气绝生亡。可怜的是,皇帝是要叫她去皇陵陪先帝。然而,这种艺术变形,在深刻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罪恶的同时生成了迷人的剧场性!如果没有她,不仅王昭君的行动失去了依据,而且很难出戏。
生与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期望生惧怕死,是人类一种普遍的心态,对人的死亡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哀怜与同情。这样,戏剧人物的死亡,不管怎么死的,总是能给受众形成一种揪心撕肺的心灵抽动。曹禺深深地把握了受众的这种心理。对于死亡,他描写了死的决然和无奈两种形态。死的决然,是指人物的死不仅是其自身意愿的结果,而且是出于对生命的追求与期待,是对自身尊严与灵魂的护卫的结果。小东西、陈白露、仇虎、鸣凤的死都是决然的。死的无奈,指人物的死虽然是自身的选择,但并不是人物自愿的,是外在环境逼迫下不得不死。周萍、四凤、周冲、潘月亭、焦大星、瑞珏、梅、宛儿和高老太爷的死都是无奈的。不管是决然的死还是无奈的死,作为一种肉体生命的终结。曹禺并没有明显地表现一种主观性的祈求,只是将它作为生命的一个阶段和一种选择,赋予其剧场性意义。他总是善于将人物死亡的过程予以强化,在舞台上直接呈现出来,渲染一种强烈的悲剧气氛,形成一种强烈的艺术效应。陈白露、小东西、仇虎、鸣凤、瑞珏等人的死,都在一种过程性和直观展示中冲击着受众的心灵。小东西自杀的情景是这样描写的:她由左屋鞍着鞋出来,手里拿着一根麻绳,仿佛瞧见什么似地在方桌前睁着大眼,点点头。她失了魂一般走到两个门的前面。一一关好,锁上。她抖擞起来,鼓起勇气到了左边小门停住。她移一把椅子,站在上面,将麻绳拴在门框上,成一个小套。又走下来。呆呆地走,……走,走了两步。忽然她停住,低声地咽出两个字:“唉,爸爸!”然后向那麻绳套跪下,深深地磕了三个头,立起。叹一口气,爬上椅子,将头颈伸进套里,把椅子踢倒,一个可怜的小生命便悬在那门框下面。这时,外面有荒凉的叫卖声,木梆声,以及男人淫荡的曲调和女人隐泣的声音。小东西挂在那里,烛影晃晃照着她的脚,毂着的鞋悄然落下一只,屋里没有一个人。于是,舞台渐暗。这样的场面刺激性很强,对受众的操纵力大,产生的艺术力量也是强大的,长久的。曹禺说:“要写那些叫人揪心的,使人不能忘却的人物,……不这样,就不会有生命力,就
保留不下去。”小东西的命运是悲惨的,令人揪心的。有情感的人看了这一幕都会刻骨铭心,情感心理、情绪心灵都会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影响,剧场性便得到了渲染和强化。
三
反抗与复仇是曹禺戏剧中的一个基本的主题。这是人类社会一种基本的人生形式,是人类生存原型的现代性置换。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时时与恶劣的环境展开斗争以获得个体的生存,延续人类的历史。曹禺的戏剧充分地展示了人物对残酷和黑暗的环境的坚决斗争,对邪恶势力的激烈反抗,对残害生命者的强力复仇。然而,曹禺的描写又不仅仅是展示一种原始的蛮性冲动。而是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审视人类自身的本能力量与文明道德之间的冲突,展现人类主体生存的一种难以自主的尴尬境况。他既展示反抗与报复的不可阻止性,又展示它的盲动性与无果性,消解了主体行为的价值与意义。于是,曹禺戏剧的主题又呈现出一种二律背反的复调效果。这就拓展了戏剧的接受空间,能适应不同层次的审美主体的接受心理,满足不同层次的审美诉求。一方面,从感性层面上,对于戏剧人物的反抗与复仇是支持的,首肯的;另一方面,从理性层面上,又会对行为的方式与效果进行深度的审视,生成新的认识。这样,不同的受众都可以得到审美的满足,形成了戏剧的向心力。
在创作中,曹禺展示了三种反抗与复仇的基本形态,即蘩漪所代表的对压迫人性者的反抗,仇虎所代表的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抗,勾践所代表的是对强权的反抗。无论哪一种形式都是紧张激烈的,撼人心魄的。曹禺说《雷雨》最初出现模糊的构思时使他感到兴奋的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残忍”和“冷酷”。这都集中在周朴园身上,是他的冷酷和专制,蛮横和压抑。他所谓的体面、秩序、圆满,都是用他的残忍性建立的!在周公馆只有黑暗和残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平等,享受不到人生的快乐和幸福。蘩漪、周萍、周冲、鲁大海等等都遭受着沉重的折磨。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之下,他们愤怒了,他们坚决地反抗着自己不幸的命运,剧烈地争执着,疯狂地报复着。无论是周萍的逃亡还是蘩漪对周萍的阻止,以及鲁大海的带领工人罢工,都是对恶劣环境的反抗,是对自身命运的抗争。他们都是对合乎人性的生活的追求,是对践踏人性者的复仇。终于,“圆满”的周公馆被“雷雨”炸破了,“体面”背后的丑恶终于暴露了。仇虎一家遭受焦阎王灭绝人性的残害,有着深仇大恨。他越狱逃回农村,直向焦家逼来,他要报仇,可罪大恶极的焦阎王已经去世。最后,他杀了焦大星,带走了花金子,报了深仇大恨。《原野》演绎的是被压迫者对封建统治者残酷的阶级压迫的复仇与斗争的神话。勾践集国恨家仇于一身。吴王夫差率军入侵越国,掳走越王勾践,使之侍吴三年,受尽屈辱。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发奋图强,越国最后战胜了吴国,驱逐了入侵之敌,使夫差自刎而死,报了深仇大恨。《胆剑篇》讲述的是弱小国家对强权的反抗与复仇的故事。这些反抗复仇的行动都有其充分的理由,都能获得受众情感上的支持与认同,反抗斗争的坚决与报复的激烈紧张,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规定性戏剧场势,能抓住受众的心理,获得一种强烈的戏剧效果。因为“对于复仇,人类有一种本能的意识与自觉,对于复仇的行为又有着一种观念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追认,即道德与正义的认同。人们总是在情感心理上将复仇当作一种正义的道德的行为,是善的表现。这就形成了复仇母题的人性基础。在这种人性基础支配下,对于戏剧人物的复仇行为,古往今来,人们都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心理上都是赞赏的。……当人们看到那种复仇的戏剧行为时,其心理却仍然是畅快的”。显然,它潜藏的剧场性是很强的。
尤其是,曹禺在描写这种反抗复仇的戏剧行动时,又注入了一种现代性眼光。虽然曹禺在情感上对这种行为持赞赏态度,但是他并不盲目张扬这种人生的举动,显示了主体内在的矛盾性和道德维持的背反性。正是这样,他使剧作跳过了普通的受众层面而进入到精英接受的层面,形成了更广泛的审美空间,产生出一种剧场性张力。曹禺前期的剧作,戏剧人物的反抗行动是坚决的,复仇是不妥协的,斗争的过程是很激烈的,但是呈现的结果则是两败俱伤,这就消解了反抗与复仇的意义,显示了主体价值取向与评价指向的疏离与分裂。《雷雨》中,周萍没有逃出去,反而自杀了,蘩漪的精神全垮了,还赔上了儿子的性命,周朴园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日出》中激烈斗争的潘月亭与李石清没有一个赢家,李石清既被开除了,还失去了儿子,潘月亭赶走了李石清,却被金八弄得破产自杀了,《原野》也是这样,焦家落得断子绝孙,仇虎也因承受不住强烈的自责而自杀了。《北京人》中曾思懿是矛盾的中心,她视愫方为情敌,可最后她与愫方谁也没有得到曾文清。这种症候传达出曹禺主体思想的活跃与忧郁,反映了曹禺独特的个性心理。客观说,曹禺在解放前对封建旧秩序存在着既憎恨又爱恋的复杂心理,虽然他心理渴望反抗和摧毁旧秩序,但这又有着一种焦虑和恐惧,这就使他对于反抗与复仇的主体价值不时失去了稳定的评判尺度,从而折射出妥协、调和与中庸思想的根基。当然,这更显示了一种现代性的思想视野。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表明,相互理解,互相尊重,和平共处,是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向,相互争斗,冤冤相报,只会给对方和自己带来更大的损伤与痛苦,给发展带来不利。曹禺戏剧的这种症候显示了这种思想特征,形成了道德的超越性与思想的张力。这种思想实际上从他一开始走向戏剧创作道路时就已经出现端倪。1929年他为纪念南开学校25周年执笔改译的Ⅸ争强》中,傲悍的董事长安敦一和顽抗的技师经过一番倔强的偏颇的搏斗,前者失去了董事长一职,后者失去了妻子,终于明白“我们两个都是受伤的人”,最后握手言和,相互敬服。曹禺认为“这段描写的确是这篇悲剧最庄严的地方。”这正是曹禺的一种理想与期待。这种现代性的视点所潜存的思想张力,使受众能够由反抗复仇的表层的激烈紧张感染中进入到深层的思想探寻之中去。由此,普通的受众可以被表层的感性的美质感染,精英型的受众可以透过表层的审美特征去做更加深层的思索,于是,作品就拥有了广泛的适应性,剧场效果优化了。
四
曹禺戏剧的一个重要的母题就是表现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对立。在曹禺的笔下,人物总是沿着主体自我的理想设定实施戏剧动作的,但是他们的理想与期待都被现实残忍地扼杀了。理想是人生的一种航标,是个体生命追求的目标,是一种生活的意义所在。它是芸芸众生抵御人生苦难的去痛剂,是一种个体精神的抚慰剂,是个体生存的精神源力。主体的人总是怀着一种梦、一种理想追求着去经历和消释着人生的酸甜苦辣,不时地将自己置于各种理想目标之下坚韧地在人生道路上行进着。但是,理想与现实总是发生着矛盾,并普遍存在于世俗人生中。现实不仅荆棘丛生,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而且非常残忍,这根无情的大棒常常将人们的理想打得粉碎。人们通常所说遭受人生挫折,实际上就是理想被现实阻隔或击破。正是这样,
曹禺戏剧的这种主题指向总是能够调动起受众的情绪情感,使他们产生感同身受的审美共鸣,对人物的命运产生深切的同情和关注。于是,戏剧也就拥有了抓住受众的场势。
从《雷雨》到《王昭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总是或强或弱,或浅或深,或隐或明地灌注着。在一定意义上说,曹禺戏剧展示的是一曲曲理想毁灭的悲歌。在曹禺笔下,人物面临的现实常与他们的人生理想相距甚远,现实的残酷性常常将人物推向理想不能实现的郁闷和困苦之中。《雷雨》的悲剧就源自一种理想的丧失。舞台上直接展示理想与现实剧烈冲突的是周冲。“他藏在理想的堡垒里。他有许多憧憬,对社会,对家庭,以至于对爱情。”但“理想如一串一串的肥皂泡,荡漾在他的眼前,一根现实的铁针便轻轻地逐个点破。理想破灭时,生命也自然化成空影”。其实,周朴园,蘩漪又何尝不是理想被毁灭的人呢?周朴园年轻时候留学德国,西方的民主自由博爱思想使他怀有一腔社会理想,可是回国后封建势力凶残地将他的理想打破了,他向封建势力投降了,并且现实化了;蘩漪说被他骗了,当初也是怀着一腔爱情的理想与之结合的,可后来周朴园渐渐地使她变成了一个石头样的人,所以她要反抗,要报复,因此周公馆就被炸翻了,《雷雨》的悲剧就发生了。如果说《雷雨》是一曲理想的悲歌,那么《日出》、《原野》又何尝不是在幻梦似的理想支撑下完成的悲剧呢?花金子一心向往到金子铺满地的好地方去,自然无需赘言。陈白露的悲剧实际上也是理想破灭的悲剧。曹禺说“她追求着她的理想生活,这就是她的生命支撑。”她爱生活,羡慕着自由,在女孩儿时代便期望幻梦似的爱情,憧憬着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为了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幸福,她追求着。但是,残酷的现实总是一次次将她的努力击垮,始终摆脱不了平庸和痛苦。最后,为着自己的理想与自尊,她自杀了,对残酷的现实进行最坚决的反抗与控诉。可以说,《日出》展示的就是陈白露理想破灭之后苦苦抗争的悲凉的主体心曲。曹禺指出:“应当清楚地指导观众怎样同情的方向,更紧紧地抓住他们的同情,死也不要放松。然而我们却万不可采用死胡同式的主题(dead alleythcme)。换句话说,我们所用的人物,以及所编排的故事,不可以写得使观众无法同情起。”曹禺剧作展示普通人的人生理想在残酷的现实中毁灭,显然能够引起普通受众的同情和共鸣,形成一种裹挟力。
在曹禺的戏剧中,人物的理想往往与救赎的行动、牺牲的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救赎的行动包括救人救己救民族国家等不同的意义层次,从周冲到陈白露到丁大夫到觉慧到愫方到王昭君,都显示了这一点。周冲爱上四凤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把自己的教育经费分一半给她上学,希望她现在受教育。“如果她不愿意嫁我,我仍然是尊重她,帮助她。”后来他父亲的一句话就将他所有的梦打破了。陈白露的理想则是救人救己紧密关联。她做过慈善游艺会的主办委员,说服潘月亭给家里有老小一大堆的李石清涨工资,不顾一切地去营救悲惨的小东西,总希望通过这些救人的行动找到救出自己的办法。但是,营救小东西失败了,她的理想遭受到致命的打击,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的进程。在曹禺的戏剧中,这种对个体、对国家的救赎,都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的。《家》不仅处处都显示了觉慧的斗争精神和反抗行动,而且始终显示了他对年轻一代的启发、引导与解救,但觉慧却被冯乐山等封建势力残酷地投进了监狱。《蜕变》中的丁大夫怀着为这个伟大的民族效死的崇高理想与精神,捐弃了一个名医在上海舒适的生活,兴奋地投入了伤兵医院。她竭力提高伤兵医院的救护和治疗知识,减少伤兵同志不必要的痛苦。但是,医院当局腐败不堪,中饱私囊,托办和克扣药品,霸占医院设备,使她的理想难以实现,为此她非常愤怒,常常一个人哭泣。王昭君是将救自己与救国家统一起来的艺术形象。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她所作出的牺牲和担负的风险比曹禺笔下的任何人都要大。曹禺说:“王昭君这个人是一个英雄。”的确,她是—个为国为民排忧解难的巾帼英雄和女中豪杰,是一个救世英雄。救赎是一种道德善行,一种义举。中国是一个重视道德评价的社会,人们崇尚道德,敬仰道德品行好的人,尤其对为人作自我牺牲的人更是钦敬不已,而且总是希望“好心人有好报”,如果好心人没有得到好报,往往会因这种结局不善而痛惜。曹禺戏剧中,人物在救赎中遭受的劫难或救赎的失败,无疑会引起受众的更多的同情,这就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吸引力。
五
在曹禺的戏剧中,家的期待与心的飘零这一主题反复被表现着。从《雷雨》开始,家庭对人生的影响这个主题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家的存在还是家的失去,都对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家成为人们主体生活的窒碍;另一方面,家的失去又导致人生的灾难。于是,家的归宿与心的期待、家的桎酷与心的漂泊就使曹禺戏剧对世俗人生的道德审视与现代性关怀统一在一起。这既彰显了曹禺对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深层的焦虑,又显示了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表现了对人类生存发展的终极追问和探索。个中原因,一方面是与曹禺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对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和人事非常了解有关,另一方面是与他的剧场性追求有关。
通常,人们总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考察家,将它看作社会的组织结构,看作社会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然而,家不是为社会而存在的,它是因个体而存在的。家是人生最普通的形式,既是个体生命的依附和归宿,是心灵的港湾,是社会巨浪的避风港和消化站,也是个体生命为之奋斗、尽责的对象,所谓“成家立业”就是个体生命对家的价值认同和观念性解读。因此,家在人的生命长途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家的有无反映出人生的基本状况,家的意识成为一种最基本的人生观念。于是,家就成为中国这个有着深厚家族文化背景的国度中广大民众心理的聚焦点。曹禺戏剧深刻地描写了社会转型和动荡时期家对人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宽泛的接受视域,对各类受众不同审美层次的接受欲望与基点都具有了适应性,能够获得更广泛的审美关注,增强受众审美接受的关切度和感应力,这显然强化了剧场性。
揭示旧家庭对人的束缚与桎酷是曹禺戏剧重要的意蕴指向。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家族社会,家族统治是封建统治的根基,家是封建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基本单位。在这里,家长是最高统治者,代表统治阶级实施统治。所以,封建社会的罪恶在封建家庭中得到了充分展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封建旧家庭的罪恶就暴露得更加鲜明。五四运动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先驱者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民主、自由、博爱、天赋人权、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所以封建家族制度受到“五四”作家的猛烈批判,封建旧家庭的罪恶被深刻地揭露出来。曹禺继承了“五四”文学传统,将自己的笔深入到封建旧家庭的内部,展示封建旧家庭对人的生命与心灵的损害,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庭束缚人的思想,桎酷人的主体性,扼杀人性,漠视人权,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