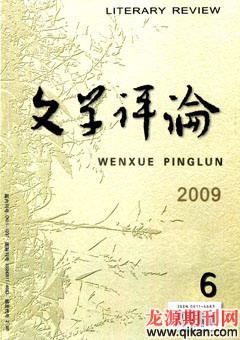文化救亡与民族文学重构
苏春生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战国策派”的文学思想是在对中外文化文学的整合、借鉴与融合、超越中建构的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系,即以民族主义的文学本质观、非理性主义的文学本体观、英雄主义的文学创作观为其特质,以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重构为指归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体系。对中国20世纪文学思想的多极化、多层化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与建设。同时,它的深刻的偏激和探索的失度在文学思想上表现出明显的过失性。
“战国策派”或称“战国派”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初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林同济、陈铨、雷海宗、何永洁、王赣愚等一批教授文人为主形成的一个文化群体。“战国策派”是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产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消失。“战国策派”的著述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法律、伦理、文学、教育、地理等各种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群体。“战国策派”以康德、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等人的哲学为基础,以哥白尼的宇宙观、卡莱尔的英雄史观以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史学思想为借鉴,形成了一套较系统的理论体系。他们的总主题为文化救亡与民族品格重建。具体而言,在文化哲学思想方面,主张“力本哲学”和“权力意志论”,提倡“尚力”与“唯意志”观,坚持反理性主义立场,在社会历史思想方面,提出“历史形态论”、“战国重演论”,提倡尚武精神,固守英雄史观,在人生哲理方面,崇拜英雄,倡导浮士德精神,批判民族活力颓萎,建构理想人格,在学术思想上提出“第三周期论”,主张“文化摄相法”。
“战国策派”在文学上也自成一体,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成员主要有林同济、陈铨、沈从文、朱光潜、梁宗岱、冯至等,已基本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评介西方文学的主要作者有吴达元、费鉴照、商章孙、柳无忌、袁昌英等人。文学创作上特出者为陈铨,他创作有大量小说、话剧以及部分诗歌、散文等作品。在“战国策派”主办的阵地上,朱自清、沈从文、冯至发表有散文,孙大雨、梁宗岱发表过诗歌。该派还培养了一些文学新人,小说作者有杨静远、金启华等,话剧作者有黎锦杨、尚依伦等人。这些文学新人,虽已初露锋芒,但作品甚少,影响很小。而该派的文学思想与陈铨的文学创作则产生了较大影响。“战国策派”力倡“民族文学”,力主开展“民族文学运动”,从而建构起了以民族主义、非理性主义、英雄主义为其特征、以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建构为指归的文学思想体系。
“战国策派”是在身处残酷战争环境、较为宽松的学术空间和重建民族新文化的人文语境中,通过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反思总结和对西方文学的考察研究,建构了在中国新文学思想史上第一个较完善的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想体系。它是20世纪40年代文坛刮起的不大不小的一股“狂飙”。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不大不小的刺激。该派的文学思想同它的文化理论,在全国抗战久战力疲之际,“予国人精神上莫大的支持,对人心亦产生莫大的鼓舞作用。”当然,用历史的眼光看,当时对该派的批判或学理的辩驳从某种视角看也自有其一定必然性与合理性。
“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思想的整合与超越,它摒弃了五四文学思想的个性主义与理智主义,吸收了它的启蒙思想与人文思想,摒弃了30年代文学的阶级论与唯物论,吸收其民族的使命意识与功利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西方文学的借镜与融合。德国狂飙运动自觉的民族意识的文学潮流,非理智主义的文学思想,浮士德热烈感情、无限追求进取的人文思想,以及西方的唯意志主义、天才主义等文化思想,无疑给他们的文学思想注入了活力“酵素”,也无疑带来了一定的迷误性。
一、民族主义的文学本质观
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战国策派”文学思想的一个核心命题,什么是民族意识,陈铨阐述道:“一个民族能否创造一种新文学,能否对于世界文学增加一批新成绩,先要看一个民族自己有没有民族意识,就是说它自己觉不觉得它是一群和世界上任何民族不一样的人”。“而且这一种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可以自己骄傲的地方”。这里表述的民族意识即民族“自我觉悟”,亦即是民族(通过它的成员)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对自身不同于别的民族地位与作用的一种认识的态度,是通常所说的民族“自觉度”。陈铨认为:“假如这一种感觉还没有发达,这一个民族的文学家,一定会成天仿效外国,不能有独立的贡献,它的文学,也不值得世界的人尊重欣赏。”他要求“要创造有特殊价值的新文学,大多数的国民必须先要有民族意识”。“必定要有一些作家,把他们的民族文化充分表现出来。”这样才能对世界文学有特殊贡献。在力倡民族意识的同时,他从负面批评了当时中国文坛漠视民族意识的状况:“现在中国有许多丧心病狂的人,不骄傲自己的祖国,而骄傲别人的祖国。这样的人,连自己的祖先都弄不清楚,还配谈什么文学?然而这样的文学口号,却风行一时,许多青年认为时髦;许多在社会上有地位的文学家,为着博取一般青年人的欢迎,也勉强在自己作品中间掺杂一些这样的口号,真是可惜!”
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陈铨认为:“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是不同的,一个民族和另外一个民族更是不同的。一个人要认识自我,才能够创造有价值的文学,一个民族也要认识自我,对于世界文学然后才有真正的贡献”。那么一个民族如何认识自己呢?那就是认识一个民族的性格,亦即民族品格。他举例论证,法国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所以成功,并不在当时作者摹仿希腊罗马,而在他们认识了法国人自己的特殊性格,和希腊罗马的气味相投,所以藉他们的形式,来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法国人的性格可以借镜希腊罗马,德国人的性格却不能借镜法国人。从德国的民族性格的立场出发德国人不能追随法国。德国人喜欢复杂,法国人喜欢简单;德国人喜欢想象,法国人喜欢实际,德国人注重情感,法国人注重理智;法国人要求完美的形式,德国人要求丰富的内容,德国民族认识了他们自己,发起狂飙运动,完全摆脱法国的文学传统的势力,天才、感情、力量,自然形成了当时德国文学界理想的目标。而仿效、修饰、秩序、规律都认为是文学的束缚。从此德国文学在世界上可以同英国、法国分庭抗礼。其根本原因是德国人“自己找出自己本来的面目”。他还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学能够永垂不朽,必须先要把自己表现出来。”可见,民族意识还要求认识民族自我和表现民族性格。
这种民族意识实际包括三个层面,即一个民族对自身觉悟的态度,一个民族对自身认识的深度和一个民族对自身表现的程度。由此三者合而为民族意识。而民族文学和民族意识的关系是:没有民族意识,就没有民族文学。“只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学。”叫民族文学可以培养和加强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又是民族文学的根本。所以民族文学“最大的使命就是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利害相同,精神相通,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奋斗,才可以永远光荣生存在世
界,他们有共同悠久的历史,他们骄傲他们的历史,他们对于将来的伟大创造,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对于祖国,他们有深厚的感情,对于祖国的自由独立,他们有无穷的渴望。他们要为祖国生,要为祖国死,他们要为祖国展开一幅浪漫,丰富,精彩,壮烈的人生图画”。他们提倡的民族意识最终以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为自己的归宿,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深沉的民族主义魂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民族意识不是由理智主义的人担当新时代的使命,“民族主义,是20世纪的天经地义,然而民族意识发展,不是肤浅的理智所能分析的,它是一种感情,一种意志,不是逻辑,不是科学,乃是有目共见,有心同感的”。“要靠意志感情和直观来把握事实,才能鼓励人生,见诸行动”。“简单的理智规律”,是不能“推动复杂的人生”的。显然民族意识实质上是以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为基质的。此外,陈铨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说“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但要特殊,同时还要丰富,特殊是新颖,丰富是伟大,特殊需要独立创造精神,丰富要有兼取并蓄的雅量,狭义的民族主义,不但不能创造伟大的文学,更不能创造伟大的国家。排外和复古,不是民族运动,也不是文学运动。”
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一个国家民族在某个历史时段体现的总体精魂,是这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生命体。大凡文学经典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它所处的时代精神,这是毫无疑义的。陈铨在《论新文学》一文中谈到什么是新文学时指出:“新文学一定要代表一个新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他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出发,考察了欧洲文学的发展,认为欧洲经历了四个明显的时代:世界、上帝、人类、社会。每个时代都明显地产生了一个新的时代精神,在希腊时代,命运的观念,是其文学的中心,因此,希腊悲剧的中心题目,就是人类在命运的绝对支配之下,怎样处理自己,命运虽然压迫,人生虽然悲惨,但人类奋斗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人格,更显出她的伟人。中世纪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上帝”,所以中世纪的人类,对人生崇高的理想,就是怎样信仰上帝,了解上帝,接近上帝,得到上帝的帮助。到文艺复兴,人类除开世界、除开上帝以外,发现了自己,他们从外在世界,回复到内在的心灵,从上帝回复到自己,人类是一切的中心,人类的思想情感,因此也就成了文艺复兴以后文学最重要的题材。18世纪以来,欧洲的工业文明逐渐发达,19世纪社会上的一切组织都改变了。人同人国同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无论任何社会经济政治行动,个人都要依赖团体。人类的尊严渐渐失掉了,个人的意识也渐渐淹没了,代替希腊的“世界”与中世纪的“上帝”来威胁人类的,乃是新起的“社会”。“社会是近代人类的一切问题中心,也就是时代精神的焦点。近代文学,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是在表现个人和社会的冲突,或社会和社会的竞争”。陈铨考察欧洲文学的演变,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同时代分不开,时代有变化,文学也有变化”。“时代精神思想,到了相当的时候,就不适应于一般人的生活,假如没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思想出来,人类的进化,就要因此停滞,人类的生活就要因此腐败堕落。”的确如此,历史永恒向前,时代在不断变迁,时代精神也随之代际更替,推陈出新。
那么,究竟什么是“时代精神”呢?陈铨界定说:“所谓时代精神,简单来说,就是新的人生观。人类不能不有生,对于生不能不有一种看法。随着地域不同,民族性的差异,和时代的变迁,人类对于人生,看法就不一致。”“人类是非善恶的标准,也就常常变换冲突。”时代就是这样行进的,人类的人生观就是这样改变的。“战国策派”认为当时的中国是战国时代,除非演变到一个大一统局面,一时是不会消灭的。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从前旧式的人生观,最近二十年从西洋输入比较新式的人生观,无疑已经不适于今日了。许多抱残守缺的老先生,受了英美自由主义的绅士们和熏染了苏联阶级斗争思想的青年志士,”都成为“一套陈腐观念”。因而他提出了一个新时代的新理想,即时代精神是:第一:理想的人生是战斗,不是和平。第二:理想的人是战士,不是君子。第三:理想的道德是征服,不是怜悯。第四:理想的快乐是胜利,不是妥协。第五:理想的自由是民族,不是个人。第六:理想的国家是统一,不是分裂。第七:理想的政治是国富,不是民乐。第八:理想的教育是训练服从,不是发展个性。第九:理想的社会是民族至上,不是阶级斗争。第十:理想的国际关系是中国民族领导下的天下为公,不是平等待我的共存共荣。这是很富有个性化创见的言说,表达了国家至上、民朕全上、军事至上的思想,陈铨认为这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他甚至惊呼:“现在的局面,不是前进,就是后退,不是生存,就是消灭,不作主人,就作牛马。”“是目前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新文学创造中最迫切的问题。”
这就要求,文学家在这时代的紧要关头,要站到时代的最前列、文化的最高峰,担负起先知先觉的责任。首先,为了要担负起这一严重的使命,在思想学问方面必须要有充分的修养,世界上没有不学无术的伟大文学家,也没有孤陋寡闻的伟大文学家。文学家不但要有才华,而且要有见识。其次,文学对于一个时代大多数人类共同的努力,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智识,都要有深刻的了解。再次,文学家不但要表现时代,同时要指导时代,一方面能够顺应时代,开创时代;另一方面又能够了解人类社会的根本,因势利导,使人类了解宇宙人生真正的意义。
陈铨所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反映时代精神,自有其见地,他所提出的新理想,显然跳动着他迫切地思考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赤诚之心。但其否定阶级斗争,宣扬天才主义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强烈反侵略御外侮的同时,不无民族扩张的嫌疑,由此,有的论者对此作出了尖锐的批判。
人本准则文学的非理性的人本准则,是“战国策派”对民族主义文学本质观的一个共识,陈铨认为:“新文学一方面是时代的,一方面也是超时代的,因为人生的问题是变迁的,人类的本质是永恒的,喜怒哀乐嫉妒仇恨同情攻击,尽管因为时代环境,反映不同,然而它本身,却是人类一天存在,它们也一天存在。”沈从文多次强调,一个文学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人性”为准则,“作家有感于生命重造的宏愿和坚信未来有所作为”,读者明白“玩味人生,理解人生,或思索生命什么是更深的意义,或追究生命存在是否还可能产生一点意义”。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所供奉的是人性的希腊神庙。林同济在《寄语中国艺术人》中所表白的是一种生命意识,人类从生到死,无时无刻不在追逐生命体验与生命终结的意义。他提出的“恐怖”、“狂欢”、“虔恪”三母题就是人生永远奋斗与无限进击的三部曲。“恐怖”是慑服,是人生绝对低谷生命意识觉醒的开始。“狂欢”不是醉生梦死,而是生命巅峰激情的进发,在胜利途中能继续奋进者所必须应有的生命状态。最后反视自身,人生耗毕生的能量,尽一世拼搏,所得较之字宙实在微乎
其微,最终宇宙之谜无法猜破,世界之势无法控制,不禁幡然彻悟面对宇宙世界而肃然起敬,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极高境界,彻底皈依“虔恪”。
他们所阐述的“人类意识”、“人性”和“生命意识”实质上都是反理性的人本思想,陈铨指出:“历史的形态是有变化的,但人性是没有变化的。人类在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方面,无论中外古今,都是一样的,他们仇恨,嫉妒,爱恋,争斗,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他们就要继续表现一天,方式尽管不同,根本却是一样。”他们所主张的非理性的人性是由其信仰的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哲学观的影响所决定的。陈铨从文学史发展角度论述:“历史上伟大作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早已过去,然而他们的作品,对于现代和将来的人类,还能够引起浓厚的兴趣,就是因为他们在人类的本质方面,有伟大深沉的观察和表现。”希腊的悲剧,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土德》,所描写的对象已经模糊,然而所表现的人类的基本情感还踊跃有生气。伟大的作家的文学作品在表现时代精神的同时必须表现人类的基本情感,而后者更是文学经典永恒的价值所在。
他们要求文学家在描写时代的变迁,提出新的解决办法的同时,“要表现出人类的本质,使人类彻底明了人生真实的情况。”要“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因所见甚广。所知甚多,对人生具有深厚同情与悲悯,对个人生命与工作又看得异常庄严,来用宏愿与坚信完成这种艰难工作。”“用文字故事给人生作一种说明,表现人类向崇高光明的向往,以及在努力中必须遭遇的挫折。”“努力鼓吹如何做人”,“来培养我们民族的活力,进取精神,感情生活,理想的追求。”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战国策派”所主张的文学的人本准则,同他们所提倡的。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融为了一体,形成了人本的民族主义文学本质观。
二、非理性主义的文学本体观
心灵创造陈铨在《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中提出了“心灵创造”说。“心灵创造”说源于康德的哲学思想。陈铨认为,康德是把人类和世界联系的问题正式鲜明地作出解答的第一位哲学家。康德把世界上的事物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物的现象”,一方面是“物的本身”。人类所能够知道的,不过是物的现象,至于物的本身,是人类的智力所不能知道的。希腊人相信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定的条理,这一些条理,包藏在物的本身。康德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本来无所谓条理,人类观察事物的现象,在心灵中组成一种条理,勉强加在事物的身上。因为事物的本身,我们没有法子知道,事物的现象不过是事物在人类的心灵上呈现出来的状态,从这种状态中组织成功的条理,根本不是事物本身的条理,乃是人类心灵上的条理。因此,人类所能知道的世界,和人类是分不开的,因为离开人类,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康德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人类是宇宙的中心,一切的规律,都是人为的,都是人类心灵对于事物现象活动组织的结果。对此,陈铨认定“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转变!”并把康德在哲学界的地位同哥白尼在科学界的地位相提并论。“从前的哲学家相信世界是一切问题的中心,康德却把这一个中心,从世界转移到人类。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尊严,无形中逐渐提高,现在康德第一次给它一个强有力的解说。”
在陈铨看来希腊的“世界哲学”支配了欧洲哲学两千多年,对文学同样发生伟大的影响。文艺复兴以后,人类渐渐认识自己,一直到18世纪,康德才根据这一种新精神,建设他的“自我哲学”,两者的出发点根本不同,前者是外物决定内心,而后者是内心决定外物,从此,确立了人类的尊严。他据此推断,“假如人类是一切事物的中心,世界上一切规律都不来自事物本身,乃是人类心灵的创造,那么在文学方面,从希腊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学批评家所认为天经地义的规律,就时时刻刻有动摇的危险,因为规律是人类心灵的创造,人类心灵有变化,文学批评的规律自然也就有变化。”因此,“我们再不要任何‘外在的规律,来束缚我们自己,我们要根据‘内在的活动去打开宇宙人生的新局面”,“从内心去创造精神”。
文学创作本来应该是一种心灵创造,可是一般“受古典主义精神陶冶的作家,往往在动笔之先,费无限的精力,寻求规律,探讨文学创作的秘诀,他们相信得了这些秘诀,才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品。至于批评家更不用说,自以为他们已经得了这些秘诀,所以苦口婆心,劝创造的作家依照他们的方案,完成不朽的事业。”事实上作家是绝不能靠所谓创造秘诀和规律写出伟大的作品的。陈铨认为坊间流行的汗牛充栋的所谓《作诗入门》、《小说方程》、《小品文作法》、《戏剧技术》等书,对于文艺创作是无用的。而受到古希腊外物决定内心的“世界哲学”的影响,美国大学开设了许多关于文学写作的课程,中国大学有无数修改作文的先生,这些显然是不符合文学创作是心灵创造的本体的,这样培养的作家是绝不会创作出伟大作品的。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心灵创造,没有所谓天经地义的规律,“规律是人类心灵的创造,人类心灵有变化,文学批评的规律自然也就有变化。”“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必须要设身处地,走进作者的灵魂,想象他当时此地内心的情致,他努力要表达的事物和心境,然后才能够真正了解,欣赏他的著作。”陈铨的本意是要确立文学是心灵创造的本体地位,说明文学创作是没有恒久不变的规律的,规律也是心灵创造的,为心灵创造服务的。
生命发泄与陈铨“心灵创造”说相呼应的是林同济提出的“生命发泄”说。共同有创意地言说“生命”是“战国策派”的重要选项,陈铨就这样认为“生命是一种力量,力量必须要求发展,没有任何消极的哲学、宗教、艺术、道德能够压迫它,解脱它。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学,就是能够提高鼓舞生命力量的文学。”这显然是一种生命文学观。而“生命发泄”说则主要是林同济在《我看尼采——(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一文中详尽阐述的。林同济非常自信的认为:创造是人生最伟大的作用,只有文艺创造是无所为而创造,纯为着创造而创造,文艺创造“最可以表现生命力的本性,因为它最能够代表人们生命力自由、活跃,至诚成物的最高峰。”是“生命力的饱涨”。
文学创作是生命力的饱涨与发泄,这是林同济读尼采与研究尼采所得。他这样评述:“尼采是生命力饱涨的象征。浑身生命力,熟燃着五脏四肢,要求发泄。又加上那副极敏锐的神经,就等于最精细的气压表,空气最轻微的压力变迁,都要立刻在他的体魄上发生强烈的反应。积弱的身体只激进了生命力跃跃欲出的倾向。于是愈病而生命力愈精悍,愈老而生命力愈加热腾。尼采是人间极罕见的天才,显然脱离了年华的支配他那如椽大笔,真是愈挥霍愈生花,鬼使神差,直到最后一刹那也不少挫。”林同济对尼采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觉得千古以来,只有庄子、柏拉图和尼采是奇人,他们的书都创出一家之说,是蔚为千古不灭的奇书,而尼采的书最为搅动心魄。他是把尼采本人作为“生命力饱涨的象征”的。
文学创造是“生命力饱涨”最好的“发泄”途经,林
同济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尼采的创作情状。“尼采的写作,是生命的淋漓。热腔积中,光华突外。”“他的写作,竟就像米薛安琪所描绘的上帝创世,纯是一种生命力磅礴所至的生理必需,为创作而创作,为生命的舞蹈而创作。”“只要把整个娘生的身体狂投进来狂舞一番,方可发泄他胸中的混沌的节奏。”“他显然只是一股热腾腾的生命力在那里纵横注泄,霍霍把横塞胸中的浩然之气妙化为万丈光芒,文字与思想本不是他的目的。目的?他本无目的!他只是生命力的一时必要的舞蹈与挥霍。文字与思想在那时只是创造的工具与数据。”尼采创造的“超人”如此,林同济仿“萨拉图斯达如是说”所竭力宣扬的文艺创作“恐怖”、“狂欢”、“虔恪”的“三母题”,正是生命力饱涨与发泄的极致。这种主张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的刺激与震撼也是罕见的。
这种生命力的饱涨与发泄的特点是恣肆汪洋、纵横捭阖、挥洒自如,并无条理与秩序可循,作者的表达是通过“暗示”来实现的。如何理解这种文学创作,林同济做了多方面的审美的论述,而其中最基本的是,他借尼采的话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猜射”,意思是通过对作品的多方的联想与统合回射其抽象的方法与功能。审美就是要“创造心灵对创造心灵的心心相印”,“领受暗示,须要猜射功夫,从具体猜射到空灵,从殊相猜射到共相,——从有限猜射到无穷之那边。”他还提出“揭理象征法”,就是“说偏说反,说其偏以揭出理之全,说其反以揭出理之真,听者因此也必当晓得如何使偏以全,就反以捉真。”在具体文字之外通过“猜射”理悟“暗示”,去探寻别样的奇异的美妙的空灵意境。
直觉达成直觉主义文艺思想是西方现代文论的核心文艺观,从叔本华、尼采强调直觉主义的文艺观,到柏格森集大成形成直觉主义文艺思想体系,一直到克罗齐以后的现代主义文论都把直觉主义作为核心命题。“战国策派”坚持反对理性,否定文艺的客观本原,把文艺创作看作是一个直觉达成体验与创造的神秘的生命过程。林同济在《寄语中国艺术人》中要求中国艺术人表现的“三母题”:“恐怖”、“狂欢”与“虔恪”,就是对人生生命极限三个阶段生命过程的巅峰体验,这是一种尼采式的对人生生命极限情状的酣畅疯狂的抒写,在中国20世纪文学的文献中是极为少见的。
这奇异瑰丽的生命极限过程,理性是无法描绘体验的,理性只能是追索真理,探求规律。而唯直觉才能感受于体悟这种生命极限过程与生命强力的辉煌。林同济曾谈到崇尚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历史上超绝古今的思想,大半都是由直觉得来。”并以尼采为例加以阐述,“尼采不愧为艺术家本色,最富直觉能力”。“忽然灵感触来,一条金光涌到心头,刹那间他对真理有所见。”同样,他认为,“艺术创造……根源于生命力的饱涨”。文艺创作“纯是一种生命力磅礴所至的生理必需,为创造而创造,为生命的舞蹈而创造”。因此,“在创造的刹那,只有创造的精神,没有人间的利害是非”。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就是“直觉得来的思想要将直觉送出去”。这是艺术人的创造与体验过程的“直觉”,因此“直觉”决定“创造”与“体验”。只有直觉才能体悟这种内心创造的过程,感受生命体验的真谛,从而创造生命存在。
同样,受叔本华和尼采唯意志主义哲学的影响,陈铨认为:“意志是人类一切行为的中心。生存意志是推动人类行为最伟大的力量。”他更进一步强讽“人类不但要求生存,他还要求权力,生存没有权力,就不是光荣的生存。”只有“达到权力意志”,才能“创造出精采,丰富,浪漫,壮烈的事业”。那么,“战国策派”所主张的“心灵”、“生命”、“直觉”正是这种“生存意志”与“权利意志”在“体验”与“创造”过程中的“生命力的饱涨”。意志才是融贯“心灵”、“生命”、“直觉”的基质。可以看出,他们吸纳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形成一个奇妙而富有魅力的体系。
“心灵创造”说、“生命发泄”说、“直觉达成”论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想,意在呼唤一种极富生命力、创造力、扩张力的文学。这些立论企图纠正中国传统文学中庸柔弱的风格,改变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的传统文学观,传统文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安眠力”,因而,林同济大声疾呼“我劝你们不要一味画春山,春山熙熙惹睡意。我劝你们描写暴风雪。”那是一种“可以撼动六根,可以迫着灵魂发抖”的文学。以此“开辟一个‘特强度的崭新局面”。这样的呼吁,在民族颓势与民力颓靡的危难之际,表达了立人保族强国的诉求,这显然是出于“战国策派”对民族品格的重构与文化重建问题的激奋思考。理性主义万能的学说再也不能成立,“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博格森的生命哲学,心理上的潜意识”“无不以非理智为目的”。他们认为非理性主义如同民族主义在20世纪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理悟其思想深刻的同时,不能不警惕它的偏至,不能不指出它烙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印痕。
三、英雄主义的文学创作观
天才作家“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陈铨、林同济、贺麟,朱光潜等人都主张“英雄崇拜”,朱光潜认为:“每时代每社会都有它的英雄,而英雄也都被人崇拜,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贺麟则批评:“凡是根本反对英雄,抱定主张绝对不崇拜英雄的人,就是‘英雄盲的人,睁开眼睛,看不见英雄。英雄是人类理想价值具体化,‘英雄盲就是‘价值盲,‘价值盲是一种精神病态。”他主张:“凡是能够崇拜英雄的人,就是不害‘价值盲的人。他不但能够认识英雄,而且能藉崇拜英雄,扩充自己的人格,实现自己潜伏的价值意识,发挥他自己固有的‘英雄本性Herosim。”陈铨更具体指出:“天才就是英雄,英雄不仅是武力方面,政治宗教文学美术哲学科学各方面,创造领导的人,都是英雄”。竭力提倡“天才作家”说的主要是陈铨和林同济。陈铨一再表明“文学创造,需要天才”。在“文学的领域里,没有平凡的人的足迹”。天才是什么呢?天才并不是仅有广博的知识,天才必须富于创造的精神,具有极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崭新的东西。“天才最大的特点,就是发明”,“天才可以随时创造规律,规律绝对不能束缚他们”。天才作家“不但要表现时代,同时还要指导时代”并且能够“打开宇宙人生的新局面”。他们不能模仿前人,但一定要作后人的典范。林同济在《我看尼采》和《寄语中国艺术人》中也明确阐述了同一观点。“战国策派”所提倡的从“英雄崇拜”而“天才论”,明显受到了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和尼采的“超人学说”的影响。当然,康德提升人类的尊严肯定天才可以创作规律的哲学思想也是其立论的理论基础。我们否认唯“天才论”,但尊重人才,肯定人的天赋,崇尚英才是无可厚非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特别是创造精神财富是需要“天才”的。
陈铨在肯定“文学没有天才,根据谈不上文学”的同时,还给天才作家提出了具体条件。他主张文学天才,应当生活在一种“智识潮流”中间。所谓“智识潮流”就是合乎时代精神的正确思想。这种思想是文学天才发展的
根基。他认为“文学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认识自我。在自我认识的时候,就是天才起首表现的时候。固然在基本训练中间,一位青年作者未尝不可以借镜他人。但是在高尚的表现,成熟的时期,一位文学家依然不能摆脱别人,建设自己,那么我们只能说他没有天才,或者有天才而没有认识自我,所以把自我毁灭了”。他还认为:“文学是一种创造活动”,“因为文学的使命,是要表现特殊的事物”,“文学家是不能仿效的,仿效就是欠天才”。此外,他非常重视伟大文学批评家对天才作家的指导作用。他指出:“历史上好些伟大的天才,因为得着伟大批评家的指导,力量用在正当的途径;才有优异的成绩。如像哥德遇着黑尔德,受他最大的影响。摆脱传统的拘束,发挥自己的天才。假如没有黑尔德,那么歌德也许还要受法国文学的支配。”陈铨在《戏剧与人生》一书中对天才戏剧家的修养作了具体的论述,包括观察、想象、思想及训练。只有具备这些条件修养,才能“使中国的文学天才向正当的有效的途径发展”,“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学”。
浪漫精神浪漫精神是英雄主义文学创作观的精魂。浪漫精神最早是陈铨在《<金指环)后记》中提出的,此后他又发表了《青花(理想主义与浪漫精神)》,该文言简意赅地阐明其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青花”源自德国作家罗发利斯的小说《亨利阿胡廷恩》,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描写了一个人看见一朵青花,若远若近,忽隐忽现,永远追求,永远不能到手,由此“青花”成为理想主义的象征,也是浪漫主义精神的象征。陈铨在文章中先为“浪漫”正名,他否定了放情纵欲,朝秦暮楚,寻找刺激的时下流行的对“浪漫”不正确的理解,他认为西方文学史上的“浪漫”并不是当时中国流行的曲解的“浪漫”。浪漫主义运动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流行于欧洲各国,影响较大者莫过于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陈铨曾留学德国,深知从康德到黑格尔以来德国理想主义的思想脉络。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理想主义对近代文学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伟大影响,他认为浪漫主义源自康德,发源于理想主义。
浪漫精神是浪漫主义精神的简称,就是理想主义的精神。“人类都有理想的,而且时时刻刻要求实现他们的理想,这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性,就是人类世界一切进步的泉源。然而真善美都是人类最高的理想,人类永远追求,永远没有达到,这是一个无穷的工作。”她“是人生理想的无限追求”。浪漫精神要靠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载体来体现,而这种人物形象必须有“高尚理想”,“他们追求的,是荣誉,是感情,是道德上的责任,为着荣誉感情责任,他们可以牺牲一切。”他们为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理想,奉献生命,亦所不惜。
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进化,伟大人格的产生都是靠浪漫精神推动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浪漫精神“就会流于物质主义、实利主义,只知道是生存的欲望,与禽兽一般”,一个民族没有浪漫精神“一定会堕落、腐化、崩溃”。可见浪漫精神是个人的灵魂,是国家的国魂,是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妙方金丹。她是一种文学精神,也是一种文化精神。
陈铨把从五四到抗战前期20余年划分为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个历史阶段,而相对应的哲学思想背景是实用主义、唯物史观与理想主义,属当下第三阶段的民族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分不开的,民族主义与“浪漫精神”也是不可分割融为一体的。“这一种浪漫精神和对人生的态度,也许是中国新时代所最需的”。“我们目前政治社会教育上种种不良的现象,都要这一种精神来拯救。”而陈铨创作的剧本《金指环》与《兰蝴蝶》副标题都标为“浪漫悲剧”的深意也在于此。剧中的人物都是为捍卫国家的名誉和民族的使命,为真善美的崇高理想而奋斗以至于献身的。
在民族主义思潮普遍高涨,抗日救亡功利意识极强,文坛盛行抗日现实主义之际,陈铨极力倡导“浪漫精神”,提倡浪漫主义运动,推动抗日民族斗争,可以说给国人以别样的兴奋和异常的激动,他的《野玫瑰》等“浪漫悲剧”确实感动过国人,抗战不仅需要现实主义,也需要浪漫主义,不仅需要“现实精神”,也需要“浪漫精神”,过去对此的批判是有失公正的。
“力人”形象“战国策派”力主“尚力文化”。林同济认为欧洲近代的文化精神可谓“柯伯尼宇宙观”,该宇宙观用极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穷的空间,充满了无数的力的单位,在力的相对关系下,不断地动,不断地变。”“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是力。”这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力的宇宙观。陈铨研究狂飙时代的德国文学得出的结论是:“狂飙时代有两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力量与‘天才。力量是一切的中心,它破坏一切,建设一切;天才是社会的领袖,他推动一切,建设一切,然而天才的本身最重要的原素就是力量。天才的发现实际上就是力量的表现。”《战国策》的《代发刊词》就是以“力”为中心的宣言:“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他们认为“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人的生活最精彩的时候,就是权力意志最充分发挥的时候”。抗战时期就如战国时代,“大战国时代的特征乃在这种力的较量。”“有力才能存在,无力必归消灭。”这种尚力思想有着中外文化的深厚累积,确可以振奋自信,强化人力国力,提升中华民族的综合力。
“力人”是陶云逵在《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中提倡的一种人格类型。他把“尚力文化”人格化、实在化。他认为:“力是个观念,要须从力人身上,从光明人格身上,具体化出来。”“说我们需要力,就是说我们需要‘力人,需要有力的人格。”他把人格分为“主人型”与“奴隶型”,中国历史的变迁与兴衰,根本上是这两种人型的浮沉争斗的过程。“力人”就是“主人型”的人格,中国历史上“力人”为数不多,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靠了这无力圈中偶而兴起而成了大业的几个少数力人。那么什么叫“力人”呢?“力人是不受传统支配的,他要创造,他有独到的‘是与‘非,他真,他意志坚决,他直爽,光明,他不怕阻挠,他不怕死,愿为他的‘是而死。”而“力人”担负实现人类最高理想真善美的历史使命,唯有“力人”才能达到真善美,实现人类的理想。陶云逵呼吁:“我们得保卫力人的种籽,培养它,使它生长,开花,结种,繁殖。这样,幽暗世界才会变成一片光明。”林同济也同样指出,“我们的文化使命”是“一面赶造强有力的个人,一面赶造有力的社会与国家。”把塑造“力人”放到民族文化救亡的首位。
陈铨的文学创作担当了“赶造”“力人”形象的使命。“力人”形象就是他在文学作品中讴歌的抗日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黄鹤楼》描写中国空军“铁鹰队”大队长刘玉彪深明大义、忍辱负重、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力人”精神。《野玫瑰》中着力塑造的特工人员夏艳华胆识过人、谋略超人的“力人”形象,西滢曾评价:“这样的一个女人似乎不是血做的,肉做的,也只有尼采式的超人才能做得到”。如果说刘玉彪是领导抗日救亡的正面的“力人”
形象,那么夏艳华则是抗日救亡之中处在特工战线的巾帼英雄,两者有异曲同工的艺术效果。
从刘玉彪、夏艳华等一批人物形象上明显地体现出“力人”的品格。这种对“力人”形象的歌颂,可以鼓励“力人增多”,“无力人减少”,“烧断了阿Q类型,而铸出一种战士风格”有利于提倡“兵文化”,进而崇敬抗日英杰,弘扬抗日英雄精神。这无疑对重建民族品格,给抗日救亡注入活力,发挥了进步作用。
与“力人”形象相伴的一个概念是“异性伴”。“异性伴”是林同济在《寄语中国艺术人》一文中因“三母题”的需要而提出的。他认为:“狂欢必须异性伴,虽然异性伴不必是狂欢。因为狂欢的最高峰必引入恐怖的最暗谷,异性伴所以对待最高峰的告辞。因为狂欢的最高峰本即是恐怖的最暗谷,异性伴所以协助最暗谷的再征服!大醉酒可以制造一时的幻觉,异性伴可以加强争斗的意力。”简言之,“狂欢必须异性伴”,“最暗谷的再征服”也要有“异性伴”的协助,其根本原因在于“异性伴可以加强争斗的意力。”可见“异性伴”是为更加强“力人”争斗的意力而设置的。“异性伴”成为陈铨文学创作上的独有景致,并不在于他的创作中常常采用三角爱情关系的结构;(《野玫瑰》里夏艳华、刘云樵和曼丽之间的关系;《金指环》里尚玉琴、马德章与刘志明的关系。《蓝蝴蝶》中婉君、钱孟群和秦有章的关系等)而在于他摒弃了时下文学作品中以爱情婚姻至上、反对传统伦理道德、或为满足性欲寻找刺激等男女关系的三角套式,为实现救亡图存抗战建国,而牺牲男女恋情与儿女情长,达到申明国家民族大义,强化“力人”的斗争意志的目的,从而更加突出真正的“力人”品格,增加了艺术的震撼力与影响力。
概言之,“英雄主义文学创作观”即是“天才作家”发挥“天才的创造”,鼓吹民族英雄的“浪漫精神”,塑造“力人”人格的形象,以图重铸民族品格,救亡图存。这种观点明显地受到哥白尼宇宙观、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尼采的“超人学说”和“浮士德精神”的影响,充分地体现了陈铨、贺麟、朱光潜等所提倡的“英雄崇拜”,雷海宗提倡的“兵文化”与“文武兼备”的“真君子”,林同济论述的“士大夫”人格和“战士式”人格等文化思想。这种文学创作观与抗日救亡的时代精神是合拍的,它可以起到增强民族自信,注入国家活力,激励抗战建国的积极作用。
“战国策派”的文学思想是在对中外文化文学的整合、借镜与融合、超越中建构的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系,即以民族主义文学本质观、非理性主义文学本体观,英雄主义文学创作观等为其特质,以民族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重构为其指归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体系。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战国策派”的文学思想,成为以民族主义,非理性主义、英雄主义等为其特征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使其成为中国20世纪文学思想史上,继激进主义文学思想、自由主义文学思想,保守主义文学思想之后又一个重要的较完整的文学思想理论体系。它对中国20世纪文学思想的多极化、多层化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与建设。“战国策派”的文学思想,作为整个文学思想历史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至今还值得深入研究。作为文化文学的历史资源自有其文献性和价值性。
“战国策派”是一个极富理论个性和探索精神的文化群体,它深刻的偏激和探索的失度在文学思想上表现出明显的过失性。其一是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它的文学思想从本质观、本体观到创作观,都主张“意志”、“情感”、“直觉”、“心灵”决定论,他们在文学思想的自律性的主观性方面作了深入的开掘,在文学的他律性,即文学的文化思考方面处处闪烁出独到见解的思想火花,但其出发点归宿点都是唯心主义的。其二是心态上的激进主义。“战国策派”成员大都是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其理论锐气、探索精神、爱国激情、学者品格可敬可佩,然而其偏激、傲气却遭到人们的不满,由此也带来理论上的过失。其三是运作上的公式主义。由于理论上的系统化完整化,造成理论上的单一化,公式化。陈铨的文学创作中表现的“民族主义”万能的概念化和“异性伴”的雷同化等也具有公式主义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