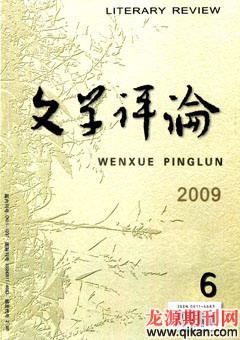从“翻案”到“影射”
刘卫东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讨论在“新编历史剧”热潮中达到白热化。曹操是历史上一直被“误读”的人物,在特定环境下,为曹操“翻案”的意义迅速被放大,竟变成史学界的“战斗任务”。当时历史剧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处理史实和评价人物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自己的历史人物“当代化”的问题。《海瑞罢官》因为姚文元的文章而被指定为“影射”作品,同一个“海瑞”,身份发生了尴尬的变化。
在1957年“干预生活”的作品普遍遭到批判后,许多作家把创作的方向转向了历史题材,出现了一股“历史剧”热潮,其中包括郭沫若的《蔡文姬》、曹禺的《胆剑篇》、田汉的《关汉卿》、吴晗的Ⅸ海瑞罢官》等作品,这一“现象”也为后来研究者所重视。颇为引人瞩目的是,围绕着这些历史剧塑造的历史人物和塑造历史人物的方法,文艺界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作品也遭遇到了不同的命运,进而,影响到了它们的作者的命运。此前的研究或分析剧目的艺术特点,或以政治结局关照作者,却很少从史学观点碰撞的角度分析在历史剧中“阶级观点”如何对“历史”进行“外科手术”,对“历史人物”进行“政治清洗”,而这一过程却是从对电影《武训传》批判开始就一直存在,在“批孔”中达到顶峰的理解“十七年”文艺批评的重要线索。
一郭沫若的“翻案”
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缔造者之一,也因为在1949年后政治上一直“高调”紧跟形势而地位重要的郭沫若,在经历了建国后一段创作上的“沉寂”(他自称“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之后,接连推出了《蔡文姬》(1959)和《武则天》(1960)两部历史剧,大做“翻案”文章,也将50年代初就开始的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讨论推向了风口浪尖。
“文姬归汉”本事见于《后汉书》,历来为文艺家青睐,被改编为多种剧目,在民间流传很广。郭沫若也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他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为蔡文姬打抱不平,对蔡文姬的文学地位进行了高度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件令人不平的事,是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所受到的遭遇。这实在是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叙事诗。杜甫的《寓同谷县作歌七首》和它的题材相近,但比较起来,无论是在量上或质上都有小巫见大巫的感觉。”郭沫若对蔡文姬非常偏爱,因为他不仅认为《胡笳十八拍》的艺术水准仅次于《离骚》而大于杜甫的《同谷七歌》(眼光不同,这倒无可厚非),而且对其他学者(刘大杰、郑振铎)认为该诗属于后人伪作的结论不以为然。即使《胡笳十八拍》真是蔡文姬的作品,她也只是一位才华横溢而命运不幸的女诗人而已,她的形象也历来被固定在这一点上。郭沫若的“创新”在于大胆突破,将其塑造为为中国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文学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创新”部分却是建立在“虚构”甚至“编造”基础上的:“我写曹文姬,一部分是根据历史上的材料,一部分是我编造的。有些人物是虚构的,有些事情的过程也是想当然的。”郭沫若用非常手段陡然将蔡文姬的地位提高,不仅仅是打抱不平这样简单,而是另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应该说,郭沫若选取蔡文姬作为自己剧作的主人公,并非难以理解,因为他已经写过历史上的多位著名女性。《卓文君》、《王昭君》和《聂蓥》这三位“叛逆的女性”,都曾为郭沫若所挖掘和表彰,虽然蔡文姬称不上“叛逆”,但是也算古代女性中的“名人”了,因此进入郭沫若的视野,十分正常。即便如此,郭沫若对蔡文姬的“另眼相看”还是超出对于其他女性,甚至把她视为自己的化身,说“蔡文姬就是我”。郭沫若在30年代的时候就说他的历史剧是“借着古人来说自己的话”,与同为创造社元老的郁达夫“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说法类似,而到了《蔡文姬》,显然未改初衷,不过,此时的郭沫若在蔡文姬这个人物身上倾注的情感要更多一些,他说自己与蔡文姬有“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有很高的认同度。联系他的生平可以知道,郭沫若这里的“经历”(被重用)和。感情”(感激报恩)显然与他在解放后的处境有关,至少他试图以此表明自己的“文姬归汉”姿态。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郭沫若写《蔡文姬》,意在赞美曹操。如果不是蔡文姬的故事中涉及到曹操,恐怕不一定会引起郭沫若的注意,或者说,郭沫若对蔡文姬的兴趣完全始于对曹操的兴趣。改变蔡文姬命运的,是曹操,这是一位在历史上一直被“误读”的人物,而郭沫若写《蔡文姬》的目的就是“替曹操翻案”,还他大英雄的本来面目。郭沫若认为,曹操自“宋代以来”,“受了很大的委屈”,实际上,“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在当时替曹操鸣不平的,不止郭沫若一个人,还有历史学家翦伯赞。翦伯赞在看了历史剧《赤壁之战》后撰文指出,“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的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郭沫若和翦伯赞拿出的理由,是“历史观”的变化:在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序列中,曹操是一个有“不逊之志”的野心家,而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中,曹操是位杰出的英雄。如此评价曹操功过,显然也有点故意“拔高”,不过这不算太大的问题,因为曹操确实需要重评,而此时矫枉过正一些,作为策略也是可以接受的。
问题不在于为曹操“翻案”,而在于为什么是这个时间。郭沫若从蔡文姬的归汉的角度评价曹操说:“他之所以赎回蔡文姬,就是从文化观点出发,并不是纯粹地出于私人感情;而他之所以能够赎回蔡文姬,并不是单纯靠着金璧的收买,而是有着他的文治武功作为后盾的”,“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事实上被曹操拯救了的不止她一个人,而她可以作为一个典型”。郭沫若对曹操的评价高的离谱,显然超过了“翻案”的范畴,其中隐藏着更深的心理动机。在郭沫若之前,毛泽东就已经表示过对曹操的好感,并且主张“翻案”,而他的思路无疑对郭沫若有很大“启发”。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汉是没落的。”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谈到曹操,“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正是在此基础上,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开始张罗为曹操“翻案”。另外,毛泽东曾经赞誉过的历史人物秦始皇、武则天也不同程度得到了“重评”,其中,郭沫若又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历史剧《武则天》,将其塑造为一位胆略过人、体恤民情的女皇帝。
为曹操“翻案”的意义迅速被放大,竟变成史学界的战斗任务,有论者说:“在人民翻身以后,替卓越的历史人物翻案,是历史科学家的职责。但是,解放以来,只是在直接诬蔑农民起义为盗匪这类问题上,完成了翻案工作,
其与农民起义间接有关的人物和事件,理应连带翻案者触目皆是。提出‘替曹操翻案,只是历史学战斗任务的开始。”这段话虽然不得为曹操。翻案”的要领,但是却以此为模板,试图改写历史人物评价的版图,这个“战斗任务”的宏伟和魄力确实让人吸口冷气。可以预见,在“人民历史观”的大旗下,整个中国历史势必“天翻地覆”,需要重新书写。大手笔的“翻案”运动即将展开,讨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工作,虽然尽量表现得小心翼翼,还是有人在学术研讨的范围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历史学家吴晗就是其中的一位。
二吴晗的“苦恼”
在对历史人物进行“翻案”的形势下,具有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双重身份的吴晗感到无所适从,他既不愿附和“潮流”,又不能反对,因此陷入“苦恼”。1962年,他发表了近两万字的长文《论历史人物评价》,表达了自己的。苦恼”和思考,打算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吴晗认为,把历史人物按照“阶级”划分成分的评价体系“造成多方面的混乱”,“编写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科学史的人经常感觉苦恼。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的出身不是地主阶级,便是贵族、官僚,他们对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方面都是有出色的成就的,但阶级成分不好,怎么办?就他们的成就说必须肯定,就他们的阶级成分说却非否定不可。假如全否定了,这本书没法写,写谁呢?全肯定了,又怕犯错误。真是左右为难,如何是好”。吴晗提出的问题很尖锐,直接指向当时历史研究理论的痛处,同时,这也是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说是“苦恼”,“左右为难”,但是吴晗分明有着自己的鲜明的立场和主张,他在文中一连列出六点,基本回答了这个问题。
吴晗是位学者,多少有些社会经验,但是又不充分,这正是他性格悲剧所在。如果他看出“翻案”背后的原因,而又不打算像郭沫若和翦伯赞一样介入的话,可以选择沉默,但是他又是不愿意苟且的学者,所以还是站出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试图阻挡“历史潮流”。吴晗深知曹操问题不容置疑,所以索性予以承认,说曹操“总的说来,他是功大于过的,是个应该肯定的人物”,但是也批评曹操“起兵镇压黄巾,杀过一些知名人士如孔融、杨修、华佗等人;军法残酷,围而后降者便屠城,这些确是坏事,不应该替他掩饰”。这段评论说明他对全面美化曹操是保留一些意见的,但是表面上还是不得不赞成。其实,曹操也不是“农民阶级”出身,对他能够网开一面,别的“地主贵族”为什么就不可以呢?相信吴晗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揪住不放,也没有在曹操的身上做文章,这也是他的“世故”之处。
在《论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吴晗表示,“根据几年来对若干历史人物的总结,对如何评价历史人物问题,提供一下一些初步的不成熟的意见。”话虽然说得很谦虚,但是提出的“意见”却很强硬,而且用的是不容置疑的语气。他说:“还应该特别注意,阶级出身决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原因,必须注意,但决不可以绝对化。有些人却以唯成分论来评价历史人物,这就大错特错了。”不但如此,他还上纲上线地说:“评价历史人物,决不可以拿今天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把古人现代化了,不但歪曲了历史,是非历史主义的,而且也失去了对今人的教育意义。”从“当代”的视角看来,吴晗的头脑是很清醒的,他看出了当时历史人物评价体系的问题,并且予以反对,他提出的观点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但是,吴晗显得过于迂腐,他是从“学理”来分析问题的,而“学理”在很多时候并不关键,尤其是在当时,这恐怕是吴晗没有充分估计到的。他的意见分明就是与主流的评价体系唱反调,而且口无遮拦,直接批评,得罪人是免不了的,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祸根。
1960年前后的历史剧都是借古喻今的,带有很强的政治“影射”色彩,为了适应时代需要,难免对人物和史实进行“加工”。工农兵形象和阶级斗争话语不仅抢占了历史剧舞台,还改造了历史人物。在当时,根据“今天”的观点来表现古人的历史剧比比皆是,还不乏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因为吴越争霸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主题在60年代初受到青睐,关于“卧薪尝胆”的剧本在全国出现了八十多种,曹禺的《胆剑篇》就是其中最为有名的。不幸的是,按照阶级成分来说,主角越王勾践是奴隶主和封建主一类的“坏分子”,所以无法正面歌颂,曹禺只好设置了劳动人民“苦成”来时刻教育、点拨他,结果,勾践“被逼迫”卧薪尝胆,最终取得了胜利。《胆剑篇》是曹禹在1949年后大失水准的作品之一,他当然知道问题在哪里,不然也不会说自己解放后的作品“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原因,曹禺也曾经对访问自己的研究者说:“做人真是难啊!……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能够在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浪中站稳脚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后悔,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于当时的文人们来说,田汉的《关汉卿》可以说是一个讽刺,因为该剧的人物和剧情完全脱离了历史事实,是作者“想象”的产物(关于关汉卿生平和性格的史料很少,而且与该剧并不相符),而“想像”出这样一个为民请命、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的“蒸不烂、煮不透、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一样的知识分子,无疑表现了田汉内心对关汉卿式人物的呼唤。不过即使是一种想象的表述,也不被允许,田汉后来的《谢瑶环》依然是为民请命的故事,但是却被看作对现实的“影射”,大批判文章认为“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田汉的创作生涯也因此终结。可能让读者和田汉都不解的是,他仅仅因为虚构、塑造了“为民请命”的人物就被指摘,而实际上距离真正的“为民请命”还差得很远。因此,当时历史剧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处理史实和评价人物的问题(吴晗为此而“苦恼”),而是如何使自己的历史人物“当代化”的问题,如果可以做到后者,大可不必考虑所谓的“史实”,而这是吴晗所不愿、不能接受的。
由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事关重大,所以吸引了不少人来关注历史剧,其中不乏茅盾这样的没有写过历史剧的大家。茅盾早在1961年第5期和第6期的《文学评论》上分两次发表了十万言、也可以说是他生平最长的理论文章《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卧薪尝胆>的不同剧本说起》,对此问题发表了值得揣摩的看法。茅盾在讨论了《卧薪尝胆》的史料问题之后,笔锋一转,开始讨论理论问题(这恐怕也是他的本意)。茅盾认为历史剧从来就是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但是批评了有的剧本把勾践写成下放干部与民“四同”、大兴水利并请外国专家帮助制造武器、搞“三反”等与现实呼应的现象,他说:“二千四百年前一个奴隶社会的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无论他怎样高明)竟可以影射我们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这不是对我们的诬蔑么?同时,这又是以今知古,严重地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可以说,茅盾是小心翼翼,但是又煞费苦心地试图将历史剧从“现实影射”的轨道上拉回来,并且
不惜给对方扣上“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帽子,不过,他的努力并未见效,“影射”之风反而越刮越烈,并在《海瑞罢官》的写作与批评风浪中达到高潮。
三尴尬的“海瑞”
“翻案”和“影射”都是从当代角度理解历史,在“史剧家的主要任务是在于根据历史真实创造出足以教育今天人民的动人的历史人物形象”“的要求下,“历史”与“现实”常常混淆,这样的要求也使历史人物的评价经常在极短时间内“判若两人”。围绕着发表于1961年,而在1965年成为文坛焦点的《海瑞罢官》的争论,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学术讨论范围内的争鸣,后一阶段则因为姚文元的强力文章而成为“影射”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作,而同一个海瑞。身份也发生了尴尬的变化。仅仅“尴尬”还不够,吴晗当初也未料到,他竟然因为这出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乃至身家性命。
《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发现民间冤情后,决定处死原宰相的儿子,虽遭威胁而不为所动,在为民除害后罢官挂印而去,这个故事的“本事”在明史上是有记载的,吴晗并未发挥,与田汉写《关汉卿》凌空蹈虚是不一样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也是“跟风”戏,因为在剧本发表的前后几年中,涌现出了《海瑞上疏》、《十奏严嵩》、《齐王求将》、《打花朝》、《五彩霞》等不下五十部各类剧种的“海瑞戏”,形成了“海瑞现象”,当然,这与毛泽东在1959年提倡“学习海瑞”有关。在京剧演员马连良约请他写剧本之前,作为明史专家和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已经写了《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等文章,热情赞美海瑞,配合形势。剧本《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1961年1月)发表后,很快被搬上戏台,吴晗的朋友廖沫沙撰文赞扬从未写过戏的吴晗做了“创造性的工作”。《海瑞罢官》塑造的是一个敢于坚持原则和“讲真话”的海瑞形象,也与毛泽东发动向海瑞学习的原意一致,再加上吴晗的特殊身份,因此获得了各方面的交口称赞。在对《海瑞罢官》一片叫好中,学术界也有批评的声音,主要还是集中在海瑞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有论者说:“海瑞迫令乡官、豪强退田和劝农的目的,仍然是恪守着从‘圣贤那里学来的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的‘治世,‘仁政之类的政治幻想。可见,海瑞正是用他所向往的‘唐虞三代之治来抵制农民的反抗斗争,用压抑豪强来制止‘民风刁险。这是封建社会‘清官、‘好官阶级所决定的绝对要求。”标准如此荒谬,而论者煞有介事,真是让人有口难辩或者无从辩起,不过总的来说,作者还是把讨论限定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内。
由江青策划、姚文元执笔,意在摧毁北京市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无疑是击向吴晗的一记重拳,也颇多理论“创新”之处。姚文元说:“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这样,凡是“封建国家”的“官”,全部被姚文元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自然包括海瑞。如此“大手笔”地对待历史人物,甚至一个也不宽恕,实在令人咋舌不已。不过,如果仅对此观点讨论,倒也罢了,说到底是对历史人物的看法问题,但是,最为厉害,也是最为恐怖的是,姚文元一定要从《海瑞罢官》中寻找吴晗写作的动机,他用咄咄逼人的口吻说:“《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把一部作品的实用性强调到相当高度,而且要求一部作品必须要有“现实意义”,是姚文元的拿手好戏,而在“影射”理论下,“历史即现实”的逻辑竟然奇迹般成立,为批评者从字里行间罗织罪名寻找到了游刃有余以至随心所欲的空间。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在当时也遭到了蔡成和的反批评,而且直指要害:“难道姚文元同志要一个明朝的的士大夫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领导农民起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符合姚文元的立场不成?!”蔡文还反戈一击:“要是能象姚文元说的那样当时就能根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广大农民的翻身问题,那末,还要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何用?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何用?”虽然句句说在点上,但是这已经不是讨论理论问题的时刻,他抨击的对象姚文元也不再是理论家。“古为今用”,姚文元抓住这根大棒,将这样的逻辑引用到政治斗争中,并且因为掌握话语权将其发挥到了极致,所有被批评者绝无还手余地。
如果这仅仅是学术争端还罢了,大家可以各自抱定自己的选择相安无事,而一旦学术观点牵涉到现实政治,问题就复杂了。由于庐山会议中彭德怀因“直谏”而被罢官,这个“罢官”就自然带上了“影射”的影子。1965年12月31日,毛泽东在评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正如党内元老之一薄一波所说:“经过毛主席的肯定,《海瑞罢官》这出戏,不仅成了所谓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而且升级为所谓直接代表彭德怀等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严重问题了。”一旦被绑上政治的战车,胜负便无法由自己掌控,《海瑞罢官》只能在政治风浪中漂浮,完全不能自控。
在吴晗、邓拓、廖沫沙组成的“三家村”必然要被“打倒”的态势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无法被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甚至,如果谁主张在学术范围内讨论问题,就会被怀疑别有用心,包庇对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反动阶级。有的批判文章要求“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你们在前几年里放出了大量毒草,恶毒地攻击党,反对社会主义……在对《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后,你们又发表向阳生即邓拓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力图把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纯粹”的学术领域中,力图把这场大辩论拉向右转,难道这是放松了阶级斗争吗?不是!这正是你们站在阶级斗争方面对无产阶级加紧进行阶级斗争!”海瑞从为民做主、敢于直谏的清官一下子沦为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动人物,这个“翻案”文章实在是蹊跷,但是,却在情理之中。树欲静而风不止,或者说,目的就是把树连根拔除,这时候,以个人力量抵抗权势的海瑞和“海瑞精神”显得如此苍白和空洞。在这里,海瑞无法是海瑞本身,只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新编“历史剧”不从史学证据考虑历史人物“是什么”,而以当时的阶级标准和现实要求来决定他(她)“应该是什么”,所有身在其中的作家都对“戏说”无可奈何,甚至争相“戏说”。在对“历史剧”讨论的梳理过程中,除了更为深切地意识到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说法的“恐怖”之处外,还不得不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掬一把同情之泪,他们可以任意扭曲历史,但是却始终无法对接上现实之榫,因此,他们只好窝囊、耻辱地成为“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