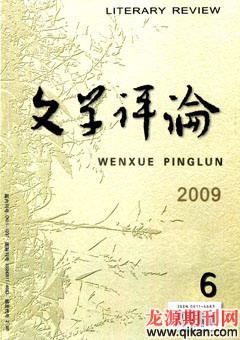清初古文三大家理论探析
张修龄
内容提要:清初散文以理论、创作见长者,还数侯方域、魏禧、汪琬“古文三大家”。三家均为由明入清的文人,因合集《国朝三家文钞》(宋荦、许汝霖辑刊)而得名,辑者宋荦以为清初“文学蔚兴,上之卿大夫、侍从之臣,下之韦布逢掖,争作为古文诗歌以鸣于世,绘绣错采,韶渡以间”,“三君际其时,尤为杰出,后先相望,四五十年问卓然各以古文名其家”。《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称扬此三家,侯方域为“才人之文”,魏禧为“策士之文”,汪琬为“儒者之文”。清初三大家在当时古文领域颇有建树,且风格各异,不仅使清初传统文学增色不少,而且为散文的发展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然而相对于诗词等理论著作而言,“关于文章的评论,历来缺乏专著”,而清初三大家的论文诸说,却为清初乃至中国古代的散文理论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要件。
文章和道统
自唐代古文运动以来,“道”便以儒家道统见世,成为古代散文理论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理论的基础。贯道也好,明道也好,或说载道也好,自此开始“道”几乎成了复兴古学、写作古文的宗旨或前提。这固然有扭转齐梁萎弱文风,包括摈弃骈文风气的因素,更有文以恢复儒家传统、重振圣人之道,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涵义。
宋代周敦颐提出了著名的纲领性观点“文所以载道也”,宋代理学家、文学家可说鲜有不以道为论文之宗旨者。明唐宋派文人重拾载道说,以八大家为法乳,而其精髓即在“道”。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孔子之所谓‘其旨远,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牺以来人文不易之统也,而岂世之云乎哉!”王慎中《与林观颐》:“古文者,非取其文词不类于时,其道乃古之道也。”学古不在于古之时,而在于古之道。时可变,而古之道是不变的。归有光《雍里先生文集序》:“夫道胜,则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胜,则文不期多而自多。溢于文,非道之赘哉?”唐宋派文人的文道之辨。是唐宋以来对文以载道说的理性化和实用化。
清初三家同样强调“道”于古文的主导作用。在三家中,侯方域相对更具鲜明的个性色彩,但侯论文也口不离“道”。在侯方域看来,“君子忧夫道之不彰,不忧夫身之不遇”,而世人多有“以圣人之道而营锱铢之利”者,往往“借圣人之道以自成其私”。侯方域以为“道”远重于“遇”和“利”,而文也就不应为“遇”和“利”而作,“学者之为经书之文,非如他体之文,求以名世已也,盖代言而述圣贤之旨,思以翼道也,是鹄焉”,明确说出了学者之文,能合侯氏之意而得其赞赏的,就是能“述圣贤之旨”,能“翼道”者。
魏禧在《愚山堂诗文合叙》中表述文道关系时,一方面将“道”视为圣人之道,倡导文人当学“圣贤之道”。使诗文“原本道义”,一方面强调“文”应以其实际内容及功用去“载道”,也就是说“惟文章以明理适事,无当于理与事,则无所用文”,基于此,方能确定“文者载道之器”(《恽逊庵先生文集序》)。魏禧的高明之处在于既认同“道”的正统意义和学理渊源,又赋予“道”以适时性和实践性,使文章所载之道,最大限度扩大了其涵容的范围,也给了古文以更加多元的发展空间,正如其《论世堂文集序》所称:“人之能载万物者,莫如文章,天之文。地之理,圣人之道,非文章不传。”
魏禧还以为古文虽能载万物,但有道之文还须注意简洁,其《八大家文钞选序》称“文章之根柢,在于学道而积理”,而“理明者辞必简,议论多则意见乱,而自相抵牾者必甚”。为魏禧所极力赞扬的汪琬、施闰章。“二家独划除一切浮腐之言,而左规右矩,与古人不失尺寸,此其所以难能也”,正是学道日久以后,才能做到“无自矜厉之气,其誉人也无过情之辞,绸缪往复,亦未尝自过其情”(《愚山堂诗文合叙》)。和侯方域相比,魏禧论道已显然具体化了,接近桐城古文之论者,也即文章须“雅洁”。
当然三子中强调载道最为直接和明确的还数吴中的汪琬。汪琬反复称说古文家为文务先“博且专”于“经”而“深于道”,学做古文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感悟的过程,即使长时间读韩欧、习六经,尚且不免“所得者或狃于才气之偏,所见者或出于聪明之臆,求诸圣贤之道达于日用事为,而根柢于修己治心者,概未有合也”。也就是说,假如“不精求道之大原,而区区守其一得之文,自以为察之皆醇,而养之皆熟”,自然是不可取的。这种浅尝辄止的态度造成学文难成,而根本原因就在“不精求道之大原”。学文者对道的深入理解,不仅取决于有否读经及读经数量与时间的多寡,更在于要与“日用事为”的实践、“修己治心”的涵养紧密相连。很明显,这与韩愈的培育道德修养、欧阳修的事关百姓日用的说法是一致的。可见,精求道之大原取决于在研读经典的基础上注重内修和加强外用的投入,否则即使“尽发其所藏六经三史,详读而细绎之”,仍会发生“其识不能穷义理之微,其才不能达古今之变”(《与王敬斋先生书》)的后果。
汪琬崇道,并扩大道的内涵,拓宽达道的门径,认为“古之作者其于道也,莫不各有所得,虽所见有浅深,所从人者有彼此,顾非是则其文章不能以传,虽传亦不能及于久且远”(《洮浦集序》)。汪氏道同而文异之说,是对曹丕“本同而末异”论运用于古文领域内的阐释,不仅坚持了道于文的决定作用和本初意义,而且赋予文以相当的独立性,凡文能尽道之变,“极文章之能事”,即可视之“与昔贤谓文章与道同一关捩”。汪琬正是从更广阔的范围内探索文道关系,自信在深植根本、旁搜远绍的基础上,便能使古文进入前所未有的驰骋空间,其于《同生说》云:“亦如富家之有田亩也,故必惫精竭神以耕且获于其中。惟其取之也多,养之也熟,则有渐摩之益,而无剽贼之疵,有心手相应之能,而无首尾舛互之病。浩乎若御风而行,沛乎若决百川四渎而东注,其见于文者如此,则亦庶几乎其可也。”
六经与义理
清初三家对儒家之道的认同,程度有深浅,表述有差异,但都在强调道是文之本同时,认定六经是文的源头,也是道的原初载体,而后世文缘何使道统长存,则因其义理贯通内中。后世文虽其形式已不同于六经,但内中义理却始终未变、一以贯之。六经固然是前圣精心结撰而成,但六经毕竟时代相隔已经久远,须仰赖内中义理而流布后代。于是,文章须宗经而不受经书之拘限,除了上文提及的联系日用、博采广取之外,还取决于能否辨识贯通于六经中的义理。所谓义理,便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之上以文的形式表达出的精要内核,大体包含与社会相关的常识、道德、学理、功用、原则、秩序等等。
魏禧在《宗子发文集序》中曾对六经和义理的关系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魏禧认为“六经四书而下,周、秦诸子、两汉百家之书,于体无所不备,后之作者,不之此则之彼。而唐、宋大家,则又取其书之精者,参和杂糅,熔铸古人以自成,其势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诸大家后,数百年间未有一人独创格调,出古人之外者。”假如后世文者只能模仿古人体制,依样画葫芦,虽未偏离古圣正轨,然而面对“古
人具在”,也即六经等仍流传于世的情状下。再多的“徒似”之作,只是“劳苦后世耳目”而已。魏禧的结论是“吾则以为养气之功在于集义,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这就从道德、文章两个方面提出了魏氏的“义理”说,而“养气”历来就是传统儒家关于在道德修养上下功夫的要论,“文章”之精髓则在能认识“耳目所见闻,身所经历”之“所以然之理”,做到既依乎古圣又自成面目。
在魏禧的古文论说中,曾反复申言学文须“积理”、“明理”。“积理”之说已见其《宗子发文集序》,在《答曾君有书》中,魏称“明理而适于用者,古今文章所由作之本”;在《论世堂文集序》中,魏以为“六经之文”因“气未尝绝”而传后世,“气”则“必资于理,理不实则气馁”,其《裹言》又云:“文章不朽,全在道理上说得正,见得大,方是世间不可少之文。”正是弄清了古往今来天地万物之所以然的道理,才能写出非见之六经,却完全合于六经的好文章,才能将含蓄之旨、难言之意诉说明白。魏禧于通达古人文章之“理”,表述了自信信人的心得:“《日录》是吾积理之书”,“汝学文须学古人文,不当以古人子孙为祖父。然同时人情事相比近,吾可得知用意力处艰难所在”(《与诸子世杰论文书》)。这里魏禧强调学文须学古,不可认孙为祖,还可广览包括“同时人”所作的各类篇什.“得知用意力处艰难所在”,也就是从特殊中读出一般,深知欲明欲积之“理”。魏禧于文章义理之所自及所在,理解可谓透彻。
汪琬作为恪守儒道的古文家,于文倡导根柢六经、深识义理,以此为其古文理论基础。汪琬称:“先儒云,经非文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经,又不足谓之文。”(《三衢文会记》)计东推扬汪琬之文,高度肯定其作文之要旨:“必根柢于六经”,并能“窥测于道之原”。汪琬本人所论,也应合了计东的认定,他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谈及虽读经却不得尽探义理的教训,这样便难以取得文章的成功:“从容闭户,尽发其所藏六经三史,详读而细绎之,则又其识不能穷义理之微,其才不能达古今之变,虽时时惫精疲思,作为文章,以求发摅其感愤不可如何之心,而蹇涩陋劣,卒无以进希作者之万一,宜在摈而不录之列久矣”(《与王敬斋先生书》)。汪琬试图说明的是“识”与“才”对于理解经史所起的关键作用,但还是间接道出了透析义理方是读经的目的所在,也是作文的必要途径。在汪琬那里,能将道统、文统合二为一,做到“嫠剔义理之丝微,钻研问学之根本,能以其所作进而继孔子者”,唯有朱熹一人,而朱熹后五百年能继之者则就数王敬哉(崇简)先生了,因为王氏之文“其辞质而赡,其义简而明,求诸文公诸书无所不合”(《王敬斋先生集序》)。汪琬于王崇简不无过誉之词,但其中追溯六经之原、深究义理之微的古文观是十分明显的。
汪琬视六经为文之根柢,那么贯通于六经中的“义理”自然对文章产生着决定性作用,鉴于此,汪氏特拈出“义理”、“经济”,“诗歌古文词”为治学所尚之三途,且以义理和经济为诗文之原:“予谓为诗文者必有其原焉,苟得其原,虽信笔而书,称心而出,未尝不可传而可咏也,不得其原,则饤饾以为富,组织以为新,剽窃摸拟以为合于古人,非不翕然见称一时也,曾未几何而冰解水落,悉归于乌有矣!是故为诗文者,要以义理、经济为之原”(《拾瑶录序》)。这样,诗文赫然与义理、经济同列,但又分出三者的层次,既确认诗文受制于义理,义理不明则文章难传,又不给小看辞章者以口实,“若诗若文,谓之学者之绪余可,谓之小技不可”,朱熹就是一位“理学之祖”而“诗文最工”者(同上)。在另文《愿息斋集序》中,汪琬表达了差不多的意思:“义理之学,一也;经术之学,一也,史学,一也;辞章之学,又一也”。
据上我们不难发现的是,汪琬所论,无论在问学之途、辞章之原,还是在文苑之祖等方面,都已经为其后的桐城派定下了初步的理论框架。
清初三家中侯方域论古文涉及儒道、经义者相对较少,有的论者批评论侯文这方面的欠缺处:“使天假之年,穷究理要,博极群书”云云,恰是说侯氏于六经义理未能深究的证明。对此,侯方域似乎也有自责:“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人之旨”(《与任王谷论文书》)。不过,侯方域也还是以“经术醇雅”作为文章的正面价值的,而且还提出作文要“发扬于理,变化于自然”,做到“达于理而无杂揉之病”(《倪涵谷文序》)。可见,即使如侯方域这样的使才纵气者,同样希望明义达理以使文章行古人之道。
才气与学识
在探寻并力图解决古文与道、与经的基本关系问题后,清初古文三家比较注重文家个人才识的培育和累积。内蕴的道统和经义,还须有独特的才力、气势而外显,还要依仗丰厚的学养和识见来表达,这些都是古文家不可或缺的条件和素养。三大家正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理论阐述。
侯方域论文好谈“才气”,曾反复申说“文之所贵者,气也”(《答孙生书》),并借苏轼“风行水上者,天下之至文”之论生发开去,以为“风之所以广微无间者,气也”(《倪涵谷文序》),正是气御风而行之水上,吹动着无边的涟漪,而文之至者,如同风拂动万物般地感人心扉、润人心田,好的文章以其气息无往不至、无间不人,发挥其充溢四处的感染力。文气因人而异,但不变的是沛然于文家心胸的道德力量和个性质素,而气“必以神朴而思洁者御之”,还须“多读书”,仰仗“道力”而行之(《答孙生书》)。在《倪涵谷文序》一文中,侯方域还强调为文“必先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以才“扶质而御气”,最终使文章之道得以贯行。“才”与“气”的连称,不时见之侯的理论阐述中。在《与宋公子牧仲书》中,侯方域称宋荦克似其先人,“守道读书”,凭其“才气超轶”,必定“何施不可”?侯方域在理论上高调倡言“才气”,并以才气贯注于古文创作中,其文“以气胜”,其文为“才人之文”,已是时人的共识,其文坛地位也缘于“才气”而被肯定:“天才英发,吐气自华,善于规模,绝去蹊径,不戾于古,而亦不泥于今。当时论古文,率推方域为第一”。
侯方域论“气”还反映出个人的好尚,侯在《与任王谷论文书》中称:“大约秦以前之文主骨,汉以后之文主气。”“汉以后之文,若“史”,若“汉”,若“八家”,最擅其胜,皆运骨于气者也。”相较于先秦诸子和《左传》、《国策》等“敛气于骨者”,“运骨于气者,如纵舟长江大海间,其中烟屿星岛,往往可自成一都会。”这也就是“韩欧诸子所以独嵯蛾于中流”的原因(《与王任谷论文书》)。侯方域显然吸取了明七子取径过高的教训,即没有像李梦阳辈欲效“敛气于骨”之文而终遭“蹶其趾”(同上),而选择了由“八家”人手,追攀《史》《汉》之学文路径。在这一点上,侯方域虽有其论文主见,但终究与魏、汪等殊途同归,汇入了清初学唐宋八家文的潮流。正是以学八家为古文门径,侯氏所作常被看成得韩欧之气,如徐作肃评其《孟仲练诗序》日:“大段是欧,然全欧之神兼韩之气以驱遣处,劲而肆也。”宋荦评其《郑
氏东园记》曰:“其机轴从韩来,丽气全用欧。”
相比之下,侯方域谈学识之论较少见其集中,这也是侯氏在学界获负面评价的主要因素。李慈铭曾评侯方域称:“朝宗文,气爽而笔灵,颇有飞动之观,惜根柢太浅,不学无术,多近小说家语耳。”平步青于侯亦有“学不逮才”的断语。不过侯方域并非完全摈弃学识,文中也常会提及之,如《贾生传》称贾“学术行业恢奇荡漾,适于致用”,《颜真卿论》又以为颜“之学术独见其大,固唐三百年之一人”。而侯自作《赠丁掾序》也被誉称有“何等识见”(徐作肃评语)。可知侯方域对于学识还有其独到的理解,那就是学应“适于致用”,学应似颜真卿般致力于经国济世,还要能“说到古今政治大关头”(同上)。
魏禧也是一位好论“才气”的古文家,每言及“才气”,多以纵横超迈者为高,如论“少年作文”,称。当使才气怒发,奇思绎络”(《与友人》);论友人孔正叔,赞其“少负才,气岸峻峭,有笼罩一世之概”(《孙正叔楷园文集序》),于三家之一的侯方域,虽认为有“是非多,爱憎失情实”之处,但对其“才气奔逸”还是肯定的(《任王谷集序》)。就“才”而言,魏禧认为“才人之文扬以急”(《张无择文集序》),又将“波澜激荡”视为“才士之文”(《裹言》)。由于魏禧受清初文尚劲肆风气的浸染,所作未免“才杂纵横,未归于纯粹”,表现出理论和创作的某种一致性。但魏禧还是有纠偏意向,对一意恃才而行的文章格调有所保留,因而更多的将论文重心落在“气”上,以为“才与理者,气之所冯,而不可以言气”(《论世堂文集叙》)。魏禧呼应苏轼所云“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气也”,以为“才于气为尤近,能知乎才与气者之为异者,则知文矣”,也即懂得养气,懂得培植根本,才算得上“知文”者。而“世之言气,则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穷,动而不止者当之”,有了这样的“气”,才能承载圣人之道(《论世堂文集叙》)。魏禧论气,与侯方域之说不无相近之处,且所为古文“易为纵横”,也正与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魏禧与侯方域不尽相同的文论主张,则可从两人对学识重视程度的差异上看出。魏禧文集中论及古文与学识关系的篇目甚多,其《答蔡生书》回答门生问古文之学时,提出“博观史传,以极古今人情事物之变。读古人书,卓然成一家言者,以辨文章之体。或综其要会,自立机轴。不必求合古人,或资学所近,诵而法者一人,冥心以求其合,则固惟人之所自处也”。“独识力卓越,庶足与古人相增益”。说的是写好古文,必须广泛阅读古书,得其要领,又要加强识力,于古人有所增益。其《与毛驰黄论于太傅书》又明言“文当为博文,又虚心好学问”。并以“识议卓荦”为追尚,唯此方能学有所本,识有所创。在《又与汪户部书》中,又标榜自己增进学识的态度:“惟能虚心以受师友之教”,无疑亦为求学箴言。此外,魏禧还著文从反面讨论学识,如“有其志无其学,有其学无其识,有其识无其事,则文皆弗极于工”(《恽逊庵先生文集叙》),如“志识卑陋,不出米盐杵臼之间,及夫临文,拘牵万状,首尾冲决,是其终身所经营,意皆在于速朽”(《王竹亭文集序》)。学识的缺失或卑陋,都无助于文意的表达和圣道的承载。魏禧论才气和学识自有其独到的见解,其“真气”说以为“今天下之文最患于无真气”,“易直淳古”之人,往往“其文多真气而又深于古人之法”(《任王谷文集序》);其论治学,义域极广,且含经世致用之意:“至于治学。则天下事无一不在其中,非有圣作明述之智,文武将相之材,鲜有能兼总而条贯之者”(《答曾君有书》),体现了魏禧传承晚明文学的尚真精神及在清初开启实学风气的理论特色。
在清初文坛,汪琬虽以醇正尊法而得文名,但同样好就才气、学识大发议论。汪琬《答陈霭公论文书一》较详尽深人地探讨了才与气在经史诸子乃至唐宋古文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仆尝遍读诸子百氏、大家名流与夫神仙浮屠之书矣。其文或简炼而精丽,或疏畅而明白,或汪洋纵恣、逶迤曲折,沛然四出而不可御,盖真不有才与气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气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读之者动心骇魄,改观易听,忧为之解颐,泣为之破涕,行坐为之忘寝与食,斯已奇矣”。“夫文之所以有寄托者,意为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与气举之也”。汪琬认为以文学性见长的散文须“才雄”“气厚”,文意须凭“才与气举之”方能打动读者,产生感人的力量。魏禧曾视汪琬为“醇而未肆”,而且认定汪文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答计甫草书》)。固然汪琬有其“不敢肆”个性弱处,但至少在理论上对宏肆、雄厚的才气做出了肯定,其赞扬金声“大率以灏瀚之气、雄放之才、沈幽哨拔之思,驰骋上下”(《金正希先生遗稿序》),推崇李振裕“其才益高,学益博,见闻益雄阔宏肆”(《白石山房稿序》)。至于宏肆、雄厚的才气缘何而生成,汪琬在《与周处士书》中将之归结为得自六经及韩欧古文:“仆于词章之学,本无深解.三四年以前,气盛志锐,好取韩、欧阳诸集而揣摩之”,后又“退而复取韩、欧阳集,伏读而深思之,未尝不叹其才识之练达,意气之奔放,与夫议论之超卓雄伟。真有与《诗》《书》六艺相表里者,非后世能文章家所得望其肩项也”。
在古文与学识的关系问题上,汪琬所论和侯、魏相比,同样主张广博和实用。汪琬在《洮浦集序》中倡导“为学自六经诸史,旁及稗官野乘、天文地理、尔雅本草、浮屠老子之书,无所不究”。其《治生说》更进一步指出丰厚的学养是古文写作的基本条件:“为学亦然,举凡《诗》《书》六艺,诸子百家,吾所资以为文者,亦如富家之有田亩也,故必惫精竭神以耕且获于其中”。在广泛问学的同时。蕴育“周详博大之识”(《与梁御史论正钱録书》),弄清“天人贯通之旨”、。王国盛衰之原”、“所以致治之大本大用”(《王敬哉先生集序》),目的自然在于经世济国,并“用以扶翼人伦,开示后学”(《答顾宁人先生书》)。归根结底,汪琬古文观念尽管在才气论和学识论方面,大致应合了清初散文肆而博的整体趋向,但其正统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最终还是力图将古文纳入醇厚有道的正途,以有助于“出仕于朝”时有所“成就”。
学古与法度
清初三大家的古文理论除上述数端以外,对学古的目标、古文的文法等也都有明确的阐述。三家的学古楷模大致集中在汉马、班,唐韩、柳,宋欧、苏、曾,王,明归有光等主要家数。侯方域、魏禧、汪琬在各自的文集中差不多表达了相同的祈向,侯方域称:“汉以后之文.若《史》,若《汉》,若‘八家,最擅其胜,皆运骨于气者也”,而“韩欧诸子”又为“所以独嵯蛾于中流”者(《与王任谷论文书》)-魏禧以为“韩愈、李翱诸人崛起八代之后,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欧、苏诸人崛起六代之后”(《杂说》)。而汪琬更以切身体会为唐宋八家文张目:“取韩、欧阳集伏读而深思之,未尝不叹其才识之练达,意气之奔放,与夫议论之超卓雄伟,真有与诗书六艺相表里者,非后世能文章家所能望其肩项也”(《与周处士书》),还特别推崇宋四
家:“同时以文章名世者,世必推欧、苏、曾、王四家”(《白石山房遗稿》)。于明代唐宋派及归有光,三人也皆有赞词。以此有论者便将三家视为明唐宋派、归有光之后继者,应该说也不无道理。当然侯、魏、汪三人推尊上述古文先导,每人各有侧重,或出自文当载道的认识,或缘于文须经国的诉求,也有因艺术精神上的灵犀相通而高唱唐宋古文风调的。
除了学古的方向,目标,清初三家对唐宋文家的褒扬包括到了具体的方法,摆明了向谁学,怎么学的理论问题。三家中虽说一般以为汪琬最为守法,邵长蘅《三家文钞序》就提出“汪氏以法胜”,汪琬本人也说:“如以文言之,则大家之有法,犹奕师之有谱,曲工之有节,匠氏之有绳度,不可不讲求而自得者也。”(《答陈霭公书》)提出作文须把握开阖呼应、操纵顿挫之法。侯方域于文不拘法,主张为文“必先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而所谓“法”,即“气之达于理而无杂糅之病,质之任乎自然而无缘饰之迹者”(《倪涵谷文序》),如此而已。三家中论文法的相关文字最多者当数魏禧,魏氏从法度之必需,到变法之必然,都有周详细密的论述。其《寄诸子世傲世俨》云:“要合古人法度,文成乃粲然可观”,其《答计甫草书》亦云:“古人法度犹工师规矩,不可叛也。”只是魏禧论文法的高明处在于。不孜孜求古人之法”(《伯子文集叙》),而是强调“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无所有,其弊为优孟之衣冠”,恰恰是“变者。法之至者也”(《陆悬圃文叙》)。魏禧已经吸取了明人学古墨守成规、句模字拟的教训,力求不致重蹈学古而不知变的覆辙。在《日录》中,魏禧则从文章的结构层次、遣词造句、繁简离合,高低抑扬等方面,深入地指出文法的精妙之所在和无穷之变化。
清初三大家亲身经历了明清易代的风云变幻,也感受到了明末清初文坛的兴衰成败,侯方域、魏禧、汪琬作为卓有成就的散文理论家,尽管观念有异同,学业有专尚,加以区域相隔、意气相左,但是终究结合各自的创作实践,为清初散文提供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清初三大家通过数量众多的专论、序跋、书札等,对古今散文的师法对象、历史传承、主客要素、正反案例、观念冲突作了全景式的展示,此后桐城派的兴起,唐宋文的流行,乃至正统文言文的体面谢幕,均与清初三大家的理论建树有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