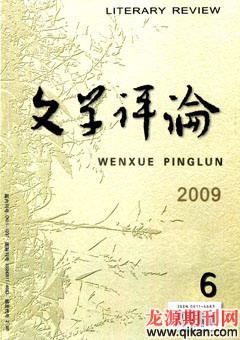诗史互文关系索解
田 蔚 史小军
内容提要:历史文本与诗歌文本在文体上虽有不同,但“史蕴诗心”,二者的互惠融通形成了文本上的互文关系。本文以同时含有“单于遁逃”这一情节的《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与唐代卢纶的诗歌Ⅸ塞下曲》(其三)为例,从语言、结构的转化上进行了互文性关照,并分析了形成这种互文性的主要原因:历史叙事文本与诗歌文本所处历史语境的契合使文本间的对话成为了可能,它们在话语叙述中所受到的想象与情感的制约以及读者在阅读时对文本的文化记忆是文本意义转换并进而形成互文关系的重要因素。
《史记》中的《卫将军骠骑列传》(以下简称“《卫霍列传》”)是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两位将军的合传,书写他们因外戚身份而青云直上、因征讨匈奴而裂土封侯的历史。传中的“漠北大战”十分引人注目,卫青率军深入大漠穷追匈奴,单于在混乱中逃跑,与自己的部属失去联络,以致匈奴的右谷蠡王以为其已身死而自立为单于。这次大战被认为是“平城以后第一吐气之功”,奠定了汉匈多年争战以汉朝得胜而结束的基础。司马迁在《卫霍列传》中对漠北大战战局、场景的描写,开启了唐诗诸多沙场点兵鏖战的佳篇。唐代诗人卢纶的组诗《塞下曲》(六首其三)“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以下简称“卢诗”)明显即是借用此事。
如果我们以《卫霍列传》的散文片段作为前文本的话,那么卢纶的诗歌可以被视为后文本,是对前文本的再阐释。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认为,后人对文本的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对象文本(前文本)和认识主体都处在各自历史的不停发展演变之中,后人的理解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原意,而是通过创造性的努力,将各自拥有的视界融合后的产物。借用西方的互文性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解读这一有趣的文本现象。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是非自足非封闭的,“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不是仅由作者一个人可以决定了的,它是在动态中不断与文本内外诸多元素发生联系的过程。基于此,笔者拟对这两个都含有“单于遁逃”情节的文本从语言、结构的转化上进行互文性关照,并进而分析形成诗史互文的原因所在。
一后文本对前文本的引用转化之表现
在《卫霍列传》中,司马迁对历次汉匈交锋的具体过程都是以“击匈奴”、“三万骑击匈奴”、“咸击匈奴”等类似的语词简略交代而过,唯有对元狩四年的“漠北大战”做了详细的叙述。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大军深人大漠围击匈奴,卫青所率之军与单于军队正面相遇。传中这样记述道: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馀里,见单于兵陈而待,於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赢,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挈,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馀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馀级,遂至寞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馀粟以归。这段历史叙写基本上是将“漠北大战”的具体经过展示给大家。有评论家认为司马迁一反平常不对战事实写细叙的笔法,而是“写得气势飞动,层折历落,与《李将军传》一样”。与《李将军传》一样之处就在于司马迁仿佛亲见闻之一般地极力摹写,写出汉匈双方厮杀之难分难解、交战时间之长、场面之惨烈,如在目前。
作为后一文本的卢诗借用了历史中的这段叙事,在重复表达前一文本的内容时进行了改变和转换。首先在时间上,《卫霍列传》中司马迁清楚地写明“日且人”、“薄暮”、“时已昏”、“未昏”、“迟明”等时间词语,根据明晰的时间发展线索,所有词语汇合交织出历史事件完整的动态过程,而卢诗则在一开始就点明时间“月黑”,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单于遁逃”,“夜”即说明单于是在黑漆漆的夜色掩护下仓皇逃窜。其次,对双方交战时的天气条件做了改变。列传中是“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大风夹杂着沙砾无情地击打将士的脸颊,沙漠气候条件相当恶劣。而卢诗中的天气条件是塞外“大雪”飘洒而下,笼罩着天地。
除以上两点之外,卢诗中最重要的转换在于情节处理上的不同。列传中叙写匈奴单于发现汉军兵多强壮难以取胜时,就在薄暮时分与几百余名随从冲出汉家包围圈,向西北方向驰去,直到天色渐黑两军杀伤相抵时才被汉军发觉逃脱。汉军急行二百余里,追了一夜直至天亮也没有抓住单于,但也收获颇丰,算是全胜而归。卢诗在得知“单于遁逃”时,集合将士们出征之际却遭遇了漫天的大雪,纷纷扬扬的大雪非但没有造成追击上的困难,反而增加了骑兵们出征的壮美威武,至于追赶与否、追上与否都已置之不论,也已无足轻重。作为后续文本的卢诗在继承保留“单于遁逃”的情节点后,改变了前文本中的时间、天气等外在因素,放弃了前文本中对完整情节的记叙,历史记述中战争的真实、严酷与惨烈转变为环境的静谧与雄奇,马踏嘶鸣、喊杀号角之声已成为遥远的历史背景,存活于读者对远去历史的回忆之中,从而表达出对将士们上马追击逃敌的天纵豪情的赞美。
二前后文本的意义生成及语言、结构分析
作为后文本的卢诗的意义是怎样生成的呢?我们先从语言角度分析其作为前后文本载体的特征。海德格尔曾言:“语言是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塞下曲》以五言二十个字完成了对列传中“漠北大战”二百三十九个字史实的重新建构与编织。名词性意象“月”、“雁”、“单于”、“夜”、“轻骑”、“大雪”、“弓刀”,在两个形容词“黑”、“高”和动词“飞”、“遁逃”、“欲将”、“逐”、“满”的串连下,运用意象的叠加法增加了语言张力,加之动词本身的情态指向,泼画出一幅黑白对比分明的塞外奇美画面,烘托出军队紧急出征的昂扬士气。有人说日常语言在走路,而文学语言在跳舞,关注的是自身而不是外在的某个目的,“在诗中,意象不仅仅是装饰,而是一种直觉的语言的本质本身”。卢诗以意象的精心择取和叠加来达到意义的生成,意象的涵容性、时间上的跳跃性构成了诗歌内在韵律的起伏跌宕,豪情喷薄,昂扬其间。而《卫霍列传》中叙事语言朴拙、质实,在实录的叙事原则下遵循的是时间的线性流淌和事件的按顺序发展,有起始有终点。
前后文本在结构上对现实内容的处理上也有不同。在结构安排上,“单于遁逃”这个历史情节的使用是诗歌获得意义的关键。情节是现实内容进入文本的方式,诗歌不同于散文之处就在于它所特有的观察和理解现实的方法与手段,散文讲究情节头尾的完整性,而诗歌的结构则不必担负这样的职责,它只需实现哪怕是刹那间的情感自足和圆融一体。“单于遁逃”这一事件本身在《卫霍列传》中是作为“漠北大战”叙事链条中的一环而存在,是唯一出现的一
次对汉匈交战情形的具体描绘。而“右卫而左霍”,既肯定与赞扬卫青创立的不世之功,又有对卫青、霍去病等大将阿附天子之意的隐约微词。清人姚芋田评道:“大将军深入穷追,战功最烈,又且因粮于敌,使幕南积聚一空,又且单于跳身苟免,使其众不知所在,汉威已极,此平城以后第一吐气之功也。及孝武以亲幸骠骑之故,务欲其腾踔而驾青之上。因令其徒部代郡,独当单于,又悉配以敢战深入之士,迨单于适与青值,绝幕穷追,而骠骑反得以斩级搴旗之功,从容而收其利,因而菀枯势异,显晦顿殊,此亦绌伸之际,不得其平之极致也”、“于去病之功,悉削之不书,而惟以诏书代叙事,则炙手之势,偏引重于王言,而裹革之忠,自铭劳于幕府,其轻其重,文人代握其权矣”。清人姜宸英也持此说:“传叙卫战功,摹写唯恐不尽,至骠骑战功,三次皆于天子诏辞见之。”究其用意,当是出于纪功的考虑,尊重秉笔直书的历史实录原则。在《卫霍列传》中,当书写将军们因战功煊赫而高奏凯歌、受赏封侯的热烈之中,也有“汉匈奴相纷挈,杀伤大当”、“颇捕斩首虏万馀级”、“悉烧其城(匈奴赵信城)馀粟以归”、“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人塞者不满三万匹”的冷静叙述文字的潜在微词与之相并行。“单于遁逃”的记叙并非没有引起司马迁情感世界的波澜,这种历史叙事背后的情感指向是复杂的,既有“使千古以下,犹若身在行间,闻鼓击而搏髀者”的豪情荣光,也有对武帝连年穷兵出塞、侈心武功的不满。这些情感指向都是附着根基于漠北大战上的相关因素。
而在诗歌文本中,“单于遁逃”事件的背景已经被悄然更换。“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将黑漆漆的夜晚与逃跑行为的鬼祟连带渲染书写,遁逃时间上的改变,戏剧化了单于的出逃行为,暗含了汉家将士们的嘲笑与洋洋得意。这一情节结构的变易消失了前文本中战争场面的艰苦卓绝,放大了汉家军取得胜利的自豪甚至睥睨而视之情,前文本中单于“直冒汉围西北驰去”的军事突围被戏拟成后文本中单于狼狈而又滑稽的逃命举动。诗歌改变了先行文本《卫霍列传》的原意所指,感情内涵也已有所不同,战争的严酷、风沙四起的塞外在司马迁的笔下具有沉重苦涩的历史感,而卢诗则将主动展示的塞外风光和战士即将上马追击逃敌的英姿气概相结合,选择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意象“大雪满弓刀”,稀释冲和了“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所带来的叙事上的粘滞感、紧张感,以白茫茫一片大雪落满了弓刀亦笼罩了天地而结束全篇,诗歌的情感表达在整首诗的上升点上产生了悬停,进一步刺激着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令读者在浪漫崇敬之情的延宕中回味军士出征之威武雄壮。历史文本的一个情节就这样在诗歌文本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增殖,并借用人所共知的历史事件的张力获得了语义上的极大丰富,诗歌文本的情感内涵和意义所指已是在借鉴之后的重新生成。
三前后文本意义转化及形成互文的原因
为什么卢纶的诗歌要吸收这个历史文本并进行重写?二者形成诗史互文关系的原因何在?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前后文本所处历史语境的契合使文本间的对话成为了可能,文本对文化空间的不同参与性是其意义转化的首要原因。我们知道,“互文性与其说是指一部作品与特定前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之中的参与。一个文本与各种语言或一种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本与为它表达出那种文化的种种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间的关系”。而司马迁笔下“单于遁逃”的含义与《史记》所参与的历史文化语境相关。《卫霍列传》的书写与分列于其前后的《匈奴列传》、《李将军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集体构成了对大臣武将们“阿天子意,摧百万之命,取无用之功,使天子意益侈大,东拔朝鲜、秽貊,南诛两越,西通月氏大夏,而汉卒以大困”的历史解析。
相比较来说,作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虽身处中唐,诗歌《塞下曲》却无疑具有盛唐气象,后世人评之“有盛唐之音”、“气魄音调,中唐所无”。通览唐诗,其中不乏有对汉室与匈奴战事以及“单于遁逃”的引用,如高适《燕歌行》、李白《从军行》、王昌龄《九江口作》、戎昱《塞下曲》、储光羲《次天元十载华阴发兵,作时有郎官点发》、张仲素《塞下曲》、李益《拂云堆》、李希仲《蓟门行》,等等。众所周知,唐朝的边疆民族关系主要集中在与突厥(可汗)、契丹、吐蕃、回鹘等上,“单于”早已不是唐朝边塞的劲敌,但对“匈奴”、“单于”的引用却从数量上明显多于前者。很明显,这些唐诗共同形成了一个场域,其中的“单于”已经是一个进入了诗歌文本的符号或载体,作为汉唐时期被武力讨伐的对象,“遁逃”则具有获得讨伐战争胜利的豪迈喜悦、期冀边境安宁的情感指向。诗人卢纶曾深入边塞幕府,具有乐观积极的用世热情,投身报国立功封侯也是激动其内心的不二选择,所以用现实当下的豪情去点染“单于遁逃”的历史片段,使其与边关塞外独特的风光相结合,结晶出一个明亮生动的诗歌空间。《塞下曲》这种对前文本形象的复现不再是单纯的含义复制,而有了文本存在于当时的新意义。
我们不妨对“单于遁逃”这一情节做一下后续文本的追索。宋李纲曾有一首《念奴娇·汉武巡朔方》:“茂陵仙客,算真是、天与雄才宏略。猎取天骄驰卫霍,如使鹰鹳驱雀。鏖战皋兰,犁庭龙碛,饮至行勋爵。中华强盛,坐令夷狱衰弱。追想当日巡行,勒兵十万骑,横临边朔。亲总貔貅谈笑看,黠虏心惊胆落。寄语单于,两君相见,何苦逃沙漠。英风如在,卓然千古高著。”明李梦阳的《送李帅之云中》诗:“黄风北来云气恶,云州健儿夜吹角。将军按剑坐待曙,纥干山摇月半落。槽头马鸣士饭饱,昔无完衣今绣袄。沙场缓辔行射雕,秋草满地单于逃。”
从以上这些文本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诗歌文本中的“单于遁逃”基本上都追随并放大了历史文本中汉家豪情荣光的一面,来维护王朝及出征将帅的尊严,后代的读者(包括卢纶自己)在创作时都是以对前文本的文化记忆和沉醉为基础,穿梭于文本意义重新编织的新领域,建造属于自己的文本世界。前文本虽然相对固定但读者却与时变化,文本所展示出来的意义也就随着历史的文化积累不断生长,成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动量。
2、存在于话语叙述中的历史叙事文本与诗歌文本,在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想象与情感的制约是文本意义转换、形成互文关系的又一原因。过去,对历史的研究常把历史看成是“阐释的稳定基础的逻各斯中心模式,认为历史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历史文本和文学作品一样是由编码组成的符号系统,不能仅仅被当作是一个指向历史真实、客观规律、因果关系的“透明物”,对历史场景的某些想象是我们得以和过去接触交往时必定要穿过的形态。
钱钟书先生曾批评一些研究者“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人们长期以来认可接受的是诗歌关注社会
历史、以诗体叙述历史甚至述古怀古,杜甫之诗可以尊为“诗史”,杜牧、刘禹锡等人咏叹历史、凭吊英雄,以诗人主体之情感体察细味白云苍狗的世事沧桑,诗可以“具史笔”。但同样,历史叙事如果有了“诗心”的润泽与含蕴,客观的历史记录带上了撰写者的悬拟设想、主观感情,历史文本则具有了更强的直达人心、洞悉真实的力量。历史文本与诗歌文本在文体上虽有不同,但“史蕴诗心”,二者又可以互惠融通,形成互文关系。《史记》以历史叙事为主,“不虚美、不隐恶”是史家客观书写历史的传统和原则,但司马迁却以历史叙事与文学情感的交融;以“史心”在认知层面的真实深刻与“诗心”在艺术层面的超然凌空相结合,创造出了《史记》这样一条全新的写史之路。《卫霍列传》中的“漠北大战”虽然是《史记》鸿篇巨制中一个小小的历史叙事片段,但也是司马迁很不多见的战争场面描写,后人多以“自‘日且入至‘行二百余里写得如画”、“大将军不加封,将夜战单于一节,描画如见”、“写得气势飞动,层折历落”等语评之,大都体会到列传在描摹战场情状所运用的想象力、构造性,并且乐于接受司马迁于此片段中蕴含情感力量的事实。在这里由诗史文本的情感差异性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更值得我们关注。人类的情感具有可以继承和激发的特点,“人类之所以优胜于其他生物者,以其富于记忆力与模仿性,常能贮藏其先世所遗传之智识与情感,成为一种‘业力,以作自己生活基础。而个人在世生活数十年中,一方面既承袭所遗传之智识情感,一方面又受同时之人之智识情感所熏染,一方面又自睿发其智识情感,于是复成为一种新业力以贻诸后来”。后文本的作者卢纶承袭着前文本久远的历史记忆,加之同时代情感的熏染和自我创造,便以诗歌文本的涟漪和霞光来融观历史。正因为历史叙事与诗歌在形成过程中都受到了想象与情感的制约,《塞下曲》的引用、模仿进而改变列传的原意所指就有了所本。
3、读者在阅读时对文本的文化记忆也是诗史互文关系生成的又一重要因素。在阅读活动中,当读者发现前人的文本从后人的文本里从容地走出来时,两种文本即互文本在意义上产生了对接、延续、增殖或转化,读者自然会以自身的文化记忆为基础,联想起另一个文本做对比参照,并对这个文本空间进行识别和解释。清代姚芋田在《卫霍列传*的总评中所引明代杨升庵之评就是一例很好的证明:“卫、青一传,叙伐胡功烈屡矣。莫奇于元狩四年之役,两军分出,彼此各叙,而虚实详略,一一针对,极尽笔力之奇,无一毫零赘也。杨升庵云:自‘日且人至‘行二百余里写得如画。唐诗‘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又‘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皆用此事,实千秋之绝调也”。杨慎从《卫霍列传》中如画的描写出发理解诗歌文本的形象意义,或者说,从两首唐诗的诗境出发对《卫霍列传》中的“漠北大战”作还原玩索,对于以他为例的读者而言就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阅读模式、阅读效果。历史文本的厚实含蕴,丰富了诗歌文本的意义深度。“不仅前文本对文本的释义施加影响,文本也能对前文本施加影响。虽然时间之流是不可逆的,但文本的释义时间却是在时间之轴上不断变动的”。时至今天,我们读者在阅读任一文本时都很自然地联想到另外一个文本的表述,诗史两个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藉由读者的记忆而得到完成和丰富。
浓缩在《塞下曲》中的“单于遁逃”这个历史文本的片段,漂浮于时间的河流上,历代的人们在撷取时它时都赋予了种种新的含义。借助于西方的文本理论,我们对《卫霍列传》和卢纶《塞下曲》进行了比照性的解读,从而看到了历史散文与诗歌文本的互文性及它们在意义生成方面的不同。有意思的是,清人吴乔在谈论诗文之别时曾形象地说道:“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无论是西方的文本理论还是东方的感悟式解说,都洞察到了诗文体性上的差异和意义交融上的可能,从而使我们的文体学研究能够融通中外,在圆神方智中从容出入、吐纳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