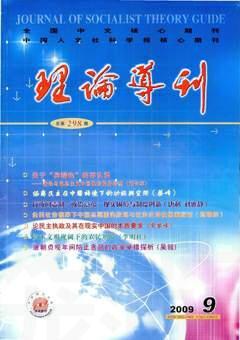撒旦的文学原型与象征
尤红娟
摘 要:《圣经》对西方文学影响至深,其中魔鬼撒旦作为恶魔原型在之后的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并演变,其文学象征性日益丰富和复杂。西方文学史中四个不同时期创作的撒旦形象展现出其形象生成和发展的轨迹。文学只要不停止对善恶辩证关系的思考和表现,撒旦形象就会一直发展下去,并不断丰富人类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
关键词:撒旦;原型;象征;圣经;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9-0125-03
众所周知,古希腊文明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艺的发生和发展,而另一支文明——古希伯莱文明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样不容低估。作为希伯莱文明的集大成作品——《圣经》,它不仅仅是一部民族的宗教历史典籍,它还是一部艺术性和思想性极强的文学名著。《圣经》中塑造的神和人的形象成为各种原型,不断地在日后的文艺作品中出现,构成丰富的人物画廊。其中有一个形象非常独特且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在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这个形象就是魔鬼撒旦(Satan)。据《圣经》记载,撒旦曾经是上帝座前的六翼天使,负责在人间放置诱惑,后来他堕落成为魔鬼,被看作与光明力量相对的邪恶、黑暗之源。
撒旦作为恶的原型,其形象和作为多次出现在《圣经》文本中:旧约创世记第三章的蛇,就是代表撒旦;约伯记第二章第一节特别提到,在神面前控告约伯的是撒旦;历代志上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也提到,是撒旦令大卫数点以色列人的;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又说,撒旦在神面前与约书亚作对。新约里也有不少经文都见证撒旦的存在:每一位新约作者都提到撒旦;基督自己就提过撒旦二十多次。新约旧约都提到不少撒旦的名字,有时称为路西弗,有时称为基路伯,有时称为蛇等等,这些都是撒旦这个原型人物存在的证据。撒旦不仅存在,还有独特个性。《圣经》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普遍简约,撒旦的性格约有三方面比较突出:曾经的智与美的化身——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第十二到十五节描写未堕落前撒旦在神面前拥有崇高的地位,天上的美物环绕他,他称为“受膏遮掩约柜的”,他在神面前拥有至高的尊荣。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提到,他是至高的天使,称他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强烈的贪欲——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三、十四节写道: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1]五个“我要”极言其贪;诡诈——他定意要打败基督做“至高者”,在神的宝座上建立他的宝座,超过其他天使,所以挑拨离间人神关系,诱惑人类。总之撒旦在堕落后恶成为其性格主导,凡提及撒旦必与狡诈、阴险、邪恶相关。
圣经文学时期的撒旦形象总体上比较扁平,伴随着西方人对人自身和社会关系认识的深入,作为恶魔代言人的撒旦在后世的西方文学传统中被赋予多重的象征意蕴:邪恶、惩罚、引诱、反抗、智慧、博学、率真、任性等。而其与人类的契约关系也成为西方文学的重要母题,不断在文学中发展演绎,本文仅就四个时期的撒旦形象作一比较分析,展示其形象发展的轨迹。这四个时期为:中世纪时代、17世纪英国清教运动时期、18世纪德国启蒙时代和20世纪早期的苏联,相对应的作品分别是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又译作《撒旦起舞》)。
(一)
欧洲中世纪文学中的撒旦形象集中体现在《神曲·地狱篇》之中。由于深受基督教神学思想影响,诗人但丁在塑造撒旦时基本沿袭了传统圣经文学的观念,即撒旦是惩罚者与被惩罚者的统一体。
作为受罚者,撒旦为他的骄傲和野心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他并不完全表示臣服,还不断用恶念诱惑人类,所以圣奥古斯丁说:“世上一切苦难都来源于他的恶意。”[2] 247即使堕落在地狱的最深处,身处科奇土斯冰湖之中,忍受黑暗和彻骨之寒,撒旦(卢奇菲罗)仍表现出对上帝的叛逆意识,但丁描写其“还扬起眉毛反抗他的创造者”[2] 243。但反抗的作用是微弱的,在但丁的观念里,恶永远无法战胜善,所以他描写的卢奇菲罗尽管身形巨大,尽管有足够的智慧和狡诈统领狄斯城中一切恶鬼和冤魂,他的权威也只能局限在深渊中且永远无法挣脱上帝的惩罚。卢奇菲罗相貌之丑怪就呈现这一观念:“一个面孔在前面,是红色的;另外那两个和这个相连接,位于肩膀正中的上方,它们在生长冠毛的地方连接起来。右边那个的颜色似乎在白与黄之间;左边那个看起来就像来自尼罗河上游地方的人们的面孔。每个面孔下面都伸出两只和这样的鸟相称的大翅膀……翅膀上没有羽毛,而和蝙蝠的翅膀一样。”[2] 243-244卢奇菲罗头上长着三个面孔,象征撒旦的三位一体性作为上帝的三位一体性的对立面。上帝象征着力量、智慧和爱的终极,而撒旦的三个面孔却象征着与此相反的三种属性:无力、无智和憎恨。作为惩罚者,卢奇菲罗与众鬼卒铁面无私,决不为同情心所动。撒旦的统治就是上帝对罪恶惩罚意识的再现,是以恶制恶,他是上帝有力的助手和同盟。
如果说卢奇菲罗性格中还有一些新特点是圣经文学所不曾细致描写的,那就是向善性。他原本就是美与善的天使,堕落后尽管心怀不满和反抗,但在永恒的黑暗之中,他也在痛苦和悲哀中尝试着转化。尽管这转化十分微妙和模糊。但丁写道:“他六只眼睛哭,泪水和带血的唾液顺着三个下巴滴下来。”[2] 244哭泣可能因于对神作战失败,也可能因于无力反抗,但也可能来自一种忏悔和无望的憧憬。诗人但丁特意安排了卢奇菲罗的处身之地——他位于地心中央,上半身在地狱中,尾巴通向净界,他处于善与恶的交界点,或者不如说,他本身就是作恶造善之一体的集中写照。屈从他,就必然深陷罪恶不能自拔,背离他则意味着对德行的追求。可以说,卢奇菲罗的“恶”成为诗人寻求善的阶梯,没有对恶的观照和体认,也不会有道德上的觉醒和净化,更无须说对至善灵境的追求。和圣经文学相比,《神曲·地狱篇》中的撒旦在性格的主要层面和原型是相同的,但基于但丁对人的复杂性的理解该形象还是增添了一丝人的属性。
(二)
清教运动时代的撒旦出现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一书中。该书取材《旧约·创世纪》和《新约·启示录》。故事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亚当和夏娃受到撒旦的引诱而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一是撒旦反叛上帝的故事。在此基础上诗人进行了各方面的再创造,使撒旦的形象比其圣经原型和但丁的创作更加生动复杂也更具艺术魅力。
在《失乐园》中弥尔顿以基督徒的身份第一次将恶魔作为史诗的主角来描写,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撒旦也被赋予勇敢、智慧、毅力的化身,但终究未脱离“邪恶”的本质。作为一个不屈不挠的反抗者,撒旦即使是被打入地狱以后,他也带着天使的余辉,召集群魔东山再起。在地狱中,撒旦威风凛凛地坐在装饰着无数珠玉钻石的宝座上面,趾高气扬地对群魔发号施令。他之所以反抗上帝的权威,在于他意识到上帝对其精神和处境的奴役状态,为此他要取代上帝结束无边的屈服。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导致了反叛,结果仍被上帝打入地狱。面对失败的惨景,撒旦毫不气馁:“我们损失了什么?并非什么都丢光:不挠的意志,热切的复仇心,不灭的憎恨,以及永不屈服,永不退让的勇气,还有什么比这更难战胜的呢?”[3]8这些豪言壮语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一个反抗者的不挠意志。但同时,撒旦又是一个邪恶的引诱者,恶在其性格中仍占据主导。诗剧一开场,撒旦就向众魔宣布:“无论作事或受苦,但这一条是明确的,行善决不是我们的任务,作恶才是我们唯一的乐事……”[3]10这句话是界定撒旦性质的关键。从其表现和本质看,他仍然体现为“恶”。他有强烈的权利欲望和嫉妒心,想要取代上帝,享受绝对的自由。他处心积虑引诱人类的始祖犯罪,使其受到上帝的惩罚,从而屈从于自己的权威。诗人弥尔顿确实赞美了撒旦的反抗特性,但并没有因此改写魔鬼的本质。且看撒旦的反叛宣言:“我们的名号理应是治人而不是治于人。”[3] 207充分暴露了他的骄傲和狂妄。在举起“自由”的旗帜的同时,又说“地位和等级跟自由不相矛盾。”[3]207前后相悖的语言掩藏着一颗暴君的险恶用心。正因为他在极端个人主义的驱使下一步步堕落,甚至到了暴虐和放荡的地步,所以最终只能以失败收场——瘫倒成蛇。显然,在《失乐园》里撒旦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而是具有邪恶本质的矛盾人物。他全部的反抗归根结底是要使自己成为人间新的主宰,凌驾在一切权威之上,掌控人类的生死存亡。从这一点上来说,撒旦又是一个悲剧人物,他不曾觉醒自己曾经极力反抗的和如今极力攫取的是同一的,其性格本身就蕴涵深刻的矛盾性。
(三)
当西方文学发展到启蒙时代,德国诗人歌德以辩证和理性的思考为读者创造全新的撒旦形象,虽然梅菲斯特(撒旦)不是《浮士德》中的首要人物,其形象仍有独立价值。在诗剧中他站在浮士德的对立面,承担邪恶的诱惑者和试炼者的角色,其形象塑造的目的不仅在于呈现其恶,更重要的是揭示其“作恶造善之力之一体”的辩证性。作为恶魔,他曾自我解释说:“我是永远否定的精灵!……你们称之为‘罪孽、‘破坏的一切,简言之,所谓‘恶,正是我的原质和本性。”[4] 35-36悲观厌世、狡猾奸诈、冷酷凶残、寡廉鲜耻构成其性格特征。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恶的象征,在某种条件下,他的恶也可以转化为善。恩格斯就曾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当梅菲斯特对封建宫廷、教会、庸俗的社会风气进行揭露和批判时,他的言语中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他的虚无主义观念——“因为发生的一切终归要毁灭,所以什么也不发生,反而更好些。”[4]35成型于封建社会末期和野蛮的资本积累时期,其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否定代表了一定的社会进步作用,所以梅菲斯特的“否定”和“恶”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有积极意义的。
就梅菲斯特和浮士德的关系而言,他主观上想方设法引诱浮士德误入歧途,却在客观上为激励浮士德不断探索人生意义和价值起到促进作用。他把浮士德从书斋引入世俗,想用低级享乐诱使其堕落放弃追求,实际上却帮助浮士德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认清自身的缺陷并以更加激进的态度去寻求真理,并最终飞向清明圣境。浮士德之所以能拥有传奇和充实的一生,正是梅菲斯特让他认识到恶的存在价值。通过梅菲斯特这个人物,歌德想向我们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人类要进步,就要行动,而动力来自于人类心灵和生活的欲求,所以恶是进步的前提,恶的作用不全是破坏、否定和倒退,恶是人类前进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这正是梅菲斯特“作善造恶之力之一体”的内涵的具体体现。不仅人类是善恶一体的复合物,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如此。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所言“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5]188海德格尔“造物主在创造人类世界时,就设置了它的对立物,男人与女人、善与恶、欢乐与忧伤、爱情与仇恨、光明与畸形……”[6]155即是此类内涵的具体阐述。所以通过歌德对梅菲斯特形象的塑造,传统的撒旦形象在此时更具辩
证色彩,也更能体现复杂深刻的社会意识。
(四)
到了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都在尝试超越传统,前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作品《大师与玛格丽特》(又名《撒旦起舞》)中的撒旦形象颠覆了以前所有文学中的撒旦形象,比之梅菲斯特,他更加生动可爱。他充满智慧,洞悉世情,对前苏联治下的一切罪恶进行无情的嘲弄和鞭挞。在小说中作家重点为我们塑造他的三重身份:阴郁的暗夜之神,严酷的惩罚者,强大的拯救者。三者矛盾地统一在一起,赋予撒旦(魔王沃兰德)以全新的艺术形象。
魔王沃兰德形象塑造深受《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的影响,所以在小说开篇作者就引用了《浮士德》中的几句诗:“那么你究竟是谁?我就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总想作恶却总是为善。”分明就是“作恶造善之力之一体”的回响。但是二者仍存在巨大的差别。作为暗夜之神,马太称他为“邪恶之灵和阴暗之王”,黑色是他的专属色。“黑色和魔鬼有着相同的词根,所以魔鬼沃兰德出场时,一直强调着黑色的色调。”[7]54沃兰德的居住地“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仿佛在地洞里” [8]296, (下转第110页)(上接第126页)沃兰德本人“脸上的皮肤仿佛永远晒着阳光,变得黝黑”[8]301。作家不仅从外形上描绘他黑色的特征,而且从精神层面赋予他丰富的内涵——洞察人的灵魂深处的恶。人类的恶与其“恶”的本质同构为魔王的“黑色”本质。作为恶的本质,魔王沃兰德并未走向上帝的对立面,作家消解了传统文学中至善与至恶的对抗性,赋予其神魔兼具的特性。在小说结尾部分,玛格丽特陪同大师和沃兰德前去释放彼拉多,在半路上她看到了魔王沃兰德的真实形象:玛格丽特说不出他胯下那匹骏马的缰绳是什么编织的,只觉得它像一条由无数月光光环组成的银链,那骏马则不过是一大片黑暗,马鬃则是一片乌云,骑士靴上的马刺原来是闪烁的星辰。两种对立象征物同时出现在沃兰德的身上,喻示了魔鬼的双重属性。
一方面,对于作恶者,沃兰德毫不容情,以戏谑严酷的态度以恶制恶,成为上帝行使惩罚的有利助手。这让我们想到了卢奇菲罗所承担的角色。但另一方面,惩罚不是魔王的最终目的,他最感兴趣的是“这些市民的内心是否起了变化?”[8]148说明沃兰德以恶制恶的深层目的是为了拯救世人日渐堕落的灵魂。魔鬼身上兼具的神性得到张扬。在他的考验下,几乎每个人都获得道德上的净化,而这一切都蒙魔王沃兰德所赐。对于灵魂真正高尚经得起道德和良知考验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沃兰德则展示其宽容博大的爱,赐予他们永久的幸福与安宁。沃兰德的“恶”成就了造善的目的,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上帝的特质和性情,而且相较之下,魔王沃兰德显得比上帝更有力量。小说结尾有这样一段描写:使徒马太来找魔王,说上帝的代言人耶稣读了大师的作品,请求他赐给大师以安宁。上帝的代言人反而求助魔鬼的力量,这本身就是对传统撒旦形象的一次颠覆。
沃兰德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样的真理:“如果不存在恶,哪有你的善;如果地球上没有阴,你又怎能看到阳?要知道阴出自各种物体和人……”[8]425光明与黑暗是同在的,善与恶也许表面不相容,但都是为宇宙中的至善服务的。耶稣是上帝的部分,撒旦也是上帝的部分。沃兰德的一切言行说明他是一个与上帝具有同等价值与意义的存在。
从堕落天使、十恶不赦的魔鬼到神魔兼容的人性,撒旦的形象一再被重新阐释。只要是基于对善与恶的辩证关系的深入思考,魔鬼撒旦决不会成为被文学家忽略的人物原型。正因为西方文学长期以来关注人性的发展,才使得撒旦一再深入文学内部,成为最复杂的表现对象之一。只要这个世界还有恶德败行的存在,只要人类不放弃对人性的关注和道德的追寻,魔鬼撒旦就不会淡出文学的视野,他将继续伴随我们参演人生大戏,以此来不断丰富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
参考文献:
[1]所有圣经内文来源于“中国基督教协会”于1996年于南京印发的《圣经》.
[2]但丁.神曲:地狱篇[M].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弥尔顿.失乐园[M].朱维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4]歌德.浮士德[M].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上)(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海德格尔. 诗·语言·思[M].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7]唐逸红.布尔加科夫小说的艺术世界[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布尔加科夫.撒旦起舞[M].寒青,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