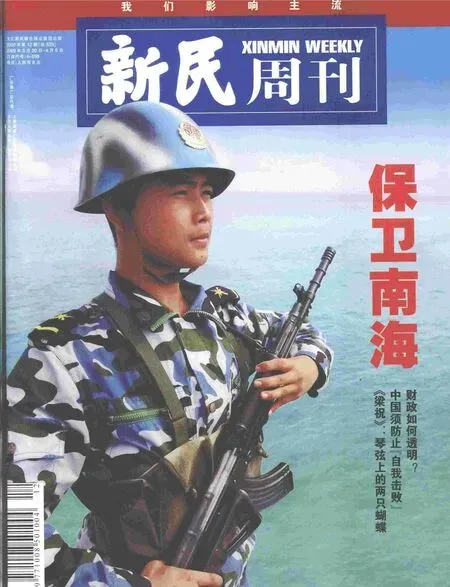《梁祝》的非典型“蝴蝶效应”
沈嘉禄

当年,何占豪、陈钢、俞丽拿等人共同造就了《梁祝》,《梁祝》也成就了他们。但谁也不曾料想,《梁祝》这对蝴蝶起飞后,产生了极大的“蝴蝶效应”,深刻影响了几代人,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
以我后来就自学了五线谱。练习曲拉到一定段位后,再将《新疆之春》上手,如小菜一碟。再后来,也能拉《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壮锦献给毛主席》等正宗的小提琴曲了。
此时,小提琴独奏曲经常在电台里播放,刚从牛棚里出来的陈钢应上海交响乐团首席潘寅林之邀请也创作了好几首,比如《苗岭的早晨》、《我爱祖国的台湾》、《恩情》、《恋歌》、《金色的炉台》和《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等,经潘寅林演奏后大获成功,在荒芜的艺术园地里它们无疑是一朵朵奇葩,给劫难中的人们些许慰藉。潘寅林因此名声大振,骑着自行车经过十字路口时,交警也会将红灯翻到绿灯,请他先行。
《炉台》和《阳光》我也是拉过的。但我们对潘寅林首演的《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特别买账,他演绎得绝对辉煌。这首曲子是阿克俭根据同名花腔女高音独唱歌曲改编的,在革命的名义下,充分展现了小提琴的各种技巧。在无法接触帕格尼尼、海菲兹、斯特恩的那个年代,潘寅林就成了我们的偶像。
这类曲子后来被陈钢称为“红色小提琴”,我想这可能是为了界定某个时段而贴上的一枚标签,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它的涵义。但我觉得,“红色”两字是容易被误读的,不希望它被当作一个卖点。
为《梁祝》殉情的女孩
不过,许多学琴的青少年都埋藏着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能拉一拉《梁祝》。因为它是如此优美,包含了爱情、叛逆与献身。从技巧上分析,它不如《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和《战斗进行曲》那般花哨,有悟性的人在学琴四五年后就会起野心,希望攻它下来。更主要的原因是被禁演了。禁果的诱惑力是不可抵挡的,也是人类启智的第一动因。
陈钢跟我说起,“文革”中有一年他去杭州,在山洞外听到熟悉的琴声,循声走去,发现原来是几个学琴的小青年在学拉《梁祝》。洞内无光,他们就打着手电筒照乐谱。还有一年他去昆明,得知某大学钟楼这几天来颇为怪异,每天晚上会发出微弱的灯光,好像在向某个方向传递信息。警惕性很高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决定在某夜突击“捉鬼”,入夜后,钟楼果然亮起微弱的灯光,他们模仿《奇袭白虎团》里的志愿军侦察排,紧逼包围,摸索上楼,一个手势后,其中一工人踹起一脚破门而入,众人一拥而入,手电筒打开乱照一气:“不许动!”谁想到,眼前呆若木鸡的竟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从学校的图书馆里搞来尘封已久的《梁祝》唱片躲在这里偷听。一听而上瘾,成了每天的节目。
沪上收藏家杨忠明告诉我,他原来单位里有个同事,小提琴拉得非常出色,能将《梁祝》完整地拉出来。“文革”后期被总政文工团招去,谁料半年后在林彪“三箭齐发”运动中被赶了出来。原因是开后门进去的,而且在部队里还偷偷拉《梁祝》毒害农村来的战友。这个倒霉蛋回到了上海,在一个街道工厂里干粗活。二十年前工厂倒闭,他也下岗了,夹着小提琴到处讨饭吃,有时还去教堂里演奏《安魂曲》什么的,每拉一曲得50元。
当时我们还听说上海某中学音乐老师教他的几个学生拉小提琴,其中一位女学生很有天分,进步神速,有一天她提出想听听心仪已久的《梁祝》。音乐老师给她找来这张胶木唱片,躲在仓库楼梯下的小角落里偷听。不料他们的行踪随即被人发现,那人报告工宣队后。很有点战术意识的工宣队没有打草惊蛇,花了几天时间守候于此。几天后,当他们再次“密室相会”时,破门而入,一举擒获。校方给这个老师捏造了个“引诱女学生失身”的罪名,关在一间破房子里隔离审查。
那个女学生呢,在学校里遭到师生的白眼,回到家里则要忍受父母的呵责。在得知老师被隔离后,她偷偷地跑到昏暗的隔离室外,通过窗子碎玻璃的缺口,将两只刚出笼的肉包子递给老师,以示慰问,不料被工宣队活捉。被押送回家后,又遭父亲一顿暴打。第二天,她趁家里没人时打碎一只热水瓶,吞碎玻璃自杀……
这下闹大了,这个老师被送到公安局,关了小半年又送到工厂强迫劳动。

里革委阿姨的《梁祝》
后来,我也終于听到了《梁祝》的唱片,那是在一起学琴的同学家里听的,破窗帘拉得密密实实,大热天啊,赤膊穿短裤听完后大汗淋漓,但绝对过瘾。而且我们永远记住了主旋律。
这位同学姓陈,他是我们几个中拉得最好的。中学毕业前,部队来学校招文艺兵,他去报考了,成绩不错,但最终没被录取。后来得知他曾在家里偷偷拉过《梁祝》片段,正巧被里革委的阿姨知道了,关键时刻去学校揭发。陈同学后来按政策发配到崇明农场,还经常在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拉几下。有一次收割稻子时,一不小心被飞快的镰刀割去了一节手指,要命的还是左手中指。回家休养时他悲伤地砸烂了心爱的小提琴。
1978年,《梁祝》开禁的那天晚上,那位政治觉悟很高的阿姨看到我同学正守在收音机旁,异常兴奋地告诉他:“现在你可以听《梁山伯》了,现在政府允许啦,我也要听听的。”后来,这位阿姨看重映的越剧电影《红楼梦》,看一趟哭一趟,一口气连看三十多遍,你只要看到她两眼红肿得像一对核桃,就知道她刚从电影院回来。
还有一位同学与陈钢同名,被昆明部队录取,其实他也在家偷偷拉过《梁祝》。也许里革委阿姨没有听到。
前几天潘寅林告诉我,1959年《梁祝》首演时,他在上音附小,是十三四岁的娃娃,老师不准他们拉《梁祝》,因为这里有爱情,“少儿不宜”。“文革”后期,他已经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但上台只能拉“红色小提琴”,《梁祝》好比是一块烧红了铁板,碰也不敢碰。直到1981年他出国后,才在日本与东京都交响乐团等五大乐团合作,先后演奏了六场《梁祝》。优美而伤感的旋律一下子征服了日本听众。
我没有拉过《梁祝》,一没有谱子,二段位不高,故不敢尝鼎一脔。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干的是力气活,手指很快又粗又僵,十年后再摸琴,发现粗硬的手指再也捕捉不到小精灵般的音符了,梦想就此破灭。不过当初躲在暗室里偷听《梁祝》的情景,是每年同学聚会时必定要重提的往事,也是一再确认我们情谊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