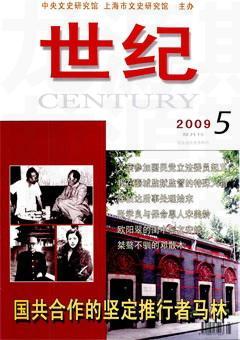父亲曾是漏网大右派
孔海珠
写下这个题目后,一直没有动笔,想说的话很多却不知从何说起,心绪很乱,心情也很不好。“漏网大右派”这几个字只有在中国才有,很难想象如果不是政治运动不断,如何能创造出这样的词汇。既然漏网了,就不是右派,哪里还存在既漏网,又是大右派的道理?然而,这个词组是一顶很大的定性的帽子,比起右派这顶帽子还大,也更为可恶。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上海出版系统,只有我父亲才有此“殊荣”才够这个资格——这顶帽子。在“文革”期间,“打倒漏网大右派孔另境”的标语是刷写在绍兴路地上的大标语,它醒目,因为占据这条马路的差不多全部的宽度,那黑乎乎的墨迹是让行人在上面踩踏的,因为这个牛鬼必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
当年鸣放事
事情要从1957年3月父亲代表上海出版界赴京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说起。这次会议即是中央鼓动“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会议。会议结束的时候,父亲在他姐姐孔德沚、姐夫茅盾家里说,“这个大会很受鼓舞……”他好像领了“圣旨”精神十足,准备回沪后落实鸣放。姐姐和姐夫劝他:“你说话要小心,说多了不好。少说为妙!”(大意)他们知道父亲心直口快,冲口而出的话,每次似乎要达到“语不惊人心不死”的境地,这样要吃亏的。父亲口上答应了,却没有牢记在心。事后他对我们后悔地说,这次运动没有听姐姐和姐夫的话,说话多了,他们是早就看出来鸣放是要惹祸的,现在给他们也惹了祸。
那年,父亲在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部副主任(最近我又电话询问了老文化出版社的先生,承他相告,当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领导人是胡炎,李小峰是编辑部主任,父亲是编辑部副主任,相当于副总编辑)。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后,他回来又参加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他作了关于通俗文艺的发言。“大鸣大放”不久即进入反右整风阶段,孔另境作为本社第一个被斗争对象,在无数次大会小会上被迫检查交代,写自我检讨近十万字。然而,性格直爽、作风坦荡的孔另境态度强硬,面对压力,没有的事坚决不承认。
现在从父亲有关检查中可以知道他到底鸣放了什么?
他对自己右派言论的检讨有如下几点:
1、“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有一次,他在学习会上说:“现在国际上革命形势显然是处于低潮了,倘还说形势大好,仍然是东风压倒西风,就不免成为阿Q精神胜利了。”他检讨说,这不但是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还因为“东风压倒西风”的比拟是毛主席在1953年提出来的,成了我对毛主席的诬蔑。
2、“个人迷信”问题。有一天,他到市政协去学习,碰到那边一个工作同志,说找他谈谈,就谈到个人迷信问题。那人问:“你看中国有没有?”他当时没有干脆回答,但心里也确实感觉有一点的,对象当然是毛主席。
3、“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专家办社”问题。当时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领导人是胡炎。社里的黄嘉音极力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李小峰筹备了专家办社,组织了各种座谈会,商谈分社的事,名单也开了出来,还请了客。父亲说:“我当时在文化出版社也是一个头头,承蒙他们‘照顾,并不把我开入他们的名单,那意思,我是不肯寄在他们的篱下,他们期望我也来一个‘独立王国。有一晚,有一个党员干部到我家来,怂恿我不甘落后也来搞一个,我谢绝他的‘好意。”然而,他检讨:“我也有这种思想活动的。对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是双手赞成的;对于专家办社我也觉得是应该的。”
4、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一系列的错误看法。对资产阶级民主有向往,代表性的有三点:一是民主选举;二是议会政治;三是人才自由市场。都作了思想检查。
5、在民进市委召开的出版工作座谈会上,附和“取消坐班制”的提议。和周煦良等人联合提出成立“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倡议。在一次市政协召开的稿费问题座谈会上,也赞成提高稿费标准。他批判自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中自由化赞同的表现。等等。
6、对一些理论问题上的“联修反帝”、“唯武器论”等认识也作了检查。
一年多以后,孔另境虽然没有被定为右派,但“漏网大右派”的帽子却一直如影相随着他,历次运动不断地被重点批斗。于是,他一边检查交代,一边又不断地申诉,精力和锐气渐渐耗尽。
右派漏网事
“文革”中披露过一则材料,即上海文化出版社“反右”大事记。这材料被父亲看到了,他亲自摘录了有关自己的一些内容,共有五项。这份抄件在我的文件资料夹中,不妨抄录,也能看出一些上海出版系统当时反右运动的概貌:
1957年3月27日
伟大的整风运动开始,社内李小峰、孔另境、许君远、黄嘉音等一伙,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大放厥词,散布谬论,猖狂向党进攻。孔另境在宣传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公然提出“只有多发展几个民主党派成员,才有力量互相监督。”又说:“私方转来的一般都是副职,有职无权。”“人事材料公开出来,有关人事方面的决定,应与编辑部商量。”……
6月20日
我社反右斗争烈火越烧越旺,贴出大量大字报,声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孔另境在石西民的掩护包庇下,竟溜到苏州去搞“创作”,以对抗反右斗争。他写给整风领导小组的信件中狂妄地说:到苏州是“迁地避嚣,正养身与写作两全之道。”公然骂全社革命群众与他作斗争是“嚣”。
6月21日
我社整风领导小组发文给旧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冰,旧出版局副局长汤季宏,反映工会委员会对孔另境抗拒运动的意见,并要求发动全社职工对孔另境反党言行进行批驳。而上海出版系统整风领导小组于7月2日对孔另境竞胡说:“孔另境在政治上尚未发现有何反党活动,在某些场合下还能表示拥护党的政策。”另一方面,不得不假惺惺地说:“但孔的品质恶劣,个人主义严重,在平时言行中对党有不满情绪,”结论却是:“是否划为右派分子处理,值得重新考虑。对孔的错误言行应继续严格进行批判,其创作假暂不停止。”
10月21日
出版局整风办公室批示:“你社孔另境,经宣传部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不列为右派。”
10月25日
我社整风领导小组根据全社革命群众要求,向局整风办公室指出:“孔另境应划为右派。”而局整风办公室仍批示:“仍按宣传部意见,不列右派。”就这样将孔包庇过关。
以上五段,充分说明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文化出版社中,基层多次上报到出版局整风办公室、市委宣传部等上级部门,据说,当时上报十八名右派戴帽名单,孔另境是排第一名,然而,只有孔另境一人上级没有批准。上级认为“孔另境在政治上尚未发现有何反党活动,在某些场合下还能表示拥护党的政策”,坚持“仍按宣传部意见,不列右派”,其余十七人统统戴帽。就这样,孔另境没有戴上右派帽子。这也就是“漏网”这一说的由来。
父亲当时并不知晓这个过程。他在胡炎领导的文化出版社整风运动中,是第一个被点名批判的对象。我记得在反右整风过程中,晚上下班回家,父亲常常把书房的门关起来,或有人来通报消息,或大人讨论如何检查过关,
不让我们小孩偷听。然而,我们总能感受到大人们很紧张,连说话声音也小了许多。后来,父亲也作好了全家离开上海到青海去的准备。因为当时右派分子大都被遣送到青海省去了。所以,以后对从青海回来养病的一些文化人,父亲很同情,也帮助过他们,因为他与他们一样“有罪”,没有陪同他们一起在青海受苦。如果当时他也被发配到青海,身体肯定受不住。这是他经常平心而论对我说过的话,为此,他感谢“漏网”。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精神上受的苦,并不比已经戴帽的右派来得少,或者更为激烈。因为运动不断,随时可以给他重新戴帽。
在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工作期间,领导人是方学武,当时,“阶级斗争”的弦是绷得很紧的,矛头也一直有所指认,使所里许多人体会到“表面上称你‘同志同志,而他们心里却一直叫你‘敌人敌人”,不寒而栗。试举一例:当时的领导针对性地在一批所谓“有问题”的对象周围,包括父亲的“周围布置了大批的‘暗探,把你的一言一动罗织成一条‘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证”。这并不是大批判中的虚妄之言,我的同班同学当年分配在这个单位,安排在我父亲的对面坐班,对他布置一项任务就是注意孔另境的动向,甚至会见什么客人,与什么人通电话,也要向上级报告,还定时找他们了解“对象”动态。这种特务式的行径,注意你一言一行的“阶级动向”,有效地掌控在群众手中,随时可以对你进行批斗。正因为你没有被戴上帽子,却随时可以再给你戴上。父亲说:“要是你是一个不善于隐晦的人,他们的成功更其会快些,这样,当一旦他们罗织成功,连你自己还不觉得,已给他们定为“反革命”、“右派分子”或“串通外国的特务”了。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之中生活,身心交瘁,精神上的压抑是不言而喻的。”
反右期间,父亲的“迁地避嚣”一说,造成的影响很不好,后来我在宋原放先生那里也得到证实。晚年的宋原放住在华师大的普通的宿舍里,有一次,我拜访他,请他谈谈父亲。他们在1957年同去北京出席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游颐和园,家里有他们的合影六寸大的照片。因为事先有约,所以,没有说上几句话,宋原放就记起父亲的这句“迁地避嚣”的话。他很兴奋地介绍,父亲信中说“迁地避嚣”是引起公愤的。大家看了他这句话以后,简直是炸了锅,议论纷纷。当时运动很激烈,你说这样的话,等于否定运动,说群众与他作斗争是“嚣”。可见这句话给宋原放的印象很深。说着我们都笑了。父亲是极有个性的人。说话很不合时宜,只顾自己一时的个人感受,逞口舌之快,毫无城府可言。现在想来,这句大胆的话,在当时这样高压的形势下,振聋发聩,不仅深刻,而且难得。充分表达他对这场反右运动的不屑一顾。
当时整风办公室多次批示:“仍按宣传部意见,不列右派。”其理由是:“孔另境在政治上尚未发现有何反党活动,在某些场合下还能表示拥护党的政策。”这样的说法是缘于宣传部领导掌握政策,了解父亲的光荣历史,他为革命曾出生入死。了解他拥护新中国,热爱新中国。民间还有一个讲法,最近有多人曾经向我求证:“你父亲与毛泽东曾经一起工作过,关系很好?还一起打牌?”还说:“反右时,有人揭发这是吹牛,不相信,是污蔑毛主席。是右派言论。”我对此人说,真有这回事。不过并不明白,父亲说出这段历史真实,对父亲是有利,还是害了他自己?
他庆幸自己漏网。其实,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
1986年,茅盾研究会在南京召开国际研讨会,有位资深的茅盾研究专家,捷克的汉学家高利克也来与会。我第一次见他,他得知我的姓之后,问我,认识孔另境吗?他还好吗?当我告知他我的身份,他很高兴,又遗憾没能访问到父亲,因为在“文革”期间父亲已经去世了。承他相告,他在1958年来中国收集茅盾资料的时候,曾到上海想访问父亲的。但是被有关方面拒绝了。究竟怎么回事?我很想知道。于是提出会议休息时带录音机访问他,他接受了。
他说,那年他从北京到上海,向上海作家协会提出要求访问孔另境,那位接待他的是王某某。我知道王某某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老师。王对高利克说:“此人反右运动期间问题严重,不宜会面。”拒绝了他。于是他求其次,要见其弟孔令杰。这位弟弟他见到了。高利克说:“孔另境与茅盾的关系更深,在很多历史时期,他是见证人。很可惜失去了这次见面的机会”。
我很奇怪,父亲当年并没有被戴上右派帽子,应该不是敌我矛盾吧!但是事实如此,反右运动带给他的政治影响很坏,“待遇”与右派没有不同,外事活动是不能参加的,是得不到信任的人。以上所述,仅限我知道的一则事例。
“文革”大字报
在“文革”抄家初期,我家后门就贴着这样《严厉警告漏网右派孔另境》标题的大字报。这件事在那个非常年代里并不是怎么的稀奇事,已经看惯了上纲上线的大字报。然而,这张大字报里还是有些内容的,它让我记起一些事。那么,事隔这么些年头了,为什么我还要牵出这些破事来?因为这顶帽子对他本人来说是缠绕半辈子的不幸,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没完没了的检查和批斗,耗尽了他壮年的生命。对我们子女的影响也太大了,不断地要我们与他划清思想界线,认清他的反动本质。尤其我与父亲同在出版系统工作,波及至我的入团,参加基干民兵组织等等,这样的委曲,给我要求上进的心制造了极大的负担;自卑的感觉,又给我在底层的生存空间里磨练成长。好在有给出路的政策,那就辛苦地改造自己吧……受到这样的精神折磨,两代人之间产生的隔阂、埋怨,甚至怨恨,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产生。
先看署名“革命出版社”的贴在我家后门的这张大字报,内容如下:
漏网大右派孔另境一贯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民愤极大。1957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白彦包庇过关,在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更加变本加厉大放厥词,对我党和我国政府进行疯狂地攻击,引起群众极大愤慨,纷纷提出要求将他严办,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方学武,用假批判真包庇将其包庇过关。
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大长了人民群众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我社革命群众莫不拍手称快,但是孔另境并不死心,当社会上刮起翻案风之际,他又蠢蠢欲动,写了一封“愤怒的控诉”竟丧心病狂地抹煞我国十七年来的辉煌成就,向我社红卫兵革命群众反攻倒算,公然叫嚷向他赔礼道歉、低头认罪,阶级敌人疯狂到极点。
为了坚决击退阶级敌人的反扑,迎头痛击反革命的翻案风,我社革命群众揪出孔另境进行了斗争,将其反动面目痛加揭露,彻底将他斗倒、斗垮、斗臭。
我们勒令他每月向居民委员会汇报思想一次,老老实实地服从居民委员会的监督劳动。不得违抗。
希望里弄群众对孔另境严加监督。
这450字的大字报没有具日期,应该是1967年2月27日以后的事,原因是这天他拄着拐杖去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交自己的小字报《愤怒的控诉》,才引来了再一次抄家和这张大字报。“革命出版社”,即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被革命造反派砸烂之后的新名称。这个编辑所果然在“文革”之后被取消。这是另外的话题。
我们家在1966年8月31日被抄。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天深夜是我开的门,一阵训话之后开始查抄父亲的家,可是,对我亭子间小屋的书籍和物品也一一查抄,并检查我的日记和私人信件。我是革命群众,参加工作已经5年,应该和父亲区别对待,要讲政策,这是我的想法。当我对造反派头头表示这个不满意见后,他们认为我态度不好,不支持这次革命行动。第二天,到我单位贴了我第一张大字报,大骂我这个孝子贤孙。就此,我也成为在单位被贴大字报的对象。这也是另外的话题。
那么,为什么在最初的抄家以后,父亲还想据理力争?他在检查书《我的检查》一文中讲到他当时心里不服,才拄着拐杖去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交自己的小字报,后来,单位里把它抄成大字报,贴出来以后引起革命群众的不满。引来更为严厉的批斗和抄家,抄家后在楼下后门贴了这张大字报。父亲出于自尊,没有仔细看过大字报的内容,他对儿子说,你去把这些文字抄录下来,我要知道上面写些什么?所以才保留了下来这份原始的记录。大字报贴出后,里弄里熟悉的邻居悄悄地向我们劝说:“对孔家伯伯说,识事务者为俊杰,何必去作无谓的反抗。”这话传给父亲听后,他叹了口气说:“真没有说理的地方。”他是个犟脾气,又很迂。
要知道,当时这批受整的人,真切地感受到不幸,似乎人间已无公理、已无人性,时间又太长了,足足十年。有的不堪受辱,早早地而以自杀抗争;有的神经错乱,葬送了前程……,而我父亲不是,他要抗争,要发言,死硬到底。他的个性让他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记得,他也曾想改改自己的“大炮”脾气,说话要有节制,在书房的墙上一角,亲自用毛笔写了“慎言”两字,时刻提醒自己不要乱说话。但是,没有多大用处,他自己知道,不久,他把这纸条撕了,……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不是这个个性,他就不是我的父亲了。
现在,父亲去世已三十七年,子女也都到了退休的年龄,追究此事没有什么功利可言。是时间,是现在宽松的政治环境,给了我这个权利和责任,追溯历史,解开谜团,父亲的反动右派言论究竟是些什么内容?
2009-3-13
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