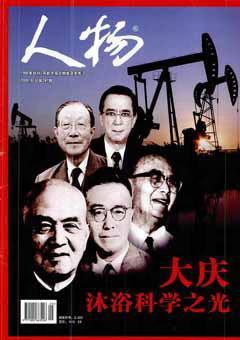景寅山 景仰陈寅恪什么?
贺 伟
那么,后人景仰陈寅恪什么呢,后人除了景仰陈寅恪杰出的学术成就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陈寅恪的学人风骨和人格情操!

公元817年初夏,被贬为江洲(今江西九江)司马的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登上庐山,写下著名诗篇《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时间过去了1113年,1930年,长住庐山的清末民初大诗人陈三立与友人李凤高、吴宗慈在白居易当年咏桃花的地方发现一块大石,上面刻有“花径”两个大字。经他们仔细考证,此石刻即使不是白居易手迹,也与白居易在此咏桃花有密切关系。于是,他们广为募捐,在此修建了保护刻有“花径”二字石块的“花径亭”,还在花径亭旁建了一座“景白亭”。景白亭前立有石碑,由陈三立撰写碑文,详细记述了“花径”石刻被发现,建花径亭、景白亭以表达后人对白居易景仰、纪念的过程。以花径亭和景白亭为中心的“白司马花径”现已成为庐山主要的自然、人文景点之一。
陈三立当然不会想到,在他主持修建景白亭的70多年后,庐山又出现了一座“景寅山”。景仰谁?景仰陈三立的儿子、国学大师陈寅恪——陈寅恪和夫人唐贫的合墓便安卧在景寅山中。景寅山和陈寅恪夫妇合墓又成为庐山一处著名的人文景点。
后人景仰陈寅恪什么?
陈寅恪原籍是紧邻庐山的九江修水县(原名义宁),陈寅恪与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大哥陈衡恪(师曾)祖孙三代4人同入《辞海》,这在中国,目前还是第一家。尤其是陈寅恪的名字,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响亮。
笔者曾参加过几次陈寅恪及陈氏家族的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活动,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谈到陈寅恪的大哥、近代著名大画家陈衡恪及其他几位亦业绩不俗的兄弟陈隆恪、陈方恪、陈登恪时,“恪”字都可以读“ke”音。唯独谈到陈寅恪时,“恪”要读“que”音,如果顺嘴读成陈寅“ke”,马上就会有很多人特意扭过头来,注视着发言者,目光中透出狐疑、甚至带点鄙夷,似乎在说“que”、“ke”都还没整明白,居然在此谈什么陈寅恪!因此,很多发言者都格外小心,但一会“ke”,一会“que”的,到底有些别扭。本都是“恪”字辈的亲兄弟,别人都可以读“ke”,唯独陈寅恪就非要读“que”,不这样读,就是对陈寅恪的不尊,就是缺乏基本的常识!由此可见,人们对陈寅恪不仅是景仰,已到了有些敬畏的程度,谁都愿为保卫陈寅恪名字的“正确”读音挺身而出。
后人景仰陈寅恪什么呢?陈寅恪的主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以及《金明馆丛稿》论文数十篇等,大都很深奥,表达方式也并不浅出晓畅。除了部分专家、学者、专业研究人员和莘莘学子外,大部分人恐怕很难真正读得进去,更甭说读通、读懂,深得其中三味了。显然,陈寅恪的主要著作不太可能成为畅销书,更不会成为盗版老手觊觎的对象。
那么,后人景仰陈寅恪什么呢?后人除了景仰陈寅恪杰出的学术成就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陈寅恪的学人风骨和人格情操!
请看陈寅恪墓碑上所刻的十个大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多么令人警醒、深思的格言!这正是陈寅恪学人风骨和人格情操的集中体现。多少伫立在陈寅恪墓前的学者、专家、莘莘学子和游人,默读着这十个大字,浮想联翩,心中难以平静。1929年,陈寅恪在为国学大师王国维所作的纪念碑文中郑重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70多年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被后人郑重地刻在了陈寅恪的墓碑上。
陈寅恪与妻子唐贫的合墓位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正式落成千2003年6月16日、陈寅恪113岁冥诞之日。
陈寅恪夫妇的合墓既高贵,又十分简朴和庄重。整个墓茔由12块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漂砾石搭建而成,这些石块已有200万年以上的历史,至今仍坚硬无比。墓垄右边的长条石上刻着“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没有任何介绍、评价的溢美之词;左边的扁圆形石块上,刻着由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题写的陈寅恪奉行一生的准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倡导正人君子要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为人处世要有节操、有原则,敢于坚持真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然而,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过于漫长的国家,历代历朝,统治者的思想就是这个朝代毋庸置疑的统治思想,“三纲五常”、唯上唯书、盲信盲从的传统习规根深蒂固。即使在封建制度表面被推翻后,这种传统习规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顽强地生存,有时甚至得到强化。所以中国有句流传极广的古训: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古训既能代代相传、历久不衰,自是凝聚了多少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足堪后人借鉴和吸取。但它有时太模棱两可,着实让人犯难,因为“时务”并不总是和“真理”、“信仰”相吻合。当“时务”与自己坚信正确的信仰、真理发生矛盾,甚至相悖时,有些人仍然能够坚守信仰和真理,纵然历经磨难也无怨无悔。而一些“善于”识“时务”者,则常常权衡再三,趋利避害,放弃一贯的信仰、原则,甚至做人的底线,即使不能成为“俊杰”,也可免灾祛祸,求个平安。
陈寅恪是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贯彻始终、从不随波逐流的。他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文中斩钉截铁地宣告:“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固守信仰、真理,有时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但固守者的人格魅力、风骨情操,常常会穿越时空隧道,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发出令后人炫目的光芒。
唯求学问不求学位
陈寅恪一生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准则,与他的家庭有很大关系。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20岁时就恩科乡试中举,走上仕途,只要循规蹈矩,自有大好的前程。但相继经历了英法联军进犯北京、火烧圆明园和中日甲午战争等惨痛事件,陈宝箴深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当他被朝廷任命为湖南巡抚,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后,便在交通闭塞、落后蛮荒的三湘大地大胆改革、推陈出新,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光绪二十四年(戊戌)4月23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开始变法维新。陈宝箴奋起响应,予以大力支持。变法失败后,陈宝箴即被革职,“永不叙用”,一年后又被慈禧太后“赐死”于南昌。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自小就桀骜不驯。参加乡试时,从不愿按要求写中规中矩的八股文,屡屡落第。1882年再次参加乡试时,已是30岁的他仍是率性而为,胆大妄为地用古散文体
作文,针砭时事,臧否人物,完全置个人前途于不顾,险些又因文体不合而落第,只因文章写得太好,主考官实在不忍割爱,才破格录取为举人。陈三立1886年中进士,官授吏部主事。可他不久就弃官离京,到长沙来协助父亲陈宝箴推行新政,时人誉他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为“维新四公子”。戊戌变法失败后,陈三立亦被革职,发誓不再入仕做官。他从此潜心诗文写作,成为清末民初诗坛泰斗,但桀骜之气并未稍改。陈三立1929年长住庐山后,蒋介石几次想见见这位久闻大名的“维新公子”,但陈三立对他的治国方针大略颇不赞同,尤其是对他“九·一八事变”后奉行不积极抗日的政策极为不满,每次都予以回绝。
陈寅恪的大哥陈衡恪(师曾)是中国现代著名大画家,早年留学日本时,和鲁迅、李叔同(弘一大师)关系密切,都是从不受封建礼教束缚之人。陈衡恪在上世纪20年代对当时中国画坛以画论画、不思进取、创新的现状极为不满,发表《文人画之价值》的著名论文,振聋发聩地宣告:中国画的内核是“文”,无“文”的中国画只会被带入一个可怕的死胡同!尽管陈衡恪的观点因“不合时宜”而被人讥为“苍白无力”、“寡不敌众”,但他却宣称“寡”则寡矣,未必“不敌众”。陈衡恪后来还将国外与中国传统山水画风格完全不同的漫画形式引进中国,又引起轩然大波。他仍是无所顾忌,照画不误,成为中国漫画的鼻祖。
生长于这样一个家庭,陈寅恪自小就养成独立思索、敢作敢为、从不盲听盲信的性格。他的特立独行的确给后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陈寅恪12岁就跟大哥陈衡恪、二哥陈隆恪去日本留学,直到3 5岁被清华大学国学院聘为导师,其间大部分时间在国外读书,学业超群。可他的口袋里,别说博士学位证书、硕士学位证书,就是一本学士学位证书也拿不出来,真是让人不解。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就曾困惑而又好奇地问过他:“您在国外留学一二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硕士学位?”陈寅恪回答道:“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陈封雄还不相信,又去问曾与陈寅恪一同留学的姑父俞大维。俞大维告诉他:“你六叔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们同在哈佛留学,他先走了,我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远不如他。”
1918年,已是28岁的陈寅恪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主攻冷僻的梵文和巴利文,由于学业突出,很快名噪哈佛校园,与吴宓、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原燕京大学名教授洪业在回忆初识陈寅恪时说道:“一个夏日,我在哈佛校园见一中国留学生衬衣露在长裤外面,且皱皱巴巴的,不由甚感惊奇。因为当时美国人都把衬衣下部系于长裤之内,以做潇洒状,各国留学生都竞相模仿。此人如此穿着,被视为极不礼貌、文雅,且有故意对洋时尚进行挑衅之过激行为的嫌疑。他却口诵诗歌,摇头晃脑,如入无人之境,丝毫不把四周投来的目光放在心上。旁人告诉我,这便是‘哈佛三杰之一的陈寅恪,我顿时倒吸一口冷气,另眼相看,肃然起敬了。”陈寅恪在哈佛学了两年半,认为该掌握的都已掌握了,马上就动身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东方古文学。老师和同学都极力劝阻,要他再耐着性子等半年,等拿到学位再去。陈寅恪说留学是为了学知识,既然已完成了任务,再待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岂可为了学位而浪费生命乎?
1924年,清华大学决定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欲聘请几位国学导师。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和已定为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尚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为国学院导师。曹云祥有些犯难,已聘定的三位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是举国公认的国学大师;赵元任是哈佛大学博士、著名语言学家;而陈寅恪既没有可以震慑人心的外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又没有让人心悦诚服的论著,在国内目前也没有什么声望,凭什么聘请他来国内堪称最顶尖的国学研究院做导师呢?何以服众呢?梁启超很清楚曹云祥的内心想法,对他说此人可了不得,将来必成中华国学翘楚,他精通和懂得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都对他评价甚高,中国不用他,就等着外国大学来重用他吧。曹云祥这才决定先试用一段时间看看。
陈寅恪应聘来清华国学院任教不久,校方就开始为找不到更大的教室而犯愁。每次陈寅恪讲课,抢先而来的教授、副教授比学生还多,学生无法靠前听课,甚至连座位都没有,又不敢和老师争抢,很有意见。教室一换再换,总是满足不了要求,陈寅恪很快就赢得了“教授的教授”的美誉。他随后陆续撰写、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扛鼎之作及大量水平极高的史学论文,为他赢得了更高的声誉。
困厄危难不改其志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是陈寅恪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所奉行的准则,同时也是为人处世,尤其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所坚持的原则,他决不会“审时度势”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更不会丧失节操人格。
1914年8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巴黎留学的陈寅恪回到中国。1915年,25岁的陈寅恪被聘为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此时,袁世凯正在筹划“称帝”。袁世凯担心具有将帅大才的蔡锷反对,将他软禁在京城,密切注视他的动向。蔡锷一边暗地里与梁启超、黄兴和云贵两省军界要员密商反袁大计,一边却曲意逢迎袁世凯。同时,蔡锷为了迷惑、麻痹袁世凯,早日离京,终日沉湎于曲院、妓院,与名妓小凤仙打得火热,不惜与家人“大吵大闹”,搅得满城风雨。蔡锷内心的秘密,当然不会告诉陈寅恪,他只要才华横溢的陈寅恪替他撰写各种应酬公文、颂扬文章。当时很多人都羡慕陈寅恪,年纪轻轻便谋得如此好职位,将来一定前程远大。陈寅恪却越来越烦躁、恼怒。他既反对袁世凯“称帝”,开历史倒车,又鄙视蔡锷的“所作所为”,更不愿去写违背他意愿的什么狗屁文章。熬了半年,陈寅恪便“自毁前程”,弃职而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余时旅居旧都,其时众人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丧尽,至为痛心。”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向香港发动进攻,12月25日,香港沦陷。此时,由西南联大准备去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并治疗眼疾的陈寅恪与家人被困香港,生活来源完全断绝。邻楼一户人家的5个女儿晚上惨遭破门而入的日兵的集体强奸,更让陈寅恪夫妇为三个女儿担惊受怕。陈寅恪在给友人的求救信中哀叹:“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数月食不饱,不食肉,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此时,大汉奸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与伪中山大学校长来到陈家,以高薪引诱陈寅恪前往中大任教,陈寅恪严
词拒绝,道:饿死、病死事小,亏损大节则万万不可!”伪北京大学校长钱稻孙以前困厄时,曾得到过陈寅恪的大力帮助,此时他为“报恩”,亦专程来港以高薪恳请恩师前往北大任教。陈寅恪痛斥道:“汝欲陷我于不仁不义,遭后世万代唾骂乎!”日本港督出资40万港币请陈寅恪牵头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新编教科书,亦遭到陈寅恪毫无通融余地的断然拒绝。后重庆方面派人帮陈寅恪一家秘密逃离香港回到四川。
1945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获得全面胜利,痛洗百年屡遭外国列强蹂躏的耻辱,中国重新昂首挺胸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蒋介石踌躇满志,自比千古贤帝唐太宗。他托与陈寅恪相知、相熟的党政要员及文化名流,欲重金请陈寅恪撰写《李世民传》,暗中为他本人树碑扬名。贫病交加、生活极为困顿的陈寅恪一口加以回绝,理由很简单:“我写文章,违背我本意的我决不写!”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国民党开始实施“抢救学人计划”,陈寅恪自然是首批被“抢救”的“国宝”。但他没有去台湾,而是南下广州。国民党党政要员、多年好友同事再三劝他离开大陆,有的直接把飞机票递到他的手中。但陈寅恪经过再三考虑,最终还是毅然决定留在广州。他认为政权更迭不应影响学术研究的独立与自由,留在大陆应比退居孤岛有着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天地。
此时,曾在1923年前后与陈寅恪同在德国柏林留学并有过一段交往的周恩来,委托陈三立的挚友李一平先生南下广州,看望陈寅恪,恳请他不要去台湾或国外,国内定居点由他定。如愿往庐山,可由新政权出资,将陈家的“松门别墅”全面整修,并给他配备相应的生活、工作设施。陈寅恪因各种原因暂未到庐山,在广州度过了他的后半生。直到他去世34年后,才终于和相濡以沫的老妻一起回到庐山,和千古文化名山永远相依相伴。
有一种声音叫沉默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后又担任中科院学部委员(现院士),受到国家政府要员的尊敬、礼遇和华南局及广东省主要领导陶铸等人的关照。陈寅恪心情舒畅,生活稳定,撰写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初步建立起自己宏大的史学学术架构。
但是,陈寅恪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准则却没有丝毫改变。
1953年底,中国科学院力邀陈寅恪回北京担任中科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中古所)所长,陈寅恪没有轻易答应。他对北京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用马列主义改造、武装知识分子头脑(俗称“洗脑”)的活动有自己的看法,对北京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生剥马列主义、立竿见影地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深不以为然,更对一些人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无原则、无道理地放弃几十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做法极不赞成。
因此,陈寅恪向中科院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研究历史不受政治干扰;二是为了确保能做到这条,请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写一个同意他这样做的“手令”,以备受到干扰和责难时拿出来做“挡箭牌”。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信中明确写道:“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的纪念碑文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我的学说也有错误,都可以商量。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时我就在瑞士通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是何等的惊世骇俗,陈寅恪的执著、刚毅的确令人惊叹!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全国随即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紧接着又展开了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陈寅恪在中山大学也开始受到冲击。虽然在陶铸等人的特别关照下,陈寅恪的正常生活未受到大的影响,也顺利过了“反右”关,但他的教学、学术研究却不能不受到较大影响。
很快,陈寅恪还算“平静”的生活便被打破了。1958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1958年6月,中山大学公开开展对陈寅恪的批判,1958年10月,广东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登出万言长文《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在众多的大字报中竞指责和嘲笑陈寅恪是“伪科学”、“假权威”。陈寅恪被深深激怒,向中大提出从此不再开课,不再带研究生。
在政治运动一波连着一波、一浪赶着一浪的情形下,陈寅恪要按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去研究、撰写、发表、出版史学的鸿篇巨制,已经是不可能了。但他又不能违背自己的准则,他只有选择沉默,近20年的沉默!这使他内心感到极大的痛楚。中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大都有一种崇高的信念,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最高理想就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也许不会去追求“修齐治平”,但还是会向往“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吧。即使在极为郁闷的年代,他仍然渴望能有继往开来、奋攀国学高峰的时机。1964年春,已是74岁、双目失明且跛一足的陈寅恪在赠老友向达(觉明)的诗中写道:“握手相逢庾岭南,失明膑足我何堪。倘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诗中流露出欲自我保重身体,等待时机,好再为探索国学奥秘贡献力量的强烈意愿。可惜历史最终没有给陈寅恪这样的机会,等来的是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他最终未能写出已成竹在胸、中国学界寄予极大厚望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等巨著。这是陈寅恪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这是陈寅恪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但是,不管心愿能否实现,不管身处何等境遇,陈寅恪自始至终坚守了他所奉行的准则。他在1964年《赠蒋秉南序》中说得直截了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陈寅恪晚年虽然沉默了多年,但并没有停止思索、停止探求。他凭着极大的毅力,在助手的帮助下,完成了长篇宏论《论再生缘》和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它们浸透了陈寅恪晚年的全部心血。
孟丽君、柳如是无所顾忌,活出真我、活出灿烂的所作所为,在陈寅恪
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愿意为她们唱赞歌。1961年8月底,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的吴宓出川前专程往广州看望陈寅恪,40年前“哈佛三杰”中的两杰饱经沧桑,无话不谈。吴宓在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之研究‘红装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道德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同时,写不违背自己意愿的文章,也是陈寅恪排遣内心苦痛、缓解精神压抑的寄托和方式。一个双目失明、又跛一足、备受冷落的老人,整天躺在床上构思、口述着皇皇巨著,虽然明知它们“不合时宜”,虽然难以预测它们是否、何时能够问世,但仍然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心灵的宽慰和快乐,这也就够了!休管春花秋月何时了,只愿一片冰心在玉壶。
然而,陈寅恪连这点可怜的“宽慰和快乐”都被无情地剥夺。在初起的“文革”风暴中,他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1969年lO月8日,一代国学大师——79岁的陈寅恪悲怆地离开了人世,身边只有老妻唐贳及家人相伴。唐篑是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比陈寅恪小8岁,与陈寅恪算是门当户对。唐贫1928年8月与38岁的陈寅恪在北平结婚,几十年与陈寅恪风雨同济,照顾极周。陈寅恪辞世后,唐贳强忍剧痛,镇静自若、有条不紊地安排好夫君的后事和家中琐事,45天后便从容地追赶“倔老头”而去。
魂归庐山,庐山何其幸也
2003年6月16日,陈寅恪113岁冥诞之日,中科院庐山植物园举行陈寅恪唐贫合葬墓碑揭墓仪式。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和夫人唐筼在辞世34年之后,终于入土为安,永眠在庐山的怀抱之中。陈寅恪1945年在作于成都的《忆故居》一诗中曾哀叹:“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松门”即庐山松门别墅),现在他终于梦想成真,魂归匡庐了。
庐山乃是陈氏家族温馨的家园,陈家4代都与庐山有紧密的联系。陈寅恪的祖父、父亲临死前都曾希望葬于庐山,都未能如愿。倒是陈寅恪的侄子、中国著名植物学家、庐山植物园创始者之一陈封怀最先归葬庐山。随着陈寅恪的归葬,陈氏家族便有两位成员葬于庐山。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40岁游庐山时,便在诗中写道:“匡庐五老(指庐山著名景点五老峰)绕乡思,真面何人写照来。”他已把庐山当做了家乡,并计划在陶渊明故里庐山南麓购置地产,为告老还乡时所用。1898年10月初,陈宝箴被朝廷革职,率家人从湖南返回江西。陈宝箴本欲在庐山购房隐居,因时间仓促,只得去南昌暂住,一年后猝死于南昌,草草葬于当地。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与庐山接触更多,1929年陈寅恪出资在庐山购买了“松门别墅”,陈三立终于实现了长住庐山的夙愿。陈氏家族成员此后时常汇聚庐山。直到1933年,82岁的陈三立因年事太高,多病,才离开庐山去北平陈寅恪处居住。陈三立1937年9月中旬因坚拒日军逼他出来任伪职绝食而死,死前留嘱归葬庐山。因战事紧张,交通阻断,未能实行。后陈三立辗转葬于杭州西湖之畔。
陈寅恪和唐筼辞世后,骨灰一直未能入土为安。20世纪末,陈家三个女儿开始商议父母落葬之事。根据陈寅恪生前意愿,她们和庐山方面洽谈此事,但并不顺利。后因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的慨然介入,才使此事出现了重大转机。
黄永玉2001年偶然得知陈寅恪欲归葬庐山而不太顺利,心中极不平静,年近80岁的老人当即决定要千方百计促成此事。黄永玉与陈氏家族并无丝毫瓜葛,纯粹是出于对陈门英杰的景仰和敬重。陈宝箴在任湖南巡抚前20年,就曾任过湖南辰、沅、水、靖兵备道两年,官署便在黄永玉的老家凤凰县城。陈宝箴为湘西百姓办了不少好事,黄永玉从小就听大人时常谈论陈宝箴、陈三立,后来又逐渐熟知了陈衡恪、陈寅恪,故对陈氏家族极有感情。完全出于自愿为陈寅恪归葬庐山义务出一份力。
黄永玉当即与陈寅恪女儿取得联系,详细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他随后又联系了湖南老乡、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毛致用。毛致用在江西任过几年省委书记,对此事亦极为热心。二老专程来南昌、庐山,与有关方面协商,终使此事尘埃落定。黄永玉还参与了陈寅恪夫妇墓茔的整体设计,书写了20多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条幅,从中精选出一张刻干墓茔的石块上。有人提议,请黄老先生将落款“后学湘人黄永玉敬书”几个字写大一点,醒目一点。黄老先生连连摆手说:“岂敢,岂敢,安能与大师比肩!能忝列大师墓碑一角,已是幸甚矣。”
陈寅恪先生辞世四十周年了,历史的蒙尘已渐渐拂去,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学术地位,尤其是人格魅力,越来越被后人所认识、推崇。拥抱陈寅恪唐贳合墓的山峰已被命名为景寅山;陈寅恪唐筼合墓现已成为庐山著名的人文景观。今天,当人们肃立在墓前,端详着墓石上陈寅恪的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会受到怎样的触动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