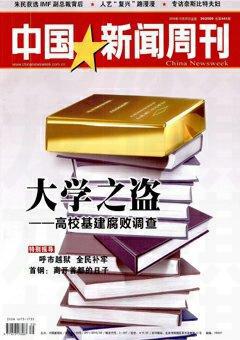象牙塔为何变身“蛀虫塔”?
王 婧

武汉大学两名正厅级官员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让“象牙塔”在公众心目中清水衙门的形象轰然坍塌。
与武大腐败案被曝光的同一天,广东湛江师范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郭泽深在学校基建、财务等方面涉嫌存在经济问题,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4天后,又爆出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张建刚、副院长王志贵因涉嫌基建腐败被“双规”。
这只是高校基建腐败的“冰山一角”。以武汉市武昌区为例——该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刘群在2009年5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因为在基建等领域“潜规则”大行其道,武昌区的8所部属院校中,只有一所院校没有人被司法调查。
象牙塔为何变身“蛀虫塔”?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工程管理研究所副所长邓晓梅表示,“高校基建腐败与其他的基建腐败存在着80%的共性,即在基建的各个环节都存在腐败的可能,但也存在着一些独特性。”
“高校成为封闭的小社会”——9年来一直研究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预防的邓晓梅用这句话来诠释她所指的“独特性”。
温床:高校的超常规发展
2001年8月,《中国新闻周刊》曾发表《腐败新灾区:高校》一文,分析高校腐败的发生、蔓延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萌芽,90年代中期的发展,以及90年代末开始大面积爆发。
7年后,南京工业大学基建处办公室主任孙义分析了中国高校基建部门100份犯罪样本,从数据上印证了《中国新闻周刊》关于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腐败大面积爆发的观点——1999年,南京市高校基建部门职务犯罪仅1件;2000年猛升至4件;2001年又翻番为8件;2002年头3个月就查办8件⋯⋯
高校腐败为何从90年代末开始大面积爆发?“高校腐败多发生于体制改革启动之际。”在孙义的论文中,他如是总结。
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而从1999年开始,高校开始超常规发展。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80万,到了2005年飙升至530万人——扩大了近3倍。
与招生人数同步增长的,是高校硬件设施的大幅度跟进。“从1998年到2005年4月,平均每年新建校舍300万平方米,大多数学校每年完成的基建工作量都在20万至30万平方米之间。新建、改建的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的面积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一次研讨会上称。
自扩招至2001年起的3年间,中国政府累计投入资金70多亿元。但这笔资金对扩张中的中国高校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如果按照当前北京大学约有3万学生计算,当年扩招的规模,需要在中国再建120所北京大学。而在短期内出现如此巨量基建项目,无疑为高校基建部门提供了腐败的“温床”。
同时,1998年《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颁布,明确了高校应“按照章程自主管理”,高校自主权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
据某高校基建处的一名员工回忆,从1998年到2006年之间该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教育厅对该校立项的批复上都会有“资金自筹”字样。而“资金自筹”也从那时起,逐渐取代了“政府投资”,成为高校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以武汉大学为例,2008年武汉大学基建投资计划共计15大项,其中国家预算投资1820万元,学校自筹7825万元,自筹资金是政府投资的4倍还要多。
对于“资金自筹”,北京某高校基建处一名员工解读——“言下之意,项目我批,但从哪里出钱我不管,至于如何用钱那就更不好管了。”
根源:一把手权力集中
在高校扩张的几年间,学校基建部门忙碌了起来。“以前就管零星的修建,偶尔有稍大一点的项目。但那几年不一样了,很多项目甚至是同时上马。”邓晓梅说,“对高校基建部门的人来说,项目管理的要求提高了。”
这个时期,高校的基建部门多采取了矩阵式的管理模式。以武汉大学为例,基建管理部由部长总负责,下设机构为部办公室、校园建设规划与土地管理办公室、基建项目管理办公室、项目投资与预决算办公室、技术管理办公室,然后由各办公室配合同时完成几个项目。
孙义认为:这一模式存在着天然的缺陷——部长拥有计划审批权、合同签订权、付款批准权、决算结算审批权、工程分包审批权等等。由于所有职能科室都设在基建部门,基建处长有权干涉、决定一切基建业务流程,权力过于集中。 “这种管理模式是基建领域通用的,如果说有问题,那也是基建腐败的共性所在,就像招投标制度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存在腐败一样。”邓晓梅表示。
而高校的基建腐败的“个性”,很大程度上源于部门的基层人员素质不够高。
邓晓梅曾经考察过北京奥运场馆的基建项目管理,高校和政府分别承担其中一部分场馆的建设,邓晓梅印象颇为深刻的是,“当时高校自管的基建项目和由北京2008工程建设指挥部集中管理的基建项目相比管理水平有明显差距。”她说。这是因为政府设置的集中式专业管理机构有条件从全社会聚合起“精兵强将”来管理项目,但高校主要还是只在学校范围内找一些懂基建的人来做项目,甚至有的就是普通老师兼职,时间精力投入和专业化水准都难以有保障。
邓晓梅分析说,“具体操办人员的专业化能力对预防腐败也是有相当大的作用的。比如负责采购的人,如果他不是很清楚两个东西究竟哪个对项目更好,当领导作出错误决定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从专业角度去反驳,去让领导清楚了解错误决定的风险后果。而本着谁做决定谁担责任的原则,他们更不愿意去承担做决定的风险。这就使得一把手的权力过大。”
比如在阜阳师范学院,尽管每一个工程都要走招投标程序,但时任阜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的张登歧利用分管新校区建设的职务便利,“想让哪家建筑单位入围就入围,想给谁打多少印象分就打多少分,倾向于谁中标谁就能中标,少有人能提出不同意见”,最终因受贿50余万元而被判刑。
在孙义调查的100名高校基建部门犯罪人员中,原任单位或部门“一把手”(起决策作用的分管基建校领导、基建处长、其他部门正职负责人)的为75人,占到总人数的3/4,其中,原任正厅级职务的为12人。
膨胀:监管的空白

根据孙义的调查统计,高校基建犯罪人员从初次犯罪到被查处为止,犯罪持续时间最长的为12年以上,平均持续时间为4.56年。人均犯罪次数为11.47次,最多的达74次。
此次武大腐败案,如果从2000年修建校外公寓时算起,至今已有9年时间。而根据媒体报道,此前不断有人检举,但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更有甚者,今年5月在相关部门调查武大基建工程腐败案时,陈昭方、龙小乐两人被“圈定”。可在接下来的6月24日的“全校干部大会”上,校党委书记却宣读了来自教育部的文件——《教育部关于陈昭方等职务任免的通知》,任命陈昭方等为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厅级)。
类似于这样“带病提拔”的状况,在孙义调查的100人中,在平均持续4年半的犯罪持续期内,没有一个人因为实施犯罪行为而职务下降,相反还有32人因为“工作实绩突出”得到提拔重用,接近总人数的1/3。
要发现高校基建领域的腐败为何会如此之難?除去龙小乐这样的人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之外,在监管上也存在着诸多不完善。
孙义表示,高校纪检审的干部对基建管理——尤其是工程技术及预决算等方面,并不在行。尽管他们也全程参与项目建设的全过程,但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譬如工程招标,由于并不懂得工程预算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因此也就不能发现评标过程中黑箱交易;由于没有工程专业技术知识,对于现场签证的必要性不能把握,由此也就不能发现可能产生的各种作弊行为等。
而邓晓梅则表示,由于高校项目很少外部审计,而内部的审计部门、会计部门与基建部门都同属于一个学校,又都由校领导主管;大家相互之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上级领导则更难以有约束,因此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很难得到切实保证。
按照高校自主管理原则,对于上述问题,加强校内民主监督或许可以弥补其不足。但实践中,高校的教职员工由于对基建不能深入其中,教代会以及校务公开等监督也没有真正形成气候。在对武汉大学的采访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接触到的多名教师均认为,教代会难以发挥大的作用。“你给我各部门的财务报表,我也看不明白。最好是能给我提供一份由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报告。”一名教师代表如是陈述教工代表的监督权的实际缺乏。
高校之外,主管部门则“鞭长莫及”。比如对武汉地区教育部所属高校,以及在十堰、恩施等武汉外市州的省教育厅所属高校,当地教育、财政部门“既管不了它的帽子,又管不了它的票子”。即使是对省属高校,湖北省省财政厅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处处长周学武也曾对媒体坦陈,过去主要只管其经费的划拨,报表的审核等,至于高校怎么“花钱”,主要靠高校自主管理。“因为高校经费来源是多渠道的,不光是财政拨款,所以许多不必经国库集中支付这一关”。
顽疾:改革滞后
事实上,教育部对高校的基建腐败知根知底。
2008年,中紀委、教育部、监察部就联合出台高校反腐倡廉政策,对高校反腐倡廉工作首次作出明确规定。2009年4月,教育部制定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征求意见。根据此办法,包括高校重大改革与决策、物资设备采购等被列入高校须向学校内部或社会公开的信息内容。同时,教育部直属基建处还成立了“高校基建监管体系调研组”,开始就高校基建监管工作情况开展调研。
武大腐败案案发后,教育部开展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视频会。会上,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袁贵仁介绍,教育系统工程建设专项治理工作自今年9月开始,至2011年5月基本结束。各单位要“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
“高校基建腐败牵涉到大学城内80%以上的高校。对基建引发的腐败,政府和司法部门想了很多方法,但没有收到满意效果。”一位参与多起高校腐败案侦查的检察官说。
邓晓梅认为,这是因为“高校自身缺乏对反腐败的关注,相关改革滞后于社会”。原因又在于,反腐败相对于高校的教学科研任务而言显然是副业,得不到应有重视;而“高校办社会”,自己各项基建、会计、审计、纪检监督等职能一应俱全,外部专业化的工程管理和监督审计力量也很难插手到高校内部,这就造成高校在反腐败的相关制度化建设问题上严重滞后。
如从2000年《招投标法》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省市都建设了网上招投标信息平台和有形建筑市场,这对于减少招投标环节的腐败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社会项目——凡属法定招标范围的,几乎都必须要进入有形建筑市场,招标公告都在网上招投标信息平台上发布,这就使众多的市场主体都有机会公平参加招标项目的竞争,减少了招投标中的暗箱操作。但由于高校自成小社会,尤其是类似于武汉大学这样的部属高校,其招投标信息,甚至不用经过当地的招投标中心,而只是在自己学校的网站上发布,这使得《招投标法》的威力到了高校就大打折扣。
政府的基建工程制度,这些年也有不少成功的探索。邓晓梅介绍,比如深圳市政府设立了建筑工务署,撤销各部门的基建办、项目办,收回相应的权力,所有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由建筑工务署负责操办。工务署的设立使政府工程管理的专业化水准得到了极大提高,并使各种外部监管力量得到了有的放矢的集中利用,政府工程的监督力度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在工务署运行的前3年,即为深圳市政府节省建设资金20多亿元。“一是人员素质高,二是所有的人都在盯着工务署怎样花钱,这种高聚焦的监管力度,使得他们很难出现腐败。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做法。”邓晓梅说。
在北京市,政府则大力推行代建制。即政府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和建设组织实施工作,项目建成后交付使用单位。这样也避免了各使用单位分散管理的非专业化的问题,减少了各使用单位的腐败问题。但与深圳的集中管理模式相比,政府发包机构本身缺乏工程建设的专业化能力,其他外部监督力量的运用还相对分散,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无论如何,毕竟在反腐败的探索上都迈出了一步。
但由于高校自主管理的特殊性,加上经费自筹成为办学的主要资金来源,使得大量高校基建项目难以纳入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渠道,其基建制度仍然沿袭着各使用单位分散自管的传统模式,专业化能力难以发展,强化腐败预防和监督相关制度建设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缺乏投入,使相关改革严重滞后于社会。这也就注定了象牙塔成为“蛀虫塔”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