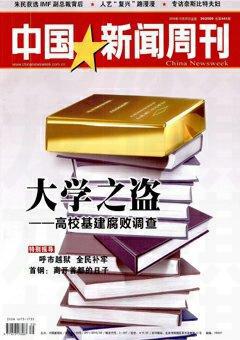首钢:离开首都的日子
张 蕾
1985年9月,381位首钢工人在比利时拆了一座名叫赛兰的钢厂。钢厂占地42亩,设备总重量62000多吨,2亿8千万个大小零件,拆迁编号写满了22册。一年后的1986年8月,赛兰钢厂从天津港上岸,中国当时唯一的一台120轮大型运输车载着转炉的炉体,14台大型拖车载着总计1300吨的设备构件在开道车、标杆车、指挥车的引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北京石景山,沿途围观群众无数,有的甚至爬到树上张望:看,首钢“搬”来了一座钢厂。
当时,朱文鑫、崔允、程国庆都看到了那宏伟的场面,而李金峰刚刚6岁。他们没想到,20年后,他们要共同经历一场更为波澜壮阔的搬迁;而这次要搬的,不再是沉重的设备,而是包括他们在内的一个个钢铁工人

“一生歉疚孩子最多的,就从今天开始。”2004年的一天,首钢员工朱文鑫在日记中写道。
作为他记录女儿成长的日记的终结篇,这一天的到来比朱文鑫料想的提早了7年——他原本打算从女儿在妻子怀中孕育开始,一直到女儿18岁成人,做全程记录。然而,这一习惯必须在女儿11岁时终止。
这一天,朱文鑫的工作地点从北京迁移到了河北唐山的迁安。确切地说,这里叫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是日后首钢集团“一业多地”的落户地之一。那时,皇城根下的钢铁公司里,多数人宁可相信,庞大的企业不可能彻底搬迁。甭管“奥运”和“环保”的呼声多么高涨,不在北京还能叫首钢吗?
2001年7月13日,从莫斯科传来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首钢领导又乐又愁。几小时后就召开会议,研究公司未来的环保发展。但他们还是高估了奥运倒计时中的首都对重工业企业的容忍度,“首鋼是北京蓝天、绿色奥运的大敌”,在北京和全国人民心中成了不争的事实。将这片“石景山区上空的黑云”赶出京城的要求,从官方到民间,一浪一浪地袭来。首钢不断压缩产能,在北京的立足空间越来越小;经国务院批准后,搬迁更加迫在眉睫。
时任《首钢日报》文化版编辑的朱文鑫感觉到,这个庞大的工厂抵挡不住时代大潮,还不如先走。同在首钢公司的妻子也同意,双职工家庭,走一个留一个,更有利于对形势的把握和适应。
“一是不想被动选择,搬迁这种事不是公司几个领导能够决定的;二是异地工作挣的钱多,你要养家糊口啊。”
从此,朱文鑫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河北北京的往返生活。他们一般周日下午从北京长安街的西头出发,一路向东,奔赴秦皇岛、迁安、曹妃甸,首秦(首钢在秦皇岛的公司)和迁钢、京唐(首钢在唐山的公司)是他们新的工作场所,但在员工的要求下,三地公司的前面都冠上了“首钢”字样。
他们都成了不在首都的首钢人。
朱文鑫:艰险的异乡之旅
1979年,朱文鑫16岁,被首钢的劳资部门“强行”从老家山东带到北京,为的是“接班”——作为首钢员工的父亲要退休了。尽管在与劳资部门的谈话中,朱文鑫明确表示对“当工人”没兴趣,但这次谈话显然不是来征求他个人意见的。
进京后,朱文鑫的钢铁工人生活正式开始。在业余时间,他坚持读书,在电大的文学班上,他与自己日后的妻子“早恋”。不久,一个典型的大型国企内的双职工家庭诞生了。
朱文鑫觉得,自己这代人和父辈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我父亲搞勘探的,40岁才回北京安定下来。咱们父辈那一代,在两地生活,好不容易到最后一起生活了,也退休了。现在我们到了中年,却开始了两地生活。”
新生活的疑惑,在周四黄昏后的首钢家属区里,朱文鑫感觉格外明显。
提前一天回来,吃完晚饭在小区里遛弯的时候,满眼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就像“35到50岁这拨男人都出去打仗了”。
“这代男人很悲壮,在外地工作、创业,其实跟参战是一样的。家里出个什么事,根本指望不上。咱说俗一点儿,家里着火了,120都送医院了,你还没赶回来呢。”
在迁钢的3年半里,朱文鑫的父亲去世,他赶路回来见到了老人最后一面;而对女儿成长历程的缺席,则让朱文鑫心存愧疚。每次回来,他都会陪女儿聊天,一直到两人聊着聊着睡过去;每次离开,他都会跟女儿隔着门的纱窗,两人食指相碰,说一句最想说的话;在外地的每一天,他跟女儿都会在晚上六七点钟时打一通电话,不管多忙都没有中断过。
为了能让家人安心,朱文鑫隐瞒了很多他在外地的“惊魂一刻”。
2004年跟他同一批去迁钢的22人里,已有两人死于往返京冀高速路上的车祸,而朱文鑫自己也有三次高速历险。
第一次,2005年,下小雪,他们几个人搭了一辆金杯车一起走。快到玉田的时候,路上已经结了薄薄的冰,车突然发生180度打滑。幸好没有后车追上来。
第二次,河北某路段,修路的路障和标识不明显,突然前面出现一个路障,急刹车一把打轮之后再贴边,差点翻车。

第三次是在晚上9点。开车的人想开开车门透透气,就这么一瞬间,方向盘就偏了,车在路上连撞了三下,翻了,朱文鑫和开车的那个朋友就跟太空人一样飞起来。他拖出已经昏迷的朋友,刚一站定,后面就冲上来一辆车,把他们那辆车顶出去几十米。车彻底报废了,万幸的是人没有大碍。
高速上发生的危险,朱文鑫从来不跟家人提起,女儿承受不了,妻子也有可能让他回北京工作。但是朱文鑫心里明白,“人已经走到这一步就不能再往回走了。”
除了交通事故,对朱文鑫来说,危险还来自于工作职责。
在迁钢,朱文鑫一开始在党群部主管纪检,查处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等违纪行为。一天回宿舍后没有马上锁门,进卫生间洗手的当口,就被人从身后袭击,住了10天院,缝了七针。
“那时候分析,是触及到某个人利益了。”
后来,朱文鑫被调到保卫处工作。总经理觉得,文人搞保卫,善动脑子,笔杆子定能战胜枪杆子。
当时的保卫工作,对一个异地建立的大工厂来说,是极其挠头的事情。迁钢所在地原是一个叫滨河村的地方,周边被几个自然村包围。因为保安需要在本地招人,而本地人的社会关系盘根错节,“什么表哥表姨的表弟,绕了半天他都能给你绕过去”,“女婿看门,老丈人偷东西”的事情时有发生,加上地方黑势力和金钱收买的诱惑,情况就更为复杂了。
朱文鑫在总经理的支持下给迁钢的六个大门都安置了门禁,员工进出门必须刷卡,有货物进出必须有朱文鑫签字的票据。本来一切似乎步入正轨,但就在朱文鑫去云南休年假时,保卫处出了件大事。
其间,有一伙人以拉废钢铁为名,把设备的备件拉出去了。装车时被人举报,派出所到现场,一共抓起来15个人,社会上8个人,迁钢内部职工7个人,包括保卫处的2人。经查,是里外勾结作案。保卫处的人找到了印出门票的印刷厂,做了一模一样的套票,得以蒙混过关。外面接应的是个有黑社会背景的人,为了抓住这个主犯,朱文鑫与警方一起跟踪、蹲坑折腾了整整30天,最后在沈阳一家大酒店将其擒获,连GPS、红外线望远镜都用上了,“跟电影里一样”。
这段没日没夜的经历让朱文鑫疲惫,更让他烦闷的是里里外外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个大案到最后“特别热闹”,甚至有点荒谬——“比如张三参与其中,结果还把他的情妇给弄出来了,因为撒网撒得太大了。”
离开迁钢调任到曹妃甸京唐公司时,朱文鑫手机里有1000多个号码,黑道白道的“朋友”结交了一堆,几乎每一个迁钢的人都认识他。他说,干保卫一年多,相当于在社会上混了10年;在外地生活,必须学会自我保护。这些年他仍然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虽然内容不可能再是他心爱的女儿。
他说,也许多年后,自己会整理出一本书,叫《在迁钢的日子》。
崔允:女劳模的青春和梦想
崔允把锅里的茄子和土豆煸炒成了黑褐色,也许跟酱油加多了有关。本来还想切点肉,但一想,麻烦,就这样吧。茄子炒土豆,是今天晚饭的一盘菜,另外两个是酱油煸菜花和青椒炒豆角。
时间已经过了20点,首钢公司的女劳模崔允才吃上晚饭。又一个在迁钢的平常日子,即将进入尾声。
“其实呢,没有人真的关心我们。你们也体会不到我们的感受。人们都比较关心那个胡什么,因为力拓的事情被抓起来的那个总经理。人们不会关心小人物的事情。”她边炒菜边摇摇头。
“人怎么都是活着。条件搁在这儿,认从这个条件,你就活着;你不认从,就灭亡。”
筹备迁钢那会儿,崔允正对自己眼下的活计不满意,“我有一阵子老闹腾,没什么事做。我又不喜欢瞎混。”于是崔允就跟时任迁钢总经理的邱世中说:“要不我跟你去迁钢?”邱世中一口答应。回家跟丈夫说,丈夫只说“你高兴就行”。以后崔允就没再问过丈夫的想法,虽然她也觉得丈夫该是不大舍得她到异地工作的。
在崔允看来,来迁钢只是个生存的选择,“对外来说,让人觉得,这人真有觉悟什么。这是瞎话。其实是个很自私的选择,自己觉得心里平衡、舒坦了,就没有想家里人什么感受。”
放出去迁钢的豪言后,调令一直没有下达。这期间,崔允心里的矛盾越来越盛,甚至有点恍忽。
“也会觉得怎么像假的一样,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我当时想,如果‘邱头儿说你们过来还要等个什么手续,有困难,好,我就不去了。我到最后的时候就这样想,最好能不去。”
最终崔允还是跟着邱世中去了迁安,那里当时还是一片荒郊。日子一晃过去了将近5年,对工作的自我满足感和对家庭的愧疚感还一直伴随着崔允。

雖然有点拿回家当完成任务,可是呢,一旦回了家,就不愿意再出来。
崔允只到首钢厂东门的班车站坐过一次班车,她讨厌那种感觉。一方面是她的家在宣武区,离厂子远;另一方面,坐地铁去厂东门的路上心里更别扭,“孤孤单单,典型的背井离乡”。
不加班的情况下,崔允一般两周回一趟家,往返都是“蹭领导的车”,“自己开车开不起,来回要400块钱。”通常是礼拜五晚上五六点钟到家,礼拜天下午四点左右从家走。也就是说,她每个月待在家里的时间不足100小时。
今年已经52岁的崔允,还有三年就退休了。
哥哥16岁去东方红炼油厂当学徒时,崔允就背着妹妹跟在一旁,身边全是炼油工人。12岁的小崔允特别喜欢那些炼油的大哥哥大姐姐,当工人的梦想就在心里扎根。1975年,崔允所在中学的化学老师为了说明什么叫氧化还原反应,带着学生们参观了首钢。那天,首钢的大喇叭里响彻着邓小平提出的“钢铁元帅要升帐”。崔允自诩是个“政治狂”,她一想:反正都是工厂,我赶明儿也来这上班吧。
没想到,工作生涯的最后几年,她又赶上了首钢的历史性搬迁。
在崔允眼里,现在的迁钢比尚还坐落在长安街西尽头的那个落魄院子好得多。“迁钢挺漂亮的。礼拜六礼拜天最好,没人,厂子里干净,就剩我自己,我看着特高兴,也有自豪感,这漂亮的地方,咱是其中一员。”
崔允把自己戏称为迁钢的“倒计时老太太”,她对工厂里的氛围已经充满依恋。
“我刚到迁钢来的时候说,应该有作者写一个小说,叫大迁移。在北京城最西边的一群人,他们横穿长安街,就到了东边来了,从东边,又轰到距北京多少多少公里以外去了,他们在那儿有好多故事。如果我来写,就以一个中年人为主角,这个人不能像王进喜那样,而是要很诙谐。我那时候瞎想了好多故事:贪污的,有跟地方勾结的,有离婚的,有瞎搞的⋯⋯后来发现,真的什么都有。”
李金峰:这里的未来以十年计
一个80后的小爸爸,退休还太遥远,搬迁后的生活虽然寂寥,却也没什么别的盼头。那就好好工作,多多挣钱,努努力把妻子也弄到附近工作,希望这里能许给这个年轻的三口之家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就是京唐公司李金峰的简单想法。
位于河北曹妃甸的首钢京唐公司,年轻人占了大半江山,都跟李金峰有着大抵相同的想法。
李金峰的妻子小他三岁,是一名医护人员,京唐公司里很难给她找到工作岗位,李金峰就盘算着把她从北京调到唐海县城,那样离得近些。
京唐公司的人把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曹妃甸直接称为“岛上”,因为其原系滦南县南部海域一带状小岛,总面积为16平方公里,距大陆最近点大约18公里。于是,在河北省政府的主持下,从陆地到海岛吹沙填海,修建起一条18公里长的公路,每公里成为“1加”,京唐公司大约位于“11加”处。
首钢公司内部流传着一套顺口溜:“围坐帐篷中,面对蜡烛灯,飞沙难睁眼,夜半机器鸣。早起穿棉袄,中午汗淋胸。水比柴米贵,买菜百里行。建设新首钢,煮酒论英雄。奇迹何人创,小岛建筑工。”说的就是曹妃甸的事情。

岛上原本一无所有,深港的优势招徕了各方的拓荒者,从此成为一方工业热土。“15加”有小菜市场、廉价服装店和三四间网吧,也有一些洗头房。
“18加”有沙滩,可以去捉捉螃蟹。但京唐公司的人还是不常出门,一方面是因为附近的住民都觉得首钢人有钱,卖东西给首钢人的价钱总是要贵些;另一方面岛上大风简直能把人吹跑,恁辽阔的土地只有汽车才是合适的交通工具。上下班坐在公司的大巴上,李金峰时常能看见,路的一边放着几根闲置的大钢管,上面张贴着悬赏寻找车祸目击者的告示;而路的另一边则乱石丛生,有建筑工人当街撒尿,两根钢管撑起一个“天沐洗浴中心”的大牌子,足有20来米高,空落落地立在一片乱石和杂草之上。
除了偶尔去“15加”的小酒馆和工友们聚聚,李金峰很少外出,他对现在的生活环境基本是满意的。“这里住的比北京的宿舍好多了。”李金峰说。
有空调,能上网,两个人一间屋子,采用酒店式管理,每天有服务员来给叠被子,并且有独立的卫生间,不用像在北京的宿舍那会儿混单位的大澡堂子,汽水、香皂等国企福利用品也是一应俱全。“这儿发的洗发水比(北京的)首钢好。”
厂前公寓是一水儿的6层楼,一排排小楼背后,就是海,一片已经被人造田包围的死海。生活污水排放在此。这里没有潮涨潮落,只有泛绿的水波轻微冲击着岸上的这座工业孤岛。如果天气不是太差,从公寓这边就能够看到对岸的厂区,李金峰他们部门那个大大的“火炬”更是突出。
吃完晚饭,有工人成群结队地在公寓周边遛弯,看看日落,吹吹海风。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喜欢游泳或打篮球、台球,台球厅和游泳馆都是6元/小时,他们觉得有点贵。也有宅在屋里的,年轻的打电脑游戏,年长的师傅就打牌。
娱乐活动就止于此了。
报告文学《曹妃甸》和《首钢大搬迁》的作者王立新曾在岛上生活过。他说必须每周回北京一次,再怎么坚持都挺不过一周。
“就是寂寞。不是一般的寂寞。那里什么娱乐设施都有,但生活的氛围没有,是一片荒漠,月球表面一样的沉寂和荒凉。大海好也不能天天看呀。”王立新直摇头。“我回北京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活动,就是感觉回归生活了。”
王立新曾经跟京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吴福来闲聊,有一句话让王立新印象深刻。吴立新说,这是个看到“花衬衫”就睡不着觉的地方。而“花衬衫”就是女人的代称。
在重工企业,10个人里能瞅见一个女人就属不易了,况且这里是岛上。
李金峰每天都要跟妻子通一番电话,要是赶上手机没电又一时充不上,第二天一早老婆的电话也一定会追到。“担心啊。”
当然,有时妻子的电话也做“查岗”用。
今年4月,“中华情•黄金宝地曹妃甸大型文艺晚会”来到曹妃甸,“慰问曹妃甸广大建设者”。一阵歌舞升平和炫目的烟火过后,岛上的人们还是要投入滩涂上的艰苦奋斗,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真正看到这块宝地的金黄丰收。
“这里的未来⋯⋯我们都是以十年计的。”
程国庆:首钢的香火
程国庆今年很高兴,因为“四喜临门”:50岁生日,60年国庆,首钢90年,进入“百姓宣讲团”。
他出生在1959年10月1日,长于一个地地道道的首钢世家——父辈在首钢炼铁,他这一辈在首钢炼钢。大哥叫程铁柱,大姐叫程铁花,弟弟叫程胜利,除了爸爸、叔叔、哥哥和弟弟,程国庆的妻子和岳父也是首钢人。这还不算完,他学工商管理的女儿明年才大学毕业,他就给定好了,来首钢工作。
“就像血脉似的,别断了。如果她不去,下一辈就没有首钢人了。”女儿也同意了,首钢什么岗位要人,她就去什么地方。
程国庆对老厂子的不舍,是从父亲程德贵那里继承来的。程德贵在世时,有一次夜里突然爬起来,戴上白手套就要推车出去,说“高炉有事故了,我要去”。儿子吓得赶忙拉住他。
首钢搬迁,程德贵也从报纸和电视上知道了。2004年,就在临终前几天,老人突然提出要到高炉上看一眼。当时的他行动和说话都成问题,儿子们不同意他的要求,但老爷子执拗得很,于是第二天儿女把老父亲送到高炉上。程德贵看到他一直牵挂的5号高炉,两眼直直的,什么句话都没有说,最后只是向5号高炉挥了挥手。这也是老人与一辈子相伴的“工作伙伴”的最后道别。
2005年6月30日上午8时,天空飘雨,首钢连续生产了47年的5号高炉停产。“我代表全家,在留言簿上写下老爷子生前老叨叨的一句话:‘五高炉,我的老伙伴,我永远忘不了你。”算是完成了父亲送别的遗愿。
2009年5月,京唐钢铁厂高炉开炉、出铁的时候,程国庆又带着父亲的照片来到曹妃甸参加了开炉仪式,以此彻底告慰了一个老钢铁工人的在天之灵。
首钢搬迁,作为老首钢人,程德贵确实留恋,但是他也坚信首钢会越来越好。程国庆说,父亲知道日本的新日铁就建在海边,曹妃甸钢厂依邻深水港口是有前途的。
为庆祝新中国建立60周年,北京市搞了一个“百姓宣讲团”,召集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去北京各区县演讲。程国庆代表首钢,演讲的题目就叫“首钢高炉和我家”。稿子是《首钢日报》、首钢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帮着修改拟就的,还请了懂讲演的老师来教授语气和动作。
“我代表首钢多少万人哪。只能讲好,不能讲坏。” 程国庆说。
为了准备这个演讲,程国庆在家人眼里“跟神经病似的”。10分钟的讲演,需要脱稿,从没上过台的程国庆要面对千余观众,压力很大,起初一上台就直哆嗦。他用了一周时间背稿子。对着墙背,在家里试讲,还坐着公交车到香山演武厅的练武台上去练习,甚至为了加強记忆,拿纸默写了十多遍。
被问到演讲的内容时,程国庆会流畅而富有感情地背诵给你听,连在台上表示胜利的攥拳动作都不落下。
“人得有精神支柱,没有精神支柱就完了。像我们这个家庭,好几辈都在首钢,根扎在这儿了。首钢人还是爱首钢。”
首钢陆续搬迁后,程国庆也填报了志愿表,表示服从分配。目前他的工作是留守北京的总公司,做些绿化、卫生清扫和设备看护的工作。
“我觉得首钢还是需要我的。我现在身体还行,还能为首钢干,我不是一个废人。国家还是会想到的,还是会安排工作的。”
程国庆所说的需要,就是首钢要效仿德国鲁尔区和北京的798工业创意产业园区,将原址改造成钢铁公园、博物馆等,这些工作还需要有人来打理。
“发展的前景还是广阔,要发展还是需要很多人的。”还有5年退休的程国庆,仍然对这段不算短的工作历程满怀憧憬。
“百姓宣讲团”也来到首钢,现场来了600多人,曹妃甸那边还搞了同步直播,程国庆是最后一个发言。宣讲结束后,首钢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朱继民接见了程国庆,这让程国庆很激动,完全没想到。
“我就一普通工人⋯⋯他呢,平易近人,特别随和,亲切,没架子。”
至今,程国庆仍然保留着1979年进厂时父亲送他的小闹钟。这个闹钟是1956年程德贵获得“全国先进生产者”时的奖品,因为这项殊荣,程德贵去了中南海,还与毛主席、周总理合影,这差不多是老人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程德贵退休后,程国庆接班,小闹钟被当作传家宝传给了这位年轻的三炼钢工人。
“父亲叮嘱我‘三班倒的时候,上好小闹钟,别误点。这个小闹钟到现在还是我的精神支柱。”
当程国庆领着王立新走进搬迁后的首钢大院时,王立新觉得“一切都静止了,三炼钢的大门锁着,铁轨长锈了。大货车停在那里,已经不动了;橱窗里以前的照片都晒得发白了。一种死亡之感。”
这时,他看到几个绿化的职工在精心地除草、修花。王问他们:停产了你们还弄它干吗?他们说:停产了也是咱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