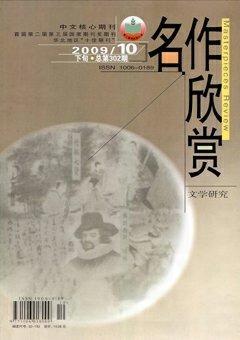醉态诗画
西人所言缪斯,国人灵感之谓也。灵感隐匿,藏而不露,醉态之间,方显紫光。张芝怀素酒辄草书,游云惊龙、奇崎异样;阮籍、刘伶齐集竹林,肆意酣畅,对杯感伤。当饮酒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人生态度时,酒已不再是酒,醉已不再是醉,陶渊明已不再是陶渊明、李太白也非李太白了。
陶渊明有《饮酒二十首》诗,千古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出自这组诗的第五首。“悠然”之态,空濛缥缈,雾里看花,“悠然”之遇,心无滞物,物我两忘。白居易有《效陶潜诗十六首》,苏东坡有《和陶饮酒二十首》,但均无宋人唐庚《醉眠》中的“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句诠释得贴切恰妥。悠然中的寂寂,悠然中的绵绵,只有遁形醉乡后,方可呈现。《醉眠》最后说:“梦中频得句,拈笔又忘筌。”醉乡中的思绪,或激昂慷慨,或柔情缱绻,恍惚中的情景,或悔不当初,或牵肠挂肚,原本失忆的往事,清晰眼前,曾经无意的浏览,顿得其趣。待酒散志定,提管寻句,往往武陵渔人不复得路,一无所获,空空如也。
醉态思维最为接近诗歌的真质。“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醉态之下,李诗立意皇皇,佳句连连。“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高峰坠石,石破天惊;“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雄浑雅健,气宇轩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心绪郁结,回肠九转;“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悲天悯人,怅然若失;“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守”,襟怀恢廓,冰心一片;“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涉猎成趣,楚楚媚人。醉态将李白导入玄境,生命在此超越时空,打破秩序,因此醉态里的李白将诗歌孤圆之月般推升到了青空天心,盛唐气象若没有李诗风尚的衬托和映带,将会是何等的逊色与缺憾。
我行我素、怪诞不经的徐渭每每于醉后挥洒泼墨,烟岚满纸。墨牡丹、黑葡萄,动静如生,悦性弄情;绝岩壁、悬瀑布,纵横淋漓,跌宕有变。其作画拒绝“空染胭脂媚俗人”,而仅以个性化的水墨直抒胸臆,排谴块垒。生宣纸楮,墨晕渗漉,虽失物象本质,层次融合却极为丰富,轮廓边际模糊,却如天然生成,为画谱不设,前人少见。加之寓姿媚于朴拙、寓霸悍于沉雄、笔法圆转、结体善变的题字,辅以戏谑调侃、抑郁不平、惊世骇俗、自我标高的题画诗,使之作品具有一股扑面而来、抹之不去、拍奇称奇、叹为观止的艺术感染力,难怪郑板桥有“青藤门下牛马走”,齐白石有“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的叹吁。文朋诗友、门生晚辈往往乘其酣适兴发之时征字乞画,于是狂涂一气,掷笔而就。其《又图卉应史甥之索》诗对这一过程有过描述,其中的“小白连浮三十杯,指尖浩气响成雷”句,写出了酒后内在冲动挣脱意志力控制时的感受。陈鼎《八大山人传》云:“山人既嗜酒,无他好。人爱其笔墨,多置酒招之,预设墨汁数升,纸若干幅于座右。醉后见之,则欣然泼墨广幅间,或洒以敝帚,涂以败冠,盈纸肮脏,不可以目。然后捉笔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花鸟竹石,无不入妙。如爱书,则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醒时,欲求其片纸只字不可得,虽陈黄金百镒于前,勿顾也。”又据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记述,熊国定曾置酒款待八大,趁其酣醉之时,请对东湖美景作画;画毕,八大接饮,有人又乘其余兴未尽,以笺索画。对索唐伯虎字画的情形,时人也有“欲得伯虎画一幅,须费兰陵酒千钟”之谓,郑板桥也曾自嘲道:“看月不妨人去后,对花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索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这其中固然有求画者的伎俩花招,但当事人的嗜好瘾头却是内因所在。板桥嗜酒如命,每至黄昏,若无酒入喉,必起咳嗽呕吐,粒米难咽,因此还镌得一闲章,曰“酒痴”。
借助酒力荡涤脑中之闷,消解尘世之累,呼得人性之挚,继尔援笔挥毫,浩浩杳杳,不滞于手,不疑于心,不知然而然。吴道子“每欲挥毫,必须酣饮”,傅抱石每作画必借助酒兴,好酒使气,“当其下手风而快,笔所未到气已吐”,其追求的大致就是这样的效果,为此,傅还刻有“往往醉后”的闲章,画室挂有清人联句:“左壁观图,右壁观史;有酒学仙,无酒学佛。”虽说饮酒的形式杯盏传唤,吆五喝六,刍豢盈盘,歌吹满耳,不免有些野腔无调、孟浪率尔、语无伦次、颠三倒四之态。宋代以画虎著名的画家包鼎,动笔之前,先洒扫画室,关门闭窗,仅以一穴透光,然后一饮斗酒,卧起行顾,踞地而吼,俨然一真虎,于是再饮斗酒,取笔挥毫。元代以绘龙著称的画家陈容,醉余即大声喊叫,脱巾濡墨,信手涂抹,顿时龙隐云水间,见首不见尾。清代画家项维仁,每遇大风雨,辄饮酒极醉,破笠赤脚,登山顶,观冈恋之冥■,云树之迷漫,鼓掌狂叫,疾走归,据案伸纸,奋笔直追,濡染淋漓,烟气犹湿。画已,张壁间,取斗酒赏之。良久,忽大哭,立毁之。他日风雨复然。有尚书督军者,阅边至温州,语及维仁画,兵备道立遣人召之。时方大雨,维仁破笠赤脚至,道降阶相迎,与抗礼。维仁曰:“某庶人耳。辱公厚召,故来。将奚役?”道以情告,陈百金几上。维仁直视曰:“某不知画。即画,岂用以媚大府者!”不谢走出。
酒后哓哓者还有张旭,据《唐书·贺知章传》云:“旭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曾与贺知章访游,见人家厅馆白壁新涂,屏幛净洁,于是趁借酒兴,忘机挥毫。更有旷古莫闻之举,披发蘸墨,龙飞凤舞,醒起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其酒后“醉墨淋衣巾,一挥三十幅”的体验,洵非虚语。杜甫《饮中八仙》称其:“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后来,张大千据此还创作过一幅《豪发作画图》。贺知章也喜醉后狂草,据窦蒙《述书赋注》载:“每兴酣命笔,好书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诗笔唯命。问有几纸,报十纸,语亦尽;二十纸,三十纸,纸尽语亦尽。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刘禹锡于洛阳见贺知章草书后,欣然赋诗道:“高楼贺监昔曾登,壁上笔纵龙虎腾;中国书流尚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固独见空惊目,恨不当时便伏膺;惟恐尘埃转磨灭,再三珍重嘱山僧。”唐人许瑶在《题怀素上人草书》中说:“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苏东坡也曾言:“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奇耳”,“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气拂拂然从十指间出”。东坡于元■元年撰写的《答钱穆父诗帖》及后来米芾的《绝句诗手卷》落款处皆有“醉书”字样。
王羲之当年醉后挥毫成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后傅山据此兴发,写过一幅名曰《右军大醉诗轴》的草书:“右军大醉舞蒸豪,颠倒青蓠白锦袍。满眼师宜欺老辈,遥遥何处落鸿毛。”其用笔拙中流畅,缠绕游丝,布局欹斜反正,相避揖让。从章法上的酣式到情感上的醉态,纵敛开合、大起大落间,便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醉起酒犹酒,老来狂更狂”,只不知是右军大醉,还是傅山大醉。诗中所言师宜为师宜官,是活跃于东汉末年的一位书法大家,善隶,其“不持钱诣酒家饮”,壁间醉书,以换酒客赏钱,待筹得后,再将书迹擦去。萧衍《古今书法优劣评》说其醉后“书如鹏翔未息,翩翩而自逝”。
明人周晖《金陵琐事》曾记吴伟事:“吴小仙饮友人家,酒边作画,戏将莲房濡墨,印纸上数处,主人莫测其意,运思少顷,纵笔挥洒,成《捕蟹图》一幅,最为神妙。”吴昌硕醉后曾以酒和墨,画出的梅花孤寂如老僧,倔强如诤友,离奇如豪侠,清逸如仙家,最是
精彩。
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言“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概基于这些事例。《庄子·列御寇》篇云“醉之以酒而观其则”,也是此意。冲破法度藩篱、摆脱理性制约的途径,却在于酒精或微醺或酩酊的傍助。苏轼《题醉草》云:“吾醉后自以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黄山谷也说苏轼:“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文味,真神仙中人。”醉不足以扰其心、使其气,反使之“奇耳”。这样的艺术规律,抽象得如同艺术本身,着实令人难以琢磨。
酒有十德,曰“百药之首,延年益寿,旅途作伴,御寒代衣,馈赠佳品,解忧消愁,结交贵人,能除疲劳,万人同乐,独居之友”也。坊间传布,功利色重,无非是酒之浅论而已,实则酒功也。酒力使气,气可冲牛斗,气可味幽婉;酒意通神,神乎其工技,神乎其妙算。更重要的是它能驱除华伪,解脱精神,唤起人性本真,催生美的意识。
绿蚁黄花、翠涛兰生、桑落竹叶、屠苏羊羔,缤纷玉壶液,皆入别肠中,殊酒一性,与先贤同醉。醉中之境,出神入化,妙不可言,故陶渊明就曾发出过“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的痴愿。酿海为酒,尽醉国民,虽是轻狂妄言,却也耐人寻思。醉态不是文化的常态,是文化的另一种生存。有一朵用酒精浇灌培植起来的花,热烈,奇崛,羽仙,酡红着脸。
作者简介:介子平,编辑之友杂志社副主编。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