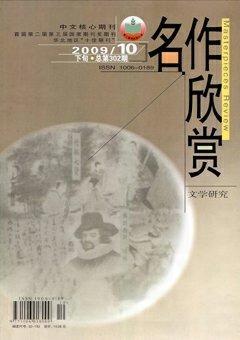从施蛰存的《石秀》看石秀的“表”与“里”
关键词:施蛰存 石秀 性变态 表与里
摘 要:施蛰存在20世纪30年代写了小说《石秀》,这篇小说其实是按照四百多年前施耐庵的《水浒》中的石秀改写的。施蛰存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剖析石秀的种种言行的深层心理动机,写了一个与《水浒》中的石秀有些不同的石秀,《水浒》中写的是石秀的“表”,施蛰存写的是其“里”。从而使石秀成为一个立体的、复杂的、合乎情理的,同时也是真实的人。
施蛰存在20世纪30年代写了小说《石秀》,这篇小说其实是按照四百多年前施耐庵的《水浒》中的石秀改写的。施耐庵用白描手法在《水浒》中塑造了一个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起义英雄石秀。而施蛰存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剖析石秀的种种言行的深层心理动机,写了一个与《水浒》中的石秀有些不同的石秀,此石秀是不是彼石秀呢?
一
有人认为,施蛰存的《石秀》“将古人现代化,将古人弗洛伊德主义化。作者是按照弗洛伊德、蔼理斯这些现代人的理论主张来写古代人的。在施蛰存笔下,石秀几乎完全成了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的色情狂和变态心理者,成了弗洛伊德学说所谓‘性的冲动与‘侵犯冲动的混合物,他不但因私欲不遂、出于忌妒而挑唆杨雄杀死了潘巧云和迎儿,甚至还变态到专门欣赏‘鲜红的血是何等‘奇丽,从被宰割者的‘桃红色的肢体,‘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简直可以说是嗜血成性,嗜痂成癖!弗洛伊德理论原是在研究精神病患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学说,它的最大的荒谬之处,便在于把正常人都当作疯子。从小说《石秀》视丑恶为美好,把残酷当有趣,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学说有时会将文艺创作引到思想倾向多么恶劣的地步。用这种指导思想造出来的石秀,哪里还有多少宋代人的气息,分明打着现代超级色情狂者的印记!”①施蛰存认为这种说法对他的作品有所误解,施蛰存在1992年3月7日给我的信中说,他与施耐庵写的是同一个石秀,两个石秀所不同的只是描写的角度不同,“因为《水浒》中写的是石秀的‘表,我写的是其‘里”。
在《水浒》中,施耐庵写了石秀夜杀裴如海,并出谋策划怂恿杨雄杀死潘巧云。从表面看,石秀是在为兄弟杨雄的利益而拔刀相助,但他的这个行为早就有人认为有些不可理喻,金圣叹在《〈水浒〉评点》中说:“石秀可畏,笔笔写出咄咄相逼之势”,“石秀又狠毒又精细,笔笔写出”。周作人也说:“武松与石秀都是可怕的人,两人自然也分个上下,武松可怕是煞辣,用于报仇雪恨也很不错,而石秀则是凶险,可怕以至可憎了。”②而且金圣叹和周作人都认为石秀的行为是“假公济私”。
施蛰存的《石秀》在金、周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发挥,他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剖析石秀的内心,解剖他怂恿杨雄杀妻子的真实心理。
施耐庵在《水浒》中描写的石秀,是石秀的表象:超人的胆识,精细的计谋,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真可谓出类拔萃,光彩照人。如石秀初上场见张保等人逼住杨雄,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张保劈头只一提,一跤颠翻在地”,然后“一拳一个,都打的东倒西歪”。寥寥数字,英雄形象跃然纸上。再如当石秀发现潘巧云和裴如海有奸情,就在肚里暗忖道:“莫教撞在石秀手里,敢替杨雄做个出场,也不见得。”这个心理活动表明了石秀要报复潘、裴二人,报复的原因是为杨雄做个出场。当然,很多人能从施耐庵含蓄的描写中,看出石秀的真正动机,如周作人说的:“为的要表白自己,完全是假公济私。”③我们可以从施耐庵的描写中的蛛丝马迹看出石秀的杀人动机,如石秀曾一再提醒杨雄:“哥哥含糊不得”,“一发斩草除根”,并亲自将潘巧云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这一来表现了石秀对杨雄的怂恿,二来表现石秀对杀人的“欣赏”,《水浒》的作者不经意地把石秀的内心世界显现出来。
施耐庵在《水浒》中尽量回避石秀的杀人动机,是由于作者封建思想的局限所致,施耐庵轻视女人拔高英雄,因为封建时代把“女人”看做祸水,把“性”视作邪恶,作为被作者歌颂的梁山好汉。当然要与邪恶绝缘。如《水浒》中的石秀所说:“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如何肯做这等之事?”
施蛰存不回避英雄人物“不光彩”的一面,他顺应事物的必然,去探究石秀杀人表象的深层动机,进入其潜意识,窥视到石秀由性压抑和嫉妒而产生的变态心理。从而塑造出英雄气概与小人心胸俱存,侠义心肠与自私自利互见,有缺点有优点的二重人格的石秀。
施蛰存作品中的石秀形象,是在人物自身存在的情义与性欲的两重斗争和冲突中完成的。“是由生命中两种背驰的力的冲突来构成的”④,这种本能的欲念与现实的抑制之间的冲突,充分表现了二重人格的心理冲突和人格矛盾。
施蛰存首先窥探到的是,石秀爱上了潘巧云,而潘巧云又是个放荡的女人,这在《水浒》中已经表现出来,她不仅与和尚私通,而且也常常对石秀“说些风话”,勾引石秀。何况又是个极美的女人,施耐庵在《水浒》中采用侧面烘托的手法表现了潘巧云的美:当潘巧云来到法坛上,一堂和尚见了,“都七颠八倒起来”,并“自不觉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时间愚迷了佛性禅心,拴不定心猿意马”。
对于这样放荡的美妇人,石秀为之动心也不足为奇。因为《水浒》写的是英雄好汉的石秀,所以作者回避了石秀对潘巧云爱恋的心理活动。施蛰存恰恰相反,他渲染了这个心理活动,表现了这个潜隐在冰山下的翻江倒海的感情思潮。施蛰存写石秀见到潘巧云以后,“石秀心里便不禁给勾起一大片不尽的思潮了”。潘巧云那“袅袅婷婷的姿态”,“乳白的肌肤”,以及使石秀“永远也忘不了”的娇脆的声音,“直害得石秀慌了手脚”,“正眼儿不敢瞧一下”,“心头也不知怎的像有小鹿儿在内乱撞了”。潘巧云“是一个使他眼睛觉得刺痛的活的美体的本身,是这样地充满着热力和欲望的一个可亲的精灵,是明知其含着剧毒而又自甘于被它的色泽和醇郁所魅惑的一盏鸩酒。非特如此,时间与空间的隔绝对于这时候的石秀,又已不起什么作用,所以,在板壁上晃动着的庞大的黑影是杨雄的玄布直裰,而在这黑影前面闪着光亮的,便是从虚幻的记忆中召来的美妇人潘巧云了。”显而易见,杨雄的“庞大的黑影”笼罩着美妇人潘巧云,从而清楚地告诉石秀,这是义兄的妻子,石秀“不得不用最强的自制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然而放荡的潘巧云并不肯放过石秀,“看着这样吃嫩的石秀,越发卖弄起风骚来”,直逼得石秀神魂震荡,目定口呆。
施蛰存细腻地刻画了石秀这个时刻灵与肉的冲突与二重人格的苦闷:
石秀靠坐在床上,一瞑目,深自痛悔起来。为什么有了这样的对于杨雄是十分不义的思想呢?……觉醒了之后又自悔自艾的石秀,这样地一层一层的思索着,终于在这样的自己检讨之下发生了疑问,看见了一个美妇人而产生了痴恋,这是不是可卑的呢?当然不算什么可卑的,但看见了义兄底美妇人而产生痴恋,这却是可卑的事了。这是因为这个美妇人是已经属于了义兄的,而凡是义兄的东西,做义弟的是不能有据为己有的希望的。这样说来,当初索性没有和杨雄结义,则如果偶然见着了这样的美妇人,倒不妨设法结一重姻缘的。于是,石秀又后悔着早该跟了戴宗、杨林两人上梁山去的。但是,一上梁山恐怕又未必会看见这样美艳的妇人了。……现在既已知道了这是杨雄所有的美妇人之后,不存在什么别的奢望,而徒然像回忆一弯彩虹似的生着些放诞的妄望,或者也是可以被允许的吧,或者未必便是什么大不了的可卑的事件吧。
这样的宽恕着自己的石秀,终于把新生的苦闷的纠纷暂时解决了,但是在这样的解决之中,他觉得牺牲太大了,允许自己尽量的耽于对潘巧云的妄想,而禁抑着这个热情底奔泻,石秀自己也未尝不觉到,这是一重危险,但为了自己底小心、守礼,和谨防,便不得不用最强的自制力执行了这样的决断。
虽然石秀面对潘巧云的诱惑,表面无动于衷,但心灵的曝光却表现出性格的巨大波动,展现英雄人物形象的另一面。
弗洛伊德说,“里比多和饥饿相同,是一种力量。”在石秀的内心出现的是两种力量的抗衡——冲动与压抑。潘巧云的勾引使冲动的力量加大,压抑也随之增加,压强也就更大了。潘巧云与和尚私通,使石秀受了很大的打击,“一时间对于那个淫荡的潘巧云的轻蔑,对于这个奸夫裴如海的痛恨,对于杨雄的悲哀,还有对于自己的好像失恋而又受侮辱似的羞作和懊丧,纷纷地在石秀底心中扰乱了。”这件事像一根导火线,使石秀产生一种变态心理,石秀决定对他们进行报复,但他的报复既是为了杨雄,而更主要的是为了自己:
“石秀好像觉得对于潘巧云,也是以杀了她为唯一的好办法”,从以前的“因为爱她,所以想睡她”,转化为“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
性变态使石秀变得疯狂、残忍,他从“皓白的肌肤上,淌满了鲜红的血”中感到的是安逸、和平和爽快,他在残酷的屠杀中得到的是性的满足。施蛰存在这里将《水浒》中石秀的性变态以及对血腥的“欣赏”大大地发挥了。
弗洛伊德在分析这种性变态的情形时说:“他们当中有许多变态的人物,他们的性活动和一般人所感兴趣的相离很远。这些人的种类既多,情形又很怪诞。”⑤弗洛伊德将性变态及性错乱现象命名为虐待症,“不近人情的虐待狂者,专门想给对方以苦痛的惩罚,轻一点的,只是想使对手屈服,重一点的,直到要使对手身体受重伤”⑥,“乃至于非使性对象全然屈服,遍体鳞伤,不足以获取满足”⑦。石秀就从潘巧云被杀的惨状中得到了性满足,石秀的行为和心理,真是“与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处处可以合拍”⑧。
然而,经过这场报复以后的石秀,感觉到的是“过分的疲劳”和“非凡的酸痛”,“石秀好像曾经欺骗杨雄做了什么上当的事情似的,心里转觉得很歉仄了,好久好久,在这荒凉的山顶上,石秀茫然地和杨雄对立着”。
施蛰存在此时对石秀的心绪把握得很准确,在石秀变态的性心理得到变态的满足以后,剩下来的只有空虚、茫然,和更深一层的性苦闷。弗洛伊德说:“实际上,性倒错的患者很像一个可怜虫,他不得不付出痛苦的代价,以换取不易求得的满足。”⑨如其说石秀欺骗杨雄上当,不如说他欺骗自己上当,落得个如此“荒凉”。
至于顶天立地的古代英雄石秀,会不会出现这种性变态呢?弗洛伊德认为:“在各方面健康正常的人,其性生活却是变态的。”⑩这就是所谓的二重人格。在这里,石秀就不仅仅是个英雄,还是个有血有肉的,有性欲有私念的普通人。
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家霍特在《弗洛伊德的机械论和人本主义的人的形象》中说得好:“如果要理解一个人,就必须知道他主观的、内在的生活——他的梦、幻想、期待、成见、焦虑和他用以观察外部世界的特殊色彩。相形之下,他那些易于被看到的外在行为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
二
英国著名艺术家赫伯特·里德认为:“整个艺术史是一部关于视角方式的历史。关于人类观看世界所采用的各种不同方法的历史。”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是一个石秀,不同的视角,能观察出不同的形象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情绪侧面,产生不同的审美效果。
中国文学史,是一个视角不断转移的历史。中国的传统小说由于是从说书起源,为了吸引听众,主要以情节取胜。重视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传奇性,人物的外在性和语言的动作性。这是小说表现的一个方面,它表现了人物是怎么做的,即人物的“表”。然而人物不单有行动,而且还有思想,我们不仅要表现他怎么做的,还要表现他怎么想的,这就是人物的“里”。
“五四”初期,作家们开始了视角的转移(当然在更早就开始了这个转移的萌芽),进行着一场由“外向”到“内向”的转移,从对外部形象的描述,转向对精神心灵的开掘,由表现人物的“显现世界”,到表现人物的“潜隐世界”。以鲁迅为代表的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这一转移的实绩。没有这个转移,中国文学就不能成为完美的文学。
《水浒》的视角选择,充分表现传统小说的特长,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一目了然。但是,由于施耐庵侧重人物的表象描写,便很少内心刻画,即使那少有的心理描写,也是采用的唐传奇中初具规模的“外部白描法”。
这种外部白描法,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可听性,而作者的主观意识、人物的心理描写则较隐蔽。“五四”运动以后,外国文学的引进带来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从视角选择,到人物描写,以至创作方法,都出现了主观因素不断增长的趋势。鲁迅的《狂人日记》、《伤逝》,郭沫若的《残春》、郁达夫的《沉沦》等等,不论是理智冷静的现实主义,还是激愤感伤的浪漫主义,都重视了主观的内在的因素。以施蛰存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则更把表现主观情绪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任务。他们不再重视小说的故事情节,不再重视惊心动魄的客观冲突,不再去表现人物的姿态和动作,而是把视角直接对准人物思想、意识、精神以及潜意识等方面的活动,专心致力于心理分析,展现以前不曾展现的人的隐秘世界。
人的表层是有限的,人的里层却是无穷的,正像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说的:“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是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在潜隐内心世界里,作家如鱼得水,如鸟凌空,自由尽情。施蛰存在这个比海洋比天空还要大的世界里,充分表现了石秀的比显现世界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也真实得多的潜隐世界。如果说《水浒》写的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石秀,施蛰存写的则是作为普通人的石秀。
中国文学对人物形象的视角的转移,标志着中国文学的成熟。
所以,我们不仅能接受《水浒》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石秀,而且要接受施蛰存对这一形象的再创造。
其实,施蛰存的《石秀》使石秀的形象更完整丰满,因为英雄也是人,他们有人的感情、人的欲念、人的弱点、人的两重性。我们不能把英雄看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英雄形象都经历了从神到人,从人到神,又从神到人的演化。使英雄回到人的行列,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如当石秀杀了裴如海以后,施蛰存写“他”看见“残月的光”“斜射在这裸露着的和尚底”,就“打了个寒噤”,“匆匆地”将刀丢下回店。在这里,施蛰存不仅表现了石秀的残忍、石秀的刚烈、石秀的快感,而且暴露了石秀的犹豫、石秀的失望、石秀的恐惧。这里描写的石秀是立体的、复杂的、合乎情理的,同时也是真实的。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施蛰存研究”(项目批号:07JA751037)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杨迎平,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
②③ 周作人:《知堂回忆录》,香港三新图书有限公司版,第660页。
④⑧ 《书评·〈将军底头〉》,《现代》第1卷第5期,1932年9月。
⑤⑥⑨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9页。
⑦⑩ 弗洛伊德:《性学三论·第一章》,《爱情心理学》,作家出版社,1982年2月版。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