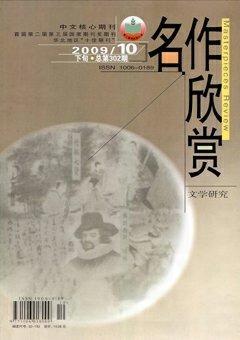嬉皮士与反英雄的契合
杨 芳
关键词:“垮掉的一代” 反英雄 嬉皮文化
摘 要: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以小说主人公迪安·莫里亚蒂为代表的“嬉皮士”们,他们颓废落魄, 过着流浪、酗酒和吸毒的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具有反英雄倾向的嬉皮士们又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美国社会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的精神。他们选择极具个性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一种愤懑和反抗。
“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一群美国作家和诗人,这场以青年作家为主体的反文化运动在6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主义的盛行,旧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面对繁华的物质时代,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垮掉派”们无法抵御酒精和毒品的诱惑——安非他明、吗啡、大麻给他们带来了幻觉的陶醉,极具反叛性的爵士乐、披肩长发、破洞的牛仔裤,流浪生活与高速驾车带来了感官的快感。因此,在当时,“垮掉的一代”作家和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曾经被认为是些“流氓”、“疯子”、“流浪汉”、“抢劫犯”、“吸毒犯”、“少年犯”和“颓废青年”等。
《在路上》(On the Road)被公认为是“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的经典。该小说是杰克·凯鲁亚克的自传性代表作,由作家用三个星期在一卷长达250尺长的打字纸上一气呵成。小说出版后,由于凯鲁亚克即兴式的自发性写作手法,招致不少批评家的抨击。凯鲁亚克被指责为真正的神经错乱,鼓吹欺骗、犯罪,他的作品被视为“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文化领域里地地道道的毒草”等等。而以小说主人公迪安·莫里亚蒂为代表的“嬉皮士”们,由于颓废落魄的外观,他们所代表的反英雄倾向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他们的声音远远无法与传统文学中的英雄匹敌。在他们身上,这些人反叛传统的革命意义并未产生普遍的冲击。所以,在本文中,笔者打算以《在路上》为例,解读小说中嬉皮士们的反英雄倾向,探讨他们反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
一
对于“垮掉派”作家们来说,造就英雄的环境正在消失,英雄对他们的号召力也在减弱。他们以颓废另类的生活方式抵制来自英雄文学的道德理念。在人际关系日益冷漠的现实环境面前,他们内心充斥着一种凄迷的感伤和丧失人生意义的茫然。他们总是显示出不得不堕落的无奈,仿佛永远也不能和世界运转的主旋律合拍,并通常对社会、政治和道德采取冷漠、愤怒和毫不在乎的态度。
对一切传统价值观念持怀疑和否定,应该说是“反英雄”形象的首要特征。小说《在路上》中的主人公迪安和他的“垮掉派”伙伴在一起,什么正事也不干,以高速度驾车四处游荡,吸毒酗酒,听爵士乐,读中国寒山诗,相信禅宗教义。作为社会的另类嬉皮们远离社会,喜欢走向旷野的自然,把自己放逐到大路之上、荒林之中。“垮掉的一代”宣称自己是“没有目标的反叛者,没有口号的鼓动者,没有纲领的革命者”①,信奉“只要太阳容你,我也容你”、“只争朝夕,及时行乐”的处世哲学。
反英雄具有较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叛逆性。小说《在路上》中洋溢着对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强烈反叛精神,成为打破社会习俗的自由风气的先锋,因此,凯鲁亚克也被认为是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先驱。小说主人公迪安·莫里亚蒂是一个疯狂的流浪者,在少年时期,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养院里度过的。长大后,他到处漫游,到处偷窃,遇到身无分文时,便去偷汽油和香烟。他开飞车,吸大麻,滥交女人。在旁人看来,他是个标新立异的疯子。他总是处于精神分裂、个性不确定的状态。萨尔曾经问迪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问题是怎么走?走到哪儿?”迪安的回答是:“生活把我带到哪里,我就走到哪里。”他必须凭借不断地奔波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迪安的野性与自我无疑是打破萨尔平静生活的尖刀,“迪安的智慧……更能给人启发,也更为完整,绝不故作斯文、令人乏味。他那种越轨的‘劣迹甚至也并不招致愤懑,被人鄙视”{2}。可见,英雄所赖以树立权威的条件动摇了。对萨尔·帕拉迪斯来说,他和他的朋友迪安·莫里亚蒂浪迹天涯,不是要回归拓荒时代的迁徙,而是缘于对自己梦想的追求。但是,这些人反叛传统的革命意义并未产生普遍的冲击。换言之,英雄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位置并没有被这批“嬉皮士”们所代替。
反英雄们对抗着越来越荒诞的外部世界,他们满怀抗争的热情但往往缺乏信心和勇气,所以就会一味沉溺于琐屑无聊的小事甚至苟且偷生。小说另一反英雄形象雷米,少年时期在法国度过,继父从不管他,备受世人的欺侮与凌辱。当他一个人踯躅在街头时,他诅咒命运和社会。当他在旧金山混上一个警察职务时,他竟毫无羞耻感地从所管辖的贫民区居民中偷窃钱财。雷米在偷窃时还拿杜鲁门总统的话“我们必须削减生活费用”来调侃他的窃行。萨尔曾问他:“雷米,你老这么给咱们自己找麻烦?你为什么不能老实点儿?你干吗老要这么偷人家东西?”雷米这样回答:“这个世界欠我点儿什么,就这么回事。本性难移呀”,“萨尔,咱们都是朋友,事情都是咱俩一块儿干的。这会儿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所有那些坏蛋都在想要咱们的命。所以咱们是得随时注意,不能让任何人陷害咱们”③。可见虽然他们的行为荒唐可笑,滑稽怪诞,但是他们的愿望往往与他们的行为方式及其结果构成二元对立的关系。他们的自我既受到本能欲望的驱策,又受到瞬息万变、混乱不堪的外在世界的煎迫。他们难以维持自身的平衡,自我处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结果导致精神分裂。尽管他们的反抗终归失败,但是他们却不甘屈服,换而言之,他们是打不垮的。
二
存在主义思潮给“垮掉的一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基础。在存在主义者看来,客观事物和社会总是在与人作对,时时威胁着人的“自我”。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就是自我的存在。存在的过程,也就是死亡的过程,从而得出了“存在”就等于“不存在”的悲观主义的结论。存在主义者把恐惧、孤独、失望、厌恶、被遗弃感等等,看成是人在世界上的基本感受。在他们认为,人与物是不同的,物的本质是先天决定的,而人则是先有自身的存在,完全是由自己的行动造成的,是自己选择设计的结果④。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个人不过是在物质主义支配下群体社会的一分子。对于“嬉皮士”们来说,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生命的意义和个人的尊严。换句话说,在崇尚多元化、反决定论的当代西方社会,他们已不可能以一个统一的、绝对的标准来区分“有罪与无罪,自由与必然,有意义与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必然没有稳定的个性,而且常常处于矛盾的精神状态中。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们看到,反英雄的品格便集中体现于他们具有较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叛逆性,他们很少表现对于人类本性或人类处境的根本忧虑,而是更认真地显示出他们个人的与众不同。
“垮掉的一代”另一代表人物卡萨迪是《在路上》主人公迪安的生活原型,在凯鲁亚克看来,卡萨迪的执著坚毅、热情疯狂与玩世不恭,最能体现“垮掉的一代”作为反英雄的个性。1951年2月,卡萨迪给凯鲁亚克写了一封长达23000字的长信,用自由联想的方式记述了他复杂的性爱关系。受到这封信的启发,凯鲁亚克花了20天时间,在服用安非他明后,坐在打字机旁用长达250尺的打字纸写出了《在路上》手稿。迪安从小就是个流浪儿,生活的煎熬、社会的逼迫,造就了他复杂的性格。一方面,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对人生有着美好的追求。他一心一意想通过自学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叔本华、尼采,以至于中国的道家思想都怀着深厚的兴趣。另一方面,他奉行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玩女人、偷鸡摸狗、吸毒酗酒。不过,他把种种恶习当作是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的方式,并企求以强烈的刺激来抚慰受伤的心灵。但这种发泄方式反而把他自己推向毁灭,而不能给他的心灵带来丝毫宽慰。尽管他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极其反感、憎恶,力图反抗它,但由于他的反抗是消极的,结果只能归于失败,而他在无出路的困境中越陷越深,变得益发颓废。
在文学作品中,反英雄总是指那些卑贱懦弱的或自我淘汰的失败者。在小说中,“嬉皮士”们很少有大幅度的动作,他们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在一间肮脏凌乱的狭小居室里睡觉。这些组成了他们生活的大部分。他们的懒惰不仅体现在生理性上,而且体现在生存方式上,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拒绝,一种逃避,或者一种厌倦。从心理分析的视角来看,一切的颓废可能都源于对现实社会的失望,因为徒劳、不解与碰壁使人心灰意冷,“嬉皮”的生活方式成了应付现实的通常策略。但是他们自暴自弃,只能以嬉皮的态度对抗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以另类的非道德的行为来和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相对抗。
当个人既定的价值体系被认为崩溃了以后,他便失去了与旁人进行交流的媒介,便自然而然地感到孤独起来。孤独,作为“反英雄”形象的又一特征,是小说《在路上》的主题之一。作为“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在他的这部小说中给读者描写的社会环境里充斥着畸形、变态和混乱,揭示了“垮掉派”们内心是孤独、困惑和无奈的。人们既不想抓住什么,留下什么,也不认真摒除什么,拒绝什么。人的理性甚至也因为多余而开始退化、模糊。也许在思想上,以迪安和萨尔为代表的嬉皮士们并非没有信仰,他们企图通过对原有生活进行主动“叛离”,来冲出似被迷雾笼罩的“蒙昧”生活状态,去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他们在东西海岸之间的公路上来往穿梭追梦,发现它很难寻觅,当他们终于在新奥尔良、丹佛、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追上它时,发现它只是一个“伤心的天堂”。他们对生活这条脚下永无尽头的道路一片茫然,当他们迷惘地从东到西在路上飞速前进时,也许并不知道为何而走,走向何方。喧闹的爵士乐掩饰不了他们心中的孤独和惆怅。从他们身上体现出反英雄们在荒诞冷漠的世界中,努力寻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却又缺乏信心和勇气的特点。这一点,正如冯亦代先生所言,“在《在路上》中,他(凯鲁亚克)表达了自己的一个古怪而又执著的信念,即‘世界唯一像样的行动是跪在与世界隔绝的地方为世上每一个人祈祷。生存是为了避免灾难的永世斗争。”{5}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一方面,对于梦的追寻可以被看成是嬉皮士们对自己理想中的传统文化根源的回归。但另一方面,梦想的失落恰恰又表明了他们所崇尚的嬉皮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和交汇,体现了嬉皮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妥协。
三
凯鲁亚克经常自称是“古怪的、孤独的、疯狂的、天主教的神秘主义者”,想要寻找“至福的道路和灵魂”{6}。可见,尽管“Beat”一词最初是从街头小混混嘴里说出来的,但对于杰克·凯鲁亚克等“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们来说,它可能代表着人在精神上回到最原始的直觉或意识时的感觉。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垮掉派”们读英译寒山诗,模仿寒山的衣着言行,自命为寒山的传人。佛教主张的“空幻”和灵魂的寂灭永生使他们认为,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生灵的痛苦都是神圣的,人的所有欲望并不是“恶”的象征,因此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应顺应自然。寒山及其诗在这样一种充满焦虑与寻觅的目光中一出现,就以其自身的魅力征服了所有骚动不安的心灵。从思想上说,寒山诗契合了“垮掉的一代”内心深处的渴望,“独居寒山,自乐其志”,寒山游离于一切社会传统之外,世俗的权威与力量不能制约他,这对嬉皮们特立独行、标榜自我的价值追求是一种鼓励。“垮掉的一代”们为了心灵的自由和灵魂的安逸甘愿忍受贫穷、痛苦和困顿。在放纵的生活中表达对自我本性的寻找,和对灵魂自主的热烈呼唤。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描写美国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迪安和他带领的一帮“彻底垮掉而又满怀信心的流浪汉、无业游民”漫无目的地在各地驭车漫游。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时而打短工,时而以偷盗为生。他们吸毒酗酒、玩女人,与社会渣滓为伍,放浪形骸,为所欲为,以此表示对这个非人的社会的抗议。嬉皮士与反英雄的契合也体现在他们这些文化边缘人与主流文化的悖逆和疏离的关系上,和对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反叛上。巨大的无力感和虚弱感困扰着他们,潜藏于心的优越感和等级观念使他们步履沉重,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定位,看不到生活的前途和方向。他们通过嘲笑现实来缓解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生活的失意。在被命运抛弃、捉弄,反过来又嘲讽命运,他们的反传统道德的行为就是对不可改变的荒诞世界的无奈表现出的黑色幽默。
显然,凯鲁亚克在其作品里塑造了一群反英雄形象。《在路上》的反英雄们用流浪、放浪形骸、寻欢作乐和对人生颓废的态度来表明他们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愤懑。一方面,这群以迪安为代表的嬉皮士们既是反英雄的代表,他们沾染种种恶习,缺乏坚强的意志和毅力,行为失之卑琐。可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反抗旧道德习俗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和幽默感。他们把对美国社会制度、对自己的生活、对一切的不满表现在一次次在路上漫无目的的游荡,和以流浪、酗酒、吸毒、性爱为外壳的生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选择却有着某些合理的因素:表达了他们对美国社会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大胆反叛,对压抑人性的社会现实的一种愤懑和反抗,在这一点上,恰恰体现出这帮处于社会边缘的文化“局外人”的一种生活勇气,展示了嬉皮文化和反英雄的契合。
作者简介:杨 芳,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 查尔斯·哈里斯:《当代美国荒诞派小说家》,高校出版社,1977年版,第104页。
② 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文中有关该小说译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③ 徐崇温、刘放桐、王克千:《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83页。
④ 冯亦代:《美国——垮掉的一代之王》,《读书》,1995(10),第48页。
(责任编辑:范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