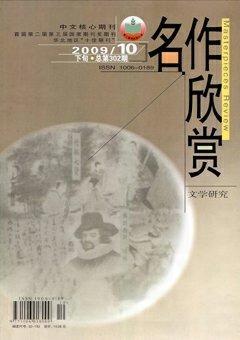对生命和灵魂的深入关注
关键词:性爱叙事 伦理诉求 生命和灵魂
摘 要:爱情是人伦关系中富有情感张力和言说价值的伦理关系,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在张爱玲、王安忆、棉棉的作品里,有着不尽相同的情爱叙事方式。她们的性爱叙事作品,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中国小说性爱描写叙事内容、叙事风格的变化;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作家的叙事伦理指向,张爱玲对人物及其谋生的爱情“无所不包的同情心”,王安忆对和谐两性、和谐人生的希冀,棉棉对生活始终充满激情与爱心,她们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对生命和灵魂的关注。
叙事伦理是一种以生命和灵魂为主体的生存伦理,它以生命的宽广和仁慈来看待一切人和事,注重书写人性世界里的复杂感受,呈现人类生活的丰富可能性。“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叙事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①换句话说,叙事伦理是通过个人的生活际遇来关怀人类的基本处境,它不以现实或人伦的尺度来制定精神规则,也不愿停留在人间的道德、是非之中,其伦理指向完全建立在作家对生命和人性的感悟上。
爱情是人伦关系中富有情感张力和言说价值的伦理关系,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爱情伦理叙事最能体现创作主体的叙事伦理诉求。在不同的爱情叙事模式中蕴含着作家的叙事意旨、道德价值判断、文化立场选择等叙事伦理因素。以张爱玲、王安忆、棉棉为代表的上海作家,以自身的情感体验和独特的生存体验为基础,以女性的情爱婚姻为切入点,描写20世纪不同时期人们的情爱生活和生存状态。
一、张爱玲、王安忆、棉棉的情爱叙述方式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爱情包含着“情”、“性”与“责”等伦理要义,是普泛性道德规约考察的主要范畴之一。完美的爱情应是三者完美的结合,尤其是作为个人心灵情感体验的“情”、“性”,更是必不可少。马尔库塞的“爱欲伦理学”对20世纪的人类伦理思想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他推崇的爱是包含着性的爱,这是一种最理想,也是最为和谐的情爱状态。但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小说作品中,“性”与“爱”并非总是二位一体的。在张爱玲、王安忆、棉棉的作品里,有着不尽相同的情爱叙事方式。
张爱玲小说中的性爱描写大致有两类:一是无性之爱,如《心经》、《沉香屑·第二炉香》、《封锁》、《多少恨》、《金锁记》、《花凋》等。《心经》描述了“纯爱”的冥想,女主人公许小寒具有弗洛伊德“恋父嫉母”情节。她小时候崇拜父亲的高大完美,长大后崇拜转为爱恋。这种畸变的恋情,不仅一点点吞噬了父母之间的爱,也使她无法接受任何一份健康的爱情。父亲在父性苏醒后移情别恋,这寄托纯爱的空间渐趋破灭,小寒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家出走。《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罗杰·安白登满怀爱心迎娶纯洁的少女愫细为妻,但妻子由于缺乏最基础的性的教育,对丈夫在新婚之夜的正常行为十分恐惧,连夜出逃并闹得满城风雨。周围所有的人也把他当作“色情狂”、“心理变态”和“神经病患者”。他百口莫辩,最后在世人的冷眼中含恨自杀。
一是无爱之性,如《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鸿鸾禧》、《连环套》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主人公佟振保在开篇时,被张爱玲描述为“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但随着故事的继续,读者逐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情欲本能的驱使下,他不顾“朋友妻,不可欺”的古训,而与朋友太太王娇蕊发生肉体关系。在传统道德与本能欲望的交锋中,他的人格开始分裂并最终成为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当“红玫瑰”王娇蕊真的爱上他并不顾一切要离婚嫁给他时,振保却选择了放弃,而娶了毫无感情的孟烟鹂。烟鹂虽然是他明媒正娶的太太,却如同他“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粒子”,从未享受过他片刻的爱情,最后导致温良贤淑的孟烟鹂与人偷情。《半生缘》中的女主人公顾曼桢原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情投意合的男朋友。姐姐为了套住其丈夫的心,设计借腹生子,顾曼桢被姐夫强奸并被囚禁将近一年。她生下儿子后费尽周折才逃出深渊,但后来听说儿子病重无人照顾时,母爱的牺牲精神又驱使她将错就错地嫁给了她曾经恨得咬牙切齿的祝鸿才。张爱玲所建构的情爱故事没有一个是健康、正常的爱,都是性爱分离、千疮百孔的。
而在王安忆笔下,性爱描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正面直接的性爱叙事作品,主要有《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20世纪90年代以后间接描写性爱,作品有《米尼》、《我爱比尔》、《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等。
在“三恋”中,“性”第一次在新时期文学中作为“叙事元素”被客观放大书写,也是王安忆开始对两性关系的探讨。《荒山之恋》讲述了男女主人公无力自拔的性爱和命运。偶然的相遇使男人与女人的爱情不可遏制、无所忌惮,他们承担着世俗的罪孽又怀着灵魂的极度自由,近乎疯狂的爱带给人命定的结局。但死亡不是软弱和屈服,而是性爱的自由和永恒。在《小城之恋》中,单纯得有点愚钝的女孩子在混沌未开的性别状态中沉入疯狂而带有罪孽的性爱过程,作家叙写了人物的迷狂与挣扎、沉沦与幸福。《锦绣谷之恋》中虽然没有涉及具体的性爱,却描述了女编辑与男作家之间柏拉图式的精神恋。《岗上的世纪》是一首对性爱的赞歌。知青李小琴为了回城,决定用自己的美丽和聪颖织就一张温柔的网,俘虏决定自己命运的小队长杨绪国。杨绪国在疯狂的性爱中获得了再生,李小琴体内的情欲也被杨绪国激活且难以割断。两个人抛却了一切烦恼与禁忌,沉迷于情欲的漩涡,尽情享受着爱的欢娱。
与早期充满原欲性质的作品不同,王安忆后期小说中的性逐渐与世俗的利益纷争扭结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物化与混沌状态。《米尼》中的米尼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满身陋习的阿康,沉沦在肮脏的性乱交中并彻底堕落成为妓女、皮条客,参与组织卖淫。《我爱比尔》中的女孩阿三先后与比尔、马丁、艾可以及一个比利时人发生了恋爱故事,“与外国人的性爱”作为一种特殊的情结贯穿着她的情感历程。当这种情感历程中的幻想支撑点逐一消失后,阿三便走上了日趋衰弱苍白的生活。她从各个酒店的大堂中寻找“比尔式安慰”,在身体的结合中满足着一种幻觉。在《香港的情与爱》中,主人公老魏用金钱换来了逢佳两年的“情和爱”,而逢佳最后在老魏的资助下实现了离开“东方明珠”去美国的夙愿。
王安忆企图通过男女两性关系来揭示人性的复杂面,因而在叙事“情爱”而不是欲望化的“性爱”场景,尤其是后期的性爱叙事,没有将“性”作为生命本能而过分张扬,而是选择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能指叙事假象。棉棉则将性与爱作为唯一的主题,进行了“本体化”表象叙事。棉棉早期的作品,如《啦啦啦》、《糖》等是“欲望化叙事”文本,作家以“私人化”的叙事姿态回到女性生命现实和生存现实本身。《啦啦啦》讲述了现代都市流浪女“我”与流浪歌手“大男孩赛宁”之间一个不幸的爱情故事。在长篇小说《糖》中,这个“问题女孩”“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生活”,作品中有很多外在的、欲望化的性爱描写:“就这么一下,他就冲进了我的身体。我一动不动,痛直接窜向心脏,我痛呆了,没法动。他的发尖分为两部分坠在我左右晃动,这让我感觉有两个他同时在我身上运动,这两个他的头发在我身体左右晃动。”小说中有很多对身体性征和性爱感受直接而大胆的展示,这跟棉棉的性爱观念密切相关:“写性的时候我比较客观,我不喜欢把性以外的东西放在性之中,《糖》里那个女孩子就是太喜欢把性和其他情感混在一起了……性的生物性会让我的写作更加充满怜悯,当然这怜悯是以残酷为代价的。”②棉棉用一个原始人的眼光来看待两性的互动。她的性描写,既不浪漫,也不猥亵,而是生物性的,从人性的原始层面发现真实。由此可见,棉棉的性爱观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包括性与爱分离、性被本质化等。
有些评论家认为棉棉的作品很颓废,其中的性描写太直白太大胆,性行为不仅有物化的嫌疑,也掩盖了其中生命的质感,连女性也成了把玩的一部分。王朔曾评价棉棉“是用身体来写作,而不是用头脑来写作”。棉棉毫不避讳自己的观点:“用身体写作首先得身体好。用身体写作并不是单纯感官的、欲望的。”棉棉的“身体写作”不局限于生理层面的刺激反应和肉体欲望的宣泄,是包含着思想与精神维度的一种整体性的感觉活动,体现出“人”性的方面。这与卫慧的以性行为为轴心的器官的“肉体写作”截然不同。在棉棉看来,“性”是表现人性的重要渠道。人类之“性”的意义在于它让生命主体获得了关于精神的生命实质的意识。换句话说,正是“由于爱,我们才得以了解:凡是精神必有属于它的实质的肉体成分。”③
棉棉将笔触探向了现代都市女性每一个无法言说的痛处,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灰色的隐蔽的世界,其中也折射出作家的痛苦无奈与不断抗争。正如棉棉在阐述小说《糖》的主题时说:生活再不幸,也要把它当成一块糖;正是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痛苦和垃圾,我们才要因为爱而活下去,把痛苦和垃圾转化成糖吃下去。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年轻,来自于爱。
二、张爱玲、王安忆、棉棉的性爱叙事伦理
张爱玲、王安忆、棉棉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宏大的叙事模式,采用了“非历史化”、“非理想化”的“日常化”或“私人化”的叙事范式。张爱玲说:“我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④张爱玲追求一种“日常”和“世俗”叙事,她笔下的爱情生活就是物质生活,爱情的情感性和生理性个人体验叙事是处于“缺席”状态的。王安忆也有意回避精神化和崇高化的爱情叙事,注重爱情体验多层次的个人化叙写,挖掘人性深处情感的复杂性。王安忆曾说:“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而且我认为,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⑤棉棉也明确表明自己拥有“另类”精神,就是游荡在所有主流之外的独立精神,一种对商业、对主流、对虚荣的不妥协的态度。在诠释“坏女孩”的概念时说,坏女孩是通过性来得到她要的东西。她没有感情,“她的爱非常物质化。我肯定不是这种人。但如果坏女孩的标准是与传统道德观不一样的女孩,我觉得我是一个坏女孩,因为我是个毫无道德感的人”⑥。
欲望的“日常性”和道德规避叙事体现出张爱玲、王安忆、棉棉有着近似的性爱伦理叙事的文化立场,但由于各自生活的年代、身世阅历不同,她们的性爱叙事又体现出不尽相同的伦理指向。
张爱玲倾注笔力于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和注定要被冷酷的现实所嘲弃的欲求。她笔下都是“谋生”的爱情。生活在时代夹缝中的没落淑女,如川嫦、孟烟鹂、邱玉清、流苏和宝络等,大多出身败落的大家庭,所受的全部教养都来自旧的文化、旧的生活方式,这些教养都是压抑人的正常情感需要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女结婚员”。因而对这些女性而言,“大多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有成家的要求”。台湾女作家平路说:“张爱玲写的不是‘爱情,而是生存,是安全感。她的女主角们,曹七巧、白流苏在爱情里所寻求的常常是经济的力量、要活下去。所以,她心目中的地母角色是蹦蹦戏里的花旦——在废墟里仍能毅然活下去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其实是没有爱情的、以身体或青春资源去换取而来的生存。”
张爱玲以悲剧性的情爱叙事消解着爱情的价值和爱情神话。在她看来,女性的这种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但张爱玲尖锐并不尖刻,她有着超越善恶之上的宽容与慈悲。正如夏志清所说的:“对于普通人的错误弱点,张爱玲有极大的包容。她从不拉起清教徒的长脸来责人为善,她的同情心是无所不包的。”⑦张爱玲自己也说:“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8}因而在《谈女人》中她写道:“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毋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分别。”深知张爱玲的胡兰成则说:“张爱玲的文章里对于现代社会有敏锐的弹劾。但她是喜欢现代社会的,她于是非极分明,但根底还是无差别的善意。”{9}因此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不乏希望地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指自私的男女主人公)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就如同鲁迅先生“反抗绝望”的人生态度一样,张爱玲也时时从世俗人生的生之悲哀中努力发掘生之喜悦,给黯淡的人生带来一丝温暖与亮色。张爱玲的情爱叙事伦理最终指向对千疮百孔的情爱“无差别的善意”,指向对所有人物“无所不包的同情心”,体现为对虚无但不乏暖意的世俗人生永不衰竭的爱。
张爱玲笔下的情爱叙事呈现出性、爱分离的状态,而王安忆却力求通过还原性欲望来还原人性、还原人类的本真状态,追求着两性乃至人生的和谐。在《荒山之恋》里,作者并没有完全忽略社会、道德、伦理的禁忌,但禁忌不是阻挡而是推进了性爱的进程,在对禁忌的反抗过程中,主人公体验到更大的自由和沉迷。在这里,性既是一种宿命,也洋溢着欢乐。在《小城之恋》中,王安忆企图在某种混沌、蒙昧的状态里面探讨人的情欲现状,其话语中隐含着作家无法遮掩的“原罪”思辨色彩:“他们真不明白,人活着是为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这等下作的行事,又以痛苦的悔恨作为惩治。”这种情爱叙事,显示了创作主体犹疑的叙事伦理理念,她既不愿意充当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也不想承担离经叛道的重大责任。在小说的结尾,母爱最终驱使怀孕的女人逃离了性爱的漩涡,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因而在此,性既是一种混沌,也是一种升华。在《岗上的世纪》中,王安忆设置了一个充满情欲、也不乏诗意的当代“伊甸园”,人物最初的功利的性关系升华为最终的纯洁性爱,实现了纯粹性的快乐与自在。其中的性“是相当纯粹的,它只剩爱情的本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参与,排除了其余的各种因素”{10}。在《香港的情与爱》中,两性关系得到了平稳缓和的解决。老魏与逢佳建立在金钱交换基础上的关系,在王安忆的笔下却有了温情的色彩,“即便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也经不住朝夕相处,就是磨也磨出点真心了”。他们彼此以“善待”代替情爱,以实用的人际良心代替明确的道义承诺,慢慢形成了一种“俗到头来反成雅,情到无处倒变真”的关系,长久的相处使两性之间产生了一种超越两性之爱的恩义。王安忆逐渐摒弃了道德的或社会的约束,使“性”超越了道德、社会,为人物寻求和谐的生存方式。
棉棉的性爱叙事经历了由追逐激情到渴望自由的转变。棉棉早期的小说中的人物疯狂地生活着,他们玩做爱,让“爱的感觉一阵阵到来一阵阵退去”,直到“身体开始疲倦”;他们玩音乐,因为“音乐不需要去搞懂,音乐离身体最近”;他们玩酒精、玩毒品、玩自杀,玩一切“现场”的东西。但他们仍然未能摆脱一种“被什么东西莫名其妙控制住”的感觉。棉棉描写了人物对当下生活的充分享受,通过人物最内在、最真实的躯体反应,真实地表现都市年轻人生命的颤动与精神的呼吸,表现了青春的迷惘与生命的流浪意识。棉棉身体写作的叙事意旨是以最直接的方式找寻人的生存价值,问询自我存在的意义。她“根本就不屑于再去打碎什么,只张扬自己想要的生活”{11}。因而她的早期作品中,洋溢着一种鲜活的生命的跃动,一种渴望拥抱生活、承受命运的真诚与激情。
在现实生活中,棉棉在不断地恋爱,她把爱情当作艺术追求。她为每一个她爱过的男人而骄傲。她觉得自己太“作”了,很多幸福都是被她“作”掉的,但她觉得跟男人“作”是其乐无穷的一件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短暂婚姻的结束,棉棉的爱情理念发生了变化。“我一直想寻找一个完美的人,一份像我的小说里那样的完美的爱。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在小说里臆想一种完美的爱,编织一种自由、开放的关系。在《熊猫》中,她塑造了一对年轻的上海情侣,他们不再整天厮守,沉迷于性爱,而像熊猫一样一年中只有两、三次性爱,他们允许对方有“第三者”,并且十分关心、体贴彼此及其“第三者”。棉棉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在这种“完美的开放关系”中过着寡居薄爱的熊猫式生活。但这并非棉棉对爱绝望了,而是因为她认为“爱情就是自由”,“爱是我永远的主题,我是因为爱而出生到这个世界,我也因为爱而最终获得自由”。因此有人说《熊猫》革了《糖》的命,棉棉革了自己的命。
总之,从个人化、日常化的叙事角度出发,张爱玲隐约其词地描写了人物的性爱分离,王安忆表达了对被压抑的性欲望的认可并作了正面的描写,棉棉则大胆地凸显性行为以及性爱享受。三位作家的性爱叙事作品,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中国小说性爱描写的变化轨迹。从叙事内容来看,小说中完整的爱情故事正渐渐消失,人物更实在的身体感觉成为情爱叙事的主要成分,情爱事件简化为一些生活的场景和欲望的碎片,爱情的精神品格遭到质疑。从叙事风格而言,含蓄暗示的审美传统逐渐被抛弃,自然主义甚至赤裸裸的性场面写实受到追求感官享受者的追捧,诗意、自由的情爱描写被性行为、性状描写所取代。90年代场景化的性爱描写,既突破了女性表达的禁区,是对男性话语垄断的一种挑战,又体现出作家无爱之性的“本体化”性爱伦理叙事取向。这源自于现代人日趋务实的价值观和大多不再崇尚的含蓄圣洁的爱情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作家的叙事伦理指向,张爱玲对人物及其谋生的爱情“无所不包的同情心”,王安忆对和谐两性、和谐人生的希冀,棉棉对生活始终充满激情与爱心,她们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对生命和灵魂的关注。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立项项目“20世纪女性作家的上海小说叙事伦理研究”(07C172)
作者简介:邓寒梅,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
② 棉棉:我不是美女不像作家[N].特区青年报,2002-7-26.
③ 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85.
④⑧⑨ 今冶.张迷世界[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49,51.
⑤ 王安忆、陈思和.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J].上海文学,1988,3.
⑥ 棉棉.我不做坏女孩很多年,http://www.ezeem.com.
⑦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355.
⑩ 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14.
{11} 白烨.2005年文学批评新选/专家年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392.
(责任编辑:范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