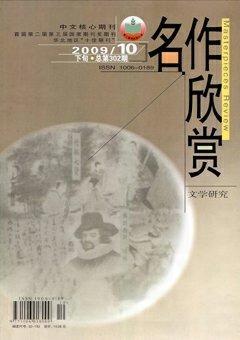余华作品中的现代启蒙意识
关键词:现代启蒙 颠覆传统 反思现代
摘 要: 余华作品中的现代启蒙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二是对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
余华作为一个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非经验性作家,在其创作之初总是以孩子的视角来铺陈人间的罪恶,以期展现刚刚过去的那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纵观其作品,看似铺陈着死亡和罪恶,但却渗透了对鲁迅开创的现代启蒙意识的延续,体现了作家深刻的忧患意识。
文中所说的现代启蒙并非广义的启蒙,而是自“五四”以来鲁迅所开创的启蒙。这种启蒙是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对人自身的反观和批判意识,也就是对人思想的启蒙。但是,在启蒙与救亡并存的年代,救亡的迫切性压制了启蒙的发展。后来由于民族国家的建立,这种挖掘自身劣根性的启蒙也曾经一度中断,直到“文革”结束后这种启蒙才又被提起。余华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开始了他的创作,1987年他在《北京文学》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并享誉文坛。此后,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90年代开始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长篇《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使得余华再一次轰动文坛。其中《活着》在1998年获意大利第十七届格林扎那——卡佛文学奖。21世纪余华一反以前的创作风格创作了长篇巨著《兄弟》,在每一个十年余华的创作都会有一个新的变化,研究余华作品内涵和风格的著述较多,但从现代启蒙的视角剖析其文本创作的很少,因此,本文试从这一角度探究其作品中的现代启蒙意识。
余华在创作初期以一种反常规的写作方式揭示人的深层心理,挖掘人的潜意识,呈现出人性的另一面。虽然这另一面的书写有着时代和历史的原因,但从其作品的内涵上却表现出一种反叛常规、颠覆传统的个性。这种对传统的颠覆一方面通过“人性恶”的书写来展现;另一方面通过对死亡原生态的描写颠覆以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中对死亡崇高品性的描写。同时,余华又从宏观的视角俯瞰民族的生存状态,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中国要发展现代化,首先要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思想意识,而中国国民的思想意识依然存在落后的一面。因此,余华作品中对国民性的揭示与批判表达了他关注现实人生的深度思考。
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
余华作品中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是通过“人性恶”和“死亡”主题来表现的。
人性是“人类的共性”。“它与兽性相对,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是人通过漫长的劳动实践和社会活动,在物种关系和社会关系上提升自己的结果。物种关系上的提升,人类在几百万年前就已逐渐完成。社会关系上的提升,则是一个正在艰难进行着、还有更为漫长的时间历程才可能完成的人类行为。由于人类还未获得完整纯粹的人性,在人的历史和现实中,人们总会看到残存的兽性,如损人利己、弱肉强食、掠夺欺诈、奴役压迫、侵略残杀等,这些都是反人性的兽性行为。”①余华通过作品中“人性恶”的书写颠覆了的传统人文价值体系中“人性美”的情感模式。
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体系中,“人性美”的三大情感模式:亲情、友情、爱情被极大地张扬了。如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人性在社会关系上的提升还远未完成,因此,人性有时还会暴露出兽性的一面。在《现实一种》、《黄昏里的男孩》、《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等作品中,余华分别以孩子、成人和傻子的视角书写了“人性恶”。
《现实一种》中余华通过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的视角引出了一个家庭的互相残杀。皮皮对摇篮中孩子的折磨展现了“人之初,性本恶”。他通过对堂弟打耳光、卡喉管之后堂弟爆发出来的哭声而获得一种满足。他的这种举动完全是来自成人世界的影响,因为他看到父亲经常这样打母亲。成人世界对孩子的影响说明了人性在社会关系上的落后。而由皮皮的过失而导致的家庭残杀,更说明了人性的丑恶,山峰对山冈的报复,山冈对山峰的死亡折磨,山峰媳妇对山冈死亡之后捐献尸体的解剖计谋,这一切显示不出任何家庭的温情。在这里,母子之间、夫妻之间、手足之间丝毫没有“爱”和温情可言,每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都是冷漠和互相仇视的,正如萨特所言“他人即地狱”。而这,就是现实一种。余华将这种现实呈现在人们面前,展示了人的兽性的一面。同时也说明了人的素质在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动物性的一面,人性在社会关系上不但没有提升,反而在沉落。
《黄昏里的男孩》以成人的视角写了一个贩卖水果的人对一个偷吃他苹果的孩子的极端性惩罚。他先是扭断了孩子的手指,然后将孩子捆绑在水果摊前大声喊“我是小偷”,直到将孩子折磨得精疲力竭,孤苦可怜地离去。文中赤裸裸地暴露了成人世界的惩恶心理,卖水果的孙福抓住孩子的过错而对其进行的残酷惩罚让人感到成人世界的恐惧与可怕,没有家长似的疼爱与说教,反而将孩子推向罪恶的深渊。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这种人性恶通过一个傻子的视角展现出来,并突出体现在人们对傻子的“笑”上。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傻子,除了药店的陈先生知道他的名字叫来发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于是,人们不断地嘲笑傻子,并以此来获得一种心理的满足:他们问来发的妈是怎么死的;他们争着抢着作来发的爹,连小孩子也不例外;他们捏着“又瘦又小”的狗的脖子要许配给来发作“妻子”;他们笑来发没有名字,所以他们打喷嚏时就叫来发喷嚏,他们招手时就叫来发过来,挥手时就叫他滚开。镇上的人们通过对来发的讥讽、嘲笑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笑声:“哇哇地笑”、“嘿嘿地笑”、“哈哈地笑”、“哄哄地笑”、“吱吱地笑”、“哗啦哗啦地笑”、“笑得像风里的芦苇那样倒来倒去”。这笑声中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就像是当年在鲁镇上生活过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人生活遭际的延续。阿Q用“精神胜利法”支撑空虚的灵魂,祥林嫂用一遍遍的唠叨来倾诉哀伤,孔乙己用“茴”字的四种写法来维护知识分子的一点尊严。而来发只能用傻来应付生活,对于人们的侮辱,他只能以傻子的无知来回应。可是人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看到来发把狗作为忠实的朋友并把它养胖后,他们又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狗吃掉,他们用了最卑劣的手段,那就是欺诈与暴力。为了炖狗肉吃,人们想尽了办法,先是叫来发“喂,朋友,快去把狗叫出来……”然后又进行恐吓“不去?不去把你勒死……”黔驴技穷后,他们经过陈先生的提醒叫了傻子的名字“来发”,这种称呼唤醒了他一丝做人的尊严而心理“咚咚跳起来”,来发把狗叫了出来却葬送了狗的生命,于是他发誓以后无论谁再叫他的名字他都不会答应了。余华通过这样一个先天弱智的人的心理和视角展示了现实世界的虚伪与罪恶。
实际上,如果用辩证的眼光把人性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发现,“所谓人性,只能是顺应、符合以至促进历史发展,使人走向人自身(而不是走向兽性)的人的基本属性。”②同时,对人性扭曲的描写也不应该停留在人性表面,应该分析产生人性扭曲的社会现实。余华正是通过人性的描写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批判,从根本上否定违背人性的社会现实。
余华对传统的颠覆一方面通过颠覆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念来展现,另一方面又通过“死亡”这一主题来消解崇高。余华的作品中常常会有一个死亡主题,作家以冷峻的笔法达到了“情感的零度”状态,对一切都不作是非善恶的道德化评述,只是向人们展示血淋淋的真实。死亡,曾经被古典悲剧作家赋予崇高的精神价值,很多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家在文学传统中都保留了对死亡的敬畏,而余华的创作却告别了死亡的崇高和悲壮色彩,把死还原给生命本身,从而消解了死亡的崇高主题。这也是一种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精神。余华通过对死亡原生态的展示表达了一种生命的虚无感。在《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鲜血梅花》、《古典爱情》、《往事与刑罚》、《此文献给少女杨柳》、《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死亡叙述》、《难逃劫数》、《世事如烟》、《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作品中余华几乎都写到了死亡。其中《现实一种》揭示的是一种消解家庭温情的复仇似的死亡;《河边的错误》展现的是生存的悖谬似的死亡;《一九八六年》中写到的是一个在“文革”中被迫害的中学老师的死亡;《鲜血梅花》写的是毫无复仇意义的并非武林侠义的死亡;《古典爱情》中的人在饥荒年代如同食物一样被宰杀、出卖,不但消解了古典爱情的崇高,而且人也成了被吞吃的动物,让人感到了血淋淋的人肉筵席;《往事与刑罚》、《此文献给少女杨柳》、《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写到的是一种虚无和莫名其妙的死亡;《难逃劫数》、《世事如烟》中的死亡更具有宿命色彩;《活着》中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死亡似乎有了些许现实的背景;近作《兄弟》是一部历史跨度很长的鸿篇巨著,其中有李光头生父猥琐的死亡,养父宋凡平凄惨的死亡,兄弟宋钢对生存感到绝望的死亡,等等。余华写了种种的死亡,这些人物的死亡或者像动物一样任人宰割,或者像牲畜一样一个个死去,后期长篇作品中虽然死亡具有现实性,但这种死亡恰好是展现现实生活中的人在各种生活境遇的压迫下是怎样走向死亡的,人的生命本身毫无意义,死亡也同样没有了崇高与悲壮。余华还原了人的原生态,通过种种死亡的描述消解了死亡的崇高和意义,从而达到了瓦解和颠覆传统价值观念的目的。
对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
鲁迅在“五四”时期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当今社会中仍有现实意义。余华在《我胆小如鼠》、《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中书写了国民性中愚昧、落后、不觉悟的一面。
在《我胆小如鼠》中,余华写了一个名叫杨高的孩子从小就“胆小如鼠”,他怕鹅,怕到河边玩,怕从树上掉下来,所以同学们都嘲笑他,甚至女同学也敢欺侮他。杨高的这种性格持续到参加工作,他原本是钳工,可是他的朋友吕前进把锉刀插在厂长的桌子缝里,于是吕前进当了钳工,他当了清洁工。可是杨高对自己的工作十分满意,因为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是他的本分,可越是这样,人们越是笑他。杨高为此而苦恼,他说:“我上班来早了,他们要笑我,我下班走晚了,他们也会笑我,其实我每次上班和下班都是看准了时间,都是工厂规定的时间,可是他们还是要笑我,他们笑我是因为他们总是上班迟到,下班早退。”③余华通过这样一个从小胆小如鼠的人的自我描绘向人们展示了文明与落后,“我”的胆小其实是遵纪守法,遵守文明公约,而吕前进等人的胆大却是真正的落后与愚昧。这和余华长篇巨著《兄弟》中的宋钢和李光头有些相似,宋钢老实忠厚却不得善终,李光头滑头老练却活得津津有味。在现代社会中,文明的进程任重道远,牟私利、占小便宜的“胆大”是不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只有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工作才是进步的动力。余华用反讽的笔法展现了生活中的种种人物,展示了生活中国民素质落后的一面,而这种落后的国民性在广大的民间,主要体现在老百姓身上。
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采取民间的批判立场,“用‘讲述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的认知世界的态度,来表现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真相的认识。”④这种民间立场的出现并没有减弱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的深刻性,只是表达得更加含蓄和宽阔。福贵和许三观身上既体现了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又表现出小人物谋求生存的能力。作家通过人物的这两方面性格表达了深邃的批判意识。
《活着》中的福贵在经历了亲人一个个死亡之后,并没有痛不欲生,反而表现了超凡的豁达和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一边同老牛聊天,一边唱着歌谣,“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这种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在许三观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许三观的一生都与卖血相关,除去为了娶媳妇和偷情卖的两次血之外,他的多次卖血几乎都与苦难的生活经历相关。可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对生命和生活的反思与追问,反而表现出一种豁达和超凡的忍耐性。为了给一乐治病,许三观一路卖血到上海。在差点丧命的卖血经历中,许三观没有被生活的苦难压倒,反倒认为他就应该这样做。福贵和许三观身上这种乐天知命的性格帮助他们熬过了苦难的生活,可是他们并没有对生活本身产生质疑,他们是中国老百姓的缩影,除了挣扎在生存线上,并没有过多的对生活的认知。余华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并不是血淋淋的哭诉,但却让人感受到了血淋淋的生活。余华在作品中也并没有人为地夸大或贬低他们,只是真实朴素地写出了他们的生活,这就是民间的力量。在宽阔的能够容纳一切的生活中展现中国百姓的生存现状,既隐含了对苦难历史的批判又投射出对乐天知命的百姓生活的无知的谴责。
福贵和许三观身上体现了一种本能的对抗苦难的生存能力。这种生存能力所表现出的小聪明和小智慧,恰好是被很多人所忽略的中国国民性落后的一面。福贵在飞机空投大饼时不去抢大饼反而去扒士兵的鞋,当他用胶鞋煮饭吃时看到那些光脚的士兵发出嘿嘿得意的笑声,他非但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落后,反而为自己这种生存的智慧而得意。许三观为了多卖血,每次都要提前喝很多水,还要跟血头进行各种周旋。福贵和许三观身上不但凝聚着中国百姓憨厚、朴实的一面,同时也时时透露出中国百姓落后、愚昧和不觉悟的一面。余华对待中国百姓的这种又爱又恨的态度正像鲁迅当年对待中国国民的态度一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社会转型期,余华能够以十分清醒的姿态俯瞰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前期作品还是中后期作品,尽管写作方式上略有差异,但其作品中的现代启蒙意识一直贯穿其中。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的仍然是现代理性,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很快,而人的现代性却相对滞后,余华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他通过作品将人的原生态展现出来,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延续“五四”时期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传统,为提高国民的现代素质深思,表现了一个作家关注当下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作者简介:荣丽春,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① 张永刚、董学文:《文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2001年6月第二次印刷,第47页。
② 张永刚、董学文:《文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2001年6月第二次印刷,第47页。
③ 余华:《我胆小如鼠》,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5页。
④ 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长春:《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第68页-第70页。
(责任编辑:范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