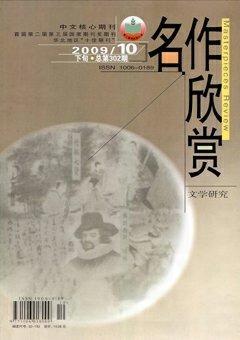当下高校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
赵树勤 龙其林
关键词:《风雅颂》 高校知识分子 精神创伤
摘要: 阎连科长篇小说《风雅颂》逼真地刻画了当下中国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们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到高校体制,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被消解,个人自由与独立人格逐渐地丧失。小说凭借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对当下存在的犀利剖析,深化了当前知识分子小说的表现题材与精神内涵。
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成为当下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反映高校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作品中,不论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境界和价值理想的肯定(如宗璞的《东藏记》、马瑞芳的《天眼》等),还是对知识分子精英神话的解构和亵渎(如张者的《桃李》,史生荣的《教授不教书》、《学者》、《导师》、《所谓教授》,邱华栋的《教授》等),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高校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价值观念进行了审视。但问题是,这些作品中所描绘的高校知识分子与其他人文知识分子的区别被淡化了,未能揭示出这个群体在大学校园这一体制内衍生的充满矛盾的精神因素,因而也很难醒悟到这一个群体被体制不断销蚀个性和陷入市场时代信仰阙如的精神危机。从这一点来看,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在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部小说不仅拓展了高校知识分子小说的思想深度和生活广度,将人们习焉不察的高校体制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奴役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示,而且更以令人惊骇的观察力捕捉到了在这一体制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精神深处的变异与恐慌。正是这种直抵精神根系的深度,使这部小说必然以其直面生活的勇气成为人们反观自我的触点,引发出认同或拒斥、褒贬不一的争议。
一
《风雅颂》主要讲述了清燕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教授杨科求学、治学的历程,透过他进入皇城到读博、留校、当教授的二十年间的经历,深刻地揭示出一个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如何被高校体制约束、委曲求全直至精神分裂的变异过程。离开家乡耙耧山、离别恋人玲珍的青年杨科,在进入大学报到的那一天便感觉“玲珍穿那件布衫儿有一千一万个不合适”。接受了中文系赵教授女儿的示爱后,杨科顺利地考研、读博、留校、评职称,过上了“一抬头就能看见晨起的曙色和日暮的霞光”式的高校生活。本科时代就能写出《〈木瓜〉新解》这样见解独到的论文的杨科,在市场语境下突然发现自己已沦为时代的落伍者,不仅论文被编辑部收取发表费,课堂上学生也因丧失了对文化经典的兴趣而人数渐少,连花费五年心血完成的学术著作出版社也要收取高额费用才愿出版。这样一个忍气吞声、低声下气的教授,竟然因为偶然撞破了妻子与副校长李广智的奸情而机遇凸现,不但顺利地保住了《诗经解读》的课程,还有可能获得不菲的经费出版学术著作。后来偶然参与到学生抗击风沙的行动中,使学校成为舆论的中心,杨科被校领导强行送往精神病院。逃离医院的杨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见到了昔日的恋人玲珍,却无法找到曾经的爱情,只能在天堂街的风尘女子身上获得一种精神的慰藉。因为不愿玲珍的女儿小敏与木匠结婚,杨科失手杀死了木匠,逃亡途中发现了古代遗留的诗城,他率领一群妓女和失意的教授来到了诗经古城,试图建构起一种没有权力、不存在压迫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学术成为手段,知识转化为权力与经济利益,不学无术者成为了高校体制的操纵者,知识分子由于受体制的长期抑制唯唯诺诺、麻木不仁,这便是小说所揭示的当前中国高校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时代真理。经历过高校体制的不断改造,杨科在小说开始时已经丧失了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责任感,遑论关注社会公平、追求人类良心的公共使命,扭曲为对体制的顺从。杨科一方面具有知识分子残留的价值追求,他希望通过对诗经的研究,“重新揭示了一部经书的起源和要义,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重塑了精神的家园与靠山”,在内心深处,他意识到自己“是教授,是知识分子……是个有尊严的人”;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无奈地认识到,权力和金钱是这个时代的中心话语。发现妻子与副校长偷情后,杨科并没有大发雷霆,反而“让我觉得有些内疚,只好一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应该先给你们打一声招呼再回来”。他所以如此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杨科在高校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得仰仗体制的认可,否则便没有生存的空间。发现妻子偷情的人物竟是副校长李广智后,杨科要求的是希望李广智“给系里说一下,古代文学教研室可以没有,但《诗经解读》这门课我不能不讲”。不仅如此,杨科还利用偷情事件要挟妻子与副校长:“我用五年时间写了这部专著你说我不能不出吧?可现在除了垃圾外,有哪一本学术专著出书学校不赞助?哪一本书不是越有价值越是没人看?我不能因为你和他有了那样的关系,反而不能不去他那儿要该给我的出版经费吧。说他要是明白人,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对不起了我杨科,这时候就该主动把出版经费送给我。”这种既渴望尊严、认同,又离不开体制规约的现实,使杨科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他在不得不“原谅”妻子、表现出“大度”的同时,内心深处又有着难以抹去的耻辱。在高校体制不断官僚化、大学日益市场化的时代氛围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和价值追求越发显得轻飘和暧昧。
二
《风雅颂》无疑是近年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一大收获,它是写知识分子的,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超越了知识分子具象,成为对这一个社会群体的灵魂状态的反思。可以看出,阎连科是一位对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十分关注的作家,同时也对他们的精神信仰的淡漠、缺失表示出了痛彻的忧虑。他在小说中写杨科、赵茹萍、李广智们,写高校体制内的弱势者、强势者和依傍权贵者,既写他们对现实利益的认同,又写其心灵的苍白和空洞,以及面对权力时的恐慌、握有权力时的心理异化,在不经意间刻画出了这个群体的不同部落的精神根性。
还在本科时代,杨科并未经过多少犹豫便作出了和赵茹萍恋爱的决定。因为赵茹萍曾这样对杨科说,“只要我俩一结婚,你就完全可以摆脱你的农民身份了,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赵家的女婿,京城第一名校的教师”,渴望成为体制内一员的杨科毫不迟疑地选择了赵茹萍。留校之后的杨科,已经习惯了体制内的生活:“撰写论文,结集成书,出版发表,参加各种《诗经》学术研讨会”,和到“讨论会上做重点发言。回来后领着纪念品,再到课堂上介绍讨论会上的见闻和各路专家对《诗经》独辟蹊径的理解和高见,有时也把自己某篇获奖论文的证书拿到课堂上展示一番”。然而,在这种习焉不察的高校体制内的长期生活中,科研、课题、出版等体制内的生存方式彻底约束了杨科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如何适应高校体制的规则,成为杨科精神的基本出发点。在这个过程中,杨科也曾清楚地意识到高校官僚的权力——“他把他的李广智三个字往某一页纸的右下角一写,某某副教授就可能成了教授、成了学术带头人、成了某个科研项目的领军人物。从此,那领军人物他们家的柴米油盐就可以在科研项目里报销了”,但是这种认识不仅没有给杨科带来警惕与帮助,反而使他在体制内越陷越深。当杨科拿着潜心五年研究的学术手稿回到家里,却发现妻子赵茹萍和副校长李广智偷情在家。他几乎没有作为丈夫的愤怒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耻辱感,而是内疚与惶恐,面对“副部级的知识分子李广智”、“管着皇城赫赫名校教学的副校长”、“全国所有大学博士点审批小组的权威组长”,杨科“想说啥,却只叹了一口气”。此时,杨科所想到的仍然是高校体制所认可的学术资源、地位,内心的价值观念、是非观念就在这种体制内的消磨中完全扭曲。在出版《风雅颂》遇到经费困难时,杨科又想到了利用妻子与李广智的偷情来获取学术资源,“我们夫妻俩就该联手向他要,趁我出版《风雅颂》这机会,打报告要他批上二十万、五十万,有可能就批上一百万。他要给我们批了一百万,过去的事我们真的既往不咎,拿二十万我出精装豪华本的《风雅颂》,那八十万就存到存折上”。当杨科牵涉到和学生阻挡风沙事件、惹怒当局时,学校领导表决送他去精神病院,李广智犹豫了一会儿才举手,这在杨科便是受宠若惊的举动:“李副校长是个好人……你一定跟他说一下,说我杨科谢谢他”。怀着对《诗经》的无比热爱,杨科被纳入到高校体制,并逐渐地沦为制度的附庸,丧失人之为人的精神追求、价值信仰,直至最后被迫变成了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
阎连科写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残缺,而这种残缺因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而成为了对时代语境的某种寓言。“意识形态主流文化的拒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僭越,人文学术的启蒙功用和现实功能在二者的挤兑下日益萎缩,其神圣的中心话语地位已然被无形消解”①。这种高校体制中的科研、评职称、申请经费、著作出版等规范对身处其中的知识者的奴役、蹂躏,知识分子面对这种奴役、扼杀时的无奈和绝望,他们陷入绝望之时所显现的文化劣根性、精神缺陷性和人格的矮化,在小说中得到了令人震惊的描绘。鲁迅终其一生的创作,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唤醒富于理性的人们认识自己的处境,并因此而清理国民性中的劣根性,以便获得重新为人的资格。而在杨科身上,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种清理劣根性的任务不仅未能在普通民众中普及,甚至在精英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隔代的繁衍,这或许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三
在当代社会中,各种权力机制都向知识专业和生活领域进行渗透,从而使知识分子不再幻想成为社会的先知先觉者。正是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和知识分子的有机化,使苏格拉底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牛虻精神在这个时代丧失了发展的契机。相反,由现代化引发的世俗化,使人们从对经典、神圣和信仰的坚守中剥离出来,转而以经济利益、现实利害关系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阎真先生曾这样阐述自己对时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的认识:“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意识和责任意识正在淡化,而这两点,正是他们身份标记,我因此痛感‘死亡之说正在成为中国的现实,我自己也强烈地感到了内心的动摇,以至崩溃。可以说,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选择了放弃,很多人利用一切机会在‘灰色地带上下其手”,正是“普通知识分子生活中那种宿命性的同化力量,它以合情合理不动声色的强制性,逼使每一个人就范,使他们失去知识分子的身份,变成一个个仅仅活着的个体,虚无主义者”②。
为时代语境规约的知识分子们,在相对主义的氛围里失却了对终极价值和乌托邦理想的信仰,崇高与神圣成为明日黄花。在知识分子的世俗化、无根化的潮流下,他们所追求的知识正在逐步地远离神圣,而成为谋生、谋权的有效手段。《风雅颂》中的赵茹萍、李广智等人,便是这些远离神圣、在权术金钱中奔突的知识分子的诠释。作为学校副校长的李广智,利用手中掌握的评定职称、评奖和分配科研经费的权力,与杨科的妻子赵茹萍公然在家偷情。事情败露后,李广智为挽救自己的仕途,他鲜廉寡耻地用保证杨科的《诗经解读》课程、拨一笔出版经费的条件进行交易。作为杨科妻子的赵茹萍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角色。抛开中学时期发生的早恋、堕胎的往事不谈,进入清燕大学之后的她成为利用规则、玩弄权色交易的行家里手,并顺利地从图书管理员成为讲师、副教授、教授。但作家并没有将这一形象简单化,而是写出了她自身的屈辱与不易。偷情败露后,赵茹萍对杨科说,“物价又涨了你知道不知道?以前鸡蛋是三块二一斤,现在是四块六一斤;以前花生油是三十块钱一桶,现在是四十七块钱一桶;以前一美元能换八块六人民币,现在这比价哗一下落到一美元兑换八块一”,将这种身处体制不得不认同、利用的无奈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出来。同时,小说还反映出了目前高校知识分子的结构上也呈现出世俗化的特点。作品中出现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无论是校长、系主任还是普通教授,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多少传统人文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意识与人类良心的特点,相反更多地体现出权力话语知识分子、技术知识分子和经济型文化人的特点,即注重为现实体制服务、注重知识的实用性、注重知识的效益原则和交换原则,他们已经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人类良知的作用,完全退守到个人生存的世俗空间和经济利益之中,几千年从未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获得过道义合理性的世俗原则,在体制内的高校知识分子中不动声色地获得了现实的合理性、合情性,这不得不说是这个时代的一大悲哀。
《风雅颂》是对当下高校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一种剑走偏锋式的冷峻逼视,是现实合理性作用下产生的荒诞事件的真实反映,它是对知识分子题材的一次集中审丑,更深层的则是对知识分子精神信仰和立足点的找寻,直接追问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体制性堕落与精神沉沦。《风雅颂》以其独特的精神力度和心灵深度,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小说应该是对现实存在的敏锐发掘和勇敢表达,而不是恰恰相反。
作者简介:赵树勤,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龙其林,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① 梁振华:《宿命与承担——市场经济浪潮中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选择》,《当代文坛》2001年第2期。
② 阎真:《时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说说〈沧浪之水〉》,《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范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