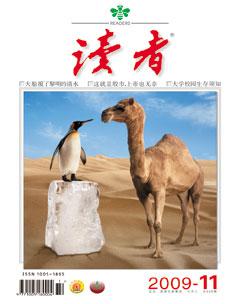小柯:生死之间念来去
王小峰
小柯跟他10多年前刚出道时一样,憨态可掬地谈论着歌坛的事情,谈他的音乐创作和他的公司、学校。如果让时间回到6年前,也许谁也不会想到,他今天还可以这样。
2003年4月13日凌晨,小柯跟往常一样开车回家,当时路上车很少,车速快了点,在途经北四环大屯附近时发生了车祸。第二天我听到的消息是:小柯身上的骨头全碎了,人躺在医院,生死未卜。6年后,当小柯回忆起那场车祸,跟我当时听到的状况差不多:“肋骨、胸骨,前面所有的骨头除了锁骨全都折了,就是说这人等于塌了,是很危险的。一群大夫围着我束手无策,不知道从哪儿下刀合适。要是折一两根肋骨是可以长好的,肋骨顺着筋可以长,但必须是正常的形状。如果是歪着的话,那长出来的都是歪的,人也好不了。咱们这些大夫也挺伟大的,想了许多高招,什么前胸拴铁丝、拴房梁上,给拉出个骨形来,但到最后还是找到了美国曾经有过的一个我这样的病例。他们采取了一种让伤口愈合的方式,就是在气管打一个眼儿,然后往胸腔里吹气,用气体使胸腔鼓起来,形成自然的空隙,就长好了。但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当你打了一个眼儿之后,你的体内就完全和空气接触了,即便在无菌病房也是有危险的,会造成体内大面积感染,这更危险。感染之后医院请了我们国家最牛的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协和医院的王爱霞,来做一个判断和选择,两种药只能打一种。原来的方案是,这个试了不行就试那个,王大夫说这不能再试了,再试人就没了,只能在两种药中选一种,还得是大剂量的。也就是说,一针下去,要么人就活了,要么人就死了,只能赌。”
昏迷了40多天的小柯,在这场赌博中睁开了眼睛。亲戚朋友来医院看小柯,他的记忆也慢慢恢复。有一天,歌手来看他,他才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公司呢,那种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他不能像一个离退休干部那样休养了,他必须要工作。
车祸让小柯的膝盖韧带都撕裂了,当他从床上起来后,发现自己不会走路了。他专门找了一个教他走路的大夫,练习走路。每天到楼下遛早儿,周围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和带着孩子的保姆,中间夹杂着小柯。
医生告诉他,身体彻底恢复至少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但是出院后3个月,小柯便带着歌手演出了。“这不是我有多牛,而是心态,你的心态不好是扛不下来的。这件事让我感悟到,你要对自己的生命有信心,同时你的亲人也要对你的生命有信心。在我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大夫、朋友都崩溃了,我父母特坚定,认为我一定没事儿。当我一睁眼发现自己受伤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想过我会一直这样,我也特坚定,我认为自己没问题。之前踢球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为了踢完球喝那场酒。在车祸之后,所有的运动习惯都是为了身体。”
“车祸对我改变很大。”小柯说,“简单说,2003年以前比较自私,很多事情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不会为别人考虑,甚至包括自己很亲密的人——父亲、母亲、姐姐、媳妇……车祸之后,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更多地考虑到别人了。比如我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会不会给周围人造成影响,或者不好的事情,我就会克制,不会去做。”
在出车祸之前,小柯有一家公司叫钛友文化,有一搭没一搭地做了几年。车祸之后,小柯想,必须要努力做这个公司,他说:“一个挺大的改变就是,比原来更珍惜时间了。原来我的生活,每天除了写歌就是玩儿,只有这两部分,恨不得变成业余写歌,主要是玩儿。每天下午起床,抓紧时间写点儿歌,就约了饭局,一混混到夜里,回来之后看看片子,睡觉。之后的生活是除了写歌之外,真的在工作了,甭管会不会,起码知道为工作着急了。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是干该干的事儿。绕那么一圈回来,你会觉得活着还是挺美的。”
车祸之后,小柯一度有3件事不能干,这让他很痛苦。一件事是不能看足球赛,看了就想踢球,但是两条腿已经不能让他从事这件事情,至今他不能从高处往下蹦。还有一件事就是不能像以前那样弹钢琴,手部的神经还不太听使唤,他说蒙一些外行还可以,但是弹奏一些比较复杂的曲子就有些吃力。第三件事就是不能唱歌。小柯说:“恢复后,发现自己没假音了,唱歌费劲。开始以为是元气不够,丧失元气了,又觉得是气息不行。这么多年了,我喝了无数中药,补得都快流鼻血了,可唱歌还是不行。后来觉得可能是声带有问题,当时毕竟插气管了,会碰到声带。找到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大夫,他说他见过我这样的病例,声带的外面有一块软骨,是控制声带松紧的,当时插气管的时候可能碰到这块软骨,把它碰歪了,歪一点儿就使不上劲。后来,他把我的声带掰过来,当时说话声音就亮了。”
一个人在生死之间往返一回,能明白很多事情,小柯也是。他说:“之前写音乐,不明白创作是什么。以前那么多歌是怎么写的,我说不出来。也许,那就是一个青年对音乐的热爱,喜欢这个就干出来了。严格来说,这不是创作。后来我明白了,创作是把内心的事儿变成音乐说出来,创作的过程就是心里有事儿,拿笔写出来是文学,唱出来是音乐。”
(马 腾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8期,束新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