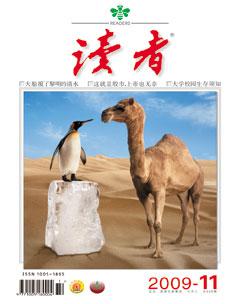音乐“流言”
2009-10-23 09:02张爱玲
读者 2009年11期
梵婀玲
我最怕的是梵婀玲,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
梵婀玲拉出的永远是“绝调”,回肠九转,太显明地赚人眼泪,是乐器中的悲旦。
梵婀玲与钢琴合奏,我也讨厌,零零落落,历碌不安,很难打成一片,结果就像中国人合作的画,画一个美人,由另一个人补上花卉,又一个人补上背景的亭台楼阁,往往没有情调可言。
古典音乐
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不是浪漫派的贝多芬或肖邦,却是较早的巴赫。巴赫的曲子并没有宫样的纤巧,没有庙堂气也没有英雄气,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却又得心应手。小木屋里,墙上的挂钟滴答摇摆;从木碗里喝羊奶;女人牵着裙子请安;绿草原上有思想着的牛羊与没有思想的白云彩;沉甸甸的喜悦大声敲动,像金色的结婚的钟。如同勃朗宁的诗里所说的:
上帝在他的天庭里,
世间一切都好了。
歌剧
歌剧这样东西是贵重的,也止于贵重。歌剧的故事大都很幼稚,譬如像妒忌这样的原始的感情,在歌剧里也就是最简单的妒忌,却用最复杂最文明的音乐把它放大一千倍来奢侈地表现着,因为不调和,更显得吃力。那样的隆重的热情,那样的捶胸脯打手势的英雄,也讨厌。可是也有它伟大的时候——歌者的金嗓子在高压的音乐下从容上升,各种各样的乐器一个个惴惴慑服了;人在人生的风浪里突然站直了身子,原来他是很高很高的,眼色与歌声便在星群里也放光。不看他站起来,不知道他平常是在地上爬的。
爵士乐
一般的爵士乐,听多了使人觉得昏昏沉沉,像是起来得太晚了,太阳黄黄的,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没有气力,也没有胃口,没头没脑。那显著的摇摆的节拍,像给人捶腿似的,却是非常舒服的。
(林 叶摘自京华出版社《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感悟名家经典散文》一书,图选自译林出版社《卡洛伊漫画》一书)
猜你喜欢
疯狂英语·新阅版(2021年5期)2021-06-21
小天使·五年级语数英综合(2021年2期)2021-06-15
作文新天地(初中版)(2020年4期)2020-05-13
环球时报(2019-12-21)2019-12-21
儿童故事画报·智力大王(2018年6期)2018-10-30
意林(2018年5期)2018-04-03
作文周刊(高考版)(2017年26期)2017-08-10
南风(2017年14期)2017-05-12
中国校外教育(下旬)(2014年4期)2014-07-17
中学生英语·阅读与写作(2008年6期)2008-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