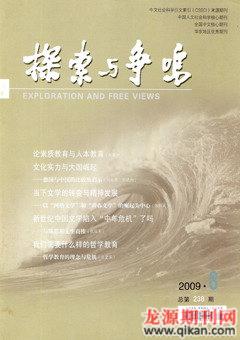论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的形成机制
何 静 李京生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带来了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型。很多大城市出现了城市贫困人口聚居在城市特定区位的现象,上海概不例外。对杨浦区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的调研发现,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的形成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廉租房保障制度缺位,“重效率、轻公平”的城市规划价值取向,城市历史空间的延续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下需要从住房保障和城市规划两方面采取行动,促进低保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的社会融合。
关键词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现状特征社会影响形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带来了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型。很多大城市出现了城市贫困人口聚居在城市特定区位的现象,甚至一些中等城市也成为贫困人口区位化的高发地区。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关城市贫困人口聚居的现象和后果已经得到广泛的讨论,尤其是美国,近30年来,社会学、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者分别从城市贫困人口聚居区的成因、聚居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对很多城市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然而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多侧重于理论探讨,必要的实证研究成果较少,并主要集中在南京、广州两个城市。此外,多数研究出于数据提取的方便性,将街道作为基本统计单元来讨论城市贫困人口聚居状况。而街道的空间范围大、异质性强,往往不能准确反映贫困人口聚集居住的真实状态。笔者拟以上海市杨浦区为研究基地,以居委会作为基本空间单元,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典型组成部分——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展开实证研究,着力探析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的形成机制。
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顾名思义就是城市中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相对聚居的区域。对贫困人口聚居区的界定是国外城市贫困人口聚居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威尔逊在对芝加哥的研究中把贫困率在20%以上的人口普查统计单元界定为贫困地区,把贫困率在40%以上的界定为极端贫困地区。加构韦斯基等学者将该定量界定方法拓展到芝加哥以外地区时,普遍采用40%的界线来界定贫困地区,认为“用40%的标准选择的地区与地方政府和人口统计部门所认定的(贫困)聚居区是相符的”。
我国目前各城市、分区、街道没有公开的居民收入信息,缺乏明确指标界定城市贫困人口聚居区,对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的相关定量研究也很少。笔者借鉴加构韦斯基等学者的定量方法,将居委会作为基本空间单元,以特定的城镇低保家庭比重标准来界定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加构韦斯基等学者采用的40%贫困率标准,是全美城市中心区贫困率的两倍左右。上海市中心城区城镇低保家庭比重约为5%,笔者也采用该比重的两倍来界定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即城镇低保家庭占户籍家庭总数的比例在10%以上的居委会。据此,杨浦区全部306个居委会中有27个居委会被界定为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2008年2-3月,笔者对其进行了实地勘察,并选择了四个典型聚居区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尽管不同聚居区间存在差异,但它们在社会经济和物质空间方面具有明显的共性。
第一,从社会经济构成来看,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的居住主体表现出较强的同质性和普遍的低层次性:(1)居住群体以低保和低收入家庭为主,少数为中等收入家庭,完全没有高收入家庭居住;(2]社区老龄化十分严重:(3)户主的失业率极高;(4)在业户主的职业类型接近,大都从事传统工业和低端服务业,且处在低技术、低工资的岗位;(5)家庭人口规模较大,家庭负担系数较高。
第二,从物质空间环境来看,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的居住环境严重衰退:(1)聚居区主要分布在旧式里弄、早期工人住宅区和工人新村;(2)建设年代久远,房屋老化严重;(3)房屋建筑等级普遍较低,以旧式里弄和第三类职工住宅为主;(4)绿化和公共服务设施十分缺乏,居委会、青少年和老年活动室用房严重不足;(5)住房困难较为普遍,抽样人均居住面积不足7平方米。
城镇低保家庭在特定区域的高度聚集,有利于集中提供社会服务,便于对低保家庭进行管理,提高公共设施的利用率:但同时也给城市和谐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其一,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的出现造成了城市空间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低保家庭相对集中居住在物质空间环境衰败的聚居区中,他们所占有的居住空间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远远低于中、高收入群体,扩大了他们在社会分配中的不平等地位,使低保群体的弱势地位在城市空间上延续,形成对其社会地位与城市空间的双重剥夺。其二。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与周边地区在居住空间环境、社会成员构成、消费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日趋明显。加剧了城市居住隔离。以居住区域为界,低保家庭在聚居区内互相结合内聚起来,把中、高收入群体排斥在交际圈之外,阻碍了积极的社会群际交往。使得不同群体或阶层之间的流动产生断裂,导致贫困的固化和社会阶层的对立,进一步强化了社会隔离的趋势。其三,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旧城改造地区的群体性社会矛盾。杨浦老城区的旧式里弄是低保家庭聚居区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很多居民同时面临经济贫困和住房困难,社会矛盾在这些地区高度集中、相互交织。在长期等待动迁的过程中,聚集区居民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同盟,个人的贫困问题极易演变成群体性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旧城改造地区的社会矛盾,影响了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决定城市空间结构的是隐藏在表面世界后的深层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和空间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交互作用。杨浦区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的形成,无疑是转型期以来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市场竞争导致大批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大量富余人员下岗、失业,生活陷入困境,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城市贫困现象。作为上海的老工业基地,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中,杨浦区大量工厂破产、停业或外迁,到2003年已有154家工厂关、停、并、迁,大量产业工人被分流,下岗、待业或进入协保,下岗再就业职工达21万余人。传统产业逐步萎缩,大量低技能的简单劳动力由传统产业部门析出却难以进入新兴产业部门,进而陷入贫困状况,不得不依靠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在2005年对杨浦区的抽样调查显示,53.1%的居民在改革过程中实际收入水平下降,55.1%的居民认为自己职业地位下降,在转型过程中原来的普通产业工人承受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大量传统产业工人经历了社会地位的垂直下降,从拥有稳定的较高工资收入的产业工人,变成失业、退休或从事其他低收入职业的低保人口。居民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变化。直接改变了城市空间的社会构成,使得一些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工人居住区迅速退化为低保家庭相对集中的聚集区。
2,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的实质性缺位。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型、统包统分的实物福利性住房制度进行了改革,1999年底上海市明确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补贴制度和住房保障政策,并从2000年开始逐步建立以城镇低保家庭为主要对象的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然而从整体来看,上海现行廉租政策的覆盖面仍然较小,绝大多数城镇低保家庭的居住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对于低保家庭来说,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已经彻底结束,高额的房价与现实支付能力之间的巨大鸿沟,使他们不可能通过住房市场改善居住条件:整个廉租住房制度体系尚未成熟,存在实质性的政策缺位。低保家庭的居住处于缺少保障的状态。随着中高收入群体“向上流动”到环境较好的新建小区居住,大部分低保家庭被迫继续居住在早期单位分配给职工家庭的公有住房中或拥挤、破旧的家传私房里,客观上促使这些地区城镇低保家庭的比例升高。
3,“重效率、轻公平”的城市规划价值取向。在我国城市规划是一种政府行为,通过高效的空间调控,政府意志被施加于城市内部空间的发展过程。计划经济时期。在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差别较小、社会利益相对简单的条件下,社会目标显得较为一致,城市规划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对城市资源进行配置。社会经济转型以来,社会利益日趋复杂,政府制定和执行城市规划政策的时候往往无法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而是有选择、有偏好地代表其中某种利益,甚至可能是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城市规划领域的实践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城市资源配置中过度追求效率,相对忽视了社会的公正与公平。政府用以调控城市空间发展的城市规划沦为“招商规划”,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的旧区改造,往往是房地产商获利,而百姓利益受损。老城区内的很多区域长期得不到改善。一旦进行旧区改造。又意味着其中的低保家庭要被迫搬迁到远离市中心的远郊去。
4,城市历史空间的延续。城市空间的演变具有历史延续性,现状社会空间结构和居住空间的分异与历史遗存紧密相关。在近代上海已形成了“西贵东贱。地顷西南”的居住格局。南京路、外滩一带属于公共租界,淮海路一带为法租界:城市西部愚园路、衡山路的花园住宅区是富人聚居区;而东北部的杨浦、闸北、宝山都是工厂区,大量来沪务工的贫困农民在工厂周围间隙地、铁路沿线、黄浦江和苏州河两岸搭建棚户简屋居住。解放前夕杨浦区共有住宅190.46万平方米,大部分为旧式里弄和棚户简屋,其中有132处棚户区,占全市棚户区的1/3以上。经过50多年的改造,至2005年底杨浦区境内仍有143万平方米的旧式里弄和10万平方米的棚户简屋。正是这些棚户简屋和旧式里弄房屋,继续构筑了杨浦区居住建筑的底部空间。在历次的旧区改造和住房解困中,部分居民离开这里到其他地区居住,然而更多的贫困群体却不得不继续居住在这些建筑衰败的地区,甚至还有一部分贫困人口为生活压力所迫而迁入这些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遗留下来的成片旧里简屋的分布与老城区的低保家庭聚居区高度耦合,历史上的贫困地区形成了新的贫困人口聚居区。
杨浦区的实证研究表明,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已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入发展,城镇低保家庭聚居的规模和密度还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已发生的贫民窟骚动,我们应该引以为鉴。笔者认为当下我们应从住房保障和城市规划两方面采取行动,改善低保家庭等城市贫困群体的居住水平,促进低保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的社会融合。
1,提高廉租住房保障水平。第一,尽快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廉租住房保障法规,从法律上对我国住房保障的目标框架、保障对象、标准、范围、资金来源及机构设置等做出明文规定,切实扩大廉租政策覆盖面,提高保障标准,拓展廉租房源供给。第二,继续推行“以租金补贴为主、实物配租为辅”的廉租住房保障方式,由廉租对象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住房地点。发挥有限资金的作用,形成退出机制,避免因集中兴建廉租房而形成新的“贫民窟”。第三,构建廉租住房租赁的服务平台,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指挥下,由专门机构为廉租筹集资金和房源,并为廉租对象提供房屋租赁或退租服务,通过服务平台将参与廉租的政府部门、房屋租赁机构及廉租对象等多个主体有机地联结起来,提高廉租保障的实施水平。
2,促进社会融合的城市规划。第一,在城市层面,城市总体规划和空间发展战略应采取促进公平、融合的原则,公平原则强调将公平作为规划的评价标准之一,使之成为规划的政策目标,包括不同收入群体公平公正的分配、接触空间资源。㈣融合原则强调对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的重视,促进聚居区的升级改善以及与城市其他地区的融合,避免“直接拆除”将土地置换成中高档商品房的做法。第二,在区和街道层面。在城市分区规划和各街道范围的社区规划中,必须充分考虑娱乐、教育、医疗卫生、老年设施等的合理公平布局。规划重点关注这些设施分配的公正性,从公平角度出发对这些资源的布局分配进行深入考虑,制定满足不同收入群体需求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优化区域性布局。对于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集中的区域,可以通过城市用地规划,调整用地结构来提高这些区域的基础设施水平,积极改善低保家庭聚居区的环境条件。第三,在居委会层面,通过规划、建设不同收入群体的混合居住区促进社会融合,为低保等贫困群体提供平等的外部经济环境,为其社会生活能力与质量的提升创造同等的外部机会。邻里或小区内部的混居,既包括同幢建筑内的混居。也包括单体同质、不同建筑间混居等情形,在邻里或小区内部应构建必要的公共沟通空间体系,促进居民个体间、群体间、阶层间的日常交往和沟通。对于已经出现的城镇低保家庭聚居区,有必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战略,在现有规划框架内为聚居区的更新和再开发创造条件,以期打破同质贫困群体聚居的格局。
编辑阮子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