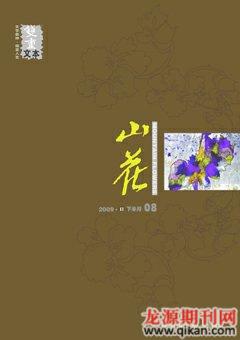独具匠心的角色
海明威是一个独具个性、惜墨如金的作家。一次与记者谈到《老人与海》的创作时,他说:“《老人与海》本来可以长达一千多页,把村里每个人都写进去,包括他们如何谋生、怎么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可实际上作家没有这么做,而是“学着另辟途径”,“试图把一切不必要向读者传达的东西删去,这样他或她读了什么之后,就会成为他或她的经验的一部分,好像确实发生过似的。”就是说,他在创作《老人与海》时,为了使作品要表达的东西成为读者的经验,产生切身感受的艺术效果,总是删去多余的人物。由此看来,《老人与海》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经过慎重考虑保留下来的。所以,作为小说中有名有姓的出场人物之一,曼诺林绝非可有可无,而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打开文学史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把研究的着眼点集中在主人公的“硬汉性格”和作家的“冰山原理”,而对曼诺林的形象大都漠然视之。其原因也许很简单,那就是《老人与海》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描写老人桑提亚哥海上捕捉马林鱼和与鲨鱼搏斗的经历,而对孩子曼诺林的描述只在故事的开头和结尾;这一人物所做的事情也不过是老人出海之前进行的“送行”和返航之后进行的“迎接”而已。况且,小说既没有这一人物的外貌描写,也没有提到过他的年龄;对他的家庭背景也没有什么交代。总之,曼诺林给人的感觉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其实,这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一样,妙在“不留痕迹”;恰恰是作家的独具匠心之所在,在人们毫不经意的情况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曼诺林的形象不仅拓展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且衬托出主人公更加丰满动人
曼诺林五岁跟随老人桑提亚哥学打鱼,多年以来,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由于“老汉教过孩子打鱼,孩子也爱他”,所以曼诺林每每看到老汉摇着空船回来,“孩子心理怪难受的,总要下海滩去,不是帮助他搬回那堆钓绳,就是帮助他扛走拖钩和鱼叉”;老人背运,孩子总是抽空找开心的话题与老人聊天;在生活方面,孩子对老人问寒问暖,送饭、买药、弄鱼饵,可谓关怀备至;在看到老人海上归来筋疲力尽的躯体时,他强忍悲痛依然鼓励老人振作起来……
孩子对老人既崇敬又爱戴,因为在曼诺林看来,桑提亚哥是打鱼的最好的把式。另一方面,雄狮一般的老人桑提亚哥对孩子曼诺林也是一往情深:他无私地向孩子传授捕鱼技艺,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人生经验,无微不至地关心孩子的成长,甚至细微到了孩子的起居生活等。在老人的心目中,孩子就是自己的精神依托,因而在海上总是时时地自语说:“要是孩子来了就好了。”总之,老人与孩子情同手足、形同父子,而且其密切的关系毫无半点功利目的。如果说,小说通过桑提亚哥的海上捕鱼和与鲨鱼搏斗的经历,谱写了一曲不屈不挠的英雄赞歌,那么,小说通过“孩子”曼诺林与“老人”桑提亚哥的友情关系,颂扬了人世间真诚友爱的伟大精神。
不仅如此,孩子曼诺林与老人桑提亚哥的关系还是圣徒与耶稣关系的一种“隐喻”。《圣经》上说,耶稣受圣灵引导,到旷野上禁食了40天,加上基督教大斋期40天,和复活节前的圣周7天,刚好87天。桑提亚哥84天没有打到鱼,又在海上待了3天,加起来恰好也是87天。其中老人海上磨难的3天,正好是耶稣从受难到复活的那3天。这种安排绝非一种巧合。还有,桑提亚哥“扛起桅杆,开始爬坡”,总会使人联想到耶稣背负着十字架走向永恒的景象;海上老汉与大鱼搏斗受伤时叫了一声“Ay”,这时作者写道:“这个词没法译得传神,也许只是像一个人感到钉子穿透他的两手,钉进木头的时候,会不由得喊出的一声吧”,这是一种“暗示”,由此可以十分自然地使人想起耶稣的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情形。
这样说来,孩子与老人“爱的关系”隐含着浓厚的“爱的宗教”的意味。尼采说:“上帝死了。”作为关爱人类的作家,海明威试图通过颂扬孩子曼诺林与老人桑提亚哥之间的“宗教之爱”,来拯救他所生存的“无爱”的世界。
小说通过对小孩及与主人公关系的描写,使得小说的思想内容更加丰富,主题也得到了拓展。同时,小说在开头、结尾通过描述孩子曼诺林对老人的尊敬和爱戴,还有力地证明了老人桑提亚哥的确非同一般;而且愈突出孩子曼诺林对老人的尊敬和爱戴,愈显出老人的高大非凡。这种“水涨船高”的衬托手法,不露痕迹地颂扬了老人,彰显了主人公的精神魅力。
二、曼诺林在强化主人公悲剧命运、导引接受者的悲剧情感、缓解读者的悲伤情绪等方面,发挥明显的重要作用
《老人与海》开篇写道:桑提亚哥“是独个儿摇着小船在湾流里打鱼的老汉,已经八十四天没有钓着一条鱼了。头四十天,有个男孩跟他一块儿。可是过了四十天一条鱼也没有捞着。孩子的爹妈对他说,老汉现在准是彻底salao,就是说倒霉透了,所以孩子照爹妈的吩咐跟了另外一只船,第一个星期就捉了三条好鱼。”桑提亚哥“背运”,八十四天没有打到鱼,这种不幸命运的境遇已经够让人伤透心了。但在老汉“背运”之时,最需要有人给予精神抚慰的时候,常年与老汉一起打鱼、交情又十分笃厚的孩子,竟然也离他而去。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印证了老人不幸命运非同一般。然而,孩子跟上了别人,头一个星期就有不小的收获,而且是三条“好鱼”。这就与前四十天跟着老汉一条鱼也没有捞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说明了老汉是悲中之悲的人物。小说开头的这寥寥几笔,就将主人公的不幸命运推向了极致。
如果小说的开头通过对曼诺林的描述加重了主人公命运悲剧分量的话,那么结尾之处孩子的“哭”,则有效地营造了浓厚的悲剧氛围。
当孩子曼诺林看到返航后的老人,小说细致地描述了孩子曼诺林的“哭”:第一次写他“哭”,是因为看见老汉的手受伤而哭;第二次写他“哭”,是离开老汉想弄些咖啡的路途中,是“一路走一路哭”;第三次写他“哭”是渔民问老汉怎么样,“他不在乎他们看见他在哭”;第四次写他“哭”是卖咖啡的老板说孩子昨儿个打了两条好鱼时,应该是孩子感到后悔没有和老汉一块出海而哭;第五次写他“哭”是离开老汉准备从药店带些油膏给老汉治手,是“边走边又哭”。曼诺林的每次哭都是复杂情感的自然流露;读者在领略孩子“哭”的情感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被孩子的悲伤情感所感染,也会像孩子曼诺林一样对老汉的不幸油然产生浓厚的同情之心。
这正是作者要达到的悲剧艺术效果。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所摹仿的行动,不但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这样看来,小说通过孩子对老人的同情既而诱发读者的悲悯之情,巧妙地实现了亚里士多所说的悲剧效果。
由于孩子是在老人“背运”之际离开老人的,致使老人只能独自与大马林鱼、各种鲨鱼展开生死搏斗;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孩子与老人一同出海,那也许是另外的一种结局。孩子曼诺林从老人的这次最大的捕鱼“失败”中体会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他懊悔之际再一次提出,坚决要与老汉在一块儿打鱼,而且表示哪怕是遭到父母的反对他也全然不顾,强调说:“因为我还有好些要学呢”,并且开始准备下次一同出海的装备。对孩子的请求和行为,老汉并没有表示反对,且在睡梦中依然梦见狮子。
这一切表明,老汉从孩子那里又看到了新的希望,再度燃起了生活的热情。孩子是人类生命延续的维系物,也是桑提亚哥不向命运低头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老人桑提亚哥正是在孩子的鼓励下,才能够在“背运”的情况下具有不屈不挠的勇气,顽强地与大海、大鱼等拼搏下去。
他意识到:“要不是孩子,我早完了,这一点不承认可不行”,而且在与对手搏斗中,桑提亚哥几次想到了孩子,总是自言自语说:“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有了孩子才会在灾难中看到希望。这样说来,孩子与老人将要再度进行的合作,一定能够改变老人的不幸命运。就此而言,小说这样的结尾已经预示着下一次捕鱼历程不再是老人的独自奋战,将是一次有希望的捕鱼过程。这就为小说的悲剧增添了乐观色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读者的悲伤情绪,从而使读者的“恐惧”心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或“平衡”。
三、有了曼诺林,更便于作家以“限知视角”叙述故事,给读者以更加强烈的身临其境的体验,从而增强小说的艺术真实感
作为一个“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写作”的作家,海明威描写人物、叙述故事,并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尽管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了如指掌,也总是略去所知道的“八分之七”,而保留其中“常见”的“八分之一”,其目的是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真实的审美感受。曼诺林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首先,曼诺林是老人悲剧的见证人。老人出海之前和从海上返回之后,或者说,老人悲剧的前前后后的故事,曼诺林都历历在目。读者通过曼诺林对老人的评价和感受,深入地了解、认识了老人,这比依靠作家的叙述和交代产生的真实感要强化得多。比如小说结尾处五次“哭”的描写,这就比直接描写老人痛苦的惨象产生的真实效果要强得多。
其次,曼诺林与老人构成了一老一少的“二人世界”,有了这“二人世界”,这就如同戏剧舞台上有了两个演员一样,使戏剧人物有了“对白”的可能。海明威让曼诺林进入作品,从而主人公桑提亚哥就有了一个“说话”的人;作品就可以借助他们的说话“对白”和交往活动,交代主人公的经历、爱好、处境、背运、现状等情况,而不需要作家以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身份,来讲述“老人与海”的故事。这是一种限制视角叙述方式,其特点是可以限制过滤掉作家的任何主观评价和感受,能够给读者以想象空间,使作品产生“张力”,而且更加符合生活真实,从而给读者以逼真的感知体验,并“参与”作品中的人物活动。假定没有曼诺林出场,作品中的人物不构成一个“二人世界”,主人公的“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作家以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身份来进行叙述,自然及逼真的艺术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更何况作家在进行“二人对话”的语言描写和“二人交往”的行动描写中,能够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只选取全部内容的“八分之一”进入读者的视野,而略去其中的“八分之七”呢!
参考文献:
[1]诺贝尔文学文库.访谈录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2]诗学].诗艺[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作者简介:
祁建立(1957—),男,河南省滑县人,濮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文学及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