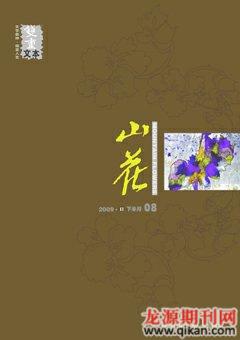唱山歌
小 米
几天前,我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朋友,在交谈中,我们说到了山歌。关于山歌,我一直想写点儿什么,却一直没有动笔。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题为《生命里的歌谣》,在那篇文章中,我有意地,把山歌排除在外,没有写。我这样做就是为了有那么一天,我得静下心来,专门地,写一写山歌。今天坐在电脑前,始终找不到思绪的把手,忽然想起几天前我们在办公室里聊天时的情景来,突然就有了写一写山歌的愿望。
朋友的话,对我是有一些触动的。他说,一位白发老人,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在答应给他唱山歌前,对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山歌只能唱,不能说。老人的意思是,山歌唱出来很好听,说出来,很可能,已经韵味全无。
这话,是懂山歌的、很内行的人,才能说得出来的。
大约还是十七八岁,在我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有了把家乡的山歌整理成书,让它们能够长久地传唱下去的愿望。我觉得,这是我,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所谓读书人,理所应当的事,是我份内的事。我把我这个愿望,在放假回家的时候,说给了我同村的一位表兄听。他因为跟我关系一直很不错,自告奋勇,答应帮我的忙,给我记录一些。后来,他甚至把他整理出来的,抄写下来,寄给了还在上学的我。由于种种原因,我当时并没有着手做这件事。表兄抄给我的那些,现在,我也不知道把它放在了什么地方,总之是,无论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它了。我心里非常惭愧,我以为,我甚至对不起我那热情而诚恳的表兄。参加工作以后,我也不是没有想过,但忙于教书,又忙于写作,还是无暇顾及。一晃,二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在这二十多年里,我由乡下调进了县城,又干起了文艺工作,虽一直没有放弃当初的想法,却也是拾不上手来。在这期间,县里有几位热衷于民间文艺的老同志,各自收集记录了好几本本地的民歌小册子。他们把自己的劳动成果送到我案头上的时候,我自然是感激他们所做的工作的。但是,在感激之余,在我仔细地阅读这些小册子的时候,我又有了新的遗憾。
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还不能让我满意。
理由是,第一,他们整理的,是民歌,不是专门的山歌,这是不同的,我甚至认为,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流传下来的民歌这个概念里,虽然也包括山歌,但毕竟有所不同。山歌以外的民歌部分,几乎都已经约定俗成,山歌却不同,只要还有人唱山歌,山歌就还在不停地发展着,变化着,更新着。第二,我不满意他们记录的文字,有许多错别字,因而显得粗糙不说,有许多地方不是很准确,没有把山歌本来的韵味,完整地转移到字里行间。第三,他们收集的,有相当一部分是相互重复的,还有许多精美之作,他们却谁都未曾收集到,给我留下了遗憾。
直到现在,我依旧未能把整理山歌的愿望,付诸行动。主要的原因,还是时间有限,精力不足。我也知道,真要这么做的话,我得寻访很多地方,很多的人,我还得润色、加工,去粗取精。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能够先以散文的方法,写一写存活在我记忆和心灵深处的山歌,也不错。虽然这是一种避重就轻投机取巧的行为,毕竟,我这样做,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家乡,都是一个交代,一次回归。
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我很少当众大声宣布自己的看法、观点,这与用文字的方式写在纸上,完全是两回事;我更加不会在众人面前唱歌,我没有敢于献丑的勇气。对于山歌,很自然地,我是不怎么唱的,没有别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最多轻声细气地,哼那么几句。我有我的自知之明,我这个人,天生不是当主角的料。我也知道自己干不成什么大事情,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所以,在生活中,我更喜欢当一个配角。拿山歌来说,我几乎从来就没有放声地唱过,我只是用心地听过。无论生活还是人生,我都习惯做一个倾听者,领悟者,而不是歌手。
在空旷沉寂的苍天之下,在坎坷贫瘠的黄土之上,突然一阵悠扬的歌声,婉转、缠绵、古朴,非常意外地,钻进你的耳朵,直达你的肺腑。那是怎样一种虽不悦目却又如此爽心的感觉呢?那声音,天然得不掺杂任何雕饰,幽怨得如泣如诉。那声音,绵长得仿佛一根你怎么扯都扯不断的无形的丝线,淳朴得又如同你的亲人,在你耳边窃窃私语。那声音,你一旦听见,你就不由得停下了手里忙着的活计,你就不由得侧耳聆听。那声音,来自于天地之间,停留在灵魂深处,似乎是一道看不见的烙印,让你经常在想起,一直都记得,而且不停地、隐隐地,在疼!真的,那感觉,那韵味,不用“疼”这个字,不足以表达我内心如此强烈的冲撞般的震撼!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在我的家乡,山歌就不能在家里唱,也不能在村里唱。这样做的人,人们会认为你缺乏教养。父母或家人听见了,会训斥你,别人听见了,会挖苦你,嘲笑你。山歌只能在野外唱。这是为什么呢?山歌本来就是人们在劳动的过程中,或在劳动之余,用来排遣寂寞和消除疲倦的一种娱乐方式,这是一。第二,有些山歌很雅,比较文明,也有些山歌,比较粗(下流),在野外唱出来,唱的人也好,听的人也罢,一笑了之,图的就是个乐,只是为了放松一下身体,愉悦一下心灵,一般不会被孩子或老人听到,也就显得无所谓,无伤大雅。在村里唱,村里有老人,有孩子,唱了,既是对老年人的不尊重,也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没有什么好处。
山歌里,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对唱。
大家都正忙着呢,埋头苦干,挥汗如雨。不经意间,对面山上,或者很远很远的地方,是本生产队另外一群人里的一个人,或者,是另一个生产队里正在干活的某一个人,突然有了唱几句的冲动,歌声就这么自然而然地,飘扬过来了。那声音虽然很远,但因为山与山之间的距离并不算太远,声音与词句,听上去,虽然隐隐约约,却还清晰可辨。你方唱罢我登台,那边刚刚落下,这边的歌声,已经飞翔了过去,回敬了过去。声音成了这座山与那座山之间的看不见的桥梁,在这桥上经过着的,不是人,是人与人之间,渴望沟通的心情。
这么接应着对唱的,一般是异性。
他们把偶然的一展歌喉,变成了情歌联唱。那边起头挑衅的,是男的,这边回答的,多半是女的。那边是大姑娘,这边就是小伙子。你来我去,一来二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谁也不让着谁。不把对面的声音压下去,不把对方驳得理屈词穷,不会罢休。对面沉寂下来了,这边就用一阵开心的大笑,作为总结。也有这边一群人跟那边一群人集体对唱的。这样的时候,生产队队长往往一声令下:大家干脆歇会儿吧!于是,一场赛歌大会,就这么开始了。
对面是什么人在唱?从声音传过来的地点,可以判断出是本村的人,还是外村的人,从声音里也能够听得出是男或女。具体是谁?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是娃他爸还是毛头小伙子?都无从知晓。虽然在对歌,但歌声毕竟跟说话不一样,音调与唱法几乎是约定俗成的模式,缺少了的,恰恰是每个人独特的口音,彼此并不能确定对方的身份。也因此,对歌的时候,是有一点儿神秘感在里头藏着的。
《刘三姐》是我们小时候百看不厌的电影之一。我究竟看了它多少遍?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吧?在本村看过,跟着大人或与小伙伴一起,到十几里以外的别的村子,也去看过。为什么会对它如此痴迷呢?还是山歌的缘故。因为刘三姐是一个生长在旧社会农村里苦命的人,还因为刘三姐跟我们一样,爱唱山歌,还爱对歌,百战百胜。我们甚至经常把失败的人比喻成陶秀才、李秀才,拿这样的“桂冠”,取笑失败者。
小时候,看电影几乎是农村孩子唯一的文化生活。在这篇文章里,我不想细说我要专门写到它。但刘三姐成了村子里无论男女老幼的崇拜对象,一点不错!我做出这样的判断,当然是用事实来作依据的。那时候还没有“追星族”这一说,不然的话,我们都是货真价实的追星族。
除了对唱的那些山歌显得活泼、热烈、外露之外,其余的山歌,往往不是唱给任何人听的。山歌,往往只是唱给自我、唱给心灵深处的另一个自己。它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着的人们,灵与肉的真情倾诉,它也是不屈服于命运的人们,对热爱着的生活的顽强的话语。
那天,朋友在我的办公室里,给我读了一首山歌,他觉得挺好:
想哩想哩实想哩
想得眼泪长淌哩
……
心颗想成核桃了
肠子想成麻花了
……
这一支山歌,相对比较长。我听过,而且不止一次。
“心颗”是民间土语,心或心脏的意思;麻花是一种条状的扭曲着炸出来的面食。比喻用得恰当、自然,而且,有一点点夸张的成分,的确不错。比个别所谓的诗人苦思冥想出来的诗句,好很多。
真是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
我记得的一首山歌,是这样的:
青石崖上滴水哩,
不缠你了还有哩;
说不缠,就不缠,
难道就你是金花银牡丹?
“缠”,还是土语,是追求异性的意思。
这是一个男人唱的。而且,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伙子,唱出来的,也是我亲耳听到的。唱它的人,我忘记了他是谁,只记得他是个“斗大的字认不得一个”的人。这样的人,在当时的农村,实在太多了。这首山歌用的也是民歌常见而且典型的起兴手法,当然,还有比喻。我仅仅听了一次,就难以忘掉,好多年过去了,它仍一字不差地存放在我的记忆深处。仅这,就已经充分地说明了山歌长久而且顽强的生命力。我能够记得它,我想,除了它的艺术手法,还在于它的立意。追求自己的意中人,却又得不到她的回应,心里自然是酸溜溜的感觉。但是,这个人,虽然在怨,但他没有因此记恨暗恋着的她,她在他的单相思里,仍然是美丽的,而且,他还很有点儿阿Q精神,他是在自我安慰。这不是高尚的爱情,又是什么呢?
这一首山歌,分寸感拿捏得,也是恰到好处!
山歌或民歌,往往流于直白。直白几乎是山歌的致命伤。但仔细一想,直白其实应该是山歌非常鲜明的艺术特点之一,尤其用来对唱的山歌,更是如此。因为表达的需要,也因为接受的需要,它要出之于心、口,到达对方的耳与心,不能不考虑对方是否明白自己的心意,自己的表达。对唱的山歌,如果不直白,就不足以传递感情,透露信息。
当然,山歌里不乏糟粕。粗俗下流的内容,也有不少。这需要整理它的人,有一双慧眼,要扬弃,而不是泥沙俱下,照单全收,统统接受。
山歌往往是随口唱来的,即兴的成分很大。它的歌词,很随意,而且经常在改动,这不足为奇。一首山歌一旦定了型,也就是说,它的歌词部分一旦固定下来,不再被唱它的人修改,就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它就已经暗暗地,具备了广为流传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经典。
《诗经》里《风》这部分内容,不就是流传于当世的民歌(或者是山歌)吗?它是我们这个民族长盛不衰的经典。时空切换,世易时移,几千年过去,到了现在,它还是经典,仍然是经典。它一直都是经典。它已经成了传统文化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它也是我们血脉里的一部分。
当我不时地沉迷在《诗经》里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想着的,却是家乡浩如烟海的那些山歌。
山歌到底有多少?即使一直唱着山歌的人,也说不清。也许,调子还是原来的调子,人也还是原来的人,可是,歌词变了就什么都变了:心情变了,环境变了,这一首变成了那一首,彼一时变成了此一时,幽怨变成了悠扬、悠远,缠绵变成了高亢、雄浑,这个世界是发展的,变化的,人的情绪也在发展变化着,没有一成不变的世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人、一成不变的心情。
山歌山歌,为什么要叫成山歌,而不是地歌、野歌?我想,最初,它也许就是只在山里才唱的歌。
在我的家乡,抬头见山,出门上山。要去种庄稼,要割草、砍柴、拾粪、放牧牲畜……大部分普通老百姓的活计,都在山上。
唱山歌,一要环境,二要心情。有了唱山歌的环境,还得有唱一唱的心情。两者缺一不可。山歌没有无病呻吟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山歌都是有感而发的。
到了夏季,下午,放学回家,天色还早。我往往约几个本村的男女同学,一起到村后的山上,在生产队的玉米地里,去“寻”草,苦苣菜什么的,我们把它挖回来,喂给家里的猪吃。这几乎成了我童年时,雷打不动的工作。这么做,既锄了草,又喂了猪,一举两得,生产队的干部,一般是不管的,默许的。
孩子们一旦钻进玉米地里,就立刻被高大的玉米林子给吞没了,而且,由于忙于把草挖够,一群孩子,各忙着各的,要不了多久,一个就找不到另一个了。但是,我们可以用声音,用山歌,找到对方。孩子之间的对唱,往往就在这时候。我所能听到的山歌,绝大部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到我的脑海里去,抠也抠不掉的。
孩子们之间的距离,相对比较近,一般就隔着三两块地。不像大人之间的对歌,距离那么远。所以,孩子们之间的对歌,比大人的,相对要文雅一些,应对得也不是那么准确,贴近,更不像大人那样,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因为彼此都很熟悉,从声音上,可以听得出来,不敢太张扬,不能太放肆。
这二十多年以来,我虽然有时候也回一趟乡下的老家,却从未参与到做农活的行列里去。从包产到户一直到现在,如今的家乡人,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在汗流浃背的间隙,是不是偶尔地,放下手里的锄头或镰刀,也唱一支山歌,用来抒发一下内心的苦闷,用来放松一下疲惫的肉体呢?
我想是的。
我认为会的。
因为,山歌已经渗透到他们的骨头里去了。他们应该跟我一样,舍不得它,扔不掉它,放不下它。
当然,毋庸置疑,现在的农耕环境,与我小时候所能够体验的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大环境,的确有了很大的不同。当年,一般都是精壮劳力聚集在一起,集体耕作生产队的土地,现在却往往只是三五个人、是一家人在一起,忙着自家的活计。后辈与长辈往往同时在场,要唱山歌,已经有了许多的不方便。
反过来想,一家人,也不一定总在一起劳动,也有分开干活的时候。也就是说,现在还有唱山歌的环境与心情。
那么,应该还有人,唱着这些来自于大山深处和心灵深处的歌。
一个村庄,往往是几个家族的联合体。精壮劳力,往往是相同辈分年纪相仿的那么一群人。他们在一起干农活,几乎没有什么禁忌,这样的情境,才可以无遮无拦,尽情地唱上一曲。可以说,是生产队的集体劳作,给山歌的发扬光大提供了异常肥沃的土壤。
这也就是我童年的时候,为什么能够经常听到山歌的原因之所在。
作者简介:
小米,男,原名刘长江,1968年生。1986年开始在《人民文学》、《诗刊》等百余家报刊发表作品1000余篇,作品曾入选数十种诗文选集和年选,并被多种报刊选载,出版诗集《小米诗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学院荣誉作家,甘肃省陇南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