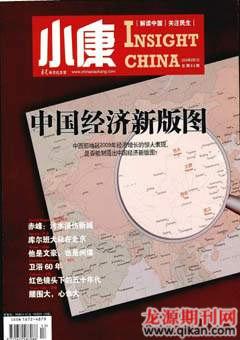红色镜头下的五十年代
苏 枫
1956年至1959年期间,中国摄影界假照片、假新闻不断。新闻摄影界在时代的局限与桎梏中,展示的荣耀与羞耻,一直延续,影响至今

摄影讲究客观、真实。然而,上世纪50年代,却是中国新闻摄影“笔底生花”的时期——孩童嬉戏于稻谷间而稻杆不折,姑娘舞于棉朵之上如飞翔云端。新闻摄影被赋予了“宣传工具”的功能。一时间,假照片、假新闻风生水起。浮夸之风盛行。
在1956年至1959年之间,国内摄影界关于照片“组织加工”与“摆布”的争论,呈现白热化趋势。此话题的讨论,最终在“大跃进”、“反右”等政治运动中酿成事端,甚至改变了诸多参与人的命运。新近出版的《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一书,便记录了50多年前,中国新闻摄影界围绕新闻真实性问题的“三年争辩”。
说谎的照片
《红旗照相馆》的作者晋永权是《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纪实摄影家,因工作关系对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新闻摄影发展、特点甚有研究。《红旗照相馆》的开篇讲的便是1950年代的“摆拍”之风。其实,在50年代早期,中国官方新闻管理机构——新闻摄影局,对新闻的真实性要求非常严格,一再强调要“大力反虚构”。
“然而,因现实中已存在造假行为,业界对采访中记者是否能干涉被拍摄的人或事物的讨论已经开始。官方观点也逐步转变。” 晋永权说,“到了1956年3月,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这个当时摄影界最高级别的官员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对拍摄现场作一些技术性的调整,比如会议桌上的茶杯暖瓶放得太杂乱,或者在画面中太突出,在不影响会议进行的情况下,对它们略加整理,这是允许的。”
石少华并没说明,“技术性调整”、“略加整理”与虚构、摆布的界限在哪儿?于是,这几个新概念,在当年的新闻摄影界引起混乱。这年7月,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的一张《北海公园儿童车》照片,让摄影界业内的口舌之战进一步升级。
1956年7月下旬,新华社北京分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带着自己的孩子及另外一位住在同一大院内文字记者的孩子,一起来到位于市中心的北京北海公园,拍摄出租儿童车的新闻照片。当天,杜修贤也拍摄了其他游人租车的场面,但发稿时却发了一张以这两个孩子为“模特儿”的照片。
分社领导在签发杜修贤拍摄的照片时,以这样做无疑是“摆布”为由,把照片扣了下来。但同时,也有一批杜修贤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不能因为坐车的是记者的孩子,便说这张照片是虚构或不真实的。
有关此事的讨论一直进行到这一年年底,也因此引发了新闻摄影业内更多“丑闻”曝光。同年底,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文字记者艾丁爆出,记者陆轲在包头拍摄的《包兰铁路昆独仑河大桥架桥》的图片,铁路附近的牛羊群本来是没有的。为了显示大桥修筑在内蒙古草原上,陆轲才要求放牧的人把牛羊赶到铁路桥附近来。另外,艾丁还举了个例子:曾有位记者,拍照时让一位妇女去绣一双已绣好的绣花鞋。

摄影界业内,揭丑的何止艾丁一人。同样是1956年底,新华社吉林分社雪印、胥志成、田建之分别给北京总社写来文章,同样都谈到了记者袁苓这年6月在第一汽车制造厂采访拍摄照片的情况。雪印指出,为了“走在试制汽车文字消息的前面”,袁苓的《第一汽车厂试制解放牌汽车》一图,在拍摄时把“解放牌”汽车的外壳罩在了苏联产的“吉斯”车上,这样,外表看起来就像国产的“解放牌”汽车。
而另一张内容是“在发动机车间,检查员郑国秀和王凤芝正在用空气测量仪检查发动机上的部件活塞”的照片,按田建之的说明,拍照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检查台上没有一个活塞,活塞早就检查过了,为了拍照,必须重新让工人把活塞摆在检查台上。另外,十多个活塞只有两三个是国产的,其余都是苏联造的。为了不使苏联活塞上的俄文拍出来,袁苓同志把有俄文的一面转到背面去。为了使画面生动一些,袁苓同志从另一个检查台叫来一个检查员参加检查。
身处这样的摄影大环境,有时,就连国家领导人身边的“红色摄影师”,也免不了要对图片“组织加工”一番。原新华社记者、毛泽东身边的摄影师吕厚民,就曾回忆自己如何为主席“导演策划”照片。
庐山会议期间,吕厚民发现毛泽东每次去会议室参加会议,都要路过一个大厅。吕厚民找来工作人员商量,在大厅的墙壁上挂上一幅世界地图,毛泽东平日喜欢看地图。不出所料,第二天,毛泽东路过时,便停下脚步专注地看起来。于是在一旁的吕厚民完成了这幅《毛泽东看世界地图》。
那张被后人称作“建国以来最有影响的虚假照片”,出现在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署名“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拍摄的一组照片——一颗早稻大 “卫星”,报道了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那块亩产3万斤的 “天下第一田”。其中一幅照片,四个孩子站在生长着的稻穗上。照片说明是: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
没多久,那块亩产3万斤的 “天下第一田”被揭露出,完全是个假典型。它是把十几亩、二十几亩快成熟水稻并到一个大田里面,而且这个稻田很小,只有几分地。从上面俯瞰,它是层层叠叠的,但其实根本不是,整个都倒伏了,所以,孩子可以站在上面。这次造假事件,使得于澄建被很多人指责为,“没有经过调查”,“严重报道失实”。
然而,在假典型东窗事发前,新闻界很多人员,却都纷纷模仿于澄建,施放照片“卫星”。在丰收的田野上,不断涌现奇迹:稻穗上能放鸡蛋;紧接着,十六七岁的姑娘盘坐在稻穗上,竟对稻颗没有多大的影响;之后,稻穗上站着三个胖胖的小孩;不几天,一张产量6万斤的“卫星”田照片上,稳稳当当地站着13个青年。
“布列松来了”
1958年6月中旬,法国著名摄影家亨利•卡迪埃•布列松来到中国。《红旗照相馆》中有专门一章描述此事:为迎接建国十周年,中国官方决定邀请西方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访华,希望能拍出为中国“正视听”的照片,让西方人了解新中国的情况。
布列松来华时,正赶上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运动,各种类型的摆布之风盛行。而布列松对“安排的”照片和“摆布的”环境极反感。
6月20日,按照中国摄影学会的安排,布列松前往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拍照。7月16日,布列松在与首都摄影界人士的座谈会上,直陈对中国摄影的建议:“我看到表现中国的照片不少,有些很好,但有些我不喜欢。我曾看到一张表现丰收的照片,一个妇女抱着一捆麦子,笑得很厉害。当然丰收是要笑的,但不见得笑得那么厉害。在地里,当然是灰尘仆仆,汗流满面,但这个妇女却很干净。安排出来的画面不是生活,不会给人们留下印象。”
最后,这位西方艺术家,以冷静的艺术视角,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中国百姓的生活。他拍摄了《前清最后一个宦官》、《镟床女工》、《大跃进的总路线口号》等著名照片。然而,由于这些照片“没有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属于世界上最著名的新闻摄影记者之列”的布列松,最终在中国得到这样的评价—— “帝国主义反动分子,用恶毒的用心和卑劣的手法,污蔑中国的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制度”。多年后,国内很多摄影家分析,“当年中国摄影界对布列松作品的严重误读,使得中国摄影停止甚至倒退了几十年。”
因照片而改变的人生
《红旗照相馆》中,有300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而有些人,正是因为拍摄了这些照片,人生也随之改变。书中就讲述了不少老摄影人的故事。

比如,摄影家魏南昌先生。他是那本被誉为“中国摄影圣经”的《暗室技术》一书的作者。然而,1956以后,魏南昌醉心“画意”、“美感”的照片,被指责为“脱离生活”、“脱离实际”。1957年,魏南昌曾四五次下乡,但面对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热火朝天的集体生产场面、鸡棚牛舍,他只拍回了一张像国画中雄鸡报晓般的“大公鸡照片”,结果被批评为“不愿表现社会主义的新面貌”。
同年,魏南昌躲开尘土飞扬的工地与田野间立起来的楼房,在北京西郊拍出了一张名为《古塔与毛驴》的照片,结果这次,他遭到了更强烈的质疑——“只对落后的东西感兴趣”。从此后,魏南昌简直成了公众敌人,有人甚至爆出他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私人摄影师,为蒋介石拍过肖像照。之后,这位原在新华社摄影部任职的老摄影家,1957年被划为“右派”,遣送到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强制劳动。再后来,音信全无,终与“平反”无缘。
由于没有亲历自己所书写的这段摄影往事,晋永权在写作时,完全依靠的是“田野调查”方式。他穿梭在图书馆、资料室、甚至旧货市场里,一次次寻访当事人。就连1950年至1952年间,新闻摄影局不定期出版过的六期《摄影工作》杂志,他居然也奇迹般地在河北石家庄的旧书店里发现。“这些珍贵资料,并没有被保护被珍视。”
晋永权说,他曾经以为“相比起来,单位里的那些摄影史料会好些。一定是像机密一般,保存在带有密码的保险柜内。”但当他偶然去一新闻机构摄影部办事,在装修现场的楼道内看到一本散落的《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讨论发言纪要 (1958.8-1959.12)》散装书页,放在“与建筑垃圾堆在一起的麻袋”里。那天中午,晋永权小心地征询这家单位的一位同行是否可以借阅。“他多少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拿走!拿走!”
《红旗照相馆》出版后,有些业内同行不明白,晋永权为何要不辞劳苦地翻旧账?“那段特殊岁月里的摄影遗痕,例如‘摆拍之风,如潜规则般一直延续,在现代新闻摄影上有所呈现,甚至浓墨重彩。”在晋永权看来, “如今谈论过去,只是为更准确地确定前行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