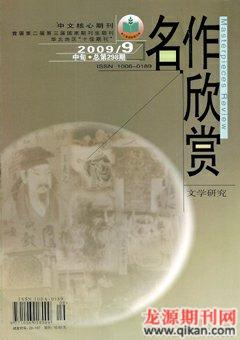“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
关键词:李清照 本真性 “我-你”关系 审美价值
摘 要: 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通过对比的方式,在文本中为读者呈现出人与自然相遇的本真状态,建立起一个“我-你”关系的审美世界,使作品具有一定的哲学内涵;阅读这样的作品,能激发读者和文本、读者和世界的交流,建立起多重的“我与你”关系的相遇。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如梦令》
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认为,“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①,作为人的本真性活动的艺术常常为我们敞开这种相遇。相遇不一定相见,相见也不一定是相遇。相见可以发生在现实界,但相遇往往是发生在精神界。在艺术世界里,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所有“在者”可以相遇但不一定相见。
读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就常常能被这种“相遇”的美丽所打动。这种相遇是多重的,首先是文本为读者呈现了人与自然的相遇;其次,我们也可以把阅读过程看作是发生在读者与文本、读者与世界之间的相遇。
一、文本内人与自然的相遇
相遇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话,一种平等的交流,一种“物我不分”的关系。在李清照的这首《如梦令》中,诗人用短短的三十三个字,用诗的语言而不是哲学的语言,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人与自然的相遇世界。
文本中的呈现过程比较曲折。诗人在一个文本世界里设置了对比,用比照的方式呈现了对世界感知的两种方式,也呈现了人与世界的两种关系,即“我与它”、“我与你”这样两种世界关系。马丁·布伯认为,当“我”以我的全部本真与一个人或任一事物建立关系时,“我”就会与这个存在的全部本真“相遇”,这种没有掺杂着任何预期和目的的关系,即是“我与你”的关系;如果把物看做相分离、相对立的客体,则物就沦为“有待有限”之“它”,或者当“我”带着预期和目的去和一个对象建立关系时,这样的关系就是“我-它”关系。可以说,“我-它”关系是麻木的、阻隔的、功利的,因而是非审美的;而“我-你”关系是灵动的、无阻隔的、本真的,因而是审美的。马丁·布伯实际上肯定了审美活动是体验性、想象性的主体间的对话活动,审美活动的发生取决于主体对待事物的方式,生命的意义就在本真性的审美活动中。
《如梦令》中,诗人首先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 “我-它”关系世界,即“卷帘人”和“海棠”的关系。在这一种世界中,人与自然虽然没有阻隔和遮挡,但是却无法交流,人对自然的变化毫无察觉。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新婚夫妇间的“斗胜”词,“词中的“卷帘人”实际上指的并非“侍女”,而是词中女主人公的丈夫。②其实“卷帘人”具体指谁并不重要。在作品呈现的世界中,“卷帘人”只是和那个在帘后的抒情主人公形成比照的一个形象而已,在“卷帘人”看来,“昨夜雨疏风骤”和海棠的“绿肥红瘦”不会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卷帘人”是不会意识到“雨疏风骤”会引起海棠有什么变化。这时,“卷帘人”与“海棠”虽然相见却无法相遇。“经验不足以向人展示世界……经验者滞留在世界之外”③,可以说,“卷帘人”所谓的“海棠依旧”就只是一种经验的展示,因而,她眼里的世界是没有神性的客体世界。“海棠依旧”的回答是一个没有诗心、也缺乏审美情趣的回答。
接着,诗人通过“知否?知否?”这一殷切反问,引领我们进入的是另一个世界,这一个世界即是“我-你”关系的世界,是一个自然向人敞开,同时也是人向自然敞开的世界。“你之世界超越于时空网络”④,能与你相遇并不一定是要和你同处同一时空。我们姑且把《如梦令》里的那一个“浓睡不消残酒”的“我”称为“帘内人”。显然,“帘内人”与海棠虽同历一夜风雨但在不同的空间。虽然“帘内人”不曾看见“雨疏风骤”后的海棠,却能凭着和自然相遇的感知,做出不同的判断:“应是绿肥红瘦。”“帘内人”通过与“卷帘人”的对话,突破了时空的阻隔,达到了和“海棠”的相遇。从文本内的时空设置看,“卷帘人”既是夜尽晨来的界限,又是室内与户外沟通的纽带,然而,诗人恰恰越过了这一中介,达到了和“海棠”的无阻碍的相遇。这种相遇不是发生在现实界,因为在现实中,作者未曾见到雨后的海棠,这种相遇是发生在想象界,或者说是在精神界,因而体现出了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性的价值。可以说,诗人在“绿肥红瘦”与“海棠依旧”的对比中为我们呈现了价值关系,那个“我”和海棠“相遇”后的“世界”,活泼,生动,富于色彩和变化。这样,作品通过对自然的体察建立了一种“我-你”关系,“我”是把海棠看做是一样具有生命神性的“你”。在不同时空的网络里,“我”与“海棠”在诗人说出“应是绿肥红瘦”的那一瞬间相遇了。这是文本给读者提供的一种人与自然刹那相遇的审美时空。“应是绿肥红瘦!”能穿过千年的时空打动着后来的读者,正是因为它饱含着本真的审美价值。
二、读者与文本的相遇
“相遇”关系同样可以用来作为文学阅读的一种关系,这种相遇也可以越过作者之一中介的阻障,实现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相遇”。
在传统的阅读中,人们往往会去寻找和追索文本寄寓作者的什么样的情感。如“借物抒情”或“寓情于景”被认为是传统的创作方法,因而从被描写的“物”中解读出创作者的情感也就成为一种主要的解读方法。很多读者认为“绿”和“红”都不仅仅是对海棠的描写,而且是各有所指或各有所喻。因而,对《如梦令》的解读,作者的心境、情态、人生际遇等被看作是解读时必须寻找的重要内容,换句话说,作者的因素决定了作品的意义。在这样的视角下,作品中的自然,或者说创作主体之外的客体世界,只是被看做是主体表现的对象,而对象自身并不具有独立性,是一种“他者”的存在。如有人认为“绿肥红瘦”中的“红”是用来自比,表达李清照感慨红颜易逝的情怀,“因为在她的感觉中,虽然‘绿肥,生理强壮,可是作为美感象征的花,女性的青春,却在无形中消逝了。”⑤有读者认为“红瘦”表达了惜春的主题,“通过自然景物和人物心志的强烈对比,使读者对作者的惜春的心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⑥还有人说李清照写的是婚后的闺中相思,是惜春加怅己。“当诗人‘试问卷帘人时,的确表现出了惜花的关切之情。但写至词末三句,庆幸中含有抹不去的失望,惜花之意已经悄悄换成了怅己的情怀。”⑦可以说,这样的解读还是基于主体性哲学意义关系下的阅读和理解,即把“物”看做是“我”之色彩的投射,万物皆着“我”之色彩,如王国维所说,解读出来的是一种“有我之境”。
寻求作者之意的解读是否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功利”的解读,是一种“我-它”关系,读者与文本的相遇会被作者这一“中介”所阻隔。因而,对“绿肥红瘦”的审美体验不妨可以是悠游相遇式的,即只把它看做是作者呈现的一种世界的本真状态。从“我-你”关系解读文学文本,那么,对读者而言,并不一定要去追索作者的某种情感。因而读到“绿肥红瘦”,可以无关是否“惜春”,也可以不顾有无“怅己”,在解读的过程中,读者也完全可以不带工具色彩和功利目的,即可以不追究作者的写作背景或是夫妻关系还是作者心境,只是从作品中获取单纯的审美愉悦,和文本呈现的世界会心一笑,恍然一悟,和千古之前的那个“我”一起与自然相遇,感知自然的冷暖变化,跨越千古的时空阻隔,实现读者与文本的无限自由的连接。
就如罗兰·巴特所区分的“文本”的阅读和“作品”的阅读,寻找作者意义的阅读是“作品”阅读,这是一种顺从而受抑于意义的阅读,因而所得的快乐是有限的快乐,算不上真正的阅读。而“文本”的阅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游戏”,是一种需要读者参与创作的活动⑧,这是一种自由无限的快乐,这种快乐才是应当追求的真正的阅读快感。当我们为词中的情景所打动时,打动我们的不仅仅是千年前的那株海棠、那个女词人、那个小小的生活片段,还有此时此刻“我”的海棠、“我”的心境。阅读李清照的《如梦令》,就是这样一次“我”和“你”的相遇,这个“你”就是自在自足的文本,气韵生动而丰富的独立世界。于是,“我”可以不知作者何人,可以不管作者是否惜春是否怜己,只知道“我”被“你”的“绿肥红瘦”打动了,这样的阅读也是一种本真性的阅读。
三、读者与世界的相遇
主体性哲学将人的生存活动界定为主体对客体的加工、改造、征服和利用。在文学中“表现论”的观点就认为人的情感表现是文学活动的主要目的,而外在世界如自然景物常常是作为主体“言志”或“抒情”的载体,自然就成为“我”之工具。而大部分现代人生活在节奏快速的都市,往往为物质和生存心力交瘁,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隔阂也越来越深,就如布伯所说,“现代的工作与占有方式几乎已把相遇人生与相遇关系之任何痕迹荡涤干净”⑨,因而,阅读这样的作品也能令读者重新回归自然,与世界的本真相遇。
这样看来,文本内“知否?知否?”这一问有着双重的对话意义,首先是对文本之内的“卷帘人”的叩问,其次也是对文本之外的读者的一种呼唤。作者用这一殷切的问句,否定了卷帘人“海棠依旧”的无情回应,而在文本之外的读者读到这样一个回环的问句,麻木的心灵也会为之一振,不禁会自我反问,是否也能感受大自然的变化与生命的流转?因而这一问既激活了读者与自然对话的心灵空间,也建立了读者与世界之间相遇的“你-我”关系。
从“我-你”关系看文学文本创作,自然世界或景物,也可以是在主体间相互观照下的独立存在,可以摆脱被客体化的非主体命运。也就是说,自然不再是被认为是作家情感寄托的载体,而具有独立存在价值,这种独立存在的价值是被创作者在作品中揭示的。自然“并不是我的印象、我想象力的驰骋、我心绪的征象。它是我之外的真实存在。它与我休戚相关,正如我与它息息相通,其差别仅在于方式不同”⑩。其实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很多这样的作品,比较典型的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山”和“我”互相观看,两相欣赏,呈现的是一种超越物我的融合与平等。“山”是自在之山,我是自在之“我”,人与物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诗人给我们呈现了一种主体间相互对话的、没有利害关系而只有审美关系的“我-你”世界。于是,通过这样的文本,读者重新感受万物的灿烂光华,和万物一起,成为谐和世界的一部分。
诗歌与哲学是近邻。阅读《如梦令》这样的作品,可以让我们领悟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领略自然丰富而有生命的美,也可以让我们放下世俗功利与自然本真相遇。所谓经典就应该是这样,她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个无限开放的文本,艺术存在的真正意义也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种与文本、与作者、与世界本真相遇的可能,在这样的相遇中,我们的人生被照亮了。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何金梅,文艺学硕士,浙江省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人文科学系讲师。
①③④⑨⑩ [德]马丁·布伯. 陈维刚译.我与你[M].北京:三联书店,1986.第27页,第19-20页,第50页,第66页,第22页.
② 张和安,韩海浪.谁是“卷帘人”——读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学海[J].1998.(2).
⑤ 孙绍振.猜到的为什么比看到的更动人——读李清照《如梦令》.语文建设[J].2008.(1).
⑥ 柯秀华.李清照两首《如梦令》词赏析比较.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J].2001. 53(4).
⑦ 王蓓.对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风疏雨骤》的现象学阅读.名作欣赏[J].1999.(3).
⑧ [法]罗兰·巴特著.屠友祥译.S/Z[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