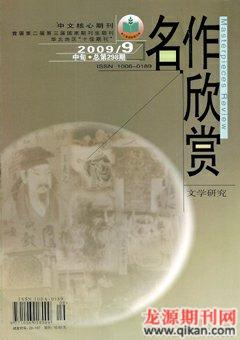守贞、戒色与“醒世”、“警世”、“喻世”
陶祝婉
关键词:三言 贞节 戒色 女祸论
摘 要:晚明的思想潮流、社会风气及冯梦龙“醒世”、“警世”、“喻世”的编著目的对“三言”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它的一些婚恋小说表现出极为矛盾的思想观念:既理解女子失贞,又要求女子绝对守贞;既尊重女性,赞美女性才情,又劝人远离女性,极力宣扬“女色祸水”,将女性视为物化的异己存在,无视女性尊严意志。
一
冯梦龙所生活的晚明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高度成熟并开始向新的近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是个真正的末世:政治腐败问题日渐突出,宦官专权,纪纲不振;官员们玩忽职守,贪贿公行,党争不息,士风败坏;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民不堪命。在另一方面,由于礼教废弛,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队伍壮大,“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和封建道德终于被冲破,王阳明吸取陆象山“心即理”的学说,认为世界的本源在于心,所谓的“天理”不外乎心而存在,而是与心合一。人只要致力于发明本心,就可以自由所如,任情纵性。继王阳明之后的王艮等人发展了心学理论,肯定人的主体性,强调心本体论,在理论上承认了人欲的合理性。在这一思潮中影响最大的是李贽,他将心释为“童心”,即人的最纯粹、最自然、也最自由的“本心”,认为仁义礼智信出之,自私自利的物欲之心出之,世人普遍谴责的私欲,也只是一种平常而自然的现象。李贽提出“穿衣吃饭既是人伦物理”,实际上把人欲提高到了“天理”的地位。另外李贽还对卓文君不待父母之命的私奔行为大加赞赏,说过“成佛征圣,维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①,所有这些都对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
不过,长期压抑人们的对“人欲”极度压制、禁锢的伦理道德一旦被冲破,整个社会心理又走向了它的反面,卷入了纵欲主义的漩涡,从皇帝、士大夫到市井平民,莫不如此,这是长期严重受制的人类自然欲求在封建道德亵渎下扭曲、变态的必然后果。据《万历野获编》记载:
宪宗朝万安居外,万妃居内,士习遂大坏。万以媚药进御。御史倪进贤又以药进万。至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俱献房中秘方,得从废籍复官。以谏风纪之臣,争谈秽,一时风尚,可知矣。
武宗幸榆林,取总兵戴钦女为妃。幸太原,取晋府乐工杨胜妻刘良女。大爱幸,携以游幸。江彬及八党辈,皆以母事之。……又幸宣府时,纳宣府总兵都督金事马昂妹。时已适毕指挥,有娠矣。善骑射,能胡语。上嬖之,进昂右都督。群小皆呼马舅。其他高丽女、色目人女、西域舞女.至扬州刷处女寡妇,仪真选妓女,又不可胜数也。
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②
帝王们如此,所谓上行下效,民间自然也是“流风愈趋愈下”,“世俗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松窗梦语》),人们追求奢靡的生活,追求一种世俗的感官享受,竞奢炫奇,风流放纵。《醒世恒言·金海陵纵欲亡身》中身为人主的金海陵利用其至高无上的权利大肆宣淫,“凡平日曾与淫者,悉召入宫,列入妃位。又广求美色,不论同姓异姓,各分尊卑及有夫无夫,但心中所好,百计求淫。”③《喻世明言·明悟禅师赶五戒》中,年近五十修行高深的五戒禅师见到自己十六年前收养的女孩红莲已经长成一个漂亮的姑娘时,“邪心遂起”,淫污了红莲。《醒世恒言·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非空庵的尼姑空照等人“真念佛,假修行,爱风月,嫌冷静,怨恨出家的主儿”,遇到风流成性的赫大卿,竟然不放他回家,日夜聚淫,以致赫大卿命丧黄泉;极乐庵的尼姑了缘,“也是广开方便门的善知识,正勾搭万法寺小和尚去非做了光头夫妻,藏在寺中三个多月”。《醒世恒言·汪大尹火焚宝莲寺》中,宝莲寺群僧以祁嗣为名将良家妇女诱入寺中成批奸污。《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庙官孙神通设巧计装成二郎神去骗奸韩夫人,等等,“三言”中这些描写正是那个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社会现实的真实映射。
面对着这种末世颓相,冯梦龙作为新思潮的追随者和大力宣扬者,一方面不免身处其中,亦有不少违背传统伦理道德之举,但也另一个方面,他作为一个有着深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自然又不能熟视无睹。他在《山歌·叙》中指斥晚明社会为“季世”,在《醒世恒言·序》中他又说:
六经国史之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自昔浊乱之世,谓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
冯梦龙是将“三言”作为六经国史之辅,用以喻世、警世、醒世,希望通过“导愚”、“适俗”的方式,“可喜可愕,可悲可泣”的描写,达到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的社会效果,从而改变这个“浊乱之世”芸芸众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最终到达拯救黑暗、岌岌可危的明季社会的目的,开“万世太平之福”。冯梦龙这种强烈的救时弊、挽颓风、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与范仲淹等中国古代众多知识分子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任命感是一脉相承的。
二
纵览“三言”的婚恋作品,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男女之间正常情欲的肯定,对女性失贞的理解宽容。《醒世恒言·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面对着刘慧娘与孙玉郎之间被其父母无意中促成的私情,作者并不是以封建卫道士的面目来裁决道德的是非,而是以情、理来评判,文中乔太守的判词知情达理,可谓千古绝唱:“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雄一雌,突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对孙刘两家儿女的私情给予谅解,肯定他们之间是正常的情欲,是“相悦为婚,合乎礼义”。《喻世明言》卷首《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文中蒋兴哥知道妻子王三巧偷情后十分生气,却是首先自责,“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她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休弃王三巧时,他虽在休书上写了“本妇多有过失,正合七出之条”,但也仍“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连王三巧用过的箱笼也不忍开看。听说王三巧改嫁,还把这些箱笼原封不动,连钥匙也一并交割与王三巧当个陪嫁。在那个“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社会里表现出了对失贞女性相当的理解和宽容,显得十分有人情味。《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宋徽宗后宫里的韩夫人身为天眷,却思想平常夫妻之爱,又被打扮成二郎神的庙官奸骗失了贞节,在文中她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反而得“改嫁良民为婚”,“了却相思债,得遂平生之愿”。可见作者对正常情欲的认可,对女子失贞理解宽容到了什么程度。这是作者作为李贽等人的追随者,作为明末尊情思潮的旗手,思想上的先进性在“三言”中的必然反映。
不过,细读“三言”的这些作品,我们有时又会感到十分困惑,它们一方面肯定男女之间的正常情欲,对女性失贞理解宽容,可在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不合理封建礼教的回归,对女性贞节的绝对要求。如《醒世恒言·大树坡义虎送亲》《醒世恒言·陈多寿生死夫妻》《醒世恒言·张廷秀逃生救父》和《警世通言·钝秀才一朝交泰》等篇中的林潮音、朱多福、王玉姐和黄六瑛等人,从未与未婚夫见过面,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情,却坚决遵从封建社会“一女不事二夫”“一女不吃两家茶”的信条,心如铁石,决不改适他人,否则甚至宁可自尽而死。她们都得到了作者的赞扬,并最终都得好报,夫妻恩爱,尽老百年,子孙繁盛。《喻世明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莫稽在连科及第后,为能另娶一个高门大户的女子,将在自己穷困潦倒时娶得并努力帮助过自己的结发之妻金玉奴推堕江心。对这种忘恩负义、富贵易妻、甚至富贵害妻之徒,玉奴最后仅仅通过一顿“棒打”就捐弃前嫌,与他重归于好,原因是“虽然莫郎嫌贫弃贱忍心害理,奴家各尽其道,岂肯改嫁,以伤妇节”。《醒世恒言·蔡瑞虹忍辱报仇》中的蔡瑞虹在父亲被杀后,忍受着歹徒污辱,费尽心机让众贼寇“一齐绑赴法场”,为父亲报了仇。蔡瑞虹与朱源生有一子,在父仇得报以后,她本来应该就此过上平静的生活,但肉体曾经被玷污的经历,使她挣脱不出“男德在义,女德在节”的怪圈,为了遵循封建礼教贞节的要求,作者安排她以自杀的悲剧结局来洗刷所谓“不贞”的“污点”。同是“三言”的作品,编著者也还是那个深受明末肯定“人欲”思潮影响的冯梦龙,为什么对失贞女子的处置会如此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