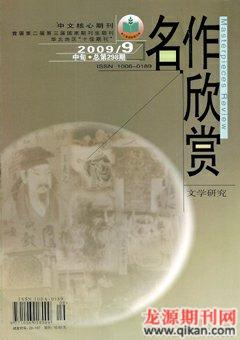尘世中飞扬的浮沫
闫兰娜 高建军
关键词:张爱玲 倾城之恋 命运
摘 要:本文以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为细读文本,从叙事中的明暗线索、男女主人公形象分析、主题中的浪漫与苍凉三方面细致地解读了该小说。
中国内地从20世纪70年代末张爱玲“复出”,到1995年张去世,“张热”达到高潮。至于对张爱玲具体作品的研究、分析、考证、发掘等工作,有众多张爱玲的喜爱者已经或正在不知疲倦地做着。本文对于张爱玲中篇小说《倾城之恋》的一些论述,即是这样的一篇不揣浅陋之作。
明线与暗线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最初发表于1943年9-10月的《杂志》第11卷6-7期。收入1944年9月她的小说集《传奇》。人们习惯于将《倾城之恋》当成一部爱情小说来读,其实它恰恰不是一部爱情小说。两位主人公在交往过程中目的都很明确,一个要找一个经济上可以依靠的丈夫,一个要找一个在精神上、情感上能够认同自己的正宗的中国女人。从本质上讲,他们要的都不是爱情;只不过一个实一个虚而已。而范柳原尽管想要找一个这样的女人以使自己的灵魂的血脉有一个归宿,但他在“具体操作上”也是非常实际、非常精明的。作者说他们:“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始终不肯冒失。”(本文中涉及的小说《倾城之恋》的原文,均引自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张爱玲文集》第2卷。下面不再一一注出。)
表面上看,范柳原似乎更“接近”爱情一点,但他的手段影响了他的目的,他是在“猎获”爱情,而爱情从来不是靠猎获得来的。在白流苏,她所有的,只有将要逝去的、所剩不多的青春,以及在范柳原看来的、那一点所谓的正宗中国女人特有的韵味。她没有退路,她只有“赌”:“然而她也是喜欢赌的,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恶气。”而范柳原则是“嫖赌吃喝,样样都来,独无意于家庭幸福”,“他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因此,从他们双方来讲,都没有纯粹的爱情动机。
所以,张爱玲在小说中实际上设置了两条线,一明一暗,明的是写所谓的白与范的爱情;暗的是写白流苏自己无法把握的命运。这条明线我们一目了然,他们如何结识,如何交往,如何调情,如何相互算计,如何斗智斗勇,如何虚与委蛇,如何争风吃醋,如何彼此妥协,如何最终成就乱世姻缘,都交待得很清楚。但那一条暗线如果我们不仔细研读却不易察觉。
首先,小说通篇都是作者站在白流苏的角度来叙述的。比如她对旧家庭的印象:“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
再比如她对范柳原的印象:“那范柳原虽然够不上称作美男子,粗枝大叶的,也有他的一种风神。”还有她在与范柳原交往过程中对范的种种观感,几乎范柳原的一举一动都是通过白流苏的眼睛传递给读者的。白流苏就是范柳原的一面镜子。这实际上是作者代白流苏发言,发感慨。
再比如,白流苏在白公馆里的揽镜自照,自叹薄命;在香港遭范柳原冷落后的无可奈何,无计可施;从香港回到上海后的前程未卜,坐以待毙;被范柳原“招回”香港后的半推半就,终于屈服;范柳原终于答应结婚时的悲欣交集,苦泪喜泪。处处是绝望的挣扎,处处是无法摆脱的宿命。
白流苏的命运在上海与香港,旧家庭与范柳原之间摇摆。她像一粒微尘,飘起来便进了云彩,落下去就成了污泥浊水。那场战争来得突然、冷冰冰、不讲道理,于白流苏却是歪打正着的一场飞来横福。大都市的倾覆、成千上万人的痛苦、惊天动地的大变革,在这一切大背景之下,白流苏出乎意料地得到了自己卑微的幸福,好比崩塌的泰山底下一只自足的虱子。白流苏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但她却被自己更无法把握的世界的命运成全了。张爱玲在这里说出了世界的命运与个体的命运之间存在着的一种荒诞而微妙的平衡。
小说最后,张爱玲写道:“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这里,张爱玲是在说白流苏——也许是所有女人——的另一种同样无法把握的命运,即:一个大都市的倾覆成全的这个女人,也不过是这样平庸、琐碎、微贱、俗不可耐。
因此,说《倾城之恋》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不如说讲的是关于一个女人的命运的故事。
白流苏与范柳原
翻译家傅雷在1944年5月发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在谈到《倾城之恋》时说:“物质生活的迫切的需求,使她(白流苏)无暇顾到心灵。”说白流苏和范柳原两人是“疲乏、困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①。此种评价非常精到。确实,白流苏与范柳原都是小人物,小到看不到对方与自己。但二人的出身与背景却存在绝大的反差。白流苏是旧家大族出来的人,这在小说里直接间接都有交待,她的家族虽然已经败落,但架子还在,她也刻意保持着大家闺秀的那“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身份。这也是她除了美貌和残存的那一点青春之外的唯一一点资本。她在家庭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有走出去;她的目的单纯而实际,就是要寻求“婚姻的保障”和“经济上的安全”。
关于范柳原,小说里也是直接间接地有几处交待,总起来有这样几点:一,他是华侨。二,他有钱,有产业。三,放浪形骸,无意于家庭幸福。四,在他身上,有着文化、精神、情感、性格上的两重性。但范柳原最根本的一点是第四点,即他缺乏一种被认同感。从这个角度上说,他是一个孤独的人。这是他放浪形骸的原因和借口。他需要回归,需要归宿,但他的遭遇和身世使他不敢轻易地相信一个人——哪怕是他真心喜欢的人。
张爱玲自己现身对这二人作评价:“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但张爱玲说的这种“自私”,又似乎是情有可原的。
一方面,白流苏没有退路,她是小本下大注,输了就会血本无归。在与范柳原的交往中,她的最后的妥协与屈服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白流苏的自私既是自我保护的必要措施,也是她在这场斗智斗勇的情感游戏中讨价还价的手段。她好比“弱国无外交”中的外交家,只能靠着这种自私的“小智小慧”来谈一个相对来讲“较优的议和条件”。因此,她不自私不行。不自私不仅会被人所卖,甚至还会被范柳原轻视。范柳原的“自私”实际上是自以为是。他想求得白流苏在文化、心灵、情感和精神上的认同,但他对白流苏既有太多想象的成分,又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顾忌与猜疑。同时,因为他在经济上的优势,也使他在心理上产生一种优越感,他要求被认同,而不管别人愿不愿认同,能不能认同。
白流苏与范柳原从一开始交往就在互相较劲,双方你来我往,攻杀战守,逗引埋伏。范柳原知道白流苏要什么,但他固执地不愿承认。白流苏不知道范柳原要什么,但她知道自己要什么。范柳原恼恨白流苏“不懂”自己,又恼恨她死活不肯放下贵族淑女的架子。因而白流苏除了保证自己不被范柳原“诱奸”外,毫无办法。不过这也是她唯一可以用来反击范柳原的武器——只是这武器太被动了些。
范柳原“拿稳了她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所以,回到上海的白流苏,他可以一纸电报就招之即来,并最终使她做了自己的情妇。可是他也有拿不稳的事情,那就是“不期而至”的战争。战争使范柳原人性中本真和朴素的东西开始复活。使他知道以前的玩世不恭过于浪费,今日大难之下的相依为命何等珍贵。战争也使本已认命的白流苏找回了自我。小说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字,描写了他们二人的这种心理的微妙变化:
柳原叹道:“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流苏也怆然,半晌方道:“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柳原笑道:“你打算替我守节么?”他们两人都有点神经失常,无缘无故,齐声大笑。
这哪里是“神经失常”?如果说小说里有爱情,这爱情就在这一刻的“神经失常”里。只有这一刻的爱情,双方才完全卸去了“武装”,真心对真心,同病相怜。但他们的爱情也仅仅是这一瞬。当他们用结婚证书将这爱情固定下来后,这爱情便迅速沉入尘世的底层,并且爬满了虱子。
傅雷说白流苏范柳原这样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②。其实《倾城之恋》从来就不是悲剧,当然也不是喜剧——尽管它有着看似圆满的结局。张爱玲在她的散文《自己的文章》里说:“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③
是的,白流苏与范柳原都是小人物,小到像两粒尘土。在他们这样的小人物的心灵的湖面上,即使再大的倾国倾城的变动,也是激不起多大浪花来的。
苍凉与浪漫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说:“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张爱玲极喜爱《红楼梦》,《红楼梦》也许是影响张爱玲小说创作最大的一部书。这种影响在《倾城之恋》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但我认为,《红楼梦》对《倾城之恋》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小说中弥漫的那种无边无际的、深远的苍凉之气。
《红楼梦》表面上繁华富丽,而其基调却是那“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深入骨髓的苍凉。《倾城之恋》也有一副苍凉的底子。白公馆的死气沉沉、香港的虚情假意、战争的天翻地覆,正是张爱玲所说的那种“如匪浣衣”式的“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在香港,白流苏与范柳原的调情,表面上风光旖旎,实际上勾心斗角、庸俗不堪,总给人一种不洁的感觉。而小说最后,大战猝起,兵荒马乱,大难之下兵隙偷生的境遇里,还有那不是基于爱情基础的结婚,回到上海白公馆,想起四奶奶,白流苏还有那蝼蚁般的胜利的微笑。结婚之后,范柳原作风习惯没有改,只是调情的对象不再是流苏,而是别的女人。白流苏有点“怅惘”的满足——卑微的满足。而这些又好像都是身不由己的,必然的,应该的。
《倾城之恋》通篇的色调有三个变化:白公馆的尸居余气的紫黑色、香港的贫血似的白色、战争中冷冷的铁灰色,没有一个是明朗的、轻松的。这三种色调依次出现,渐渐过渡,最后融合在一起,恰成为那万丈红尘背后的遥远的苍凉的天空。
然而《倾城之恋》又似乎是浪漫的。旧家大族的凄美的少妇、风流的中产阶级华侨、具有强烈殖民色彩的国际大都市,这一切仿佛都是“浪漫”的理由和要素。但是,《倾城之恋》又确实不是浪漫的。小说一开始时的死寂,中间耍心眼儿多过谈恋爱的调情,最后潦潦草草的婚配,以及逐渐沉入庸常世俗生活的女主人公,都让人觉得惘然、怅然。真正的浪漫不应该是这样的。《倾城之恋》的浪漫是表面的、不真实的,是“飞扬的浮沫”,是建基在苍凉之上的华丽的薄薄的幻象。吴福辉说:“任凭你读《倾城之恋》的结尾如何粗心,这时也会猛然悟到怪不得缺乏一种‘大团圆或‘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气氛。人生的部分终结,划定的一个句号,实潜伏了落花流水的无奈和偶然,想想心里酸楚楚的,悲从中来。”④
小说最后,作者说:“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倾国倾城”是浪漫的;但“大抵如此”,则是由绚烂归于庸常和平淡。任何人都逃不脱这样的宿命。女人更是如此,白流苏当然也不例外。她得到的不过是“经济上的安全”和一个并不十分爱自己的丈夫,但在她看来,为了这些而倾覆一个大都市是值得的。范柳原得到的是一个自己并不十分爱的女人和一个自己并不十分情愿的婚姻。当白流苏笑吟吟地“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的时候,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和倾国倾城的故事都已经完结。
《倾城之恋》中的所谓浪漫,使故事深处的苍凉旷味变得刻骨而“恶毒”,令人恐怖;《倾城之恋》中的苍凉,使故事表面上的那一层浮薄的浪漫变得颤巍巍的,像春季最后一天的花蕊。
《倾城之恋》从总体上说,是华丽的、机智的,但又是深沉的、悲天悯人的。小说让两个小人物的所谓爱情,背负了远比他们的爱情更深广、更沉重得多的关于人的命运的故事。其实,任何文艺作品从根本上讲,表现的都是人的命运的主题,只不过有的人写得好一些,有的人写得差一些。《倾城之恋》当然属于前者。
(责任编辑:张 晴)
作者简介:闫兰娜,文学硕士,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高建军,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①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423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② 同注①
③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7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④ 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第1页-第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