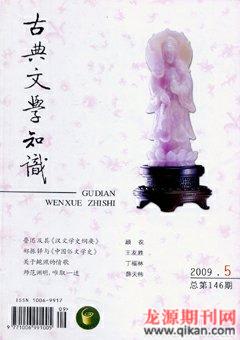眼光照映 境界全出
陶文鹏
清末文学批评家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说:“‘词眼二字,见陆辅之《词旨》。其实辅之所谓眼者,仍不过某字工,某句警耳。余谓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体之眼,有数句之眼,前前后后无不待眼光照映。”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王氏虽未用“词眼”这一概念,但他显然把“闹”与“弄”二字当作能使“境界全出”的“词眼”。但对此二字,也有不同的看法。吴世昌先生说:“‘闹字、‘弄字,无非修辞格中以动词拟人之例,古今诗歌中此类用法,不可胜数。”(《评〈人间词话〉》)鉴于“闹”、“弄”二字已被古今论者屡加评论并有不同看法,这里另外拈出几个“词眼”来赏析。
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晚唐词人温庭筠《菩萨蛮》词云:“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这首词写闺中女子生活。上片前两句,写她居住在挂着水晶帘子的室中,暖香缭绕着。此刻,她枕着玻璃般明洁温润的枕头,盖着绣有鸳鸯图案的锦被,做着一个旖旎的梦。后两句紧承上句“惹梦”,描写她的梦中景象,也可看作是实写她居室外的景色,展现出一幅凄清迷离的江天月夜图。下片写她的穿戴打扮。“藕丝”句,藕生长在秋天,淡紫近白色,称藕合色,故说“秋色浅”。这句写她穿着藕合色的丝绸衣裳。“人胜”句说,她的发鬓上戴着参参差差的剪成人形的花胜。“人胜”,又叫花胜、春胜,是用彩纸或金箔剪刻而成的古代妇女的装饰品。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七日为人┤铡!…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花胜以相遗。”“参差”,长短不齐。“双鬓”句说,她的两鬓隔开在脸庞两边。“香红”,美称她的脸颊。“玉钗”句意谓,她头发上插戴的玉钗在春风中微微颤动。“风”在这里是名词作动词用。这个字用得灵活,它使下片四句所描写的静态事物顿时生动起来,读者自然想象到这个女子的鬓发、玉钗、藕合色衣衫,以及插在鬓边的人胜,一并在风中轻轻摇曳。正如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所说:“末句尤妙,着一‘风字,神情全出,不但两鬓之花气往来不定,钗头幡胜亦颤摇于和风骀荡中。”(《读词偶得》)的确,词人有意把这个用作动词的“风”字安排在全篇最后一字的位置,宛如丹青妙手的画龙点睛之笔。
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
温庭筠《菩萨蛮》词云:“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词中“玉楼”,美称女子的居处;“袅娜”,柳枝细长柔软的样子。“画罗”句,意谓丝罗帷帐上绣着金色的翡翠图纹。“翡翠”,鸟名,有蓝绿色羽毛,常用来做装饰物。“香烛”句,蜡烛燃烧滴落下点点烛油似泪,故称“烛泪”。“销”,指烛燃而减少。“香烛”,因蜡烛制造时掺杂着香料,燃烧时散发出芳香气息,故名之。这首词起笔便以“长相忆”揭出一篇主旨。唐圭璋先生《唐宋词简释》说:“此首写怀人,亦加倍深刻。首句即说明相忆之切,虚笼全篇。每当玉楼有月之时,总念及远人不归,今见柳丝,更添伤感;以人之思极无力,故觉柳丝摇漾亦无力也。‘门外两句,忆及当时分别之情景,宛然在目。换头,又入今情。绣帏深掩,香烛成泪,较相忆无力,更深更苦。篇末,以相忆难成梦作结。窗外残春景象,不堪视听;窗内残梦迷离,尤难排遣。通体景真情真,浑厚流转。”对此词抒写怀人情景的艺术表现,作了层层深入的细致分析。而从“词眼”的角度来看,篇末的“迷”字,蕴涵的情味尤为丰富微妙,读者宛若看见这位绿窗中的佳人于耳闻目睹鸟啼花落时的痴迷神情,从而感触到她那颗凄怨的心。因此,这个“迷”字堪称一篇之眼。温庭筠的《菩萨蛮》,除了这一首的“绿窗残梦迷”与上一首的“玉钗头上风”之外,还有“镜中蝉鬓轻”与“燕飞春又残”,都是在结句最末一字点睛传神,才最终完成整体意境的营造。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南唐词人冯延巳《谒金门》词云:“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刘永济先生《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说:“此闺情词也。上半阕写一闺人行于池旁芳径中,且行且以红杏花蕊抛入水中,引鸳鸯为戏。下半阕写其行至斗鸭栏边,忽闻鹊噪,举头而听,不觉搔头坠地。盖鹊能报喜,因思行人或将归来也。全首如观电影之活动镜头,闺中少妇之行动、情思、态度,历历呈现,极其生动。”分析细致。开篇两句,描写风忽把满池塘的春水都吹皱了。这个“皱”字形容水的波纹如皱,把一池春水拟人化,说它就像少女皱起了黛绿色的眉毛,从而将静景写成了动景,将无知无情的春水写成了有性灵有感情的人,这就写活了。有的选本,“皱”字作“绉”,说波纹似绉纱,不如“皱”好。“皱”字不仅暗喻抒情女主人公的蹙眉神态,而且暗喻她的心头荡起了涟漪。兴中有比,生动传神又委婉细腻,意味深长,又为下文写她闲引鸳鸯、手搓杏蕊的无聊动作张本。所以,这个“皱”字看似平常,细品却新奇巧妙,堪称词眼。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一载:“元宗(中主李璟)乐府辞云‘小楼吹彻玉笙寒。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在这段对话中,可以体会到李璟对这两句词的赞赏。近人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评:“‘风乍起二句破空而来,在有意无意间,如絮浮水,似沾非著。……”而“皱”字,正是这脍炙人口的名句之眼。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北宋词人秦观《踏莎行》词云:“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是绍圣四年(1097)春秦观自处州再贬郴州后写的。上片因情造景,写他幻想中的仙境已淹没无存,高远的神仙楼台因雾而失,指引济渡的道途因月而迷,桃源乐土亦无处可寻。他正独自闭居在春寒的客馆之中,聆听杜鹃那一声声“不如归去”的悲鸣。过片两句,连用两则友人投寄书信的典故,极写思乡怀旧之情。“驿寄梅花”,语本《荆州记》:“吴陆凯与范晔善,自江南寄梅花诣长安与晔,并赠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鱼传尺素”,用古乐府《饮马长城窟》的诗意,盖以该诗中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之句,故以“鱼传尺素”代表寄书信意。这三句说:亲友们的来书和馈赠,并不能给他带来丝毫慰藉,而只能徒然增加他的离愁别恨。因此,书信和馈赠越多,离恨也积得越多。词人用一个“砌”字,说恨可以像砖石一样堆砌。这个“砌”字的新颖妙用,把抽象无形的“恨”予以具象的表现。那一封封书信、一束束梅花积累出的恨,就好像突然化作一块块砖石,层层垒起,垒成“无重数”。“砌”与“恨”及“无重数”的连接,也使词人新抒的“恨”情显得更沉重、坚实,正如砖石垒成的城墙一样。这个“砌”字使全篇渗染了沉郁的悲苦、怨恨情调,正如南宋词人姜夔《踏莎行》结尾“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管”中的“冷”字,表现出情人魂魄在月照千山的清冷环境中独自归去,就不仅是一句之眼,而且是数句之眼乃至通体之眼,堪称王国维所最赏爱的“著一字而境界全出”之灵眼。
浪挟天浮,山邀云去,银浦横空碧
宋末词人张炎《壶中天•夜渡古黄河,与沈尧道、曾子敬同赋》词云:“扬舲万里,笑当年底事,中分南北。须信平生无梦到,却向而今游历。老柳官河,斜阳古道,风定波犹直。野人惊问,泛槎向处狂┛?迎面落叶萧萧,水流沙共远,都无行迹。衰草凄迷秋更绿,唯有闲鸥独立。浪挟天浮,山邀云去,银浦横空碧。扣舷歌断,海蟾飞上孤白。”该词为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秋,张炎与沈尧道、曾子敬被征召北上大都(今北京)写金字《藏经》途中作,词中描写夜渡古黄河的情景,抒发亡国之痛、身世之悲,以及旅途的孤寂,具有张炎词集中不多见的苍凉悲壮的风格。其中若干字千锤百炼,精警异常。如上片“笑当年底事,中分南北”两句,一个“笑”字,写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表现出词人面对着“中分南北”的古黄河所触发的深哀巨痛。又如“老柳官河,斜阳古道,风定波犹直”三句,“老”、“官”、“斜”、“古”四个形容词定语都用得贴切,状景逼真,写出词人独到的古老感、沧桑感。尤其是那个“直”字,摹写河水波纹平直如矢,可见水流之急,正如昔人散文中常用的“急湍若箭”,既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体现词人内心的紧张、惊奇、焦急。这是对北宋词人周邦彦的“柳阴直”(《兰陵王•柳》)的借鉴与创新。而“浪挟天浮,山邀云去”一句,写夜间舟行,但见黄河波涛宛若挟带着整个天空在眼前浮动,迅速后退的山峦好像邀请着云远去。“挟”、“邀”两个动词,把黄河水与岸边山峦、云彩,都拟人化,写得仿佛有情有知。而且一刚一柔,前后映照,表现出舟行的动感,十分真切。而“银浦横空碧”句,写他在舟上举首仰望,粲粲银河横空,犹如一条白练,横铺于碧蓝的夜空中。天上“银河”与地上“黄河”相互映照,气象开阔,令词人在一瞬间心头上也涌起一股豪气。而此句气象的形成,主要得力于“横”字,这个动词用得刚健有力,能显出阔大的空间感。总起来说,“挟”、“邀”、“横”三字,分别是这三句词之眼,显示出张炎炼字的功力。
羡寒鸦、到着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
宋末词人蒋捷的《贺新郎•兵后寓吴》,抒写他因元兵南侵流寓吴中的漂泊孤凄之感,其下片“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数句,笔者曾在《生活细节,真实感人》(载《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4期)一文中作了赏析。这里从“词眼”的角度,赏析上片“羡寒鸦”三句。在这三句之前,词人已经描叙了他“东奔西走”的狼狈境况。“羡寒鸦”这三句说:我真羡慕那些乌鸦,它们在黄昏之后,便可归巢,一点点飞落到杨柳树上。这个“羡”字,看似寻常,其实下笔沉痛,饱蘸泪水。这里词人已把自己的命运与寒鸦作了对比:乌鸦尚且有群可依,有巢可归,自己却形影独吊,无处可宿!一个“羡”字,写出词人内心的酸涩、凄凉、孤寂、痛苦,也显露了他在沉痛中不乏自我揶揄的幽默。这是作者触景生情自然引发的感受,当然也得力于他对涌来笔底的各种字眼的精心选择与锤炼。